汉字结构中的血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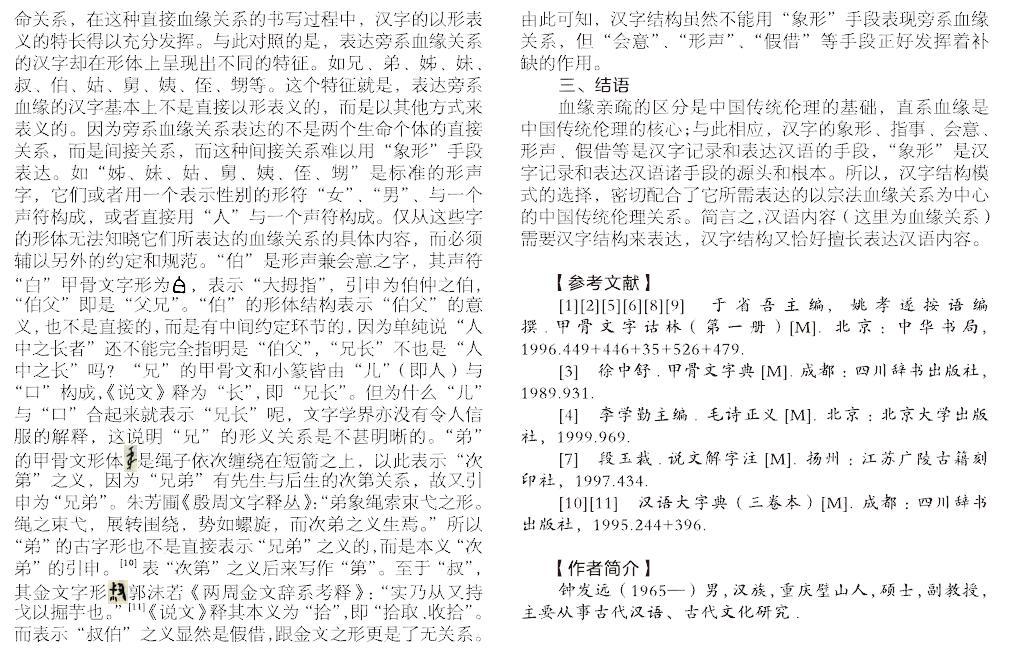
【摘 要】 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清楚而系统地记录了中国传统伦理极为重要的血缘关系。基于以形表义的结构特长,汉字在表现直系血缘关系上可谓竭尽所能,诸如母体的形象,新生命的孕育,生命的降生,无不充实丰满、栩栩如生;而对于旁系血缘关系,在“六书”中的“象形”手段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会意、形声、假借等恰巧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总之,汉字的形体结构,变成了强有力的语言表达手段;汉字结构模式的选择,密切配合了汉字所需表达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关键词】 汉字结构;血缘关系;以形表义
中国文化自西周以降,就以重人伦关系为特色,而人伦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即人伦关系都是通过血缘的有无和近远来区别。这种血缘纽带关系,从亲疏而言,可分为直系血缘关系和旁系血缘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清楚而系统地记录了这种直系血缘关系和旁系血缘关系。下面试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一、汉字结构中的直系血缘关系
在所有直系血缘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是最近的。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清楚而系统地记录了这种最为密切的生命关系。
1、汉字结构表现母体作为生命之源的特征
如“母”字非常突出母体繁衍下一代的形体特征。《说文》:“母,牧也。从女,象怀子形。一曰象乳子。”《广韵》引《苍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象人乳形。”徐锴《系传通论》云:“于文,女垂乳为母。”[1]母与女在甲骨文中形体没有分别,有等形,其中的两点,甲骨文字学家一般认为是女性双乳。郭沫若、李孝定、赵诚、陈炜湛皆持此观点,如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中说:“骨文及金文母字大抵作,象人乳形之意明白如画。”他认为“母字即生字崇拜之象征”。[2]汉代到宋代的文字学家们虽未见到甲骨文,但他们对字形的认识是准确的。
2、汉字结构表现儿女新生命在母体孕育
如“身”、“孕”、“包”、“妊”、“娠”等字。
甲骨文中“身”、“孕”是一个字,有等形,都突出隆起的腹部,有的有“点”或“子”,显然是表示所怀的胎儿。徐中舒解释字形说:“从人而隆其腹,以示其有孕之形。本义当为妊娠。或作腹内有子形,则其义尤显。孕妇之腹特大,故身亦可指腹。腹为人体主要部分,引申之人之全体亦可称身。”“甲骨文身孕一字。”[3]“身”用作“怀孕”义可见于《诗经·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亨传:“身,重也。”郑玄笺:“重,谓怀孕也。”孔颖达疏:“以身中复有一身,故言重。”[4]按李孝定的说法,小篆的“”是由金文等形的横画变来的。[5]由李的分析继续解构,则可知小篆形体除去“”剩下的部分就是母体怀胎之形。其实,甲骨文中还有的形体,下面已有一短横,小篆与这个甲骨文及上面所列金文诸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说文·子部》:“孕,怀子也。从子,从几。” 小篆形体的上面部分其实不是许慎所说的“几”,而是“人”字的变形,下面确是“子”字,合之则为妇女怀子。对此,李孝定说:“篆文‘孕子从‘乃无义,‘乃为之形。”[6]
“包”的小篆为,其结构表示胎衣裹着胎儿,本义就是“胎衣”。《说文·勹部》:“包,象人怀妊,巳在中,象子未盛开也。”段玉裁注:“巳字象未成之子。” [7]“包”即是“胞”的古字。
“妊”的甲骨文有一形体为,甲骨文有“妇妊”之用例,其中“妊”是表示一个妇女的名字,未见直接用为表示“怀孕”义的。但李孝定《甲骨文集释》举到一个甲骨文形体,他分析为“从女从人,当为妊之初文,古文衍变(人)或作(壬)”。“本象妇女有身之形,及后变为形声,乃为从女壬声,篆又变从干支字之壬为声耳。” [8]比较甲骨文二形,前者表现母腹中有人(胎儿),是一个会意字,后者将“人”换成同音的“壬”,是一个形声字。联系李说中由到的演变,可以说“妊”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娠”的甲骨文字形为,从女辰声。《说文·女部》:“娠,女妊身动也。”
3、汉字结构表现新生命从母体降生
后、育、毓在甲骨文中本为一字,其形体较多,如等。基本上由母体与“倒子”构成,文字学界大多认为象产子之形。有的形体有两处或三处的小点,王国维认为“象产子时之有水液”,李孝定认为是羊水。“毓”的形体与上面的甲骨文形体有何联系呢?这里“人”、“女”、“母”是相同的,而“母”即同“每”,“倒子”尤其是下面有羊水的“倒子”就是。“育”的形体与上面的甲骨文有何联系呢?王国维举到二形,并分析说:“其作者,从肉从子,即育之初字。”也就是說,用“月”替代了甲骨文诸形中的母体及羊水,这种替换表达了血浓于水的亲缘联系。王国维还进一步举出,并分析说:“而所从之,即《说文》训‘女阴之‘也字,其意当亦为‘育字也。故产子为此字之本谊。” 可心说,对生殖过程和血缘关系的表达更加大胆和直露。“后”的形体与上面的甲骨文有何联系呢?王国维说:“后字本象人形,当即之变,则倒子形之变也。后字之谊,本从毓谊引申,其后产子之字,专用毓育二形。”[9]《说文·后部》:“后,继体君也。”继体君就是君的继承人。对于这个解释,郭沫若予以否定,他指出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的用例。他考证说,卜辞和典籍中“后”的用例“均限于先公先王,其存世者则称王而不称后”,因此他认为“后者乃古语也”。接着他说:“后当是母权时代女性酋长之称。母权时代族中最高之主宰为母,母氏最高之德业为毓,故以毓称之也。毓字变为后,后义後限用于王妃,亦犹其古义之孑遗矣。”郭沫若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说明“后”本指因生育之功而成首领的女酋长。由郭说可推,后来“后”指君王帝王,是所指扩大了,再后专指帝王配偶则词义范围又缩小了,但恰巧是古义“女酋长”某些意义要素如性别上的遗存。
今天的“后”字的形体在金文中已出现,如后母戊鼎的,吴王光鉴的。而“毓”在《说文解字》中为小篆“育”之异体。
女性生育过程,在汉字结构中有着突出的印记,同时,这个过程的风险,亦有充分体现。如和,字形上一个有倒着的“子”,一个有横着的“子”,皆蕴含有难产的信息。
二、汉字结构中的旁系血缘关系
前面所论述的,表达直系血缘关系的汉字的形体结构,实际上是书写直系血缘两代之间“所从出”和“所出”的生命关系,在这种直接血缘关系的书写过程中,汉字的以形表义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与此对照的是,表达旁系血缘关系的汉字却在形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兄、弟、姊、妹、叔、伯、姑、舅、姨、侄、甥等。这个特征就是,表达旁系血缘的汉字基本上不是直接以形表义的,而是以其他方式来表义的。因为旁系血缘关系表达的不是两个生命个体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关系,而这种间接关系难以用“象形”手段表达。如“姊、妹、姑、舅、姨、侄、甥”是标准的形声字,它们或者用一个表示性别的形符“女”、“男”、与一个声符构成,或者直接用“人”与一个声符构成。仅从这些字的形体无法知晓它们所表达的血缘关系的具体内容,而必须辅以另外的约定和规范。“伯”是形声兼会意之字,其声符“白”甲骨文字形为,表示“大拇指”,引申为伯仲之伯,“伯父”即是“父兄”。“伯”的形体结构表示“伯父”的意义,也不是直接的,而是有中間约定环节的,因为单纯说“人中之长者”还不能完全指明是“伯父”,“兄长”不也是“人中之长”吗?“兄”的甲骨文和小篆皆由“儿”(即人)与“口”构成,《说文》释为“长”,即“兄长”。但为什么“儿”与“口”合起来就表示“兄长”呢,文字学界亦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这说明“兄”的形义关系是不甚明晰的。“弟”的甲骨文形体是绳子依次缠绕在短箭之上,以此表示“次第”之义,因为“兄弟”有先生与后生的次第关系,故又引申为“兄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弟象绳索束弋之形。绳之束弋,展转围绕,势如螺旋,而次弟之义生焉。”所以“弟”的古字形也不是直接表示“兄弟”之义的,而是本义“次弟”的引申。[10]表“次第”之义后来写作“第”。至于“叔”,其金文字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系考释》:“实乃从又持戈以掘芋也。”[11]《说文》释其本义为“拾”,即“拾取、收拾”。而表示“叔伯”之义显然是假借,跟金文之形更是了无关系。由此可知,汉字结构虽然不能用“象形”手段表现旁系血缘关系,但“会意”、“形声”、“假借”等手段正好发挥着补缺的作用。
三、结语
血缘亲疏的区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直系血缘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与此相应,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是汉字记录和表达汉语的手段,“象形”是汉字记录和表达汉语诸手段的源头和根本。所以,汉字结构模式的选择,密切配合了它所需表达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关系。简言之,汉语内容(这里为血缘关系)需要汉字结构来表达,汉字结构又恰好擅长表达汉语内容。
【参考文献】
[1][2][5][6][8][9]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449+446+35+526+479.
[3]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931.
[4] 李学勤主编. 毛诗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69.
[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434.
[10][11] 汉语大字典(三卷本)[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244+396.
【作者简介】
钟发远(1965—)男,汉族,重庆璧山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代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