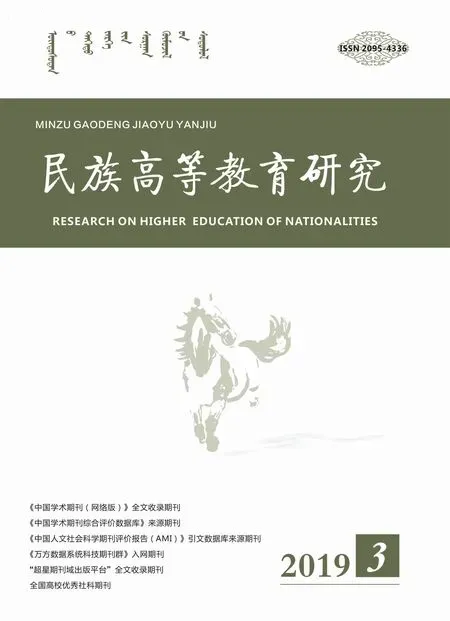通识教育选修课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
阿拉腾巴特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内蒙 古通辽 028043)
一、问题的提出
通识教育选修课,是指高等院校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而开设的,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的非专业课程。在国内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也有“公共选修课程”“全校选修课”“综合素质选修课程”等不同称谓。通识教育选修课既可以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广泛的知识面、较高综合素质的全方位人才,又可以通过丰富校园生活,开拓视野,活跃思维来达到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目的。通识教育制度在国内高校逐步得到确立之后,通识教育选修课也开始在高校课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借鉴了西方大学经验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在国内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存在定位不明确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近年来,有较多研究涉及了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实施现状。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研究将综合素质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作为分析对象,涉及内容包括课程设置和管理、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等。
王迎吉在《高校综合素质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认为,选修课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当前高校综合素质选修课在课程类型、教学安排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必须从课程设置、规范教学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1]。王伟亚在《我国高校公共选修课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中通过借鉴美国、日本、韩国等高校公共修课管理的先进经验,提出学生是学习中的主体,高校应该设置科学的选修课结构和提高公共素质选修课质量的对策[2]。陈爱良、田庆华等人在《推进高校全校性选修课有效教学的对策探讨》中认为,全校性的综合素质选修课的教学是高等学校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全方位的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邹吉高的《浅析高校选修课的作用及其教学管理现状》认为,在当前高校的课程改革中,选修课教学与管理日益加强,但是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想要保证和不断提高选修课教学质量,就必须加强对选修课的教学与管理[4]。
第二种研究以具体的某一门通识教育选修课作为分析对象,围绕该课程的设置与定位、课堂教学与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
朱晓勤在《〈清洁生产〉公共选修课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初探》中认为,学生通过《清洁生产》公共选修课的学习,既可以拓宽知识面,又可以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实施清洁生产,不仅是综合素质提高的体现,也是个人修养提高的表现[5]。申健等人的《浅谈公共选修课教学方法改革与完善——以〈食品营养与卫生〉课程为例》认为,公共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与专业课程不能等同,要灵活变通进行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6]。
上述两种研究对我们加深理解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现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侧重点在于通识教育选修课实施效果的分析。笔者认为,研究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现状不仅应该考虑实施效果,还应该以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作为参考坐标,明确其课程定位,这样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较为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将通识教育选修课在高等教育中的历史演变作为研究当下问题的切入点。这一分析具体涉及通识教育的发展史和大学选修制度的演变过程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国内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面临的特殊处境。
二、对通识教育选修课历史演变脉络的梳理
要澄清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定位问题,就必须厘清其历史演变脉络,主要涉及两种教育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即通识教育制度(general education system)和选修制度(elective system)。
(一)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通识教育源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课程称为自由技艺(liberal arts)。自由教育最初出现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教育视为“自由人”的教育[7]。这里的“自由人”指的是城邦的统治者,也就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一方面有权利直接参与城邦的公共政治和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奴隶主管理自己的奴隶,学习自由技艺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和管理奴隶。因此,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自由教育理解为“培养统治者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行业的实际操作是奴隶们的事务,它有损智力的发展,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违背自由教育的原则。“自由人”如果醉心于狭隘的功利,学为干禄,必然妨害对纯理论的钻研,同样是不自由的。
自由技艺在中世纪欧洲发展成“七艺”(seven arts),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其中,文法、修辞、辩证法称为“前三艺”(trivium);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称为“后四艺”(quadrivium)。“七艺”也是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主要教授科目。学生修完“前三艺”可获得学士学位;如果继续学习“后四艺”,毕业时可获得硕士学位。
17世纪以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在欧洲逐步形成,诞生了以物理学为首的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应用到社会生产活动中,改变了自由技艺高于实用知识的局面。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有关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形式教育论认为,人的心灵具有多种不同的官能,每种官能都可以选择一种难度较高的教材通过教学加以训练,使之充分发展,然后用来学习其他不同的教材,这样便于学习者学习和掌握其他知识。实质教育论认为,普通教育应该以获得具体、实用的知识为主要任务,学习知识本身就包含着能力的培养,能力无须特别训练。工业革命以后,科学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并且在19世纪逐渐取代了以“七艺”为主的古典课程。这种趋势在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家英国尤为明显。19世纪30年代掀起的“新大学”运动更加注重实用知识和市场的需求,大学专业教育得到长足发展,自由教育在新兴大学中被逐步边缘化。对此痛心疾首的纽曼于1855年出版的《大学的理想》中系统论述了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捍卫了欧洲自由教育的传统。他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以此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纽曼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8]。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在西方大学出现一种妥协趋势,并且推动了通识教育制度的诞生。通识教育制度克服了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二者择其一的困境,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专业知识也要掌握一定的非专业知识,理解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在20世纪的教育理论中,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都强调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通过通识教育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以此捍卫欧美自由教育的传统。哈佛大学在1945年发布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标志着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制度的诞生,成为许多国家的大学借鉴和学习的典范。
进入21世纪,国内许多高校开始实施通识教育。不同高校虽然在指导思想、教育模式、组织管理、资源摄取等方面有差异[9],但是对通识教育的基本定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余瑞君指出,通识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以及沟通交流、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艺术鉴赏和价值判断能力,探究问题的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具有道德观念、责任感和同情心。”[10]因此,通识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着专业教育无法替代的功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专业教育“主要侧重培养学生某一学科的学术素养和基本技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具有一定的通识教育的理念”[11],通识教育“致力于经典,着力体现人文和科学的有机融合,而人与自然联系通道的打通也主要依靠人文方面的课程。”[11]通识教育是高校学生拓展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途径。一般高校的通识教育学分和学时比例为学生毕业所需总学分和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哲学等极个别专业除外),这样的比例较为合理。
(二)选修制度的历史演变
选修制度是允许学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专业和课程的一种教学制度。选修制度在17世纪末起源于德国,并于18世纪在德国大学得到普及。当时欧洲的大学开设的都是必修课程,教学形式采用统一的班级授课制,教学计划整齐划一,学生没有任何选课自由。随着近代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大学开设的课程逐渐增加,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数量繁多的课程。加之上述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争的激化,选修制度成为解决传统大学教育弊端的一剂良方。19世纪早期,选修制度传入美国,被美国大学接受和发扬。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和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选修制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较为稳定的教学制度。随后也被各国大学效仿。
汤建认为,欧美大学选修制度的三大要素是学术自由、以人为本、适度自由。学术自由是选修制度的理论渊源,主要体现在学术组织有独立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允许教师“教得自由”和学生“学得自由”。以人为本是选修制度的指导思想,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身心发展特征。适度自由是选修制度的存亡原则,过度的自由会造成学生滥用权利,避难就易,选择的课程之间缺乏相应的逻辑性,导致选修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适度的自由才能促进选修制度的健康发展[12]。
随着通识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西方大学的选修课程也分化为两种类型,即专业选修课和非专业的通识教育选修课。
三、通识教育选修课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
(一)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现状
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识教育选修课是通识教育制度和选修制度在西方大学结合的产物。通识课程不同于必修课,学生有一定程度的选课自由。选修课程不同于专业选修课,必须是学生所学专业以外的课程。
21世纪初,随着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的引入和普及,通识教育选修课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当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必修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修养、政治理论与时事、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等,这些课程是通识教育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的课程为选修课程,开设情况因学校而异。总体而言,当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通识教育选修课未能充分发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功能。
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学生选择专业一般不在入学之前。学生考取的是某大学,而不是某专业甚至某院系。即使有专业划分,学生在入学最初的一到两年只有范围较广的“大专业”,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或者三年级才会选择针对性较强的“小专业”。这些国家有较为灵活的转专业制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调整专业。因此,大学第一年乃至第二年没有专业课程,而是安排大量的通识课程让学生选修。学生在学习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确定方向,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将来学习的专业或者更换专业。这种教育生态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高校引入通识教育制度之后,大学第一年也禁止开设或者少量开设专业课程。这仅仅借鉴了通识教育制度的形式,而没有发挥通识课程的优势,尤其没有发挥通识教育选修课本应发挥的功能。通识教育选修课与学生的专业选择在国内高等教育环境中出现脱钩现象。很多教师和学生对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认识只停留在非专业教育的层面,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深入理解通识教育选修课的重要功能。
其次,学生的选课自由度不高。
当前通识教育选修课在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不大。无论是应修门类还是应修学分,选修课程远远少于必修课程。课程的学分比例一般不超过通识教育学分的20%,远远低于国外大学超过50%乃至90%的比例。再加上课程资源有限、选修学生数量多等因素,学生实际的选课自由非常有限。
再次,受自由教育传统的影响,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历来有“务虚”的倾向,即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这种做法很难在国内高校推广。
西方大学将探究真理置于神圣的位置。美国教育质量较高的大学一般极力淡化大学教育的功利性目标,而将公民教育、人文修养教育作为接受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直接考虑学生将来的就业形势。我国高校推行以理论知识为主的选修课程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国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学习知识并不只是为了探究真理,更主要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大学本科专业的设置也以就业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因此,在国内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中有不少技术类的或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学生也更喜欢选择此类课程。这样就同自由教育传统中博闻强记、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相冲突,通识教育选修课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专业教育。
由于上述原因,通识教育选修课这个“舶来品”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环境中变得面目全非,通识教育选修课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也变得极为模糊。
(二)通识教育选修课应该有符合我国国情的课程定位
如前所述,在西方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选修课既是学生培养兴趣的一种途径,也是选择专业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我国高校尚未普及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通识教育选修课很难发挥这种功能。同时,国内通识教育选修课在通识教育中的比重小,实用色彩较为浓厚。考虑通识教育选修课理念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我们有必要对通识教育选修课给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明确定位。这既不是对西方经验的照抄,也不应该是对现实需求的简单回应。
首先,通识教育选修课是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
国内高校推行完全学分制条件尚不成熟,在大学入学伊始,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的学习就应该有明确的主次关系,专业教育仍然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因此,通识教育选修课在通识教育中的学分比例也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也符合国内高校通识教育的现状。同时,通识教育选修课可以结合“校园行为文化的建设”[13],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传播途径。
其次,通识教育选修课以学生专业外知识、技能的拓展为主要目标。
通识教育选修课虽然是专业教育的补充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有助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14]。第三方教育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34%的2016届本科院校毕业生三年之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15]。通识教育选修课无疑能够为这类学生提供学习非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目前,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应修课程学分一般为每名学生10学分以下,而且包含部分必选课程。因此,高校可以将学生应修课程学分增加到14至18学分,学时可以由目前的200学时以上增加到300学时以上。
再次,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设置应该符合教育民主化的平等原则。
学生的需求是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如前所述,我国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应用性强的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设置应该充分满足大部分学生对实用性知识的需求,同时不能忽视少数学生探究真理、学习理论知识的声音。学校开设选修课程应该是全方位的,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让所有学生获得同等教育关怀。仅仅以多数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开设课程,既违背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也违背教育民主化的平等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这里设想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定位并非永恒不变,而只是针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针对地方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校应该探索更为开放的通识教育制度。笔者也期待通识教育选修课更大程度地发挥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