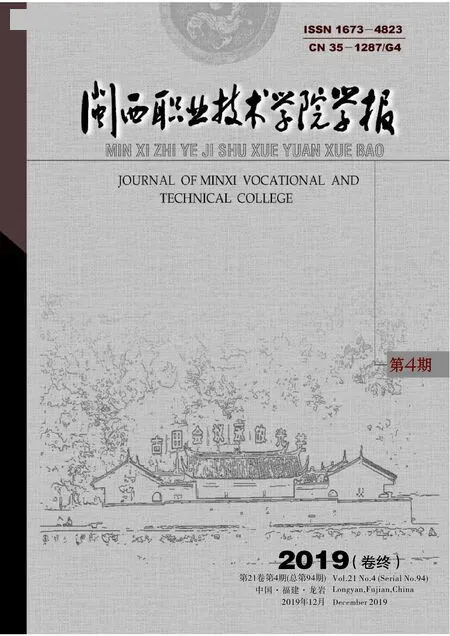石黑一雄的访谈式悲悯
——复调视角看《伤心情歌手》
瞿超域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州 350000)
《伤心情歌手》(Crooner)是当代著名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背井离乡的吉他手扬、曾红极一时的歌手加德纳以及他的妻子琳迪在威尼斯的邂逅。
在小说中, 石黑一雄采用嵌套式的叙事结构——通过叙事者扬讲述加德纳的故事, 又通过加德纳来讲述即将被自己抛弃的琳迪的故事, 这种结构被认为具有反讽性质, 而话语里透露的加德纳对琳迪的爱“又使得这一反讽染上一抹辛酸”,体现石黑一雄的悲悯情怀[1]。这种结合确实使人物形象多了几分酸楚,然而加德纳抛弃琳迪而显得作茧自缚,即使有悲悯的色彩,也极为寡淡。
真正能深刻体现石黑一雄悲悯情怀的在于他的包容,正如他曾说的“我并不想指手画脚地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2]。 在《伤心情歌手》中,石黑一雄放低作者的姿态,选择像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一样,将人物当作他的嘉宾,倾听他们全部的声音。他笔下的主人公们都积极地描绘自己,向他者揭示自己,人物话语中充满了他者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反驳。
M.M.巴赫金(M. M·Bakhtin,1895—197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 一书中提出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和大型对话(great dialogue)。大型对话指的是“结构上反映出来的主人公对话”,而当对话“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就形成了话语的双声,即微型对话[3]。本文拟分析人物话语中由双声语形成的微型对话, 以及人物在名利场与情感需求问题上不同立场交锋所形成的大型对话, 揭示《伤心情歌手》中石黑一雄独特的访谈式悲悯。
一、为自我发声的主人公
石黑一雄对人物的悲悯情怀体现在其访谈式的写作方式, 突出表现在笔下人物独白中渗透的自我揭示。这里的独白不是封闭的自我阐释,而是受到他者影响、揣测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后,在自己的独白中加以反驳和回应。
(一)主人公意识里的“你”
他者的影响始终徘徊在主人公的话语里。 小说的开始, 叙事者扬就表露出对他者敏锐的感知——“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 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4]。 话语中的“跟你说”表明扬在向他的倾听者讲述一个故事。对他而言,这个倾听者是在他讲故事时就“在场”的“你”,这里的“在场”是他者与叙事者在叙事者意识里的会面。 他者在随后的叙事者自白中一直时不时出现∶当扬解释自己工作的非固定性质时,“你”二度登场——“总之,实话告诉你吧……”[4]当扬说明自己见到加德纳激动心情的缘由之后,“你” 又一次现形——“现在你知道……”[4]“你”的反复出场揭示本应封闭在框架内的独白被他者的闯入打破而形成了对话的通道——由叙事者强烈的对话意识形成的通道。
同样,加德纳的自白也是开放的、对话的。 当叙事视角切换为加德纳时, 叙事者扬就成了加德纳的“你”,确切说,“你”是加德纳意识中作为对话的另一方的扬。加德纳时不时在话语中带出“你”——“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觉得呢”“我想告诉你的是”等[4]。他者在加德纳话语中反复出场表明加德纳对他者存在警觉,促使他产生被认可、被理解的强烈诉求,表现为在话语中竭力提醒对方认真倾听并参与, 促成了主人公话语里多次显形的“你”。
他者的影子更多时候变得模糊。这时,对他者警觉的对话意识就向更深层渗透, 进入话语的字里行间,使其中渗透着他者的质疑声和猜测的声音,而主人公的声音则紧随其后作出回应。 叙事者扬和加德纳的立场在话语内部的他者话语与人物自己的话语之间展开交锋。
(二)加德纳话语中的微型对话
强烈的对话态度使主人公与他者在自己的意识里会面。在主人公的意识里,他的每一句话都伴随着他者听到这句话的回应, 就像动物眼睛的色斑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stain)——“因为想像自己将被看而对形体可能的视觉效果作出拟态性的改变”[5],他们的言语也因此开始变形扭曲, 形成访谈式的微型对话。
加德纳话语与他者的话语交锋围绕琳迪的过往展开。琳迪出生于普通小镇,靠着依附当红明星步步为营走到了“富有、美丽、周游世界”[4]。 表面上,他诉说着曾经的琳迪的故事,为琳迪发声,实际上话语中的交锋是呈现自己的立场, 在为自己即将抛弃琳迪的行为铺陈理由。
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 是,她们也谈这些。 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 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4]
这段话是加德纳对琳迪在加州打拼经历的讲述,可以拆分成明显的对话形式∶加德纳先摹仿他人的口吻提出问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随后又转换为加德纳的语气来回答——“是,她们也谈这些……”在回答之后又变为他者的疑惑语调——“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 ” 随之而来的是加德纳的口吻——“当然了。 但是她们谈的是……”话语被拆解以后,成为一来一往的问答∶前者是通过模仿他者说话风格语调的提问,而后者是加德纳的回答。他者的好奇追问嵌入了加德纳的话语框架之中, 服务于新的主人加德纳。两个声音在话语框架内平行行进,形成互不冲突、彼此推进的双声语。它就像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访谈者之间开展的对话——主持人抛出问题,进而引导着访谈者更多地剖白自己的故事。而在加德纳这一段话中, 他者的疑问语调刺激着加德纳作出解答和叙述,二者共同将琳迪的故事呈现出来。
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 加德纳话语中他者的声音时而从疑惑变成质疑,而此时,立场就随之越发明显。
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4]
加德纳一边讲述故事, 一边察言观色——积极主动地去猜想他人的看法和怀疑。 他揣测着对话者的想法——“琳迪没有蒙过羞”, 随后将他者的看法嵌入“你以为……”的话语框架之下,形成全新的“镶嵌他人话语的语境”,这一全新的语境“形成一种促进对话化的背景”[6]。此时,他者的声音,即“琳迪没有蒙过羞”,染上了加德纳的否定和反驳的情态,而加德纳的情态又在他者怀疑声音的基础上生发出来。也就是说,两种声音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峙,在同一个话语框架内交锋。
话语的后半部分可以被拆解成明显的一来一往的对话形式∶一方质疑——“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 另一方反驳——“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 “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是他者对琳迪遭受过挫折的惊疑[4],是世人对琳迪的看法——以琳迪的美貌一定顺风顺水上位。从话语内容的角度出发,加德纳将他人的话语为自己所用,引出自己的观点——“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 加德纳的意向同他摹仿的他者话语的意向彼此对立, 使得摹仿带上了讽刺的意味, 而讽刺意向需要原话语中质疑意向的映衬才得以实现,于是就形成全新的对话化的语境。
他人的质疑推动着琳迪故事的明晰, 并使加德纳的立场逐渐明朗。 他回击着世人对琳迪的看法和怀疑, 并毫不吝惜地表现出对琳迪用婚姻换取名利的赞许。
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 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 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 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4]
这段话是加德纳讲述琳迪如何离开迪诺和自己在一起。 表面上看, 话语中没有明显嵌入他人的声音,但加德纳仿佛关注他者的表情和反应,保持着积极的对话意识,因此他的话语出现了扭曲,包括说话时情态的波动急转、语词的重复以及不断的解释。一方面, 加德纳的语气从平稳的故事讲述一下子变为激动的感叹∶“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这里,加德纳觉察到对话另一方的不认同,情绪发生波动,急切想要为琳迪和自己辩解。另一方面,他人的声音在话语中无需现形, 却引起了加德纳言语中的反复和种种对同样内容的翻新阐述和辩解。随后,加德纳的两句话——“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和“我猜你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听我的歌的”,都在描述当时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以此为琳迪离开迪诺寻找说辞。他的意识里徘徊着他者的惊疑, 三度强调这种行为的无可指责∶“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
扭曲了的话语使加德纳的立场愈发清晰∶他与琳迪是一路人,在内心情感与名利浮华之间抉择时,他们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加德纳的重复说明不仅仅是希望听故事的人理解琳迪, 更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决意抛弃琳迪的做法。
(三)叙事者扬话语中的微型对话
叙事者扬的对话意识较之加德纳更加敏感、激烈。他者的存在、怀疑和嘲讽声从一开始就推动着扬的自我揭秘。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 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4]
这里不妨将“我”替换成“你”,第一句就成了“瞧你说得好像你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 也就是说,扬模仿着他者对自己的嘲讽,用他者调侃的口吻,带着讥讽的意味。 同时,话语由被嘲讽的对象说出,表达对嘲讽者的怨念。 他者的嘲讽甚至直接被逐字保留嵌入扬的话语里。 “吉卜赛人”是平时其他人称呼他们的方式,而扬延用了这个称呼来指代自己,实现了自我解嘲,传递了扬对他者话语的气愤。
接下来,话语出现了察言观色型语言“所特有的语言阻塞”[3]。 主人公似乎觉察到他者对于“吉卜赛人” 这个称呼的不解, 以插入语的形式解释了来源——“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 又继续解释称呼背后的含义。 整个话语都以顾及和回应他者的形式推进, 揭露出扬是来自异国且没有固定工作的漂泊乐手, 随后继续以话语内部的对话揭示他是不受欢迎、并被当地人看不起的吉他手。
可是在这里? 吉他手! 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 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4]
上述话语可以分析出对话。 他者提出困惑∶“可是在这里? ”“吉他手! ”接着是经理们的声音∶“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 ”
扬将自己解释的口吻说出的言语“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插入在第二个对话中间[4]。 本该由三个人说出的三种不同语气的话语相互重叠融合之后,由扬一个人说出,催生了三个声音之间的对立交锋。这种对立冲突渗透到话语的细节之中,表现为语气的急转直变,并体现在标点符号上。扬的处境和身份就在话语内部的一来一往中更加明晰, 而扬的立场也同他的故事一起浮出水面。
唱针“嗞” 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 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4]
在提及自己破坏唱片被母亲责骂的事件时,主人公似乎感觉到他者的疑惑, 担心他者将母亲的发怒视为大惊小怪,在话语行进到一半时插入了“那时还没有CD”,然后才道出自己被母亲嚷嚷。接着在提到自己伤心的时候, 对话意识又使他猜测听者的想法——因为母亲的“大声嚷嚷”才伤心,因此他先否定了这种猜测,紧接着说出了原因——“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 每一句话都在为前一句话提供解释,都是小心谨慎、察言观色的结果。小心翼翼的根源在于扬对母亲的在意,对情感羁绊的在意,也正是因为重视情感羁绊,扬才会在看到加德纳的时候激动无比。
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4]
扬的兴奋溢于言表, 以至于话语中连续出现两次感叹号,重复了两次“为了”,甚至表示自己完全不在乎他者的嘲笑——“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小听差”是他者的嘲讽,这一他者的形容被引入话语中, 反映了毫不在意只是表面现象,而事实是,这个声音在他意识中徘徊并影响着他。 将对自己的慰籍建立在他者的嘲讽之上正是自我意识的挣扎, 因而两个声音在话语内部僵持冲突。在这场僵持中,主人公扬的自我意识尽管没能消灭他者的意识却依然压制住了对方——选择和加德纳搭话。
二、未完成的复调曲
主人公的立场通过话语内部的对话慢慢呈现,但对话还跳出框架之外形成主人公与真正在场的他者之间的沟通,形成大型对话。
小说共有三条线索, 其中两条线索是围绕某一主人公展开。一方面以扬的叙事视角展开一条线索,回溯扬的过往经历来揭示他的立场。另一方面,当叙述视角转换至加德纳一方, 小说开始描绘琳迪与加德纳的过去以形成加德纳的立场。 在两位主人公的广场会面以前,两条故事线索平行发展,互不干扰。在扬的故事线索中,扬像受访者一样倾诉,而作者就成了访谈主持人——引导访谈者说出自己的故事和倾听,却不作出评判。 在加德纳的故事线索中,作者的受访者从扬转为加德纳。 两条线索都以讲述回忆的形式插入小说的主线之中。
小说的第三条线索从扬和加德纳相遇开始,围绕两个主人公发展,直到曲终人散结束。在这条线索中,两位主人公彼此倾诉,就情感羁绊的主题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发表自己的观点。扬无法理解加德纳与琳迪相爱却要分开,认为两个人相爱就该在一起,像“那些歌里唱的”那样,因此他一再表示疑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开呢”“我还是不明白”等[4]。而加德纳将感情羁绊视为事业的绊脚石, 为了重返歌坛, 决定舍弃他心爱的琳迪。 在主人公的交谈之间,他们都把对方当作受访者对待,发问并认真倾听对方的解释,形成访谈式的对话。
这种访谈式的对话使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未完成性,正是这种未完成性成为访谈式悲悯的关键。所谓悲悯是因慈悲而怀抱同情,对他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并“以一种理解、了然、同情的态度去对待”[7]。在小说的最后,两种立场都没有被否定而消灭,都被保留了下来。扬不认同加德纳,认为相爱就不该分离,所以回想起来的时候“黯然神伤”[4]。 加德纳知道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我知道你很难明白这件事情”[4],但也不强求对方认可自己。 故事的结尾,两人分道扬镳。扬依然是漂泊的、在异乡讨生活的吉他手,而加德纳最终和琳迪走向婚姻的终点,牺牲爱情以换取复出重来的机会。
小说的情节走向终结, 但小说并没有像很多复调小说一样,作者没有充当裁判磨灭任何一个立场,而只是“制造一个讨论的局面”[8],将两种观点呈现在读者眼前,走向一个未完成的结局,以博大的胸怀来理解角色们的种种无奈。
三、威尼斯的狂欢
叙事者扬是来自曾经东方阵营的无根咖啡馆的吉他手,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被当地人轻视,是具有浓重贫民窟色彩的人物。 而加德纳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有亲密的爱人,也名利双收过。 二者在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上存在差距, 使对话在现实中难以发生,因此对话要求以狂欢化(carnivalization)作为手段消除这种距离。 在民间狂欢节上, 对权威的脱冕(crowning)和对底层人民的加冕(decrowning)消除了等级制度,人们开始随意而亲昵地接触,而狂欢化正是这一节日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加德纳和叙事者扬的对话起源于加德纳的脱冕和叙事者扬的加冕。从加德纳的身份看,他是一个明星,是应当被仰望的存在,但问题在于,这些都是曾经,往日的辉煌已经消失,属于明星的光环已褪去。他的过气使他被脱冕,他的地位随着脱冕发生降格。
加德纳过气了却不安于现状, 他渴望回到自己的事业高峰期。对于渴望再度红火的加德纳来说,需要歌迷的支持。当琳迪语出不当的时候,他就会责怪琳迪——“别对人家无礼”, 并且这样的训斥多次出现,就像琳迪说的“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4]。 叙事者扬自己虽然算不上是歌迷, 但扬的母亲却是加德纳的忠实歌迷, 并且扬也因为对母亲的感情而尊重欣赏加德纳。有着一个歌迷母亲,加之扬本人对加德纳的热忱态度都为叙事者扬的地位升格加冕。
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人相遇的地点——威尼斯。水城威尼斯聚集着外来观光的游客、演员歌手、当地居民以及外来谋生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相逢,使得威尼斯染上了一种狂欢的意味。 作品中有两个重要的地点——圣马可广场和威尼斯的河面。
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3]。 在圣马可广场,加冕和脱冕同步进行,权威和等级的界限模糊。普通人可以议论名人,甚至带着调笑的语气——“看,是沃伦·比蒂。看,是基辛格。 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4]。 圣马可广场成了两人亲昵接触的狂欢舞台,促成他们的相聚,而夜晚的威尼斯河面则将狂欢推向了高潮。在河面上,伤心的情歌手开始揭露他的孤寂——他的过气第一次摆上了明面,因为他听到了“笑声”。笑声由叙事者扬的一句话所引发,“真有意思。 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4]当船驶过一家热闹的餐厅的时候,叙事者扬随意地说出了这句话。随后,船夫维托里奥就“笑了一下”[4]。维托里奥的笑是对叙事者扬这句话的回应,表面上对叙事者扬发起讽刺,但实际上却将讥嘲指向了加德纳的过气,唤起了一个全新的、坦白的加德纳。
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 谁知道呢? 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为什么要呢? 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4]。
从整体看,这句话是加德纳讲的,但将其分解成部分之后就会发现叙事者扬和那些进餐者的声音分别被镶嵌在了其中∶“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是叙事者扬说话的口吻,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被镶嵌到加德纳的话语中, 由加德纳讲出并沾染了加德纳的情态。 而“为什么要呢? 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则是通过非直接引语的方式插入,以进餐人的口吻说出, 夹杂着进餐人的理所当然和加德纳的苦涩自嘲。 “镶嵌他人话语的语境,形成一种促进对话化的背景。 ”[6]加德纳的话语语境中嵌入他人的声音,标志着加德纳的对话意识就此觉醒。
狂欢化使小说的世界进入“脱离了常规的生活”[3]∶对人物身份的脱冕与加冕将歌手加德纳从高位拉下,也将叙事者扬从低位抬起,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消除;情节发生的地点——广场和河面的狂欢色彩,促成二者的相逢和亲昵,唤醒了加德纳的对话意识,进而发展成以对话的形式自白和为自我辩护。
四、结语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9], 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的重要思想。 而石黑一雄对待笔下主人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像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引导主人公说出他们的故事,给予主人公自我辩护的权利。无论是扬还是加德纳,我们看到的不是其他人眼里的他们,而是他们眼中的自己。 在威尼斯,所有人表达着自我,他们观点相左,但尊重对方的观点。他们就像彼此人生中的过客,各自为自我发声,保留立场,这是石黑一雄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不高高在上作出裁判, 尊重和理解不同观点, 以尽情对话打破消费社会和媒体时代下的疏离感,这就是石黑一雄的访谈式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