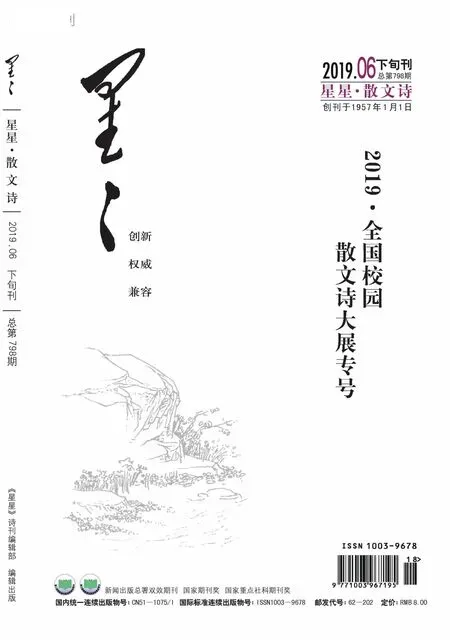灵魂的发现与寻找(随笔)
转 角(黑龙江)
如果说与散文诗相遇是宿命,那么灵魂与肉体的一见倾心亦是宿命对我的指引,而灵魂的存在,既是思考的存在,二者彼此印证。为了自我灵魂与生命的完美呈现,为了实现存在的可观照性及对自身归宿的终极寻找,2011年11月我连续用十个夜晚完成了近一万字的长章散文诗《荆棘鸟》,以此对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进行了一次洗礼与放歌。
生命恒有变数。《荆棘鸟》中作为男权的替代物“太阳”“豹子”等意象是所有渴慕爱的女子的一种奢侈愿景,在追寻真爱的旅途上,路遇伪善、伤害、背叛、生离、抉择等“萤火虫”、披着“花衣”的猎豹的多重考验,苦痛与血泪交织呈现,并歌吟着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生命体验。然而“荆棘鸟”又是开悟的,她坚守着自己的忠贞与孤绝,不惜以满腔碧血挽救人们真善的良知;她用爱大写着爱,并最终以崭新的方式进入新的生命的轮回。从生命的孕育到出生跋涉,从生到死,《荆棘鸟》貌似是对小我命运的回顾,是一种反抗和对灵魂家园的坚守,实则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的一次生命的释放,是超越自我、返璞归真的一种探求,她昭示着光芒的所在和源于一切美好的精神慰藉。
为了更完整地切近自身,完成一次生命与灵魂对自我的另一种召唤,2014年7月我来到了心之神往的西藏——这个带给无数人心灵震颤的皈依圣地。回来之后完成长篇散文诗《藏地书》11章。而选择以长篇散文诗的形式来列述途中所感,是希望能够借助自己鲜活奔腾的血液展露对此地不同的审美及对自我的深度抵达,以期完成一次向内行走的不一般的旅程。
虽然写作时间不长,但自《青龙》系列之后我发现当我们完成一次对自身的寻找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以不同的审美情态颠覆抒情、哲思、理论、诗意,以探测不可估量的内心深度而发现一个全新的本真世界,从而使“我”的存在感不再被疏离,不再失去弹性,这是多么的美好。如果说三十六章《荆棘鸟》是对小我命运的一次回顾,那么,《藏地书》则拓宽了我生命得以奔突驰骋的疆域及其价值取舍,借用“我”和“我”的分身(灵魂)这个主诉体完成心与心、自我和他我、人神、灵肉、信仰……这些矛盾且彼此依存的存在进行了一次大检阅。在此漂泊过程中,我试图拯救自己的过去,矫正曾经错误的认知方向,或者说我是在时间的瞬间借用散文诗这个客体倾诉我们无法把握的命运的不确定性。
当然,在天路的一旁我也寻得了自我救赎走向光明的法门。
而近两三年,我遵从内心的声音,逐渐趋向短章散文诗的探求。因为在散文诗的世界,我时刻观照甚或期待突破另一个我,神秘的,无意识的,甚至可以理解为灵魂与宿命对我又有了新的要求与祈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深陷其中,发觉短章散文诗更具有诗的特性,她更严谨,有张力,即使是情感堆积的碎片,亦有着灵魂取舍时的伤痕;即使她意象,隐晦,甚至暴力,跳跃,也只是着力点不同,是有着敏锐嗅觉的文人对散文诗的最亲切的发现与遇见。如《向金的太阳》《令人费解的南多女士》《一位女博士头顶的帽子》《失落的天堂》等。虽然在创作中,缺少性别指纹的我偶尔也渴望回归为一个温柔女性的细腻温婉,也曾尝试过,但这种改变令我沮丧,我无法让自己热爱的倾诉方式与刻意而为的 “突破”互换身份。那么,我想,这也许就是散文诗给予我的终极魅力吧。
路,是回旋的,是向着远方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内陆,在创作上,我所见到的都不是风景,而是灵魂的发现,是对自我的寻找与识别,是命运和因果轮回的反复叠加,沿着行走线路,我解构着“自我”与“他我”,剖析着内心的感知,虽然带有某种主观性,但这种精神寻找是灵魂的归属,是活着的力量与希望,是生命大秩序的维持与延伸。当然,在表达方式上,“我”变身为肉体的统治者、神灵的切近人、虚无的载体,被哲学所统领,被自身的灵魂所分割,但同时我又还原且丰富了“他我”这个真身,并企望以更加饱满诗意的文字呈现给听众、过客、狭隘者、红尘中的隐士、善良人,最终成为死之绝唱,归还给大地……
至此,阳光,方铺洒向远方……
——浅析《荆棘鸟》拉尔夫神父的悲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