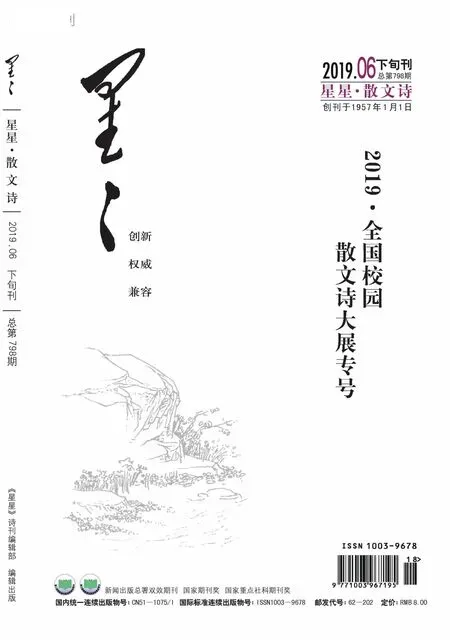自然书(组章)
孙文华(四川)
我的心跳和大地的心搏联系在一起。
——特丽·威廉斯(美)
春天的号角
春天的号角在一枝藤条上,吹响了蕴蓄一冬的思想。
早前的枯条和零星点缀于枯条上的叶片开始返青了。
现在,藤条里仿佛注入了新生的力量,活力四射,就像一个青年有力的臂膀。
而那些先前的黄叶,也一点一点褪去了黄,彰显生命蓬勃的生机。
是春的号角,冬雪无法阻抑的声音!
满世界都长满了新奇、新鲜的,聆听的耳朵……
行走大地
草木在大地上行走。从没有停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它们趁着早晨的露珠行走,趁着夜晚的月光行走,没有终止符。
它们要去向哪里?
大地的深处,无边的辽阔!
我在大地上行走,拥有一棵草木的姿态。向着大地的深处。无边的辽阔。
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请将我撒于这棵树下。
这林子里的随便一棵树,都是我的安栖之所。
我只想与地,与树,与树根,亲密接触。
相吻。只想与树相伴相依,相濡以沫。
只想成灰了。还被一棵树护佑着。
在浓氧离子中安眠,安寝安息。
还有阳光照着,即便成灰,也被漫天的阳光照着。
雨来也蛮好呀,我可以入地入根。
然后呀,枝繁叶茂天蓝水清。百年之后。我觅到了安眠之所。
自然之声
喜欢这丛林掩映的小溪,能听见潺潺的水声,却不见源头。
不必去寻觅,有耳福听到就甚为满足。
琤的声音,在我心里缓缓流过。
“黄四娘家花满蹊”,不是花,却有同样的意境。数十种绿,在溪流的两岸滴翠,组成了这让人眷恋的世界。
而一个人,不经意间,被谁的妙手,悄无声息画进了一幅画里?!
与一株盆景对话
你的身形那么矮,那么小,却可以顶出别样的风景,别样的天地。
最初,你树身上只那么一点芽,不曾想,你潜滋暗长,抽枝展叶,成今天的模样。
你不语,但你浑身似乎长满了嘴巴,急切地想要诉说什么。看,新的芽儿又不断地冒出来了,又会长成什么样呢?
还会长成你喜欢的模样,内心的风景,你的pose定格,你在,无所不在!
鸟和树
只听见鸟声,却不见鸟。偶尔看见树叶在颤动,没有风,一定是鸟在五线谱上跳动。
这是一株非常繁茂的树。我常站在树下,或者坐在树下的石凳上。
听鸟起落的叫声,婉转的歌喉。我不知树上是什么鸟,但有鸟足矣。
有鸟,树不寂寞;有树,鸟便有了家,其鸣声更欢。
是亲密的恋人么?我是树下一盏闪亮的灯泡。
野 地
真好,这么一片野地!哪怕只有十来平方米!
没有人管它,或者,是鸟衔来的种子,在这儿生根、发芽,滋长成现在的模样。
有十几种草木的芬芳哩!不用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儿,它们兀自在这里茂盛着,绿着。
喜欢把心腾空了来盛它们,一次次让它们在我心里尽情地伸胳膊、展小腿儿。
我的心不在别处,尽兴在这里。
百草疗疾
百草的芬芳弥漫,升腾。我浸在百草的芬芳中。
芬芳祛毒。身体的毒。心灵的毒。
百草汇合。百草和鸣。
百草在疾患处发力。百疾顿消。百疾无处可藏。逃之夭夭。
我看到那个尝采百草的人。他正背负一个背篓,穿过荆棘,去采摘百草,有名、无名的草。那背篓是他的命,日日相依。
尝草。那是一个敢于献身的人,那是一个在舌尖上跳舞的人。为着众生。
菩萨心肠。他的眼神明亮,那些草药,也具足了人性的光芒。
疾患之人。足以从深渊,或黑暗中走出。
背负满满的自信,神圣的使命,那个尝采百草的人,迎面向我们走来。走入历史的深处。
迎着他的曙光,我们在百草的芬芳中,在无疾处,把生命擦亮,磨亮。
与一丛植物轻语
非草非木,亦非花,该怎样叫出你的名儿。我汗颜地叫不出。那就泛称吧。
你不在乎,怎么称呼无所谓,不在乎符号,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必须蹲下身来,把高昂的、不可一世的头颅埋下来,低到低,一直低到一丛植物的根部,你才能将它打量,你才能感受它博大的心跳。
天生是这样,没有粗壮发达的根系,但哪怕只一块根,你也紧紧地攥紧泥土,攥紧大地,就像握起的一个拳头,就像无言的宣誓,却是一场不可或缺的盛大的仪式。
我的手指可以触抚你,但我只是定定地出神地看着你。
我打开鼻翼,呼吸你的清香,草木何处无清香啊?!清香入我肺腑,清香润我心田。
我的心充满了无上的喜悦,肺开合自如。
脑子也灵光、灵动呀,献给你这么一首小诗,在我的心底。
没有炫目的色彩,没有花开的吸睛,兀自在一隅,绿着,生长着,葳蕤着。
我该怎样赞美你,我只有把头低下来,把身子蹲下来,近近地贴着你,定定地瞧着你。唯一的选择,我心如此。你不语。
会思想的芦苇
背靠任一根廊柱,坐成时光里的一抹剪影。
刚好正对夕光。刚好见着夕光如何在水面撒下金鳞。
有芦苇随风摇曳。会思想的芦苇,站立水边。
没有水鸟,没有白鹭和野鸭。我的目光钓着,就像钓一尾鱼。
没有出现,它们的家在哪儿?黄昏或许就要归来,栖息于水边,栖息于这苇丛。
我闭上眼睛,背靠着廊柱,融进波光里了。会思想的芦苇。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