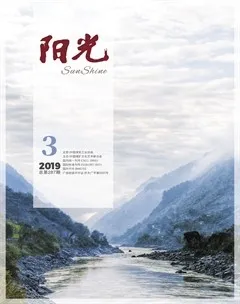生存镜像的历史意蕴与审美表达
吴子长的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一直往南走》是2018年《阳光》杂志在头条推出的重点篇目。作为一个差不多是专事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这个中篇不独显示其中篇创作的不凡实力,更体现出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上的新思考新探索。
《一直往南走》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小说主人公徐老三一家饿死,唯独他一人逃出家乡,一直向南走,靠着乞讨,走出灾区,被淮河岸边的一家煤矿招为矿工;他在矿上娶了一个带着女儿的寡妇,生存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一家人赶上好时代,过上幸福生活。这样的故事,初读会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因为这与吴子长以往的中篇小说主题很相近:似乎还是命运主题与日常书写的重复。但认真阅读之后,就会发现,《一直往南走》与吴子长以往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区别。吴子长从以往着重写人物命运变迁,过多地关注人物外在的命运走向,那样地在故事情节上的拓展与延伸,转而朝向对人物的存在状况的探索与揭示。他是通过对徐老三个人的生存史的叙述,着力钻探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和解剖人物灵魂的层面,努力表现出那些在存在中发生的人物内心与心灵的看似平凡而实在深刻的变化,进而折射出社会的理想与时代的变迁。应该说,这样的主题挖掘是深刻而新颖的,而与此同时,小说在艺术上的创新与变化,也很值得关注。
一
首先,《一直往南走》是一部普通人的生存史。它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的求生欲望,真实地表现了人的生存本能,从而揭示出人内在的更为本质的力量与动机。相较于以往的关注一般的命运变化的叙事,《一直往南走》将笔触转向对人物生与死相搏的叙写,无疑这是一种更加向内的或者说更加纵深的书写。小说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场旷世大饥荒的凄惨场面,徐老三的家乡徐大郢子“近百户”的村子,“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死沉沉的。像一个巨大的坟墓”。徐老三已经不记得是两天前还是三天前吃过饭——所谓的饭不过是嫁到邻村的姐姐“偷偷”送过来的烂掉了半边的山芋母子。“他饿瘫在家里,再也动不了了”。小说就是这样将人物置于如此残酷的生存场景之中,不由使人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的名篇《热爱生命》。所不同的是,杰克·伦敦的小说是属于美国式的淘金冒险那种具有硬汉派风格的英雄主义叙事;而在吴子长这里,却是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面临的天灾人祸的大饥荒,这样的生死考验,是如此地充满绝望与恐怖,却又如此地普遍与真实,没有丝毫传奇可言,而是中国民间平凡而广大的苦难,是更加残酷更加使人绝望无助的人间悲剧。千百万人饿死了,徐老三差不多就是其中一个了,因为死神已逼近。吴子长写道:“徐老三的脑子里也像这弥漫开来的雾,一片糨糊。他不知道他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小说正是这样揭示了作为人——徐老三无比真实的生存状况。徐老三怎么办?活的路在何方?小说接着写道:“似乎是第三天的早晨,他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在他爬起来的那一刻他就决定,他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出村庄,如果就这样死在家里,还不如走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命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实的一切,在此时对于徐老三都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此刻,他只剩下了本能,人的求生的本能。吴子长正是这样,在小说开始就将笔锋直接切入人的内心,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能,去寻找决定一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更为本质的东西。而正是这样的本能的力量驱使他在后来,“顺着河堤向南走”,“他觉得只有太阳不嫌弃他”,“他想,即使死也要死在这明晃晃的太阳底下”。而当他走出死亡的阴影,他不禁感叹道:“外面的太阳真好,活着真好!”我们说这种感慨是发自本能的感慨,更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对生存的展现,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它既写出了生存的残酷,更写出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显示出生的抗争的力量与意志。而小说不仅写出了这样的本能,更写出这种本能的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揭示出其方向指引性与存在的真理性。它指引着徐老三,也指引着人类——活下去。
其次,《一直往南走》也是一部矿工的成长史。小说不仅有求生欲望与生命本能的揭示与书写,更真实细腻地描写了徐老三这样的农民成长为一个现代矿工的过程。比如,在写徐老三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当上矿工之后,却又面临职业的风险这样的考验。小说写到徐老三每天从地面下到井下时,“都有一种从天堂掉进地狱般的感觉”。这时的徐老三心理是怎样的?小说写道:“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往往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这么好的日子谁也不想这么快就过到头了。”这样的对生命的珍惜,对日子的审察,与其说是求生本能使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经过了大饥荒的逃难之后,获得新生的一种觉醒,一种对人生对生命的顿悟,或者说新的期盼与渴望。小说写他刚下井“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被头顶上突然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砸中。他一步不离地紧紧跟在师傅后面,任何地方,哪怕有一点儿响动,他都要揪着师傅的衣襟,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后来,看见矿灯,就觉得“像夜晚的星空一样,非常灿烂,非常壮观。渐渐地,徐老三的胆子也大了起来”。这里的“渐渐的”,是一种熟悉,更是一种成长,是对旧的农民徐老三的告别,是新的矿工徐老三的诞生。还有,徐老三在妻子死了之后,独自带着两个女儿,既要照顾家,又有繁重的工作,“每天像陀螺一样旋转着,似乎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紧的绷直的”。他就想办法,于是学会了随时随地睡觉的本领,“他还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如此等等,则不独展示了一个父亲的责任感,那种对亲情的守护以及由此萌发的巨大的生命能量;更是一个新矿工的职业操守,那种对工作的热爱、感恩与敬畏。如此等等,构成了徐老三成长的生命历程,那种身份的变换的背后,是一个人精神、品质与人格的崭新的变化,是一个新的人的诞生、生长与成熟。
再次,小说写徐老三经过大饥荒,经过上山下乡,经过改革开放……这种“一直往南走”的历程的展现,不独是徐老三个人的生存史与成长史,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是历史的镜像,是一代人生存的真实写照,甚至是一个民族苦难与奋进的缩影。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代矿工的生命历程、精神风貌与性格品质,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苦难中挣扎抗争,在漫长的岁月里艰苦度日,在默默无闻中的顽强坚守与相互搀扶,在日常生活中本分、善良、勤勉、节俭地生活与繁衍的人生故事。可以说,这是一部质朴而生动、形象而厚重的当代矿工生活史,也是中国当代煤矿发展变迁的缩影,是中国当代社会与历史的一个有力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长的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是具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的。
二
小说以朴素而自然的书写生动而富有深度地塑造了徐老三这个平凡而质朴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徐老三和千千万万的当代矿工一样出身农民,他没有文化,不懂得家国大计、人生哲理、前途理想以及爱情与浪漫。他们本该在乡村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地活着,像他们的祖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儿育女。他们不了解城市,对矿山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内心有着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的期盼与追求。这是徐老三们内心最强大的生命的能量,像小说中写的就是“一直往南走”。“南”意味着什么?是阳光,是温暖,是无限的勃勃生机,是无穷的生命与希望……小说抓住这点塑造人物,最朴实,却又可以说是最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灵魂,这是徐老三这样的农民矿工最本质的精神特征。这样的朴实自然里显示出的深度与高度,在以往写农民也好也矿工也好都是很少见的。
小说将“一直往南走”的信念融入到主人公一生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徐老三成为矿工、娶妻生女、工作生活直到光荣退休的生命历程。小说通过这样的过程化描述,向人们揭示了徐老三的质朴憨厚,比如他最初学徒时的胆小木讷,他怎样一步步由对下井的恐惧到融入矿工群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矿工。这样的过程实际就是他从生活的绝望一步步走向美好的新生活的过程。小说写了徐老三从当上矿工第一天,“抹着嘴打着饱嗝走出饭店,感觉外面的太阳真好,活着真好”到写徐老三“第一次从会计那里领到厚厚一沓人民币……有一种从地狱升到天堂般的感觉”再到徐老三与张永和相亲之后,顺便送给张永和带来的女孩一个泥公鸡,“小女孩手里的小公鸡吹响了,像吹响了徐老三与张永和新生活的奏鸣曲”,再到自己的女儿第一次叫他“爸爸”,“徐老三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有些麻木的心……顿时变得柔软起来,甚至被融化了”,感到“有了这两个字,他无论多么苦多么累,都觉得值了”……这些不仅是写了徐老三的求生的过程,简单的活下来的过程,更是写了他心灵的觉醒,那种对人生对生命的顿悟与领会,那种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获得,一句话,就是那种心灵深处的“一直往南走”信念的不断完善、升华与深化。如此,小说实际上是写了徐老三这样的人从活着吃饱向吃饱活着再到好好活着,这样不断地觉醒、领悟、追求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就不再是观念化的或静止的,而是活生生的立体的,有着人的成长脉络更有着昂扬向上的精神轨迹的形象。而且,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抓住了“一直往南走”这样的核心,使得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诸如此类,无不显得真实自然、质朴生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我们这个民族的古老的精神传统与民间日常的价值准则。
小说还着力刻画了他的一些个性与品质。比如他与张永和第一次见面,虽不如想象,却心里接受,“毕竟都是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能从大难中存活下来,本来就是很幸运很不容易的了,对生活还有什么其他奢求呢!”这就写出了他的知足与本分,对生活与命运的感恩,对同病相怜的人的善意、厚待与怜惜。再比如妻子病重,他不离不弃彻夜不眠地照顾,妻子死后,“他欲哭无泪”“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足见其淳朴厚道,重情重意。还有,妻子死后,他一个人既要照顾两个女儿又要工作,累得走路都在睡觉,“体重比以前轻了二十多斤”,但他“无论多么苦多么累,都觉得值了”,则是显示出他内心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与坚韧意志。而他的养女出嫁,他尽其所能使得养女体面地出嫁,尽了一个父亲的心意,赢得了矿上人们“好人”的评价……这些笔墨很好地描绘了人物的形象,揭示了其性格与精神气质,使之趋于饱满丰富。还有,小说最后还写了徐老三染上性病,这写出了他在妻子走后,儿女成家立业了,他退休后的寂寞与无聊,内心的极度空虚;从另一个侧面也显示出徐老三生命能量的强盛与本能欲望的强烈。这不但使得人物形象立体饱满,真实可信,而且从更深的寓意上揭示出像徐老三这样的群体,“一直往南走”,还远远不能止步,远未抵达精神的自由境界。小说以此喻示了徐老三们不仅要活着,更要美好地活着,有尊严有体面有信仰地活着,而这本就是徐老三们的永恒的追求,是人之为人永无止境的修行与进化。小说最后也写了徐老三的悔悟,写了他的再婚,享受着美好的晚年。这显示出作家的美好祝愿与悲悯情怀。
当然,小说中其他的人物也写得较有个性与层次。如果说徐老三们代表着一代矿工的形象,那么,张永和和马明安的妻子则代表着千千万万矿工妻子的形象。她们勤劳、节俭、持家、贤惠,爱丈夫,疼孩子,起早贪晚,为家庭为矿山献出了一切,她们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华女性的优良传统美德。除此之外,像热情仗义、乐于助人又心思细密的马明安,早熟懂事、孝顺能干、秀外慧中的宋萍,朴实大方、庄重心细的徐燕等等,都塑造得栩栩如生。这样的不仅有个性又有深度的人物塑造,既保证了小说整体的水准与质量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更凸显了“一直往南走”不独是徐老三一个人的人生追求,更是人们共同的美好追求,是一个时代的潮流,这无疑深化了主题。而小说这样的处理,使得徐老三在与他个性有别却又具有美好的共性的人物群像的簇拥与烘托下,就显得更加真实又更加突出。
三
在吴子长以往的中篇小说里,一般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能视角,或者是上帝视角,写起来比较灵活自如,方便运转。这也是许多作家共同的选择。在《一直往南走》里,吴子长在这方面,自觉借鉴了西方先进的叙事技巧,在小说人物视角的运用上,有了新的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当然是第三人称的全能视角。在全文四万多字的篇幅里,这个是占主导性的,便于作家主观意图的实现与创作目的的顺利达成,同时,也给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便于向读者提供阅读和理解小说整体的框架、营造小说中时间的流逝感与空间的存在感以及人物事件的关系。因为整个小说时间的跨度相当长,有几十年的变迁,这样相对稳定的视角运用,避免了因为视角过于频繁交替造成的凌乱与混杂,从而有了清晰明确的事件指向与叙事节奏。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吴子长很好地加入了一些人物视角的变换,起到了锦上添花的叙事变奏效果。
在第三人称的视角运用的间隙,作者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视角或角度的叙述——之所以说是掺杂,因为作家并不是生硬地搬用视角理论写作,而是将其自然而然地化在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语流里,几乎是了无痕迹。比如,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作者采用了徐老三的视角,突出了人物内在的主观感受与情感色彩。小说开始写道:“太阳照样升起来了,黄黄的,圆圆的,像一个大大的鸡蛋黄”“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黄黄的,像一个大煎饼”“天气彻底晴了,气温也在迅速上升,泥泞的小路上冒着像馒头一样的热气”等等。这些人物视角的描写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自然气候、具体时间,渲染了气氛,而且生动传神地烘托出此时此地人物细腻真实的内心活动,那种强烈的饥饿感,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小说不仅写人物运用这样的视角看自然环境,还让人物看周围的社会环境与个人命运的变化。再比如,在徐老三成为矿工后,小说写道:“第一次从会计那里领到厚厚一沓人民币,徐老三有一种从地狱升入天堂般的感觉”;而最初的下井,则是“每次由大罐从地面吊到井下时,都有一种从天堂掉进地狱般的感觉”。而当他渐渐熟悉了矿工井下的生活时,他眼中所看到的则是“只要一坐下来休息,每个人头顶上的矿灯就像夜晚的星空一样,非常灿烂,非常壮观”——这样的观感,只有像徐老三这样的新矿工,这样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感受到。在正常的第三人称叙述流里,融入这样的人物视角,作者让人物徐老三不仅看外界,还看自己,看自己的人生变化,看自己生命的行进轨迹。这样,在全能视角之外,有了新的视角的进入,有了声调与语气的变换,人物心理更加真切生动,形象刻画也有了层次递进,小说的底蕴也变得丰厚了。
不独如此,小说还运用其他人物的视角,写别人眼中的徐老三。比如,用马明安的眼睛来看徐老三。小说写道:“每次井下休息时,当工友们,包括他自己在内,在黑暗中大谈特谈女人时,他身边的徐老三就显得焦躁不安,将身子扭来扭去的……马明安知道,这个徒弟该有个女人了。”这样的叙述视角的变化,更加突出马明安对徐老三的关心,细致生动地写出了他的热情、细致与为人真诚厚道的性格。又比如写养女宋萍眼中的徐老三,则是这样写的:“徐老三每天下班回来几乎都要去菜园,把它整理得好好的,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蔬菜或瓜果,家里需要什么,她伸手去采摘一下就可以了。房子破了漏了,也不用她操心,徐老三早早地搬来梯子,在雨季到来之前,把屋顶上该修的地方都修理好了。”还有:“第二双鞋子她是准备给徐老三做的,徐老三天天下井,很辛苦,回来后还穿着那双又脏又破的劳保鞋。她也想尽尽一个养女的孝心,给他做一双能养脚的新鞋子,晚上洗了脚,穿了养脚的鞋子舒服舒服。”这就很好地表现了宋萍这个养女的早熟懂事、孝顺能干、秀外慧中的性格,使得她的形象更加美好可爱。而当徐老三在晚年,因为寂寞难耐染上嫖妓的毛病时,小说也通过女儿徐燕的眼睛写了出来,则既写出徐燕的朴实大方、庄重心细,更是将两代人的差距体现出来,隐喻了“一直往南走”精神的传承与延续这一深刻而美好的主题。
上述的视角的变化,在以往吴子长的小说里也许也曾有所运用,但像这么大的范围,取得这么显著的艺术效果,还是第一次。在《一直往南走》的创作中,这样的视角运用,不仅丰富了主人公徐老三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展示了一个矿工的成长史,更是借助这样的视角变换,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出一个矿工生命轨迹的变化。同时,这样的视角也折射出像徐老三这样的中国一代矿工真实的精神世界,进而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近半个世纪发展变迁,而这样的变迁与我们民族自身深层次的精神气质性格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内在的渊源。当然,除此之外,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细节描写上以及行文节奏与线索穿插上,《一直往南走》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吴子长的中篇小说创作,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与风格,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好的作家无疑总是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上述对《一直向南走》的简要评述中可以看出,吴子长的创作是在不断创新与变化的,《一直往南走》就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又一次新的突破与超越。我们相信并祝愿他在中篇小说这个文体上的探索与写作之路能走得更远更扎实,能有更加辉煌的奉献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