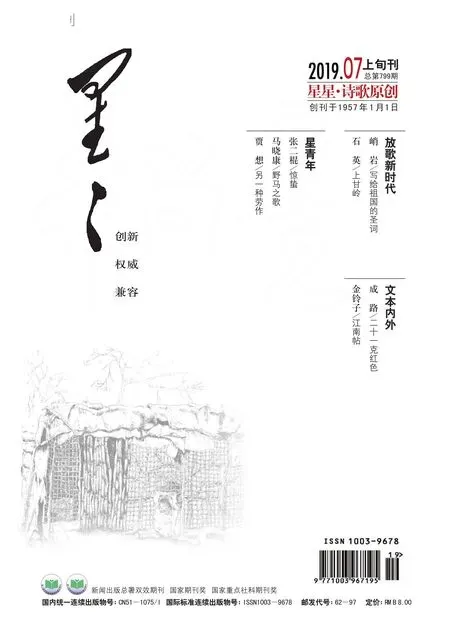仰望与垂首(组诗)
弓 车
神圣的……
仔细看,一位位美少女,从桃花里私奔
为时不久,再度回到花里,紧闭门扉
坐成果子的姿态,多么纯静、淑娴
仔细看,我田里的玉米、大豆讨论着哲学
一层层将绿衣脱下,可我怎么也找不到
仔细看,这只蝴蝶窃取了三分之一的秋色
竟如此轻盈地飞过我菜园的篱笆
让这个世界失重,让我失重
仔细看,正在下飘的雪花,挎着篮子
让我想到,该丢弃多少,方能被一片雪花提起
仔细想,我可以涉河,可以拈花、微笑
可以摘果子、舂米,可以种菜、种菊
如此随意,竟然不会有谁干涉……
想 象
我们想象出了银河,水流和缓
我们想象出了牛郎织女,他们的一副担子里
不再是一对儿女
现已多达60亿人众
我们想象出了月宫和月桂树
想象出了金马车、圣诞老人
光,是他们送来的,幸福来自祈祷
我们想象出了金满囤、粮满仓
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美地飞来
栖落在我们的桃花扇上
我们想象出大地是我们的
于是种上庄稼、植起果树,适时浇水
莳菜时想到爱情的颜色,菊花插满头
我们想象出的这一切多么真实
当我听到鸟儿唤我起床的鸣叫
头顶的星空
“需要挪动各自的位置
需要调整
需要重新组合”,是神说的?
像肖邦一样,用钢琴上的二十四个键盘
让银河改一下道
像我的诗经里,最喜欢的长短句?
在这之前,我已学会了垂头
对这样的事实,我视而不见:
于头顶一寸处,果实累累
为寻找一颗颗星星一般的种子
我需要垂头,哪怕几亿光年
拾荒者
贝多芬走了
我不要他的指挥棒,我要他的暴风雨
凡高走了
我不要他的画笔,我要他的向日葵
秋天走了,我不要他的庄稼
我要他放逐了的蜜蜂蝴蝶和蚱蜢
我的村庄走了,我不要他的泥土
我只要他废墟里的一座孤坟
播种者
他脱下身上的所有衣物
那些人间织的、人间缝的
他披上云
五分之四的是乌云
五分之一放在他的额际
他拒绝了天堂的诱惑,将靴子脱下来
赤脚往自己创造的苦难里走
一下一下踩着画刀
流出的血
与十九世纪人的血不同
与二十一世纪人的血不同,是黄色的
惊悸的黄。跳跃的黄。
他的血溅到画布上就是一幅画
流到土里就是小麦或者玉米
或是鸢尾花、嗡嗡叫着的黄蜂
他的牙齿是黄色的,是颗颗向日葵
云里的闪电做成草帽
对,他是凡高
我是他画的那个播种者
只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向左转
从他的画框里掉出来,摔到了现在
我手里的种子已不是小麦或玉米
是他的耳朵
一只一只,试图种在
板结的、沉默无声的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