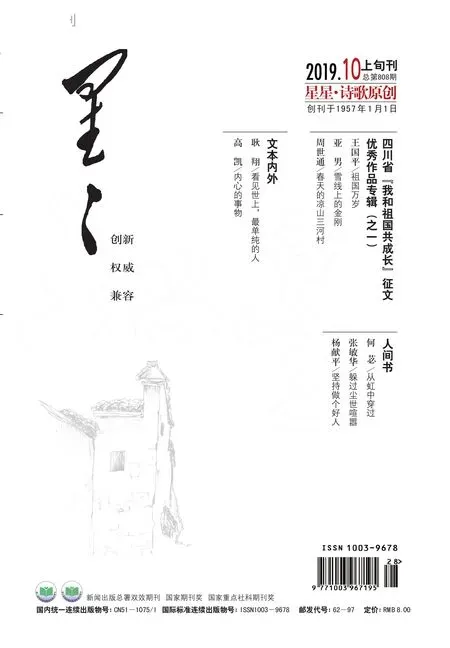反刍着过去的时光(组诗)
2019-12-29 09:56华子
星星·散文诗 2019年28期
华 子
三 月
青蛙与蟾蜍先于我们醒来,
跳出蜗居,水性十足的受精卵
散开一冬的力气。青蛇拨开草丛
虚晃舌尖的刀锋和寡言的预谋。
先于父辈上路的小蛙小蟾,
骤雨似地蹦跶,前仆后继。
它们对周身兴致盎然又了无所知,
更像一群虔诚的朝圣者,但汽车和
我们的脚步并不因此停止践踏和碾压。
它们一出生就得给这世界献上大礼:
有的是一张皮,有的是一点肉浆。
多数好像是幸运的,照样又蹦又跳,
全然不知世界的门槛正随着气温上升。
一只蜻蜓翘立枝头
站着睡着都是飞。
捕食和做梦像空气从两对薄翼滚落,
爱情和包袱被扔进雨点大的尾箱,
做一架自由升降的小飞机。
满脑瓜都是眼睛和反光镜,
生怕有一样东西没找着,没看清。
雷达一般的复眼——这
思考的胃:反刍着过去的时光,
又咀嚼着眼前的一切。
它伏在流动的时间里,始终不为所动。
停留的落点是心尖上的阵地,
宁愿犯错被捉住,也不在树枝的
加油站让油箱空着。即使“蜻蜓点水”,
那也是波及下一代的生育的涟漪。
它转动多少次脑袋和眼睛,就有多少次
意念的反擒拿,就有多少次将我这样的
庞然大物,消化得干干净净。
和一只蟑螂共用一张书桌
一张书桌刚刚配备了两个书生:
我和一只蟑螂。
它优哉游哉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溜达,
显然不是为了觅食。就像我,
吃饱了才踱到书桌前。
我随手一页一页翻书,它可翻不动,
只能用鼻子嗅,用长长的触须
探测。看来,它真要上学读书,
难度,就像从眉山的小石堰,
一跃而上西藏的珠穆朗玛峰。
就算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我是否可以无视它满身的病菌和坏习气呢?
就算我俯下身子贴近它,
它是否可以无视江湖险恶而对命运感恩戴德呢?
它慢慢溜下那本书籍,顺着桌腿
从容离场。蟑螂的背影
貌似一个书生优雅的风度。
猜你喜欢
快乐语文(2021年35期)2022-01-18
少年文艺·开心阅读作文(2021年10期)2021-10-18
少年文艺·我爱写作文(2021年2期)2021-01-11
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20年20期)2020-05-28
中华戏曲(2020年2期)2020-02-12
电影(2019年2期)2019-03-05
东方少年·布老虎画刊(2018年11期)2018-05-14
小猕猴学习画刊(2017年12期)2017-12-26
小溪流(画刊)(2017年9期)2017-10-12
军事文摘·科学少年(2016年9期)2016-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