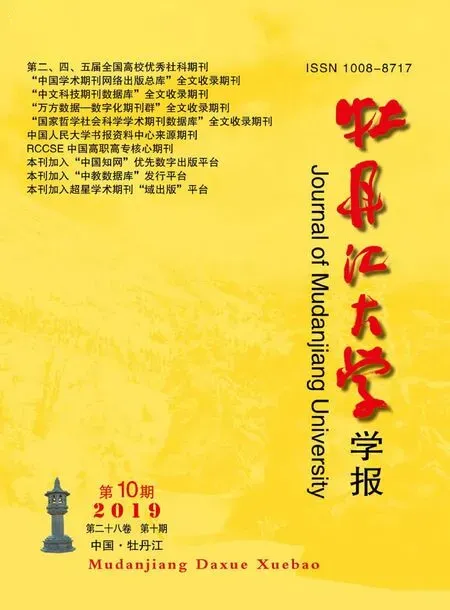聚焦华裔新移民之困境
——以欧大旭短篇小说《帆船》为例
郭 颖
(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一、引言
经过几代海外华裔作家的打拼和积累,不少华裔文学已经逐渐得到了西方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不再是远离中心、无足轻重的边缘。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等经典作品均已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扛鼎之作,深受英语世界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新世纪以来,海外华裔作家依然人才辈出,常有佳作发表,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他近年来所发表的长篇小说《和谐丝庄》(The Harmony Silk Factory)、《五星富豪》(Five Star Billionaire)等均令人感到眼前一亮。其中《和谐丝庄》于2005年入围英国文学最重要奖项之一——曼布克奖的长名单;《五星富豪》于2013年再次入围曼布克奖的长名单。欧大旭的作品不仅深受读者的青睐,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近年来国内海外华裔作家研究的新宠之一。《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与其相关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英国《卫报》、香港凤凰卫视、上海《上海作家》等多家国内外重要媒体都曾对欧大旭进行了采访或者报道,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大旭在国内外声望渐隆、人气高涨。
除了《和谐丝庄》《五星富豪》等优秀长篇小说之外,欧大旭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也颇有建树,短篇小说《帆船》(Sail)2011年发表于美国文学季刊《公共空间》(A Public Space),并入选了《2013欧·亨利奖短篇小说集》(The O.Henry Prize Stories 2013),该短篇小说集每年出版一次,致力于选录当年在北美地区发表的优秀英语短篇小说,只有年度最佳、影响力最大的短篇小说才有资格入选,基本代表了当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此外,欧大旭本人也在2014年成为欧·亨利奖短篇小说三人评奖小组成员,参与了2014年欧·亨利奖短篇小说的遴选,无不显示了其在欧美学界受关注和重视的程度。
二、“乡音难改”——新移民交流之痛
《帆船》主人公彦祖(Yanzu)曾在北京上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开北京移居香港。抵港之后,彦祖为了生计而奔波,历经坎坷后终于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生意遍布全球,旗下拥有数家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如设在江苏的造纸厂,该工厂生产的可回收纸张远销大洋彼岸的美国;设在河北的面粉厂,生产的有机小麦和米粉出口到东南亚;在香港的芝麻湾,他运营的公司使用瑞士最新技术建造了生态家园,在富有的年轻一代中大行其道,他思考着将此类模式扩展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二十年前初来乍到、不名一文的新移民 相比,如今的他在事业上风生水起,财运亨通。小说似乎也刻意强调这一点,开头第一幕就描写了他高调购买奢侈品“帆船”(流线型、如箭般锋利的豪华帆船)的场景:
“这是全香港唯一的一艘”,卖帆船的法国商人说道,“即使是全亚洲也没有其他人拥有这样的帆船,它为你量身定做”。法国商人奉劝彦祖早点购买,“它很快就会被人买走。这里一些有钱人会为他们的儿子而购买。或者我会把它运到上海。他们会在湖里驾驶它,现在那些大陆人很有钱。”(122) 欧大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华裔新移民的经济成功,这与之前众多华裔流散作家所描述的早期移民迥异(在那些作品中,华裔移民往往生活困厄、经济拮据)。
然而,“有钱了”的彦祖并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新香港人”。他的第一只“拦路虎”是语言关,作者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彦祖的语言障碍和英语学习,这也是小说重要的隐形情节线。在短短21页的短篇小说中,与语言障碍和英语学习相关的场景竟达到14次之多,这在一般小说当中,尤其是短篇小说当中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欧大旭对华裔新移民语言能力的重视,他敏锐地捕捉到语言和文化、语言和人物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且匠心独运地在小说中进行了充分的演绎。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视角不仅独特而且非常准确。事实上,国外一些媒体以及社会学研究者均作出过相类似的观察。例如,美国《侨报》就曾报道,根据移民问题专家的研究,过去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长幅度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但其英语熟练程度却低于其它族裔移民的平均水平,语言不通是中国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最大障碍。
小说描写了彦祖遭遇语言障碍的主要场景:场景一是在书店邂逅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紫罗兰(Violet)时,蹩脚的粤语出卖了他的身份,紫罗兰说:“哦,大陆人(Mainlander),我该想到的。我还以为你是ABC 或者其他呢,你的广东话讲得很差。”(128)此外,当捧起英文版书籍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虚伪造作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诈骗犯,因为他根本看不懂里面的句子和词汇。场景二是彦祖和紫罗兰约会了几个月后,去她父母家拜访。当紫罗兰一家用英语侃侃而谈时,他却只能置身局外,尴尬地保持着微笑。场景三则是彦祖生意越来越红火,而他必须依靠口译助手才能和美国商家进行谈判。谈判之际,彦祖端坐那里,除了寒暄客套外,完全无法进入对话当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哑巴CEO”,只能时不时点点头,或在听到笑话时微笑一下。而他的口译员却尽情地用英语谈笑风生,这些都让他备感耻辱。
为了跨越语言障碍,彦祖走马灯似地换了多个家庭教师,包括加拿大的骑警、澳大利亚的会计师、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成为他婚外情女友的丽兹等等。并且他还尝试了不同的英语学习方式,如通过课堂模式、家庭口语训练模式、实地场景模式(参加外籍沙龙聚餐、去星巴克点单)等等,但最终的效果均差强人意。在小说的最后,“他曾认为他能听懂她(丽兹)说话,她说话时元音水晶般清澈,节奏非常稳定,但是现在他觉得她的英语让他痛不欲生。”(140)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语言障碍正是他难以真正融入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华裔英美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伍慧明的《骨》、谭恩美的《接骨师的女儿》、郭晓橹的《恋人版中英恋爱词典》等作品中,均有小说人物因语言不通无法融入移民社会的描写。
三、“情归何处”——新移民情感之殇
婚恋和家庭是人类基本的情感需求和生活需要,对于移民来说尤为如此,只有拥有了感情的归宿、稳定的家庭,才能算是落地生根、发枝散叶,否则永远只是一叶飘零的浮萍,随波逐流。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爱情和婚姻,对于移民而言却常常充满波折和坎坷。尤其是种族、语言等方面与移入国有巨大鸿沟的华裔移民,他们更是有“一家难求”之殇。因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海外华文作品致力于反映华裔尤其是男性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所遭遇的难以愈合之痛。
以美国华裔为例,由于历史原因,早期美国华裔社会是典型的“单身汉社会”,最初踏上美利坚土地的华裔(华工)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当中已婚的抛妻弃子,未婚的只身独往。这是美国移民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薛玉凤指出:“这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畸形婚姻家庭形态的长期存在有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种种原因。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吃碗茶》《女勇士》和《中国人》等,形象地再现了这种‘分裂家庭’生活给夫妻双方带来的身心两方面的巨大痛苦。”[1]1221882年的《排华法案》明确禁止中国男性帮助他们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移民,这一畸形的政策助推了不自然的华裔单身汉社会。曾有学者估计,当时在美国的华人男女比例高达28:1。因此,华裔族内婚恋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而另一方面,华裔与美国其他族裔的通婚又存在着许多劣势和障碍。不少文学作品探讨了华裔男性的这种尴尬和悲情,王宇指出:“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被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存在,被集体边缘化,甚至被‘阉割’,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只能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他者’。”[2]123张敬钰也指出华裔(亚洲)男性的边缘化地位“在非常受主流文化欢迎的亚裔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与电影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边缘化的亚洲男人”。[3]112
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华裔新移民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情感和婚姻方面,他们依然经历着曲折和坎坷,貌似简单的幸福常常遥不可及。小说中,彦祖也一直都在情感的沼泽中苦苦挣扎:尽管与紫罗兰结婚成家,但两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别、家庭的悬殊、性格的迥异等,在婚姻的道路上貌合神离,越发疏远。
之后他和英语家庭教师丽兹发生了一段婚外不伦之恋。远离故土,浪迹香江,乡愁和孤独让他们产生了共鸣,再加上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密切接触,两人之间渐生情愫。彦祖曾期待真正成为丽兹的恋人,融入她的生活,“他希望能够认识她的那些外国朋友;他希望能和她在一起,哪怕冒着被别人看到的危险;他希望能够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136)然而,在一次读书俱乐部的活动当中,彦祖目睹丽兹翩翩然穿梭于朋友们之间、与她们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再次觉得自己完全是局外人。彦祖终于明白自己错了,他和她并没有真正的融合,他只是她的生活调味品而已:“丽兹在香港并不孤独,她只是觉得生活有些枯燥。”(138)在这个意义上,彦祖既没有能真正融入紫罗兰的生活——成为真正的香港人,也没有融入丽兹的生活——成为像她那样融入香港社会的外来移民。激情过后留给他的依然是空虚、寂寞和挫败感,“她曾说,男人恋爱的时候会做最愚蠢的事情;但他不同意,男人失恋的时候才会做最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挫败了。”(123)
小说的结尾,爱好帆船运动的丽兹带着彦祖一起驾驶帆船出海,他们的感情也在这次航行中走到了尽头。帆船是一个隐喻,小说中彦祖不懂得如何去驾驶帆船、如何升帆、如何掌舵,象征着他对自己未来的感情生活感到困惑和迷茫,无力驾驭,也不知道该驶向何方。
四、“乡关何方”——新移民身份之惑
新移民的身份认同(Identity)危机,是流散作家偏好的主题。“移民作为典型的流散群体,他们不断地从旧有的‘想象共同体’中飞散,迁徙到各种陌生的异质性文化环境中,这种变动不居的移民生活不断地催生出他们对认同的新关切、新思考、新建构。”[4]7英美文学中,以身份认同危机为主题的小说不胜枚举,英国移民作家、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都创作过大量相关题材的小说。在文学批评领域,流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身份认同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覃明兴指出:“关于身份的研究是现代语境中文化研究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涌动的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和与其他人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的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乱、离解、甚至是消失,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使身份问题研究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显学。”[5]88相较其他族裔作家,华裔流散作家似乎更热衷于书写身份认同和身份危机。其主要原因是相对其他族裔的移民而言,华裔新移民在宗教、政治、语言、生活习惯方面与移民目标国家的差异更为巨大,更容易产生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遭遇身份认同危机。
《帆船》着力书写了主人公移居他乡之后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尽管移民多年,但彦祖依然困惑于哲学的基本命题——“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对他而言,一方面,家园已然渐行渐远,大陆人的身份被模糊、忘却。曾一心想成为作家的他,坦言已经无法清晰的形容故土和家园,无法描写北京:“他想,这很奇怪,每当我更多地写北京,距离就似乎越遥远。”(126)当初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冥冥中就已有此预感:“也许自己不会再重新回到这个城市,如果命运将他带回北京,他将是一个外国人,不能够理解他周围的人,那些和他一同长大,一同吃饭,一起欢笑,一同睡觉的那些人……”(126)
另一方面,彦祖又与新的环境格格不入,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精神上都难以真正融入香港社会,这使得他对身份认同产生困惑。“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6]7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徘徊在“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迷失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正如丽兹让他用英语所造的两个句子:“离开家乡是很不容易的……,香港也不适合我。”(135)彦祖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小说有多处正面和侧面的描写,主要包括:因为粤语和英语不同而产生的交流障碍,在社交场合所遭遇的窘境,和香港女性紫罗兰貌合神离的婚姻,和丽兹的婚外恋情,内心的孤独寂寞等等。反观小说开头的那一幕——彦祖给自己买帆船,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为了疗伤一段失败的感情,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试图从炫耀性的奢侈消费中寻找成就感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2013年欧·亨利奖短篇小说集》的编辑对《帆船》一文也作如是评价:“欧大旭小说《帆船》写的是一位感到被孤立(isolate)的人物,他与祖国隔绝(estrange),无法意识到自己是谁。”
欧大旭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吉隆坡,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定居,其作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均颇为流行。这种典型的流散经历使得他骨子里就充满了对流散、身份等主题的深刻思考。王宁认为华裔作家自身的身份对作品影响很大:“探讨华裔流散写作首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裔作家的身份问题,这是困扰每一位华裔作家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扰他们。”[7]5朱崇科指出了欧大旭特殊的流散经历,“频繁的空间位移—台北、吉隆坡、英国、新加坡—让欧大旭的身份认同确认不无漂移性,这在《和谐丝庄》中反映得尤为突出。”[8]232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谐丝庄》等一些作品中,欧大旭很多时候还是难以离开马来西亚这个空间维度。“从约瑟夫·康拉德到安东尼·伯吉斯都试图给我们马来西亚生活的感受,但是在欧大旭的第一部小说《和谐丝庄》中,我们有了新的马来西亚:他从小在那里长大。”[9]22但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他开始尝试跳出大马这个空间维度,如《五星豪门》就是讲述马来西亚华裔移民上海的故事,“在小说中,五位马来西亚华裔顺应时代号召,来上海谋求发展。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份差异悬殊。”[10]28在《帆船》中,欧大旭思路更为广阔,叙事更为大胆,他不仅跳出大马的这个地缘,而且讲述了与马来西亚完全没有任何联系、与他的真实经历也没有太多交集的大陆和香港的故事,这种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不断异位和错置使得人物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显得更有意义。
五、结语
《帆船》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彦祖离开北京,只身来到香港谋求发展。作为新一代移民,他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开办了许多企业,业务甚至拓展到了包括美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在内的许多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作者映射出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对世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然而,欧大旭很敏锐并且深刻地指出,经济成功并没有使主人公能够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并从语言、情感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进行了书写和映证。
语言障碍常常是新移民难以融入移民目标地的重要因素,对于华裔新移民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帆船》聚焦了多处主人公因语言障碍而无法进行交流的场景,尽管彦祖作出了各种努力,试图跨越语言障碍,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欧大旭本人谙熟英文和中文,其英文创作的小说多次获得国际大奖,英语水平受到西方读者和学界的认可和赞赏,这种经历使他对新移民的语言问题情有独钟。与此同时,在情感上彦祖也难以找到真正的寄托,从结婚到婚外恋再到失恋,显示了新移民在情感上的苦闷,内心的孤独,小说名——“帆船”就是他情感迷航的隐喻。此外,由于作者自身特殊的流散经历,他对空间的错置、异位特别感兴趣,在叙述发生在这些变化空间中的故事时,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常常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读罢《帆船》,读者一定会掩卷而思,在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新移民为何还深陷在“文明的冲突”和“身份的迷失”的泥淖之中?对于新移民,“当他们的移民活动得以实现之后,究竟会如何去寻找适合于自身生存的文化身份,去建立自己与那个新世界的文化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地去探讨的问题。”[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