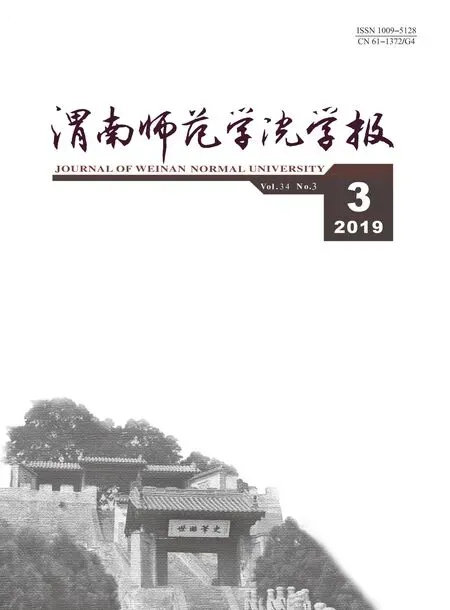论《雨花香》《通天乐》的善书属性
——兼论清代劝善小说的创作
郑 珊 珊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合肥 230022)
所谓“劝善小说”指的是针对下层民众创作,以道德劝诫为目的,并以浅显的语言叙述果报故事的一种文体,最迟宋元之际已经出现。宋元之际陈录《善诱文》、李昌龄《乐善录》、题“淮海秦氏集”《劝善录》、李元纲《厚德录》等都属于这一类。我国古代劝善小说的创作是在南宋以来民间劝善文化或曰善书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从创作动机和体制内容来看,这一文体应属于善书的范畴。
明代胡应麟将小说家一类分为六种,其中有“箴规”类。[1]282-283宋元之际出现的劝善小说也可以说是“箴规”类小说中的一种,然不同于宋代以前“箴规”小说之处在于“劝善惩恶的善书气息很强”[2],据此,有研究者指出宋元之际劝善小说当属于善书的一类。[2]清代劝善小说则沿着善书化的途径进一步发展,用通俗语言甚至方言叙述果报故事以诠释善书观念,或作为善书的案证。《雨花香》《通天乐》以及清中后期出现的“宣讲小说”即是劝善小说的代表。
当代治古代小说的学者将清初石成金所创作的《雨花香》《通天乐》两部作品集归入拟话本小说的范畴进行讨论,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在拟话本小说批评理论的框架之下,这两部作品集遭遇的几乎都是消极的评价。然而,这两部作品集无论是在创作意图,还是体制内容上都与拟话本小说存在很大的区别,相较之下,同善书的关联却更为紧密。
一、《雨花香》《通天乐》的劝善意图
《雨花香》《通天乐》是清初石成金的两部作品集。作者在《雨花香自叙》中自陈写作动机,云其因“欣羡”云光禅师于江宁城南说法,劝化众庶,由是感召上天雨花的事迹:
乃将吾扬近时之实事,漫以通俗俚言,记录若干,悉眼前报应须如,警醒明通要法,印传寰宇。……种种事说,虽不敢上比云师之教济雨花,然而醒人之迷悟,复人之天良,与云师之讲义微同,因妄以《雨花香》名兹集。[3]1-2
石成金宣称自己创作《雨花香》是受到云光禅师说法的启发,用“通俗俚言”记录“吾扬近时之实事”,以“醒人之迷雾,复人之天良”,清楚地表明其作品旨在劝善。这种以时事、实事进行劝善的意图在袁载锡所写的《雨花香序》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袁氏对《雨花香》的创作作如下评述:
兹观《雨花香》一编,并不谈往昔旧典,是将扬州近事,取其切实而明验者,汇集四十种。意在开导常俗,所以不为雅驯之语,而为浅俚之言。令读之者,无论贤愚,一闻即解,明见眼前之报应,如影随形,乃知祸福自召之义,一予一取,如赠答焉。神为之悚惧,心为之憬悟,志行顿然自新。[3]3-5
石成金在《雨花香》的“自叙”和袁载锡“序”所强调的“福祸自召”的果报观念尽管非劝善小说所独有,但却是善书的一大要义。石氏在《通天乐》的“自序”中又重申了这一观念,只是换了一套说辞,其云:“予不揣愚昧,乃将明达语事,漫用俚言纪述数种:某某因在天理,即受许多快乐之福;某某因天理为私欲所蔽,即罹许多忧愁困苦之殃。各赘浅说,著书曰:‘通天乐。’谓人能通达乎性天之乐,则随时随境皆享极乐于无涯矣。”[4]1尽管类似于这种指称作品意在劝善的表述在小说作者、作序者和刊刻者的自陈中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种言说的格套,令人难免心生疑窦,而且也的确有部分作品只是将这套言说方式当作幌子,内容与其自述创作意图之间存在极大的分裂。然而,这种情况在《雨花香》和《通天乐》中显然是不存在的。
石成金《雨花香》和《通天乐》中的作品显然是围绕明确的劝善意旨精心结撰而成,这从作品目次安排中能够看出。五十二篇作品的题目基本上前后两两相对,形式整齐。如第三种《双鸾配》和第四种《四命冤》,第五种《倒肥鼋》和第六种《洲老虎》,第七种《自害自》与第八种《人抬人》等等。不仅前后题目对仗,内容亦相关联。如第十一种《牛丞相》和第十二种《狗状元》都是宣说因果;第二十一种《刻薄穷》和第二十二种《宽厚富》劝济施;第二十五种《掷金杯》和第二十六种《还玉佩》都关涉公门劝善;第三十三《晦气船》与第三十四《魂灵带》戒财色;《通天乐》第九种《上为下》与第十种《尊变卑》劝诫善待婢仆等,此处不必一一列举。这种安排作者乃有意为之,如在《雨花香》第三十四种《魂灵带》中开篇作者即明白地说:“前一事,因色致死人。此一事,因财又致死人。虽是致死他人,即自致自死。因财色丧命者,岂止此二人而已。”[3]365-368显然,这种前后相对照的形式乃是出于作者的刻意安排,而通过这一安排来表明作者旨在劝善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雨花香》《通天乐》与拟话本小说的差异
《雨花香》《通天乐》与典型的拟话本小说在文体形式上大异其趣。不少研究者对此早已做出了评价。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评论《雨花香》云:“这部话本集的特点是专记明末清初扬州地区的新闻故事,富有地方色彩。但说教气味很浓,思想感情和语言风格都很庸俗卑下,以视冯凌诸家,诚不可同日而语了。”[5]623欧阳代发在《话本小说史》中指出石成金的创作“强调根据个人耳闻目睹亲历之事来写作,这在话本小说史上是仅见的”,认为石成金是“六朝志怪之法写拟话本”“标志着话本小说的大衰落”[6]469。胡士莹和欧阳代发指出了这两部作品集与拟话本小说的不同之处,但还是将之纳入“话本小说”或“拟话本小说”的范畴,依据后者的创作模式对之做出了消极的评价。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石昌渝认为这两部作品“在体制上已非话本小说,实际上是用白话写的笔记小说”[7]288。刘勇强也认为《雨花香》《通天乐》“满足于题旨故事的陈述,几乎失去了对文体的关注,类似于白话笔记”[8]。所谓“白话写的笔记小说”“白话笔记”的提法体现了研究者对《雨花香》《通天乐》与拟话本小说在文体上所呈现出的差异的正视。
首先,《雨花香》和《通天乐》在叙事中往往强调事件的真实性或亲历性。这是异于拟话本小说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52篇作品表现的多是“吾扬近时之实事”,所描摹的人物也多来自于扬州的市井细民。石成金为强调事件之真实性,往往以第一人称“我”“予”来进行叙述,“我”不仅是事件的亲见者、旁听者,甚至还是参与者。如《雨花香》第七种《自害自》中的故事乃是“我”的一位“从不虚言”的老友告知的[3]116;第八种《人抬人》的故事是“我”亲历的;第十四种《飞蝴蝶》中的事件是“予”“随众往看”于人群围聚中目睹的[3]122;第二十种《少知非》讲述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奢华败家复又重整家业的事[3]240;《通天乐》第十一种《投胎哭》中所述之奇幻投胎事竟也是“我”所亲历的。[4]109如此刻意强调“我”之亲历,乃至戴不凡称石成金“纯以个人耳闻目击身历之事为短篇小说者,彼似为小说史上第一人”,此类叙事很多,不必赘述。[9]188在晚明以来的拟话本小说的创作中,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关系的作者不乏其人。如明无碍居士认为野史小说的创作“事赝而理亦真”[10]776-777。凌濛初的《拍案惊奇》的创作也自觉地依照“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10]785“亦真亦诞”的原则。[10]789尽管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大多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承“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11]1182的创作观念,强调创作“大多真切可据”[10]788,“皆出于目见耳闻,凿凿可据”[12]5,“考必典核”[10]827,然而如石成金《雨花香》和《通天乐》这般,将“凿凿可据”的创作观念发展到极致,在小说史上尚属少见,以至于孙楷第认为其创作“与生心作意为小说者殊异其趣”[13]152。其实,这种“殊异其趣”不难理解,之所以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推崇“凿凿可据”的创作观念,是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些事迹皆“吾扬近时之实事”,这是由作者的劝诫意图所决定的。讲述的事件越趋于真实,越具有近地域性,就越能吸引读者或听众,就越有说服力。
第二,《雨花香》《通天乐》语言通俗,极少使用说书套路式的韵文。这是这两部作品集不同于一般拟话本小说的又一特点。《雨花香》《通天乐》中每一篇作品的题目都使用三个字,大多语言直白,意旨明确,读者一看即知。如《刻薄穷》戒刻薄,《宽厚富》劝宽厚,《旌烈妻》劝节烈,《剐淫妇》戒淫奔,《下为上》戒虐待婢仆,《尊变卑》戒骄傲等。篇首的劝诫主旨和正文故事也都追求语言的通俗浅直,孙楷第因此指出这两部作品集具有“记事用俚语”的特点。[13]152这52篇作品不仅没有篇首诗词和篇尾诗词,叙事过程中也极少出现韵文。以明末“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中往往有大量雅化的韵文,包括诗、词、骈文、偶句等形式,用以“静止地描绘品评环境、服饰、容貌等细节”[5]142等,尽管清初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已经明显地减少了韵文的插入,但很少如石成金这般彻底。这两部作品集中仅有《双鸾配》《掷金杯》《宽厚富》《亦佛歌》4篇作品出现了带有说书套路韵文。另有若干篇出现了韵文,然形制、作用与拟话本小说中雅化、格套化的韵文殊异。如,第六种《洲老虎》劝诫乡人的俚言口号[3]114;第十八种《真菩萨》中的戒溺女歌[3]215-217;《雨花香》第二十种《少知非》劝朋友郑君戒奢的鼓儿词[3]240-257;第二十八种《亦佛歌》中宣扬佛法的《中峰大师歌诀》[3]332-333;《通天乐》第二种《莫焦愁》中劝化愁苦不悟之人的“我”所自撰的《新七笔勾》[4]22。这些插入的文字尽管都具有韵文的性质,但却与叙事联结紧密,是为了强调某一特定的劝善主题,并且有的具有民间曲艺的色彩。这些文字可视为劝善诗或劝善歌。
第三,《雨花香》和《通天乐》与拟话本小说“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诗词”[5]133的标准文体格式有很大不同。这是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这两部作品集中的作品几乎都采用了同一种模式:劝诫主旨+正文故事。部分作品的故事叙述完毕后,还会附上一篇教化色彩浓重的文章或诗歌。劝诫主旨的内容基本上是议论性的文字,用于交代该篇作品的写作意图,突出劝诫主题,相当于一种读法提示。这一部分与拟话本小说入话的作用相类,然而却与后者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这类提示性的文字有的篇幅短小,意旨明确。《通天乐》第四种《麻小江》只一句话便直接进入正文故事。[4]49-54有的篇幅竟与正文内容相埒。不仅议论,甚至还会简单叙事。如《通天乐》第九种《下为上》在劝诫主旨中提示本文的创作意图在于劝诫善待婢仆,在一大段议论后,又叙述了户部尚书马森之父善待奴婢因之获得善报事。[4]93-97这两部作品集中的作品正文故事内容大多叙事简略,部分故事仅具梗概,几乎谈不上叙事艺术。稍具规模、叙事委婉者仅《雨花香》第三种《双鸾配》、第四种《四命冤》、第十种《锦堂春》等数篇而已。正文故事后附录劝诫性文字的模式在《雨花香》40篇中仅有数篇,然《通天乐》却12篇每篇皆有附录。18篇附录中只有《雨花香》第三十八种《剐淫妇》后附《戒食牛肉说》,显得有些突兀,除此而外,其他各篇与附录文字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且大部分篇章关联紧密。
也有研究者对《雨花香》《通天乐》文本和内容上异于拟话本小说之处做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两部作品集“没能最终完成话本小说转型的任务,但他们却为新型白话小说作了准备”[14]。这其实将《雨花香》《通天乐》与拟话本小说“殊异其趣”之处作为小说发展中出现的新变,认为是这些“新变”以及作品强烈的教化色彩致其在小说史上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这些“新变”预示了新型白话小说的到来。这一诠释方式有其合理之处,但似乎对这两部作品集的“拟话本小说”身份过于执着,没有意识到将之归入“话本小说”的范畴内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这些所谓的“新变”也恰是其善书属性的一种体现。
三、《雨花香》《通天乐》的善书色彩
《雨花香》和《通天乐》中反复申明的劝善意图,以及作品形式和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极为浓重的教化色彩,使这两部作品集更具善书的特征。
首先,《雨花香》和《通天乐》52篇作品的劝诫主题与同一时期的善书之间存在重合。这52篇作品的劝诫要旨根据其所针对的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公门类和庶民类。公门类即针对公门官员、属吏的道德劝诫。庶民类也即是针对一般民众的道德劝诫。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仅以公门类劝善为例来讨论这两部作品集与善书的关系。
《雨花香》40篇作品中涉及对官员进行或“劝”或“戒”的作品有10篇,其篇目为第四种《四命冤》、第八种《人抬人》、第九种《官业债》、第二十三种《斩刑厅》、第二十五种《掷金杯》、第二十六《还玉佩》、第二十九种《枉贪赃》、第三十二种《一文碑》、第三十五种《得会银》、第三十六种《失春酒》。这些作品充满了石氏对公门官吏道德的殷切期待,与其说他在讲述官场故事,不如说他是在精心选择案例以阐释自己对于官吏的劝诫观念。《雨花香》第四种《四命冤》中讲述了一个清官因偏执而造成一桩冤案事。作者的劝诫意图在正文故事之前已有明确的表述:“可知为官聪明、偏执,甚是害事。”[3]63-90正文选择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孔县官因偏执己见、枉害人命受到报应的故事。第九种《官业债》的劝诫主旨在于“总因前世做官,粗率错打,所以今世业债,必然还报”[3]129-136。正文讲述姚广孝前生曾令人无辜受杖,现世遭遇此人杖责的因缘。作品篇幅短小,叙事简略,几乎没有情节可言。石成金关于“刑求”的公门劝诫观念还体现在其《官长约》《公门修行》等劝善文中,《官业债》等故事可以看作是其“刑求”观念从善书到小说的延伸。
石成金《雨花香》和《通天乐》中关于公门劝善的写作并非随意生发,这从他针对公门官员、属吏编撰的善书《功券》中能够体现出来。《功券》中收入了熊勉庵的《不费钱功德例》和石氏自撰的《官长约》和《乡绅约》。石成金《功券自序》中云:“熊勉庵先生著有《功德》一书,备指不费钱者甚多。予添续若干,并载官长、乡绅二约,著为功券一卷。”[15]15可知,《功券》的编撰直接受到《不费钱功德例》的影响。熊勉庵的《功德》是明清时代善书的代表作,陈宏谋的《训俗遗规》和酒井忠夫所见日本内阁本的《晨钟录》《同善录》等大型综合性善书都有收录。在《不费钱功德例》众多的劝善项目中,“官长”“乡绅”“公门”尤其受到善书编撰者的关注。晚明颜茂猷《迪吉录》[16]489、清初李日景《醉笔堂三十六善》[17]280-283等经典善书都对公门劝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清时期,包括官员、属吏、乡绅的地方精英阶层在民间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地方社会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如石成金在《官长约》中的评价:
论行善,是人人分内事,原无哪个该行善,哪个不该行善的说话,也没有哪个善是人所能行的,哪个善是人所不能行的说话。只是有一等善事,凡人力量万万做不来的,唯有做官的,轻轻就做来了。且是凡人行善,一善且成一善。只有做官的人,做一件善事,便胜如凡人百件善事、千件善事,更有一件胜人万万件的善事。以此,做官的人更当急急行善,更与凡人不同。[15]23
《功券》收录在石成金编撰的《传家宝全集》中。《传家宝全集》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在清代颇受重视,被张祎琛[18]、游子安[19]5等善书研究者列入清代善书的范畴内。
第二,《雨花香》和《通天乐》中存在大量的劝善文。教化色彩浓重是这两部作品集最为研究者诟病之处,部分作品后附的劝善文和劝善诗即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如,《雨花香》第四种《四命冤》戒为官偏执,因而文后附录了一篇《为官切戒》;第十五种《村中俏》戒调戏妇女、戒娶风流妇女,文后附录了《风流悟》;第十八种《真菩萨》劝济施,讲蔡善人收养弃婴,故事的叙述中因此插入一篇“戒溺女文”等,如此之类,大约有20多篇作品。这些文末附录的劝善文和劝善歌,无论是从形制还是内容方面来看,都与一般民间善书收录的劝善文和劝善歌没有差别。另有一些作品的叙事中也插入了作者自制或民间流传的劝善文或劝善歌。前文已述,此处不赘。《传家宝全集》的《常歌》中收录了一百多首劝善歌,几乎囊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各种的道德情境,其中《醒色欲》《醒吝施》《劝公门人》《戒溺女》《戒食牛》《戒赌博》《戒奢费》[15]166-211等诗歌的劝诫主题与《雨花香》和《通天乐》中所插入或附录的诗文劝诫态度完全一致。若将《雨花香》《通天乐》和《传家宝全集》中相关作品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甚至可以说,两部作品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是石成金善书观念的诠释和案证。此外,《雨花香》和《通天乐》显然接受了晚明以来经典善书的影响,袁黄、颜茂猷等人的善书观念,甚至善书中的措辞都被直接引用。
第三,石成金《雨花香》和《通天乐》中的作品在当时和后世被作为善书来对待。这两部作品集中的部分作品同时也被收录在石成金善书《传家宝》中。今人对《传家宝》和二书之间的关系做过考证。如学者戴健通过考证不同版本的《传家宝》和《雨花香》《通天乐》之间的关系,认为:“二书皆为《传家宝》 的组成部分, 与单行本的不同只在篇目、卷次的出入上。”[20]另外,在民国时期这两部作品集也被视为善书。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中介绍了一部作为善书流通的小说集《醒世小说》:
《醒世小说》一册……上海明德书局出版,无版权页,而代以“明德书局出版书籍”计七种之介绍广告。据广告前说明以及封二“上海爱华制药会社赠送善书办法”,知书局实附设于“上海南市里马路太平里”该制药会社;殆为药厂所附设之一宣传机构耳。据封二所载,凡购该社药品一元以上,均赠价值一角之书券一张,换书局出版之善书一册,书目记《醒世小说》等六种。……而书则印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
该小说集“首页署‘扬州石成金天基撰集’”[9]185。根据戴不凡的著录,《醒世小说》收14篇小说,其目录是:《今觉楼》《铁菱角》《双鸾配》《村中俏》《乩仙偈》《再生福》《枉贪赃》《空为恶》《官孽债》《篆外缘》《假都天》《真菩萨》《长欢悦》《莫焦愁》。[9]186其中,除《再生福》不知所出外,其余篇目皆出自《雨花香》和《通天乐》两部作品集。胡士莹也指出:“(石成金)别有《醒世小说》石印本一册,选石著小说十四篇。内《再生福》一篇,为刻本所无,疑系某篇的改名。”[5]564据此,民国时期作为善书流通《醒世小说》可能是从《雨花香》《通天乐》中选出部分作品汇集成册另行刊印的一个别本。由此可知,这两部作品集是被当时和后世的一些出版商或出版机构作为善书来刊印和传播的。
四、清代其他劝善小说创作
除《雨花香》《通天乐》而外,以《跻春台》为代表的宣讲小说也应该纳入劝善小说的范畴。宣讲小说指的是在清代劝善文化背景下伴随着宣讲圣谕和善书的活动而产生的辅助宣讲的案证,又或文人模仿这一文体的拟作。宣讲活动在有清一代始终盛行不衰,正如周振鹤论述清末的宣讲活动时指出:“大到一省有宣讲总局,而小到一县有宣讲所,善书与宣讲活动的无孔不入由此可见一斑了。”[21]625-626那么,何谓“宣讲”呢?据陈廷英 《劝善书目提要》指出:“凡叙事处用白话,谓之讲;长短句用歌体,谓之宣。”[22]6根据游子安的研究,这类宣讲本多援引善书或辑录因果报应事例,以提供宣讲人讲解圣谕训条时使用,与仅供案头阅读的“案头本”善书正相对照。“案证”则是指这些讲因果报应的故事集。[23]
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将《跻春台》作为清代的“最后一种拟话本集”[5]827,这一观点至今被小说研究者反复引用。然而,《跻春台》与拟话本小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从作者写作意图来看,“借报应为劝惩”[24]4是该书的唯一创作目的。林有仁序言中云:“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劝善惩恶一书,名曰《跻春台》。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集成四册。……省三问序于予。予曰:‘此劝善惩恶之俗言,即吕书五种教人之法也,读者勿以浅近薄之。诚由是积善,必有余庆,而余殃可免;作善必召百祥,而降殃可消。将与同人共跻于春台,熙熙然受天之佑,是省三著书之意也夫!”[24]4-6正如林序中所揭示的,《跻春台》的写作意图是“劝善惩恶”,这与石成金写作《雨花香》《通天乐》的目的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案”的性质,以及与“宣讲”的关系。如林有仁所云“列案四十”,作者亦自云“特借报应为劝诫,引案以证之”,“俾善宣讲者,传神警觉人也,闻清夜钟声也”[24]4。“案”“引案以证”“宣讲”这些字眼是研究《跻春台》文本属性的关键。不少篇目中的确出现了“宣讲”“宣讲圣谕”“宣讲生”等字眼,以及宣讲的场面。有研究者指出,书中40篇故事有7篇可以认定为出现了宣讲场面。[23]此外,大多数作品的结尾议论文字中还有“观此案”的表述模式。因而,可以认为作者是有意识地以案证的手法来进行文本创作的。
从文体上来看,《跻春台》与拟话本小说有较大差别。首先,这一差别用林有仁的评价可表述为“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24]5。所谓“俗言”,在这部作品中应理解为四川方言,不少研究者已对此进行了论述,此处不赘。以当地“俗言”宣讲劝化正是宣讲作品的特征。这并不仅仅是地方持教化权柄之精英的发明,清帝也对方言宣讲的方式一再致意。乾隆十一年议准:“转饬各乡约正、直月朔望宣讲圣谕之后,即以方言谚语,为愚民讲说。”乾隆二十三年覆准:“宣讲圣谕务须实力奉行……或不妨以土音谚语,敬谨诠解,明白宣示。”[25]335所谓“兼有韵语可歌”更体现了《跻春台》文体上与拟话本小说的差别。如上文所述,拟话本中的韵语采用中国古典的诗、词、骈文、偶句等形式;而《跻春台》的韵文则使用民间曲艺的形制,包括十言、七言,以及杂言体制。“长短句用歌体,谓之宣”,此韵文正是“宣”的部分。游子安在研究圣谕宣讲向说善书的衍变中指出,因艺人常用“未开言来,泪流满面”开场,故民间戏称讲善书为“未开言”。[23]49-59“未开言”的表达方式也不时地出现在《跻春台》的韵文中。其次,《跻春台》的韵文主要是人物的独云或对话,对推进故事情节具有关键的作用,不同于拟话本小说中格套化的韵文模式。
对于《跻春台》与拟话本性质之间的差异,张一舟在《〈跻春台〉与四川中江话》一文已经指出,并认为这部作品集是“供‘讲圣谕’的宣讲生宣讲时用的底本”,是一种“善书集”。[26]这可能是较早对《跻春台》的拟话本小说属性进行质疑,并提出将之纳入善书范畴的一个观点。日本学者阿部泰记也提出《跻春台》不是一般的“拟话本”,是宣讲圣谕时使用的案证集,是具有话本体的宣讲本。[27]游子安在对清代善书进行研究时,更是明确指出《跻春台》“是供宣讲圣谕时用来劝善惩恶的案证”[23],汪燕岗则首次使用了“宣讲小说”的概念,他认为《跻春台》等川刻小说不能纳入拟话本小说的范畴,而应名之为“宣讲小说”。
汪燕岗将“宣讲小说”定义为:“圣谕宣讲和说善书的底本及记录本,或是文人按照宣讲体制拟作而成。”[28]其实,在汪燕岗之前,耿淑艳已经提出了“圣谕宣讲小说”这一特定的概念,用以指称这类“以人物形象为媒介来阐释圣谕的主旨”“把政治观念转换成艺术形象”的小说类型。[29]汪燕岗认为用“圣谕宣讲小说”来概括这一小说类型不全面。理由是“清代各地在宣讲圣谕时也常常混合着说善书”[28],两位学者命名方式的不同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地域性差异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处无法详论。然汪燕岗指出圣谕宣讲时混合着说善书,这一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宣讲小说”这一命名方式似更为合理。
汪燕岗还指出,圣谕与劝善小故事合流的书所见最早的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圣谕灵征》。[30]其实,圣谕和善书的融合至迟在明嘉靖十五年唐琦注《圣训演》时就出现了。[31]572入清后,随着圣谕宣讲活动制度化,圣谕宣讲和善书更进一步融合。王尔敏曾论述清代这一文化现象云:“宣讲圣谕通行民间,在内容上就知书之士,多予附加民间流行善书,尤其故事性之短篇说唱,成为《圣谕》之外之附加品,并在民间兴盛流传。”[32]游子安在研究宣讲圣谕到说善书的衍变时,以《感应篇直讲》一书为例,讨论清中叶以后善书与宣讲圣谕活动的结合。并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宣讲题材更趋向于通俗化,宣讲者为引起共鸣,往往掺入地方上的近时果报事件。[23]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宣讲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根据汪燕岗、耿淑艳的相关研究,宣讲小说可分为白话宣讲小说和文言宣讲小说。白话宣讲小说或直接以“宣讲某某”命名者,如《宣讲集要》《宣讲管窥》《宣讲拾遗》《宣讲金针》《宣讲福报》《圣谕灵征》等,直接昭示了文本与宣讲活动的关系;或不直接以“宣讲某某”命名,如《跻春台》《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辅化篇》《大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济险舟》《孝逆报》《保命金丹》《阴阳普度》《挽心救世录》《万善归一》《阴阳宝律》《解倒悬》《觉无觉》《惩劝录》[30]《俗话倾谈》[29];目前已知文言宣讲小说有《宣讲博闻录》《圣谕六条宣讲集萃》《宣讲余言》《吉祥花》《谏果回甘》[29]。这类宣讲小说尽管有以“宣讲”命名者,但不能用来直接宣讲,如同宋元之际的劝善小说,只供案头阅读,或作白话宣讲小说取材之用。白话宣讲小说主要出现在四川、湖北[28];而以上文言宣讲小说则皆成书于岭南。[29]
据王家瑞的研究,善书的案传繁多,至1980年发现案传约328案,实为“一笔很可观的文化艺术遗产”[33]16-17。大量民间善书案传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一叙事类型提供了一个方向,也为小说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雨花香》《通天乐》以及《跻春台》等作品的劝善意图非常显豁,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这类作品无论是体制还是内容都显然与拟话本小说迥异,而与清代的善书和善书文化呈现出密切的关联。尽管宋元时期与清代的劝善小说在文体上存在着一些差异,然其共同点是这些创作却都是在善书文化兴起或繁荣的背景下展开的,与同时期的善书文本关系密切,这种关联在《雨花香》《通天乐》以及《跻春台》等清代劝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显明。因而,这些作品纳入善书的范畴进行观照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由此展开的评价可能才更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