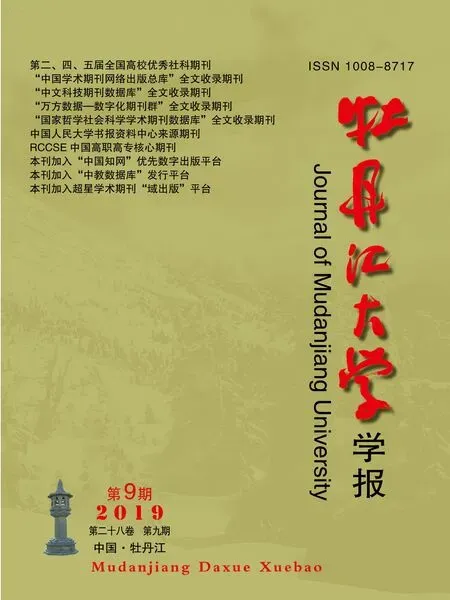现代化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出版
——评《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
王 金 龙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使古代中国在世界出版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截止15世纪末时,在中国印刷、抄写的书籍已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1]13官刻、坊刻、私刻等三大出版体系以及皇室、私人、寺院、书院等四大藏书系统的形成,使得古代中国的出版物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就其质量来看,皆难有国家能望其项背。然自西方工业革命始,中国传统出版业在与现代工业文明支撑下的西方现代出版业的对比中,在出版技术、发行体系、营销手段等各个方面皆已明显处于落后状态。故而出版行业的现代化,自然就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必经之途。著名出版史学者邓咏秋博士新近出版的《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1800—194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一书,采用现代化的研究视角对1800年以来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表征及其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周延的叙事结构以及所承载的理论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皆足称道。
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广义上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狭义上的现代化,则专指落后国家通过学习世界先进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技术革新,以带动本国社会变革进而追赶先进工业国并适应现代世界发展环境的过程。[2]16-17一般而言,中外学界所进行的现代化研究往往包含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自然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也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以现代化的研究视角考察整个19世纪以来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不仅具有研究上的理论依据,而且多能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做到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
首先,该著作以现代化的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出版史研究中存在的古代-近代-现代这一传统研究分期的桎梏。“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的。”[3]99故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革命史研究范式几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唯一解释模式。此种范式下的中国出版史研究,“通常将19世纪以来的历史分为几个时期,如古代、近代与现代,这种分期研究往往忽视了不同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尤其对近代和现代的分期标准及分期意义众说纷纭。”[4]2而采用现代化的研究视角考察19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则不仅能避免研究时段划分上存在的分歧与争议,更能展现以往革命史研究范式下一些隐而不彰的面相。正如作者所说,“将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注意到它与前现代和现在的联系,而不是把它放在若干阶段进行孤立的研究,这样更有利于把握出版业的发展脉络,研究过去被忽略的若干重要问题。”[4]32例如,将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新式出版活动的在华出现——而不是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肇始,“有助于把握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全局,有助于我们研究新的变化是怎样在中国出版业中一步步产生、发展、被接受和被阻挡的。”[4]34
其次,该著作广博的现代化研究立意,突破了学界以往多将出版业现代化等同于出版技术现代化、革命化的狭隘理解,从而将近代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标准(表征)大为丰富。在众多现代化的概念中,技术变革因素往往占据首要地位。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将现代化直接概括为“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5]3-4受此概念因素的影响,国内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往往将出版技术的革新等同于出版的现代化。其实,出版的现代化,“不是某一环节具备了现代因素,而是指整个出版行业的现代化。”[6]正是在对这一观点的认可上,《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指出,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标准除出版技术的现代化外,还应包括出版主体的现代化、图书流通体系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出版同业组织的现代化、现代出版法律与版权观念的形成、稿酬制度的建立以及现代编辑家、出版家的形成等众多标准范畴。如此丰富、具体的出版业现代化标准,就将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有效地展现出来。
二
在结构设置与叙事理路上,《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堪称周延、完备。在总体布局上,该著按照“现代化的背景”“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的影响”这一基本架构,完整梳理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在考察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诸标准之前,该著首先对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背景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包括因国门被迫开放而产生的对现代知识与出版技术的急迫需求、因现代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的提升、以条约口岸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城市对出版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学校教育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从而导致的识字人口增加、现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对图书出版的刺激等等。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可以说是19世纪以降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
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现代化各标准的细致梳理构成《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的主体内容。值得称道的是,在对出版技术现代化、图书流通体系现代化、出版主体现代化、同业组织现代化、企业制度现代化、现代出版法律形成等近代中国出版业现代化各标准的叙事与梳理中,该著仍能大致保持叙事结构的前后周延与完整,从而使各章的脉络清晰可寻。例如,在对图书流通体系现代化进行考察的第四章,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直接指陈近代中国图书流通体系现代化的具体表征,而是先用两节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图书流通体系(包括销售方式)以及近代中国现代交通、邮政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对古代图书流通体系进行前期介绍,不仅能将其与之后的现代图书流通体系作一鲜明对比,而且还能使读者更为深刻地洞悉到图书流通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背景与过程。而现代交通与邮政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则是近代中国图书流通体系现代化的直接动力。“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洋纸和现代印刷工具从国外输入中国,从沿海运输到内地出版中心,现代交通还把出版中心与各级市场更好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促使商品输出和输入增加。现代邮政的发展促使邮购这种发行方式普及开来,使读者可以方便地订阅书报,书籍得以传递到邮政网络所覆盖的广大区域,包括没有开设书店的乡村。”[4]106在中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分馆(局),成为近代各大出版机构开拓国内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寄销代销、特约经销、预订、发布图书广告、编写图书目录、成立读书俱乐部等,就成为现代图书发行、营销的主要形式与手段。图书流通体系的现代化对近代中国图书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故而对这一影响的考察就显得颇有必要。所以在本章第四节,作者以统一图书定价制度的形成、总体书价的不断下降、图书发行总量的急剧增加为重点,详细论证了图书流通体系现代化的影响,从而使得该章的叙事结构得以周延、完备。
在对近代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背景以及现代化各标准进行爬梳之后,该著最后一章以图书为例,详细论证了中国出版业现代化对近代出版物产生的重要影响,包括译书出版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图书类目的丰富与总量的大幅上涨、新式图书分类方法的逐步确立等。将其作为图书出版业现代化的主要结果置于最后予以考察,在结构上可谓有始有终,更显完整。
三
从理论价值上来讲,出版业的现代化是中国出版史学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将现代化理论用于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过程中如何把握那些具有现代特征的出版业标志性因素。《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明确提出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众多标准范畴,并且将这些范畴共同置于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中予以综合考察,这对学界后续的出版业现代化标准研究、树立衡量中国近代出版业现代化的评价体系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具有丰富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现今的中国出版业仍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故而该著对近代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梳理自会对当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起到较强的借鉴作用。中国出版业的现代性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基本具备,但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与“公私合营”下的中国出版业,在组织形式与管理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出版业更是趋于黯淡,这表现在出版机构数量的大幅减少——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的一百余家迅速减少到1971年的四十余家,稿酬制度的取消,《出版法》《著作权法》的长期缺失等诸多方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中国出版业才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迈出改革的步伐。随后出现的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向经营性企业的转型、全国统一出版大市场的建立、新《著作权法》的制定、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两大国际著作权公约等等,都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在20世纪末所取得的硕果。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其中,如何与世界顺利、有效的接轨就成为中国出版业改革的重点与难点,这涉及到现代出版市场的经营、出版行为的管理、出版法制与出版理念的构建等众多问题。由于当下的中国“尽管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但是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方向”[4]281,故而以上各种问题的解决,皆可视作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照此来看,该著以现代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对当下中国出版业更好地走向世界亦具有较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一书以现代化的独特研究视角与完备周延的叙事结构,将19世纪以降近代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具体过程与标准完整再现出来,不仅对出版史学界相关的后续研究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下中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亦颇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