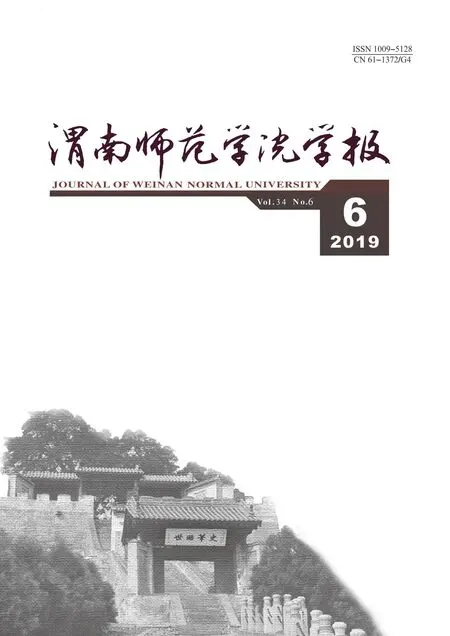象征修辞视角下社会与人性缩影
——论横光利一的短篇小说《蝇》
姜 丽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在新感觉派的文学盛宴中,横光利一成为日本新感觉派的灵魂作家。他对于自己初期小说这样评价:“初期作品中我最先创作的就是《蝇》。……那时候对于文学表现并没有严格的概念,仅仅在写作态度上,非常严肃认真。那个时期我对艺术的象征性的关注胜过其他一切,并且笃信构图的象征性之美远远超过写实。”[1]584可见,《蝇》中登场人物的象征性构图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本文欲从作品《蝇》中的车夫、乘客、包子店老板娘、包子、苍蝇这些角色为出发点,分析他们的象征体及本体含义,探索作品文本背后表达的两次世界大战夹缝下,人们的生活现状和社会体制。
一、横光利一和《蝇》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评论家。年仅25岁的横光利一在亦师亦友的文学大师菊池宽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文坛成为令人瞩目的一颗文坛新星,同川端康成一起活跃在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文坛中。他凭借《蝇》《日轮》两部作品华丽登场后,又借《机械》一跃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大师。后发表长篇小说《旅愁》,用多彩的文笔表现东西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被誉为“日本文学之神”。
短篇小说《蝇》1923年发表于杂志《文艺春秋》。《蝇》不仅是横光利一的成名作,也是“新感觉派”成立前的一块基石,是新感觉派风格的指向标。小说篇幅不过3500字,分为十小节,每小节都有新的人物登场,用驿站这一场景将不同人物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如同一部小型电视剧,更如人生缩影。这种文本结构同夏目漱石的《梦十夜》的文本结构异曲同工。《梦十夜》的结构设计如同参观一幢大楼,每个房间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装修风格。《蝇》这部作品更像是参观中国明清时期的长院,每幢房子用走廊连接起来,一幢套一幢,每幢各不相同。横光利一用环环相扣的文学形式,幽默诙谐,寓意深刻的内容,使整个小说虽短小精悍却能象征社会百态,包容万象、笔底烟花、不赞一词。作品以苍蝇掉进蜘蛛网后拼命逃脱的场景开篇,接连登场的分别是盼见病危儿子的农妇、带孩子的母亲、为爱私奔的年轻男女、同贫穷抗争了几十年的乡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乘坐马车开启新的旅途。作品中迷恋象棋,心念包子的车夫是主宰发车时间的关键人物。作者通过驿站这个场景设置将这些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一起。苍蝇从蛛网逃脱后落在马背上休息,尽情吸吮着马背上的汗水,睁大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并随着马车一同开启了旅程。马车伴着人、马的悲鸣声一同坠崖,所有的矛盾、争端、欲望、期盼都随着马车的坠崖变得烟消云散,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大眼苍蝇挥动有力的翅膀朝空中飞去,小说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二、象征修辞在小说文本中的重要性
关于象征,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修辞、艺术创作方法、文化三种层面的研究。修辞层面的象征指的是一种修辞策略和艺术技巧,与“隐喻”含义相近。王希杰在其《汉语修辞学》中说道:“象征,就是不直接描绘事物,而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借助联想,说的是乙,叫人联想到甲。”[2]406在象征中,人们主要借助事物间的相似性和类比性,努力阐述、揭示未知领域的事、某种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东西。象征所暗示的客观对应物是一种与日常世界有所不同的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它赋予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的一个重要维度。象征主义将象征看作一种艺术创作模式,这对象征的本质的揭示和把握非常有利。但目前,大部分和象征相关的研究都是只停留在对象征的经验描述,没有深入到艺术家想要体现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意图中,因此也不能阐述艺术家使用象征艺术方式展示独特个性的深层原因;文化层面的象征作为一种哲学概念,指的是“象征作为人与世界的异质同构联系”[3]的方式,是一种建立在人的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的基础上的文化现象。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无物不是阴阳。”[4]1604这里的“天”和“地”是象征体,“天”的本体是“阳”,“地”的本体是“阴”。也就是说将简单的物体提升到意象化阶段,形成两个对应抽象符号。这种层面的象征等同于文化现象,有意识地将象征本体扩大化。
象征是近现代小说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它比直接的描述更为重要,也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运用象征手法对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文本思想的传递和表达。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作者以一种不言而喻的特殊思想表达方式引导读者的思考。文学作品中的象征体并不总是代表某种特定的本体,往往只是通过这种途径来进行暗示。因此,读者有时会对同一象征体持有不同看法,这是基于读者本身对小说的理解不同。在分析具体象征体的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尽管某些象征体体现的本体很明显但由于读者对作品当中特定的主题理解角度的不同,对作品中出现的象征体及象征本体的解读也产生了很大差异。
王天慧在《〈苍蝇〉中生命的哲学及艺术特色》一文中明确指出:“横光利一主张所谓象征是将人物形式化构图化,在表现作者的世界观时应该基于时代感觉、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而时代感觉也绝不是时代的退步。”[5]横光利一所强调的这些理论,正好印证了他的文学理念——“反对作家创作时从人生观角度进行创作”。此外,横光的好友川端康成在评价横光文学时谈到,在横光文学中拟人手法的描写随处可见,主观思想由无数分散的片段组成,再重新赋予作品的对象之中,也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赋予万物以生命体征。小说《蝇》在登场角色上就被注入新的思想,每个角色都是一个象征体,在角色形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本体。
三、《蝇》中的象征体与本体
(一)象征体苍蝇与本体旁观者
苍蝇由于传播疾病等各种原因被人们厌恶,但众所周知苍蝇在很多极端环境中都能冲破命运封锁顽强地生存下来,它顽强的生命力为人所叹。《蝇》中,苍蝇一共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在小说的第一节、第九节、第十节,整部作品的故事发展与苍蝇毫无关系,但作品在角色设置上苍蝇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开篇描写了一只大眼苍蝇一头撞在了蜘蛛网上,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其努力抗争,来回蹬着蜘蛛网,最后终于死里逃生,飞到了马背上休息。第九节内容属于承上启下的过渡章节,大眼苍蝇随着马车的出发,从马的腰间飞到了车顶上,车顶的设置则是作品的一个关键,是所有场景的至高点,可以俯瞰而下,纵观全局。第十节关于苍蝇的描写一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大眼苍蝇一会儿默默地眺望着大片的梨树,一会儿仰望着被阳光照的赤红的断崖,一会儿俯视着激流;第二部分,苍蝇从车顶飞到了车夫半白的脑袋上;第三部分,大眼苍蝇吸吮着马背上的汗水补充能量后,悠闲地在空中飞翔。开头苍蝇拼死挣扎,结尾部分苍蝇养精蓄锐、整装待发。它用自己的大眼观察着农妇因为怕见不到病危儿子最后一面的悲凉无奈;看着乡绅将所有财产带进浴室被人讥讽的窘态;欣赏着远处的梨树林与近处的潺潺的溪流;斜视着车夫虽然驾着车但却早已进入梦乡的惰态;眼睁睁地看着车马翻下悬崖,变成碎片。在马车临危之际,相较于双目紧闭进入梦乡的车夫和戴着眼罩盲目拉车的马,苍蝇却始终睁着大眼保持警觉。作者在作品中用“大眼”作为苍蝇的定语成分来修饰苍蝇,在整部作品当中重复出现了四次。作者用反复的写作手法,强调“大眼”的观察与记录能力。它就像是一台摄像机,摄录着驿站里每个人的举止,洞悉着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作品的最后,马、车夫、乘客随着马车跌落悬崖的瞬间,大眼苍蝇在人马的悲鸣声中,充满力量地向天空飞去。所有的纷争、焦虑都随着马车的坠崖而尘埃落定,唯独苍蝇充满生机,独自悠然地飞翔。苍蝇冷漠无情,对他人的灾难视而不见,更甚者可以说是幸灾乐祸、麻木不仁。而这种心理表现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被鲁迅怒斥为“看客心理”。“看客”,简单而言就是,“旁观者,是指人们以旁观者的姿态面对事件与人,不论何种性质的事件如同看戏一般,对当事人没有理解与共情的心理反应”[6]。作者刻意用“大眼”作为苍蝇的修饰语,旨在让苍蝇发挥“看客”而不“移情”角色作用,象征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中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只顾自保的旁观者。
(二)象征体车夫与本体权力支配者
在作品的第二节,驼背的车夫正在驿站旁边的包子铺门前下象棋,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看起来悠闲自得。在第三节中,焦急的农妇向车夫的房间连问三遍:“还有车吗?”没有得到车夫的回答。农妇用焦急的口吻再次询问时,车夫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头也不回地答道:“还有第二趟车。”农妇提到病危的儿子,欲用自己可怜的遭遇博取车夫的同情而早一刻发车。可车夫完全沉浸在棋局的快乐世界中,哪里能留意到农妇的焦急心情,面对农妇的再三询问,沉默和无视是他的应对方式。车夫是冷漠的,他人的生死和遭遇一点也不会影响他对棋局的兴致。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7]157除去“污蔑庶民”看不起老百姓的这层意思应予批判摒弃以外,这句话也算说得精辟。他指出人虽绝大部分同于动物,但却具有“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部分(孟子称之为“性善”);要做好人做君子,关键在于克制同于禽兽的部分而保存发扬那“几希”的“人性”。车夫是冷漠的、霸道的、恰恰缺少上述的“人性”。在第六节中,车夫面向包子铺的老板娘问道:“包子,还没有蒸好吗?”这里的询问并不是由于乘客的焦急,而是由于自身对包子的渴望。作品中讲到,对于这个有洁癖的车夫而言,吃谁都没有碰过、刚出笼的热包子,就是他常年独身生活每一天至高的慰劳。第十节中车夫吃光了围裙里的包子,弓着背打起了瞌睡。车夫在整部作品中的形象是慵懒的、自私的、随心所欲的。农妇的苦苦哀求,其他乘客的迫切心情,所有乘客开始的大汗淋漓到汗被蒸干的等待过程中的无限悲凉,都未能呼唤起车夫的几许“人性”。
权力是“指社会资源,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资源。拥有资源越多的人的权力越大”[8]。发车时间是乘客最关注的问题,是车夫的权力范畴,也是他可以漠视一切的源头。车夫是发车的关键,因为他拥有唯一的社会资源——马车。这一社会资源赋予他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无视其他人的正当诉求,对旁人冷漠与霸道,只以他的个人利益为中心,这都源于车夫是唯一社会资源的掌控者。资源的支配者拥有无上的权力,为人冷漠、霸道的同时,也沦为了欲望和享乐的奴隶。车夫因为长时间对棋局的沉迷,导致休息不足;对刚出笼的包子带来美味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才会导致兴奋感降低,被睡意侵袭,疏于驱马,最后导致坠崖的悲剧。在作品当中,“驼背”作为车夫形象的修饰语,是身体残缺的体现,或许也正是作者对社会中权力支配者的一种反抗体现吧。
(三)象征体乘客与本体普通民众
小说《蝇》中,乘客的角色主要由农妇、年轻男女、带孩子的中年妇女、乡绅构成,他们的年龄层次由幼年到老年,坐车目的也各不相同。农妇是第三节的出场人物,她想去镇里探望自己病危的儿子,多次询问发车时间并哀求早点发车。被车夫漠视之后,她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乘客,希望大家和她一起催促发车,他人的无动于衷让她几乎绝望。《蝇》中,农妇前后共四次向别人提及自己儿子就快死了的事,前两次出现在向车夫询问发车时间的时候,后两次是和乡绅的对话中。对一般人而言,“死亡” 一种特异的存在,人们敬畏“死亡”。但此处的“死亡”并未引起车夫和乡绅的情感波动,他们对他人境况的冷漠程度可见一斑。为爱私奔的年轻男女出现在第四节,他们从家里偷跑出来,怀着可能被发现抓回去的担心和不屈于现状的决心,他们怀揣忐忑却对未来充满期待。第五节是带着男孩的母亲。她要带孩子去哪里,要干什么作品当中都没有提及。从男孩“妈妈,马!马!”“妈妈,梨!梨!”的对白可以看出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幼童。作者把男孩看到马时流露出来的好奇与兴奋用简短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男孩见到马时的好奇心同兴奋感贯穿始终,男孩的心思同成人的心思有天壤之别,不懂世事,充满了可爱纯真的天性同成人世界的利欲熏心形成鲜明对比。第六节出场的是43岁的乡绅,究其一生都在同贫穷抗争,终于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800日元。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是同贫穷抗争了四十三年的战绩。此时的乡绅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规划,乘上马车或许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作品共设置了六个乘客的角色,他们身份不同、追求不同,汇聚于驿站。农妇心怀亲情,年轻男女心怀爱情,小男孩执着于兴趣,乡绅执着于金钱。他们的任何行为举止与艰辛不易丝毫不会引起权力支配者的决策改变,他们是一群不被关注的人物,是社会当中底层的普通民众,众多而渺小,生活规规矩矩,为了小小的希望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他们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的同时,等待着奔向希望的发车,命运的车轮无情地带着他们跌落山崖。命运被隐形的权利之手控制着的普通民众对此浑然不觉。在笔者看来他们的生存状态还不如作品中的那只大眼苍蝇,苍蝇起码可以和蜘蛛网抗争,悠闲地吸吮马儿的汗水,随心所欲地飞翔。而本可掌握命运的人却要受控于权力支配者,作者用强烈的对比讽刺当时日本社会以及表达生活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无力与悲哀。
(四)象征体包子店老板娘与本体中产阶级
作品的第三节中,农妇心神不宁地朝车夫的方向张望,紧张地询问:“还有车吗?”等不到回答的农妇焦急地来回徘徊。之后再次询问,可还是没有人回答。农妇第三遍询问的时候,“刚才就走啦!”答话的不是车夫而是包子店的老板娘。乘客并没有买包子,因此,包子店的老板娘和乘客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和利益往来。作为一个拥有基本道德素质的人,面对一个陌生人焦急的问话给予了回答。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听话者农妇而言却是极大的心理安慰。另一方面,包子店老板娘和车夫,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社会阶层的掌权者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关系。车夫想从这里得到未经任何人手的刚出笼的包子满足味蕾的需求和常年以来的心里慰藉,包子铺老板娘也可以从车夫那里得到相应的报酬。因此,包子铺的老板娘象征着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他们基本上在感情需求和社会尊重方面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但是还不能够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他们或许对一般民众存有同情,但是面对权力者的冷漠无情也是无能为力;他们不受权力支配者的奴役,但是也依附于权力支配者的庇护而生存着,饱含着些许的无奈。
(五)象征体包子与本体欲望
在《蝇》当中,包子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意象。在作品第七节中,有一段充满幽默感的旁白。
马车究竟几时走呢?谁也不知道。如果说有人知道,那这个“人”之可能是灶上那渐渐隆起的包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个有洁癖的车夫而言,吃谁也没碰过、刚出笼的热包子,就是他常年独身生活的每天最至高的慰劳。[9]85
农妇、年轻男女、乡绅、母亲与男孩作为主体的人都无法让车夫尽快发车,而作为客体的热腾腾的包子是牵制车夫发车时间的唯一因素。车夫为了能吃上一口热包子,无视了所有乘客的恳求,一拖再拖发车时间。这一幕看似非常简单常见的表象,却值得人深思。究其原因是车夫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包子看似是常见又普通的东西,但在车夫眼中包子是他心灵的慰藉,是他胃袋鼓腹含和的渴望。因此包子作为象征体,它的本体是“欲望”。欲望是人命运的支配者。马车坠崖悲剧产生的真正诱因是包子,车夫饱餐了一顿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包子,味觉和洁癖似的精神世界得到慰藉之后而诱发睡意,进而使马、马车、乘客一起坠入山崖、丧命黄泉。可以说包子就是欲望的化身,欲望具有支配人的情感和行为的魔力。权力者为了自己的欲望不顾周围人的乞求,他的冷酷无情也必然会导致冷酷的结局。假设《蝇》这部作品最后的悲剧不是由于包子,而是由于山洪,地震,泥石流等不可抗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话,或许,也不会有后人的反省了吧!
四、文学中的社会及人性的缩影
鲁迅先生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地描绘社会,尚有力,便又一转而形象社会,使之变革。”也就是说,文学是纪实的艺术,现实主义文学亦是如此。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描述社会百态,能够引导和拯救人的心灵。关于1923年发表的《蝇》,虽然很多学者更加关注作品的表现技巧,即“与自然主义照相式的平板写法技法相对,作品通过感觉的表现,构建雕刻性的文体,来完成构图的象征性的美”[10]182。但是作品中通过描写乘客同马车之间、车夫与包子之间的依存关系,着意说明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以权势财势为中心的社会里,人的心灵被扭曲的现实,使《蝇》蒙上了一层社会小说的某些成分,揭示当时日本社会的现状。
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着战争及军需订单,日本国内生产极速发展,基本积累极速推进,出口贸易增加,摆脱明治时期长期以来的经济入超状态。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的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到了1920年左右,日本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镇压工人革命运动,封杀无产阶级文学,整个日本处于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加之,1923年9月1日这一天,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这次灾难不仅使日本失去了13万民众的生命,也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当时的日本,自由放任主义是经济界的主流思想,商品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导致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政治、经济的大混乱,给日本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深化了资本主义危机。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无产阶级文学方兴未艾。占据资产阶级文坛的菊池宽创办的同人杂志《文艺春秋》固守成名作家忽视新晋作家。于是,以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等无产阶级文学派于1924年6月创立了文艺方面的统一战线创办的杂志《文艺战线》。《文艺战线》在成立的纲领中指出:“(一)我们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艺术的统一战线上;(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个人思想和行动是自由的。”[10]169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感觉派”的产生和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新感觉派”文学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段来展示主观感觉对周遭社会的真实反应。颓废、悲观、讽刺、象征,这些都是“新感觉派”文学不可缺的有机构成。《蝇》虽然于1923年5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但从时间上来看,不难推断出作者横光利一在完成《蝇》过程中未必没有受到《文艺战线》统一纲领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作者新奇的表现手法,通过作品《蝇》来反映日本当时的社会百态。
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但是也同其他作家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文学延伸线《文艺战线》并制订了其纲领。《蝇》以新颖的技巧来完成构图的象征美这一点上来看,确实已初露“新感觉派”的特征,但也不可忽视其含有“革命文学”的成分。《蝇》这部小说虽然是短篇小说,却用精练的语言、新颖的技巧、精密的构思、象征的手法反映了日本当时思想被禁锢、人身被束缚、难以喘息的、压抑的、扭曲的时代,通过强烈的讽刺构写了人性与命运的哲学。在资本社会中,社会资源的掌控意味着权力的支配。只对棋局和热腾腾的包子提得起兴趣的车夫,掌控着唯一的社会资源——马车,他无视周围人的哀求,只以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为中心,站在社会的至高点,是冷酷无情的裁判者,更是权力的支配者。通过车夫可以看出当时日本资本市场下,资本家当权者的冷漠。包子店的老板娘在作品中既不属于任人摆布的普通民众,但也没到权力支配者的高度;对底层民众抱有同情,又需依附权力支配者才能生存的一类。她属于社会层次当中基本可以满足现状却无力改变现状的中产阶级。苍蝇是游离于社会阶层之外,冷漠无情,对灾难视而不见的“看客”即旁观者。包子原本是极其常见的食物,在作品中是支配着人的情感和行为,它是欲望的化身。小说中的苍蝇虽然渺小,但它勇敢无畏地和命运抗争,最终逃离蜘蛛网的约束,悠闲地吮吸马儿的汗水,随心所欲地飞翔。相比之下,作品中的每个人物角色都各有特点,怀揣梦想,却受制于权利和资本的管辖之下,最后都随着马车的坠崖而消亡,这无疑让人感到异常讽刺。横光利一用象征的手法,通过驿站这个小舞台将社会中的各种角色汇集到一起,上演了一部精彩绝伦的舞台剧。这个小型的舞台剧正是当时日本社会下人们生活处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