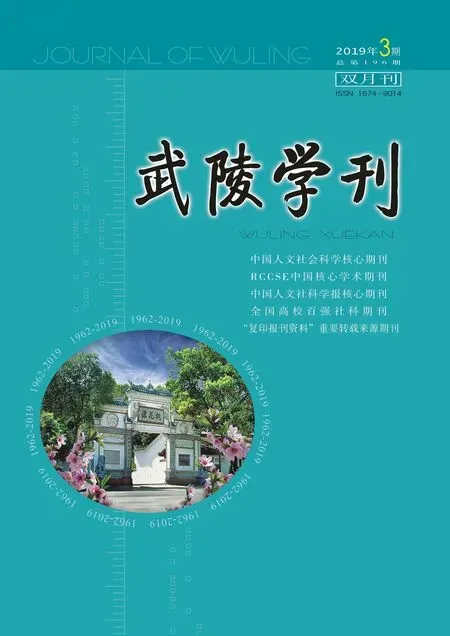凝视理论视域下中国形象生成逻辑研究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为例
粟 超,杜俊华
(1.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编辑部,重庆 400041;2.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00)
凝视作为视觉特性的一种形式,不仅是一种观看行为,更是一种观看方式。作为观看行为,它以其观看动作的延时性区别于“浏览”及“一瞥”;作为观看方式,它以其带有权力机制和欲望冲动的观看具备了鲜明的社会特征和意识形态意义。19世纪中后期起,一批日本人深入中国腹地,留下大量见闻录、日志、游记、报告书等。凝视理论与旅游体验中首要的视觉特性不谋而合,为研究旅游行为中所裹挟的权力和欲望的观看提供了极佳的观照视角。借助凝视理论,能够有效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对华心理的生成机制,进而深入把握他者视角下中国形象生成的内在肌理。
一、凝视的背景——中日交往格局的转变
日本与中国互为邦邻,一苇可航,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日两国在文化、商贸等领域有着频繁而悠久的交往历史,并在长期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共通性,同属东亚文化圈。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在锁国政策的高压下度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直至19世纪与美国、荷兰、英国、俄国、法国签署五国公约后,紧闭两个世纪的国门才逐渐打开。锁国期间,中日交往大大减少,仅限于中国商贸单向度地输入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日本社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向欧美诸国学习,包括派遣使团出访欧美、派送留学生到欧美诸国求学等。与中国的交往肇始于“千岁丸”号商船所承载的与清通商的初衷。在脱亚入欧的吸引下,日本社会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摇摆不定,并愈发呈现出摆脱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因循而不断向西方文明靠拢的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横滨至上海、日本—芝罘—天津—牛庄两条海上航线的开通为日本人进入中国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为日本殖民触角的萌芽准备了温床,在殖民扩张的驱使下,在访史朝圣的牵引下,身份各异的日本人怀着不同的初衷来华漫游。
(一)日本文明体系的中国色彩浸润
中日最早交往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适时中国国力强盛,日本相对落后,两国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欲望,源源不断地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到隋唐时期,中日交往愈发频繁。日本遣唐使赴中国学习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现象,对中华文明的被动接受与吸收,开始转向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模仿。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少则不下百人,多则达六百人左右,遣唐使到达中国后所学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中国的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同时留学生和学问僧也随船同行。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中日在贸易和文化上依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中国商船远航日本,相应地,每年都有遣明船驶入中国海域。近代以来,中日交流更为频繁,众多日本官员、学者来华,留下了大量的游记作品,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官员、学者远航至日本考察学习,以期寻求救亡图存之法。17至19世纪,中国主要处于清朝统治时期,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两个世纪里,中日的官方交往均被闭关锁国的政策所禁锢,然而二者的闭关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前者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苏醒,后者则在闭关锁国中进行反思与探索,这为二者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虽然两国官方交往受阻,但民间交往依然得以继续发展,甚至频繁程度超越以前。中国商船依然不断驶往日本,受日本锁国政策的禁锢,这种交往只是单向度地输入日本,并无日本向华输出的反馈过程。20世纪伊始,大批中国有志青年,如郭沫若、鲁迅、郁达夫等赴日留学,学习先进思想,希图改造中国社会。
以20世纪初为时间节点,大致可将中日一千多年的交往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鲜明的特征。东汉到南北朝时期是中日交往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主动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体现出“尊崇与怀柔”[1]的特征。第二阶段为隋朝至明朝初年。与上一阶段相比,日本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迅速发展,中国却呈现出故步自封的趋势,“赶超与因循”[1]概括了这一阶段的特征。从明朝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是中日交往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日交往格局发生逆转,尤其到清政府统治时期,朝不保夕的清王朝一变师者身份,转而以日为师,学习日本变革发展经验,试图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征体现为“挑战与转折”[1]。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华态度勾勒出日本人看待中国的不同立场,中国形象由“文化母国”到“衰败帝国”再到“停滞国家”的转变,蕴藏着日本人凝视中国的权力逻辑转变。
截至清朝前期,日本一直师法中国。通过对中国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全方位的学习,并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最终衍生了本土文明体系和特色文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就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做过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他用豆浆比喻日本文化,用盐卤比喻中国文化,强调倘若没有作为外力的中华文化的助推,日本不能形成自身的文化:“我却认为比如做豆腐,豆浆中确定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不加入使之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2]此语道出了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以及作为文化母国的中国在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日本禁教锁国下的稳定发展
锁国被当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往往被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加以运用。中国明、清两朝试图通过这一方式使自己免受他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入侵。继16世纪前半叶频繁地对外交往后,从16世纪后期始,日本国内通过禁教、限制贸易等手段企图达到抵挡西方天主教传入及垄断贸易的目的。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闭关政策阻绝了和他国的贸易往来,但仍保留了与中国、荷兰等国严格限制的贸易关系。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触角向远东地区延伸,西班牙、葡萄牙于16世纪进入日本,与日本的海外贸易也始于此。伴随商贸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进入日本,基督教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无疑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社会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随着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和推广,它逐渐发展为下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慑于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所引起的民众反抗心理,德川家康于1613年颁布禁教命令。自此之后,幕府通过颁布天主教全国禁止令、限定通商口岸等措施使日本一步步走向了闭国之路。之后的两个多世纪,日本社会都笼罩在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阴影之下。在民间交往上,幕府颁布律令禁止本国人民与外国人交往;在对外贸易上,规定不得建造大型船舶,日本船只不得出海航行,同时也限制外国船舶来航。一方面,幕府通过该措施维护了其统治的稳定;另一方面,限制商贸自由有力地切断了大名与外来商船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幕府最大限度地攫取了商贸利益。禁教锁国操控日本社会长达两个世纪,这也使得日本与西方先进技术及文化隔绝长达200年之久。然而,日本并非全然与外界断绝交往,锁国时期开放的长崎港是日本吸收来自中国、荷兰先进文化和技术,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门户。总的来说,禁教锁国发挥的自卫功能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安稳的环境,在这两个世纪的自我封闭中,日本社会经历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之象。
(三)日强中弱的地位逆转
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西方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的逐渐强大激发了西方国家海外扩张的野心,部分西方国家甚至将侵略的触角延伸到了遥远的东方。日本地处远东航线末端,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欧美国家侵略蓝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美国家赢取远东利益的前哨。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屡次试图打开日本门户,却一直被日本国内坚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拒之门外。直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通过风说书传入日本国内,日本上下大为震颤,惯守的封闭格局才开始逐渐松动。自19世纪中期起,日本不断与西方国家签署合约,打开门户。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打破了锁国体制。1858年,日本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五国先后签署了《修好通商条约》,即《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将神奈川、长崎、箱馆作为贸易港,这标志着日本社会奉行了两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分崩离析。
中日两国均是被迫打开门户对外开放,但就发展速度而言,日本远快于中国。伴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与英国签署条约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待西方文明的拒斥态度以及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中举步维艰,经济社会并未取得较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事实给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日本幕末维新志士都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昂奋的抵御外敌心理,与吸取清朝屈辱西洋的教训有一定关系”[3]116。西方扩张所带来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压力在给日本社会带来焦虑的同时也使得统治者孜孜寻求西方强权政治下的生存之法,与生俱来的岛国意识加上清朝战败造成的冲击推动了明治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日本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如解除大船禁造令,向荷兰人学习航海术,培养洋学人才,派使团出访欧美,派遣留学生赴欧美留学等,一步步向近代化国家迈进。另一方面,《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与美国、荷兰等国陆续建立了贸易关系,促进了日本海外贸易的发展。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权政治的威逼下,日本一步步驶离了风平浪静的自我封闭之海,逐渐驶进了由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近代化的滚滚浪潮之中。被迫开国后采取的系列举措极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不久,日本便成为了东方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国家,危在旦夕的清朝政府与蓬勃壮大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攻守之势易转。
二、凝视的动机——政治诉求与精神复归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书本到风闻的纸上言论再到间接报告的演变过程,由他人传导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形象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疏离感。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中断达两个世纪之久,实行海禁政策两个多世纪后,“千岁丸”号商船成为了日本官方派往中国的第一艘船只,自此之后,大量日本船只驶向中国,随之而来众多日本人踏上中国国土,以其亲身体验留下了在中国生活、游历的点滴记录。
(一)“千岁丸”号商船上海行对传统认知范式的打破
1862年夏季,“千岁丸”号商船抵达中国上海,这是1854年实行开国政策后日本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派遣官船,“千岁丸”号商船上海行缓缓拉开了中日重新交往的序幕,颠覆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范式。
上海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上海在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方面十分活跃。于日本而言,上海乃是最靠近长崎的中国大陆港口,拥有极佳的地理位置,且“上海是迎受近代世界八面来风的屏幕、演出牵动全体的种种悲剧的大舞台,从而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走向近代社会的领先之地”[3]36。因而,解读上海成为了日本了解中国甚至是了解近代世界动向的捷径。初登上海,藩士们便震惊于上海的繁华,映入眼帘的各国商船鳞次栉比,场面蔚为壮观,不仅如此,他们还见识了与本国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对中国的考察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千岁丸”号商船上海行不仅续接了中日两国中断多年的商贸往来,同时为日本国民再度了解中国民众及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随船来华的日本藩士及家眷对中国形成了最直观的体认,他们纷纷提笔记录所见所闻,“处在古今中西交汇点的上海,提供了斑斓多彩的社会转型情景、纷至沓来的东西方信息,大大充实了他们饥渴的心灵。藩士们奋笔记录目睹身受,留下数量浩繁的纪行文字”[3]77。对中国社会急切而细致的观察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日本幕末志士以清为鉴、开国维新的爱国心迹。随行人员通过对中国社会实地考察,询问对外贸易、土地政策,与中国知识分子笔谈交流等,了解中国文明之现状,并由此诞生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情状的文字资料,这也成为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国文明认识的最早记录,他们将在中国搜集到的资料传入国内,成为了日本国民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
事实上,直至日本开国前夕,日本人对中国形象仍旧怀有美好幻想,视中国为圣贤之邦,“千岁丸”号商船入华使日本人得以接触体验现实中国,耳闻目睹中国社会之情状,凋敝衰败的现实中国与诗意古典的想象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此行也成为了日本人中国观的重要转折。
(二)因公受命下的政治考察
“千岁丸”号商船上海行拉开了日本船舶航行中国的序幕,此后,日本官员、学者、记者或因公受命、或旅行观光前往中国腹地,并根据在华的亲身经历写下了大量记载中国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逸闻趣事的文字。游记作者身份各异,目的不一。如竹添进一郎为驻华使馆外交官,山川早水为教员,桑原骘藏、宇野哲人、内藤湖南为学者,芥川龙之介为作家。不同的来华目的导致凝视主体不同的游历心态及不同的观察立场,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游历动因:一是因公受命的政治诉求,一是朝圣访史的精神复归。
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日本民族从古至今都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即所谓的“岛国意识”。刨除17至19世纪日本幕府的锁国之举,历史上,日本始终孜孜不倦向先进文明学习以强大自我,谋求生存。明治维新后的迅猛发展使日本不再满足于国内的狭小市场,从19世纪下半叶起,日本开始实行大陆政策,妄图称霸亚洲、征服世界,而征服亚洲的首要目标是将中国和朝鲜两国收入囊中。追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离不开对神国主义思想的解读。神国主义思想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究其实质,乃是天皇借助神的名义实现对内维护统治稳定、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幌子。山鹿素行、本居宣长等专门著书立说宣扬神国主义思想,《谪居童问》《中朝事实》集中反映了山鹿素行的神国主义思想。本居宣长曾公然宣扬征伐中国,指出如果中国有所过失那么日本将对中国进行征伐,言论具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日本统治者正是利用日本神国理念与天皇神权意识和虚伪的征服世界的‘使命感’,才大肆宣传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并利用这种优越性鼓动对外侵略扩张。”[4]“海外扩张论”的提出更是将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和朝鲜两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统治则是近代日本的核心战略。
近代日本人来华漫游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驱动。以神国主义、海外扩张论、军国主义为核心搭建而成的日本大陆政策渗透到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来华的日本人少之又少,相反,他们来华往往以调查中国文化、政治、军事等为动机,政治家、间谍等常常假借游览之名对中国大陆进行实地勘察或调查,搜集中国的各种信息并反馈至国内,如内藤湖南漫游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考察中国时局,《燕山楚水》字里行间始终将日本的利益扩张置于首位。“社会空间的基础是领地、土地、地域和帝国与文化的竞争的实际地理基础。”[5]107漫游不仅仅是一种游历行为,更是一种对地理空间带有政治意味的巡视,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进行殖民占领的预热。
(三)文化牵引下的精神溯源
在以政治意味为导向的漫游中,不乏以朝圣访史为目的中国行。适时出游中国的日本文人往往以寻找精神困顿的出口为目的。一方面,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席卷了近代日本文坛,以此反击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欧洲近代文明对日本的冲击,表现在文学上则主张回归日本古典,描述日本九州等落后地区。文本中国的美好想象构筑起日本文人心中诗意的乌托邦,寄托着日本文人的浪漫愿景,对理性原则的逃避和疏离,使得部分日本文人试图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从原有生活中跳脱出来,借由世外桃源般的中国抗衡日益西化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厚重的底蕴以天然的磁力强劲地吸引着日本人。在入华之前,来华日本人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挚爱之情者。中国古典诗词所营造的朦胧动人的意境,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高风亮节,中华民族璀璨悠久的历史以及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深深吸引了来华日本人的关注。作为一种高势能文化,中国文化向四周散发出巨大的能量,处在文明边缘的日本一直以来视中国为文化母国,然而文本中国形象已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因此,他们急切地想要踏入中国境内,亲眼打量、亲身体验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的真实面貌。如学者宇野哲人主要以考察中国风貌为出发点进入中国,《中国文明记》则是他在华纪行的结晶。
政治诉求和精神复归从不同维度引导了来华日本人的中国漫游,促发了他们的凝视行为,不同的出游动机直接导致观察视域的不同侧重,在来华日本人的漫游中,这样两种动因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是常常统一融合于凝视主体的凝视目光中,共同孕育出来华日本人的中国体验和中国认知。
三、凝视的维度——权力话语操纵下的选择性观看
来华日本人的中国凝视包含着两种不同认知,一是经由他者形塑形成的关于中国形象的前认知,一是入华后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关于中国形象的新认知。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漫游中国使来华日本人得以入境问俗、亲历中国,搜集到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出版发行的游记作品为身居国内的日本人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最及时最全面的信息。通过阅读游记,日本民众得以及时更新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于国家而言,来华日本人的勘查和考量使其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为日本在华侵略扩张的政治意图出谋划策。来华日本人的切身体验与国内的中国观形成双向互动,他们的所见所闻既印证了国内业已转变的中国观,又反作用于本国国民意识,促使日本国民的中国观不断变化刷新。
(一)个体认知与权力主体的协同共谋
来华日本人对中国的凝视包含着私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理解;与此同时,适时出游的日本人,因公受命者居多,出于国家策略的指引,最大限度掌握中国的信息,配合日本对华的谍报战略是近代日本人来华的重要目的。个人凝视视野与权力主体形成一种共谋关系,使得凝视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青年军官曾根俊虎因公受命被派往中国,以间谍身份在中国腹地活动。自26岁以“判任随员”身份第一次被派往中国后,曾根俊虎长期在中国收集情报,几乎每到一地便绘制该地地图,收集相关信息。《北中国纪行》记录了曾根俊虎1874—1876年在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各省市漫游的见闻,他的漫游考察以天津为起点,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气候物产、民俗风情等。值得关注的是,在曾根俊虎所著的游记中总共有191幅插图,这些插图大部分为其手绘的军事地图,他不仅根据对环境的考察绘制出了地图,还常常站在军事立场上对其进行战略分析,并根据自身对华认知提出了一系列对华政策建议。由于对中国社会的熟稔,1878年,曾根俊虎将《清国近世乱志》及《诸炮台图》呈给明治天皇。在漫游中国的过程中,曾根俊虎提出了成立兴亚组织推及亚洲诸邦的思想,作为“兴亚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曾根俊虎希望通过自身在华所见所闻,为日本国内提供更多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消息,尤其是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希望获得日本军界对其主张的支持。通过对中国的凝视,个人的认知与权力主体形成了互动和共谋。
小林爱雄通过对中国社会进行考察,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情况。桑原骘藏抱着学术目的来华,足迹几乎遍布了北中国,所著游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芥川龙之介、竹添进一郎、中野孤山三人以踏寻中国风光为主要目的进行漫游,但他们的中国游记不限于向国内日本人重现古典诗意中国,尤为重要的是,在对中国自然风光进行描绘的同时融入了作者本人对中国社会的体察和感受。
近代日本的中国游记大部分出自个人之手,部分由专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编写。如东亚同文书院每年组织毕业生到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回国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满韩修学旅行纪念录》收录了1906年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和学生在中国东北和韩国的旅行记录。日本人的中国游记部分满足了日本政府了解中国的意图,他们的在华旅行见闻被编写成书整理出版,打通了日本人了解中国甚至是了解世界的通道。如,德富苏峰的两次游记均刊载在由他主持的《国民新闻》报上,国内民众借由游记了解认识了中国;中野孤山曾在游记的序言中提到:“就所见所闻之自然状况记叙于此书,取名《游蜀杂俎》,绝无杜撰。作为了解中央中国的一个途径,尽可深信,无须质疑。”[5]1
游历具有亲历性和现场感,这种特性使得其叙事话语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并按照它的话语模式导向日本人中国形象的生成。实际上,游记文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亲历特性遮蔽了意识形态色彩,这势必造成读者对游记文本内容的盲目信服。这一时期,中日关系逆转,强大的日本试图在衰败的中国身上寻找优越感,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日本国民不可避免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他们的凝视立场沾染着权力机制的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对凝视客体的选择,因而,此时的日本游记作品更多呈现出负面叙事的倾向,游记中所刻画的中国形象,所传达的中国观均经过了来华日本人文化观念的选择和过滤。虽然游记作品具有很大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对现实的复制。
(二)文化母国“祛魅”与自我身份确认
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信徒,对文化母国抱有虔诚和敬畏之心。从19世纪中期起,中日关系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千岁丸”号商船上海行对日本社会的未来走向影响颇大,藩士带回日本国内的中国观察促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对内改弦更张、对外殖民扩张的两种趋势。清政府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无能为力,极大地动摇了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与此同时,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叩响国门之后,幕府末期的对清策略更是摇摆不定,要么主张联合中国抗击西方强国,要么提倡征服中国从而强大日本。随着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日本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国实地考察,他们的中国漫游之旅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子国对文化母国的“袪魅”之旅,考察的结果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社会早已萌生改变的中国观的强化。
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璀璨丰富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来华日本人,在入华之前,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都抱有美好幻想,视中国为诗意浪漫的圣贤之邦。来华日本人中,许多都拥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在日本国内之时就曾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对中华文化怀有挚爱之情,如山川早水、内藤湖南、桑原骘藏、芥川龙之介、竹添进一郎、宇野哲人等。内藤湖南自幼受汉学熏陶,挚爱中国传统文化。《考史游记》的作者桑原骘藏大学时主修汉学科,研究生阶段学习东洋史,有着极为深厚的史学功底。芥川龙之介自幼爱读《唐诗选》等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怀有向往与憧憬之情。在中国漫游之际,很多日本人主动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希望与他们畅谈交流,可见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之情。然而,伴随他们在华逗留时间的增加,以及对中国社会考量的深入,来华日本人的美好期待逐渐被现实打败。尤其是甲午一役后,日本由古代的“慕华观”开始向近代的“蔑华观”转变,中日两国地位逆转,中国社会的衰败和落后使来华日本人的想象中国观念屡屡受到冲击。
周宪认为“前理解”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凝视者的凝视目光,并且不断地与当下目力所见形成对比,从而导致当下视觉体验的形成。耳闻目见所形成的中国形象与通过文本阅读想象生成的中国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来华日本人游弋在这两种中国形象之间,并不断将现实中国与想象中国进行对比。适时中国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吸食鸦片成风,行路中所接触到的中国普通民众,所见识到的中国社会风俗让来华日本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中野孤山在谈到中国的教育时说道:“讲文明的国民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文明开化,哪怕是落后文明一天,他们都会觉得不堪忍受。可是现在的中国至少落后了一百年吧?而它的国民大多数还抱着过去的美梦不放。”[5]192昔日,日本长期以华为师,广泛学习中国社会各项典章制度、器物文明,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大,又适逢清政府的落后衰败,日本一改往日对华态度,转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无情地揭露中国社会现状,这无疑是个体层面对神圣母国的质疑。在宇野哲人的想象中,中国房屋其外观应该颇为壮观,事实上,街市上到处笼罩着衰败感。中国人随地大小便的恶习也让宇野哲人瞠目结舌,“予曾屡屡于偏巷街角之处见彼等蹲踞解便……彼等之举,乃为不可为之事,然毫无惧色”[6]25。芥川龙之介与友人同游湖心亭,却无意间看见一个中国男人悠然地往湖里小便。“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6]10。破败的风景已然让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想象濒临破灭,偶遇中国男人的不文明行为愈发使其心中的中国理想主义色彩不断褪色。在乘坐火车时,芥川龙之介认为中国的乘务员不如日本的乘务员敏捷利落,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想来是我的偏见在作祟……我们也很容易用我们惯有的尺度去衡量。”[6]58尽管对中国情趣憧憬着迷,目睹中国国民的堕落后,芥川龙之介失望至极,并得出结论:“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6]136日本的城市运动诞生于16世纪中叶,并持续至19世纪初,到19世纪时日本社会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日本人在凝视中国时常常以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为标尺,以落后、愚昧的中国为参照从而凸显日本的进步和文明。“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在被迫接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政治经济秩序后,也在文化上相继主动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东方化’的过程。”[7]日本正是在自我东方化的过程中,不断否定和疏离曾经的文化母国,以此完成新身份的确证。
丰臣秀吉执政时,就表现出摆脱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倾向。至江户幕府时期,日本自称为“中华”,将周边等国视作“四夷”,企图建立以日本为本位的华夷秩序。明治维新前期,日本人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产生了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得益于西方文明的助推;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抛弃自我主体性,试图找寻既不拒斥西方文明又能保持自身主体性的路径。作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精英阶层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脱亚入欧是日本摆脱来自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落后的危险性进而转向西方吸收现代性的一种战略选择。从广义上来说,“亚”主要指东亚地区,这一地区在文化和历史方面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系,包括了中国、朝鲜等国;从狭义上来说,“亚”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圈”。脱亚,即是脱离亚洲的文化身份,不仅要祛除自身的亚洲性,还要与具有亚洲性的国家划清界限。子安宣邦曾断言如果不对中国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确认其自立性。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尽管日本的国土在地理上属于东亚,但是国民精神早已脱离了东亚文化的固陋之处,转移到向西洋文明学习,与西洋文明国家同进退。因而“脱亚”,确切地说“脱华”成为了日本确立主体地位的关键。因此,才有了对华态度的迥然转变。
与此前视中国为圣土,对中国顶礼膜拜的中国观相比,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呈现出复杂多元的一面。在对中国辽阔山河、厚重人文赞叹不已的同时,又大肆展示中国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一面;在赞扬中国城市繁荣昌盛的同时,又不吝言辞直陈其肮脏混乱的一面,帝国子民凝视弱国子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在凝视目光的作用下,中国形象与日本形象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保守的中国与开放的日本,半开化的中国与文明的日本。总的来说,来华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诗意浪漫的想象中国形象,充满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一种是现实堕落的中国形象,笼罩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来华日本人通过对中国的前认知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形象大多充满乌托邦色彩,他们试图在异域中国显示自身作为文明社会的优越感,并通过中国进一步印证强化文明帝国的主体地位,乌托邦式的中国想象逐渐让位于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帝国权力操控下的观看,本能地过滤掉中国社会好的一面,沉淀中国社会坏的一面,舍弃中国民众善的一面,留下中国民众恶的一面,中国形象不再是原原本本的再现,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构,重构的目的在于使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摆脱长期以往处在“巨大的他者”阴影之下的社会现实,从而完成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