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头村的孝
阎海东

在我们村,老人孤寡,对儿女来说,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
连生已经至少七年没出门了,他必须守在家里照顾孤寡老母。
自从七年前老父亲去世,他的打工生涯就中断了,此后,他陪着老母亲,在黄土高原因远离城镇的村庄里度日。平常日子里,老家并没有太多的活计,连生看起来游手好闲,浑浑噩噩,但村里人都知道,他在伺候老母,是个孝子。
庄里的青壮年如果不出门打工,是万万难以被众人理解的。留守乡里,必须有残疾痴呆等十足的理由,否则会遭遇鄙视和唾弃。连生五十多岁,也是壮年劳力,不出门谋生,而在村里度日,唯一的理由,就是老母孤寡。
翻过年头,连生的老母亲已经八十二岁。2018年春节回村,我在路口遇见她,确实已经十分衰老,枯瘦如柴,只有小小的脸盘上保留着些微红润。即便这样的年龄,在日上生活中,她依然坚强地自理着,所以连生看起来无所事事,似乎像是个多余的闲人,实际上他必须每天做饭,烧炕,处理类似的琐事。
父亲去世之前,连生夫妻一直在外打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护工,工资还不错。那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人生似乎也都在上升,过年回村,见人散烟点烟,高声说话,议论外面的动态和行情。
连生中断打工那年,大女儿刚考上大学,大儿子也已经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挣钱的事务,是万万不能中断的。然而,因受到父亲过世的影响,老母亲忽然病倒,身体状况很差,年后开春,连生无法出门,只能由四十多岁的妻子独自返回北京打工,继续在医院当护工。
原本,看母亲的状态,连生以为只需要在村里守候一年,然而母亲的身体却渐渐恢复过来。此后,连生也曾产生过重新出门打工的念头,但母亲的一次意外晕倒,打消了他的念头。他不敢把母亲独自留在家里。
连生守在村里的这七年,大女儿甚至已经读完了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连生考虑到妻子的负担太重,一度不愿意让女儿继续读书,但他的意见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妻子那时候虽然为难,却也支持女儿。事实上,对于这件事情,连生也没有发言权。于是,女儿读研的负担,大儿子读大学的负担,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去年,大女儿硕士毕业,连生建议她回到老家考公务员,以此缓解家庭的财务压力,女儿听了非常生气,因为按照她原本的计划,她是打算去新加坡留学的,她甚至已经申请了奖学金,这一次,连妻子也开始劝慰女儿,说,家里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实在无法支持她继续读书。
在父女争执的过程中,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女儿甚至指责连生作为一个男人毫无担当,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窝在村里混日子。连生知道,女儿的抱怨,其实也是妻子的抱怨,由于七年时间的漫长分居,夫妻之间的感情,实际上已经很冷淡了。以前过春节,连生盼着老婆孩子回家,但现在他反而很怕他们回家,他似乎已经无法承受那种吵闹和指责。
但连生还得继续下去,母亲年事越高,他越不能离开,曾在外打工二十多年的他,似乎已经习惯了乡村的日子,并且扮演红白喜事的重要劳力。春节过后,看着零零散散的青壮年出村务工,他站在路边,心情已近非常平静,对他而言,纠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三月的风刮来,整个高原都被刮得空荡荡的,春种前后,暖烘烘的阳光下,村子非常寂静。能行动的老人,都在自家地里忙乎,因此,偶尔,连生只会遇到另外两对老夫妻,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丈夫,用轮椅推着同样高龄的妻子,在白花花空荡荡的村路上散步,这两个坐在轮椅上的妇女,都是几年前突然中风瘫痪。
听说,姓杨的老汉在伺候得失去耐心的时候,也会咒骂抱怨:你生了那么多儿女,为啥每天烧炕做饭端屎端尿的是我?但是老太太已经基本不能言语。节后临走前,我听说,轮椅上的这位老太太,已经去世了。
连生说,春节后的二三月是最难熬的月份,草木由枯黄渐变为绿色,然而每天的日子特别漫长,连生也经常会倍感无聊,“无聊得人想上墙。”他笑着说。他平时很少与妻子儿女联系,按照他的说法,即使妻子电话打通了,也只是无休止的抱怨和吵闹,至于儿女,早已经与他没有共同语言,出于礼貌接通电话之后,只是哼哈两句。
今年春节,妻子回来了,按照连生的说法,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市里某得一份工作,算起来年龄也不小了,但没钱买房,婚事便无法提及。连生只能低头无语,坐在板凳上听着。妻子说,这个家快要散了。即使妻子说出这样的话,连生也只能低头无语,没有一句强辩,他知道,强辩没有任何意义,他当然很担心这个家真的散了。
作为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今年整个春节,许老先生似乎都满怀巨大的歉意。
许老先生家与我家对门。两年前,他看到我时,还跟我讨论一会儿国际时政,今年春节期间,我每天遇见他在院子门口挪动小步转来转去,顶着满头白发,低头不语,偶尔抬头跟我说话,只是长吁短叹。
腊月二十八,许老先生家里给长孙说亲事。这当然也是许老先生的一个重要心愿,他希望自己过世之前,至少看到一个孙子结婚。长孙二十三岁,虽然年龄不大,也该娶妻生子了。
说亲的气氛很热烈,但结局却是令人沮丧的。众人散去之后,许老先生来到我家院子,不断地叹息,女方的要求是:在市内买一套楼房,另外还要一辆十万左右的小轿车。如此算下来,结婚起码得近百万。
事实上,在乡村,许老先生家条件也算不错。他是一个退休老教师,一个月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因为有两个孙子,在镇子上也买了两院地方,这两院地方,就是为两个孙子结婚准备的,他原以为自家优势明显,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许老先生的妻子不到六十就生病去世,因此,孙子出生之后,他不得不协助照顾。照顾大孙子的时候还好,儿媳没有出外打工,情况要好一些。等大孙子长到五岁,二孙子出生,家庭矛盾不断升级,二孙子一岁半的时候,儿子儿媳一起出门打工,两个孩子就由许老先生一个人照顾了,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多年。

一个老头子在家独自带着两个孙子,艰难可想而知。我听我母亲曾经说过,小孙子两岁多的时候,许老先生带着孩子到自家地里干活儿,正午日晒,孩子饥饿焦渴,七十来岁的许老先生实在扛不住了,便在正午的烈日下,趴在亡妻长满荒草的坟头上放声大哭,鼻涕眼泪糊满了脸,路人看见,不禁心酸怜悯。
过了七十五岁,身体明显不行了,四十多岁的儿子便留在家里照顾老父,柴水米油盐,做饭,烧炕,洗衣服,扮演一个原本属于家庭妇女的角色。儿子脾气很温顺,虽然待在家里无聊苦闷,但极少与父亲顶嘴,每日耐心地做着这些琐碎的伙计。因为是少有的青壮年劳力,在二十多户人家的新农村居住区,他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义工。我每次回家,母亲经常对我感慨他的孝顺,说开口说话必先笑呵呵的,这便是养儿防老的眼前实证。

在许老先生看来,明显是自己拖累了儿子,使他不能出门打工赚钱,然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即便出门打工,要应付这么巨大的结婚成本,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许老先生的收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除买了两院地方之外,就全开销在照顾孙子上了,手里几乎没什么余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许老先生才知道儿媳出门打工的正确性及重要性。在我母亲看来,这位儿媳妇是个吃苦耐劳的贤妻典范,在外打工十几年,有钱只进不出,常年租住二三百的小屋子,生活用度极为节俭。十几年下来,少说也攒下五六十万元,按照两年前的行情,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今年春节,儿媳满怀希望回家过年,原本计划把自己大儿子的亲事确定下来,但说亲遭遇的现实,无疑又是当头一棒。
这个年过得并不喜庆,相互指责是在所难免了。媳妇埋怨的重点,是老公公和丈夫,在家没有把两个儿子教育好,弄得两个孩子很没出息,年后到了娘家,媳妇依然在对娘家人哭诉自己常年打工的委屈和婚姻市场的残酷。许老先生只能自责,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拖累儿子无法出门赚钱。
两年前,因堂弟结婚,我回过村里一次。在那次婚礼上,我见到了十几年不见的李老太。
尽管旁边的人解释说李老太已经痴呆,但她依然能认出我,坐在路边柴堆旁,没完没了地跟我说话。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我逐渐地感觉到,她确实已经痴呆。她一直在跟我絮叨自己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一家在北京打工二十年,女儿嫁到北京后,全家就几乎不再回家了;小儿子跟着媳妇做小生意,在邻近的县城买了房子,也常年在外不回家了,而丈夫去世已经五六年,只有李老太一个人依然住在破旧的窑庄院里。每月,由嫁在几十里外的女儿专门赶来给拉一趟水,生活其他方面,只能全靠她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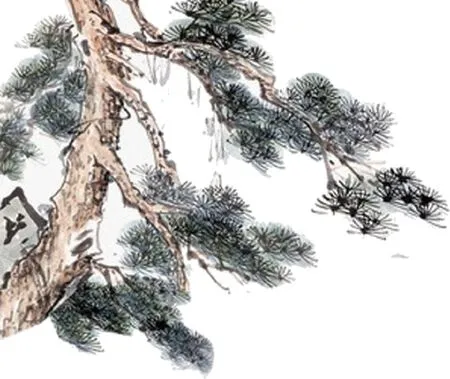
她当然很想两个儿子,尤其是大儿子。二十多年基本不回家的大儿子,成为她对外面世界的全部想象,在她的想象中,大儿子人生十分成功,日子过得金碧辉煌,成了永远的北京人,她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一直问我是不是能经常见到她的大儿子,我向她解释说,北京很大,一个人要见到另一个人,很不容易,况且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大儿子一家似乎在怀柔某个地方。但李老太坚持认为我能见到她五十多岁的大儿子,后来,我不得不谎称见过几次,确实过得相当成功,她很满意我的回答,并反复嘱咐我,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就找她大儿子。显然,相比之下,她认为小儿子不算太成功,因此,她也很少说到他。
在这些基本理智清醒的问答之后,李老太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的大儿子还会不会回来,我说,应该会回来的,李老太又一次笑了,说,我活着他不回来,我死了他肯定会回来埋我。我点了点头,在她的重复追问中,旁边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你不要跟她说话了,她已经傻了。
她确实已经老年痴呆,据说到了神鬼不分的地步,据村里人说,她经常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让迷信盛行的村人惊悚不已,有的人甚至因此相信她真的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今年春节回村,四婶举例说,李老太经常到她家来,让她感到害怕、不安,有一天,她忽然嚷嚷着走进院子,说是在找自己的婆婆,而她的婆婆已经死去二十多年,但她坚持自己的婆婆在四婶家串门。初二那天,我在村口的路上遇到了李老太的已经快五十岁的小儿子,他说,去年后季,老太太忽然一场急病,他赶回了村子,本以为她已经快不行了,但照料了几天之后,又渐渐恢复,看着老太太的样子,小儿子实在没法再离开了,只好带着孙女回村,照顾一老一小。
我问李老太的小儿子,老人高寿?他说,过年就七十二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阵苍老袭上了他的额头,这当然是一份尴尬和无奈,妻子是断然不会回来的,这意味着他在年近五十的时候,必须自然地接受分居生活。而看起来,他为此也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
南头村并不大,在村里,七十岁以上不能独立生活的老人,少说也有近二十个,有老伴相互协扶的要好一些,儿子还有在外打拼为孙子赚取婚用的机会,一旦孤寡,作为儿子,必须强行掉头回村。孝道的传承,在这个小村庄里以这样默默无闻的方式延续着,成为村子最珍贵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