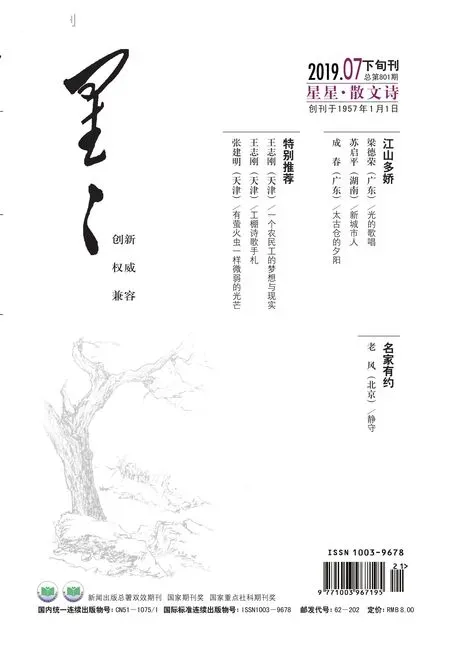有故事的人(组章)
徐 源(贵州)
掏 出
掏出牙缝里的菜丝,掏出喉头上的声音;
掏出衣袖中的尘埃,掏出关节间的火焰。
在下水道劳作的工人,从身子里掏出钳子、刀具及隐秘的生活。
他掏呀!掏呀!掏呀!掏出一根陈旧的电缆线,插在傍晚的太阳穴上。
在荒原般的城市,他多么努力,掏出了夜晚的灰烬,和人生的所有敬畏。
他掏出一日三餐,也掏出女儿的补课费;掏出老父亲的医药费,也掏出妻子的笑靥。
他掏出自尊,也掏出青春。
他从下水道里爬出,抹了一把汗。起伏的喘息,漫延远方。
放下那卷沉重的电缆线,背对城市,他悄悄掏出一撮泥土,和眼睛里温暖的河流。
补 碗
这活计已绝迹,如今谁还补碗?
天破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谁在乎?不是古董修复,我说的是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比如补盆、补锅、补衣服。
比如,半个世纪前,我还没出生,世界已喧杂,墙壁上写满口号,像着了魔一样,有人每天嚯嚯嚯地磨着阶级的阳光,有人却心如水平,把碗补得密而不漏。
碗在生活中,碗在神龛上;碗为瓷,也为梦。
山魈吹火虫入碗,碗被历史藏在衣襟下。
每一只碗,盛过沉默的五谷;每一只碗,盛着一段岁月。
我家一位老亲戚,曾当过十年补碗匠,变形的手指,十年后指向远方,怎么也伸不直。
送水工
他每次送水,都要感叹一句:这水,哪有农村的好。
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眶里荡漾一汪清澈的井水。
送一桶水,赚两元钱。他说,每天能送四五十桶,到了晚上,脚底板就火辣辣地痛。
这憨厚的送水工,我小学同窗。我从他身上的汗味里,闻到了泥土的味道。
他感恩这份艰苦的工作,而我总抱怨生活的细节。
他的背影,与我的虚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曾经暗恋过同一个女生,同一条道路,同一个贫穷的村庄。
许多年前,在夜晚,我们都是被月光镀亮的人。
造桥者
一千米之上,他被透视原理拉成一只鹰。小小的黑点,像烟头烙在蓝天上的一次心跳。
他必须小心,秋天来得太早。
被钢筋绞破的手指,显现出最后的金黄。
他的影子还要些许日子,再消瘦一点,才能延伸到河流的对岸。
这样的场景中,呼出的白气,证明冬天的属性。汗滴在一千米之下,吻着某颗鹅卵石。
否则,一条河流不会知道他的秘密。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所有规律,深信不疑。
否则,我们看到的流水,也不会因一个造桥者的理想,而执著、久远。
山村教师
有时,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有时,他用指头在生铁上写字。
光阴在发丝间变换颜色。三十年,他与这所小学的关系,就像声母与韵母的关系。
有时,他在教室里踱着步子;有时,他在生活中举步维艰。
梦想在旗帜上迎风飘荡。三十年,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像数字与公式的关系。
没有权位,出入不了庙堂之高;没有政绩,写进不了方志之远。
没有人为他塑像,而他的学生遍布天南地北。天南地北,都有他温暖的塑像。
哑 巴
孤老院的哑巴,每天吃过午饭之后,提着一根铁钩在大街小巷的垃圾里掏,他想把那些遗憾的都重新钩上来。他越钩,过去的事物就越深,他把卖垃圾换回的钱,一角两角存起来,从不用它们,谁也不知道,百年之后他想把它留给谁。
他是一道风景。他把所有语言,刻成了额上深深的皱纹,当他在黄昏踉跄着脚步走进幽静的孤老院,天空显得一片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