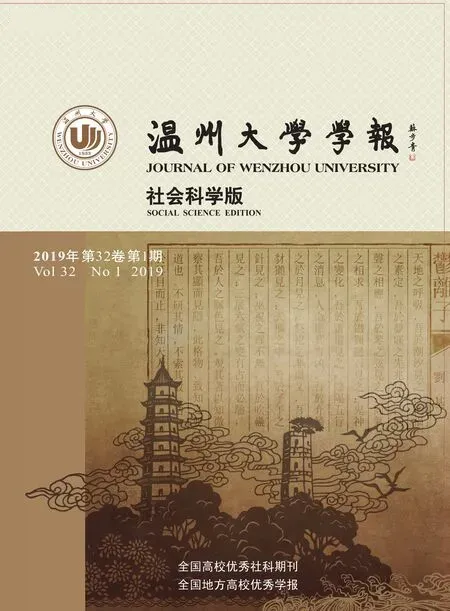“一本一稿”的《琵琶记》及其版本成因
王良成
(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05)
晚明藏书家陆贻典曾说,《琵琶记》虽然“刻者无虑百千家”,但它们的版本内容却是“几于一本一稿”①参见:陆贻典《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旧题校本琵琶记》,清康熙十三年陆贻典钞本。。《琵琶记》《荆钗记》《拜月亭》《南西厢记》等经典戏曲作品之所以“一本一稿”,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底本几乎都不是剧作家的原稿,而是当时不同的舞台演出脚本的整理稿。不同的出版商以不同的演出脚本的整理稿为底本,自然就形成了“一本一稿”的现象。
一、现存的《琵琶记》文本基本印证了“一本一稿”说
早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琵琶记》的版本数量就多达70余种[1]。此后,随着读者需求的增加与审美趣味的改变,各种内容不一,版式各异的《琵琶记》文本更是源源不断地被各地出版商梓行。直到清宣统二年,天一阁仍印行了5卷本的《琵琶记》。由此看来,陆贻典所说的“刻者无虑千百家”虽有夸张之处,却也基本符合实际。毕竟,无论从版本数量还是版本形态上来看,只有《西厢记》才能与之颉颃,其他戏曲都难以与其比肩。即使从现存的版本来看,举凡中国古代戏曲的各种版本体式,《琵琶记》都不包括。如白文本、插图本、朱墨套印本、巾箱本、校注释义本、评点本等。以上还仅仅是全本系统的版本形态,如果加上选本系统,《琵琶记》的版本形态堪称繁多。不过,陆贻典所说“几于一本一稿”并不是指《琵琶记》花式繁多的版本形态,而是说这些版本在内容上的不统一。虽然陆贻典经眼的《琵琶记》文本是否真的“几于一本一稿”,现已无从考知,但只要仔细比勘现存不同版本的《琵琶记》文本,不难发现,明刊《琵琶记》“几于一本一稿”的现象确实比较明显。即使明代的《六十种曲》本与新都黃正位所刊的巾箱本《琵琶记》在内容上看似一致,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本一稿”的现象。例如《六十种曲》本不仅忽略了各曲牌所属宫调的名称,而且将各个脚色的舞台提示“唱”与“云”一律简省,黄正位本不仅将上述忽略与简省逐一补足,而且在文字表述上也和前者略有差别。如第3出《牛氏规奴》之“知否,我为何不卷珠帘,独坐爱清幽”下的一句夹白,《六十种曲》本作“清幽,清幽,怎奈人愁!”而黄正位本则改“怎奈”为“争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正是这些的细微的差别导致了这两个版本之间“一本一稿”现象的形成。又如,明代继志斋刊刻的《重校琵琶记》,除了增加大量的评点内容,其正文和《六十种曲》本等差异性也很少。但只要仔细比勘,不难发现第3出《牛氏规奴》中【雁儿落】下面的一段宾白,继志斋本有1 175字,而《六十种曲》本却只有1 066字。此外,刊刻于明代中后期的“继志斋”本、“玩虎轩”本与金陵唐晟所刊的《琵琶记》不仅在曲白的内容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更在评点的内容上也迥然不同,因而属于较典型的“一本一稿”现象。
如果说只有通过仔细的比勘才能发现《六十种曲》本与黄正位本《琵琶记》之间的微小差别,那么,晚明凌濛初主持刊刻的朱墨套印本《凌刻臞仙本琵琶记》(以下简称“凌刻本”)与盘薖硕人(徐奋鹏)改订的《词坛清玩琵琶记》(以下简称“槃薖硕人本”)等,却能让一般读者即可轻易地得出“一本一稿”的结论。与《六十种曲》本等相比,“凌刻本”不仅对曲、白多有删改,而且还增出整整两折的剧情(第39折蔡伯喈、赵五娘和牛氏自京城返回陈留郡时蔡伯所唱的【中吕引子·菊花新】与【仙吕入双调过曲·朝元令】等5支曲子,以及第42折牛太师及从人前往陈留郡旌表蔡伯喈,途中驻跸一处驿站,从人索贿不得而刁难驿丞的滑稽情节)。另外,凌濛初认为他所刊刻的底本是明初宁献王朱权藏本,属于“元本”,而元本每一出都没有标目,因此“凌刻本”只用第1折、第2折等区分不同场次,并无标题。他说:“历查诸古曲,从无标目,其有标目者,如《末上开场》《伯喈庆寿》之类,皆后人讹增也。且时本亦互相异同,俱不甚雅,从臞仙本,不录。[2]”对于“凌刻本”与其他版本曲白的不同,凌濛初要么认为他的版本精良,要么认为是他精心校对的结果。如“【宝鼎现】系诗余名,今人改‘现’作‘儿’,误。时本‘巷’字下增‘里’字,‘最喜’下去‘得’字,‘似绣’改作‘如绣’,即非【宝鼎现】本调矣。”①参见:凌濛初《凌刻臞仙本琵琶记》第2折【双调引子·宝鼎现】处眉批,明末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难茂’即含下一子不忍遣求功名之意,时本作‘堪茂’,无解。‘芳年’先埋伏下‘早’字,今本作‘芳妍’,自称对‘荣秀’为工者,非。”②参见:凌濛初《凌刻臞仙本琵琶记》第2折“叹兰玉萧条……得早遂孙枝荣秀”处眉批。除上述差别之外,凌濛初还在眉批或夹批中不时将“凌刻本”与其他版本对比,指出时本、京本、徽本、浙本、闽本等错误既多,又内容各别。在这些眉批中,凌濛初虽然没有明确地将时本、京本、徽本等定义为“一本一稿”,但他却不经意地用事实验证了陆贻典的观点是正确的。对于“凌刻本”与其它版本之间之所以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凌濛初认为其是在颂正指误,读者应当以“凌刻本”为准,才不至于误入迷途,如“诸本少‘早晚’二字,调亦不全矣”③参见:凌濛初《凌刻臞仙本琵琶记》第5折“你爹娘早晚,早晚里吾当陪伴”处夹批。以及“诸本此词后妄增入姓字、问志等白,而反诡云古本所有,可恨。徽本又以《易》《书》《春秋》《礼记》为题各唱一曲,益可笑。”④参见:凌濛初《凌刻臞仙本琵琶记》第7折【仙吕过曲·甘州歌】“数声啼鸟不堪闻”处眉批。当然,无论“凌刻本”是否最接近剧作家的原创,无论徽本是否“妄增入姓字、问志等白”,“凌刻本”把《六十种曲》等多数版本第7出中唯一且机趣横生的一段680余字的宾白,缩减为索然无味的区区50余字,用事实凸显了“一本一稿”的特质。这种特质也造成了其他版本该出的剧情戏味十足,近乎一支接着一支曲子连唱的“凌刻本”场面却非常清冷。不仅第7折,只要是大段的插科打诨或展现热闹场景的宾白,“凌刻本”差不多都大幅度删减,因而和多数版本迥然有别,故而同为舞台演出本,“凌刻本”的戏味明显比《六十种曲》本等淡了许多。
盘薖硕人本对剧情增、删的程度比“凌刻本”有过之而去不及,是“现存的全本《琵琶记》中,对元本改动最大的一种版本”[3]39。在其他版本中大同小异的曲词和宾白方面,盘薖硕人要么“订曲改白”,要么“改曲增白”,要么干脆“改曲增曲换局又增白”,就连深受读者的“吃糠”、“尝药”“遗嘱”等剧情也一并删去。除了伤筋动骨式的删减,槃薖硕人还像“凌刻本”一样,适度补充一些看似合理的剧情。甚至连一般读者根本不会深究的细枝末节,他也一律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分别予以改正。如“如牛相招婿处,曰‘奉旨招婿’,曰‘官媒议婚’,曰‘激怒当朝’,曰‘金闺愁配’,元本于此何其多事也?且其中词调亦觉散赘,无甚雅致。裁而合之……里正之为赵女扼也,拐儿之为蔡生诳也,虽系打诨,实乃关情。但里正之家宜饿死,拐儿之身宜雷击,必增设此端,方见天理之报,而可以为作恶者之警。”①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改琵琶定议》,明刊本。对于删改的原因,他也一一予以解释。“饥荒困饿,至于双亲以咽糠毙,此岂人心所乐见者?予自孩年闻此,即切齿有恨于蔡中郎,故兹苦情酸态,不忍著于笔端,虽东嘉体极到处,而即擅删之,亦自觉其为宜者。”②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改琵琶定议》,明刊本。对于为什么要增出《沿途苦棲》以及“嘱杖”等内容,槃薖硕人认为“赵女携真容、弹琵琶往京寻夫,此传中大关会处也。而元本于此只草草着【月儿高】三套语,何其太简耶?!且曩出时所撰琵琶之曲谓何的?宜增之以见路途所历尽苦情也。”③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改琵琶定议》,明刊本。“增‘嘱杖’以了前张公受杖之案,且见存先人遗嘱,而死者不可欺也。又增‘立碑书字’等意,则大有意义存焉。……兹借张公之口以规蔡君,料蔡君无辞也。”④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尾批》,明刊本。至于改“状元”为“学士”与“订曲改白”等原因,槃薖硕人的理由更是非常充分,他说:“既托为蔡邕事,既当论邕之世。邕处汉末,无制科词场之事,无状元之名,今改以四科显达,承谟制也;而易状元为学士”;⑤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改琵琶定议》,明刊本。“诸本皆云‘孝矣伯皆’,邕岂能当得?今改‘惨矣伯皆’”;⑥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伯皆总题》“惨矣伯皆”处眉批。“京本作‘桂花堪茂’,与上句意不贯。闽本作‘难茂’,大死煞了。今改作‘期茂’,得之。”⑦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高堂祝寿》“一朵桂花期茂”处眉批。
和全本戏相比,零出戏曲选本中所刊载的《琵琶记》更具“一本一稿”的特征。从现存数十种收录《琵琶记》的选本来看,各折子戏再现的内容不仅与全本戏的相应场次差别较大,即使同一名目的折子戏,也因不同的选本而呈现出不同的剧情。无论《乐府红珊》《词林一枝》还是其它戏曲选本,其中的《琵琶记》折子戏不仅与全本戏中的相应场次迥然不同,甚至不同选本中同一场次的折子戏也鲜明有别。例如,《乐府红珊》和《词林一枝》都选录了《赵五娘描画真容》,但这两个折子戏在内容上还是差别明显。
【驻马听】(旦)两月优游,三五年来都是愁。自从我儿夫去后,望断长安,两泪交流。饥荒年岁度春秋,两人雪鬓庞儿瘦。常想在心头,常锁在眉头,教奴家怎画得欢容笑口?——《乐府红珊》本
【驻马听】两月优游,三五年来都是愁。自从我儿夫去后,望断长安,两泪交流。自我丈夫离家之后,三载连遇饥荒。饥荒年岁度春秋,两人雪鬓庞儿瘦。常想在心头,常锁在眉头。教奴家怎画得容颜依旧。公婆呵,在生时节,终日思虑孩儿不回,又且遭此饥馑年岁,度日如年。教奴家怎画得欢容笑口?——《词林一枝》本
除了增、删或改易曲白,《风月锦囊》同样通过整合关目——剧情,把42出的全本《琵琶记》缩减为34折的小本戏。《乐府玉树英》本则增加了《书馆托梦》1折,《乐府红珊》《大明天下春》等在《赵五娘描画真容》中增加了一段的《琵琶词》。另外,和其他选本采用官话不同,《缀白裘》则将宾白改为吴语;这些都明显体现了“一本一稿”的特质。
综上所述,陆贻典的《琵琶记》“几于一本一稿”说虽不免夸张,但却也基本符合实情,其正确性至少在现存的各种明刊全本以及几乎全部选本中都得到了印证。
二、现存的《琵琶记》文本几乎都是不同时地舞台演出本的整理稿
现存的《琵琶记》文本几乎都是舞台演出脚的整理稿本,这一看似武断的结论,同样也可以通过现存的《琵琶记》文本得到证实,如刊刻于明末的著名戏曲选集《六十种曲》,其所有剧本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较强的舞台性,而且还被出版方直接冠以“绣刻演剧”之名。显然,包括《琵琶记》在内的这60种剧作文本就是当时或此前的舞台演出脚本。又如,“凌刻本”虽然和当时的时本、京本、昆本、浙本、徽本等有着较大的不同,但它并不是剧作家的原稿,而是明初《琵琶记》演出脚本的整理稿。这既可以从凌蒙初不断将“凌刻本”与时本、京本、昆本等舞台演出本反复比较可见端倪,更可以从“凌刻本”的眉批和夹批不断指出时本、京本、昆本等演出失误得到证明。例如,“俗本此处旦挂真容礼拜,而增一【赏秋月】曲云:“在途路,历尽多辛苦。把公婆魂魄来超度,焚香礼拜祈回护,愿相逢我丈夫。”且批云:“无此,觉挂真容时冷淡。不知古本只有落真容,无挂真容也。若挂,则岂遽落哉?”①参见:凌濛初《凌刻臞仙本琵琶记》第33折“【中吕过曲·缕缕金】时不利”处眉批,明末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即使槃薖硕人改定的《词坛清玩琵琶记》,也绝不是仅仅为了案头阅读,它同样本着为舞台演出服务的目的,因此完全可以将这个版本视为当时的舞台演出脚本。毕竟,“清玩”一方面可以指案头阅读剧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指“清唱”,而“清唱”虽然是非舞台性的演唱,但这种自娱自乐性质的演唱有时却比商业化的舞台性演出要求更高。另外,姑且不论《词坛清玩琵琶记》在整合、改削等方法上和当时的各种舞台演出本特别是折子戏演出本大同小异,就连槃薖硕人也明确指出这个整合、删改本其实也有为舞台演出提供脚本的目的。如“古本拐儿并不曾有名字,正见俗家演场有马扁八之名,今从俗以便观场者。”②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思亲觅寄》“小子姓馬,賤名扁人”处眉批,明刊本。“原本‘咽糠’‘尝药’二出非不见作者之情,至动观者之必伤。第世间学演梨园多是华堂乐事,而双亲继没已为太惨,况又以咽糠亡乎?今俱存而不论,止于‘祝发’出内旦白表出公婆继没缘故。若观者必欲求备,则自有东嘉原本在,可寻而演也。”③参见:槃薖硕人《词坛清玩琵琶记·祝发葬亲》标目处眉批,明刊本。其他诸如《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以下简称“巾箱本”)《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等,虽然是标准的案头读本,但它们的主要内容却与《六十种曲》本等相差无几,其底本同样可以视为某个时期的舞台演出脚本的整理稿。不仅《琵琶记》,《荆钗记》《拜月亭》《白兔记》《南西厢记》等南戏的现存版本,也都是以各种不同演出本为底本,因此都属于是不折不扣的舞台演出脚本。如《南西厢记》就是李日华等人将王实甫的北曲《西厢记》翻改为南调,以适应当时昆腔演出的实际需要。随着《南西厢记》在舞台上的风行,出版商们便纷纷刊刻这些经过不同演出团体改削后的舞台脚本。
与全本戏相比,刊刻于明清时期的各种零出戏曲选本完全是当时各种折子戏舞台演出脚本的选编。郑振铎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说:“我们在这些选本中,便可以看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于剧场上的剧本,究竟有多少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更可以知道‘究竟某一种传奇中最常为伶人演唱者是那几出’。”[4]朱崇志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戏曲选本即为戏曲舞台传播实况的文字载体”[5]。不仅如此,零出选本的发生、发展轨迹也基本吻合了折子戏的发生、发展轨迹。如折子戏大约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当时的舞台上,而最早的零出选本也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折子戏繁荣于明代万历年间及以后,零出选本的刊刻也在这个时段最繁盛。另外,由于折子戏的体制短小,用时较少,因而一场常规的演出时段中不仅可以上演两个以上的折子戏,而且这些折子戏还可以分属不同剧作。零出选本也仿效这种体例,在同一部作品集中选刊南戏、杂剧、传奇等不同戏曲形式的折子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刊刻于清代的《审音鉴古录》不仅有明确而详细的舞台提示,而且它还将演员的穿着与扮相一一予以规定。如在《琵琶记·嘱别》中,剧本不仅提示“正旦黑紬袄上”,又在眉批中特别说明“赵氏五娘正媚芳年,娇羞□忍,莫犯妖艳态度”[6]37。需要说明的是,由“俗作‘卖了’,非”[6]69与“俗将此白移在前”[6]82等眉批或夹批中的内容来看,《审音鉴古录》所收录的折子戏从表面上看是改编者在演出前的规划,事实上,它们都是根据当时舞台演出的经验而整理出来的舞台范本,因而它们属于典型的舞台演出脚本。既有他人直观的舞台演出为参照,又有《审音鉴古录》之类的文本为规范,因此,只要依样画葫芦,稍有专业素养的演员便可以将类似零出选本中的折子戏搬上舞台。《乐府玉树英》《大明春》以及《缀白裘》等刊刻于明清不同时期的零出选本,在舞台提示与规范上虽不如《审音鉴古录》详细明确,但对于当时经常观看舞台演出的读者来说,后者的很多提示与规范有可能是画蛇添足。当然,即使没有那么多舞台提示和规范,也不能改变这些零出选本就是舞台脚本的事实,例如“《缀白裘》所收的戏曲,都是当时戏台上通行的本子,都是排演和演唱的内行修改过的本子”[7]。
三、“一本一稿”的形成原因
在明清两代漫长的刊刻过程中,《琵琶记》之所以形成了“几于一本一稿”的现象,显然不是刊刻者的失误,而是不同的出版商采用不同底本的结果。更为关键的是,几乎所有出版商都无缘剧作家的原稿,他们只能不得已地选择各自满意的舞台演出脚本为底本。从表面上看,不同版本的《琵琶记》在内容上的差异源于案头接受后的读者反馈,但事实上,它们却主要是不同剧种、不同戏班根据观众的反馈,然后不断二度创作而衍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刚刚上演的剧作,越是接近剧作家的原创。如果采用这时舞台演出的脚本为底本,相信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性会很小,从而很难出现“一本一稿”的现象。如“巾箱本”虽然经过明人的初步加工,但它还是和最接近剧作家原创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以下简称“陆钞本”)之间差别很小。即使在文献价值上,“巾箱本”也和“陆钞本”相差无几。对此,钱南扬先生曾有明确的辨证:“两本(陆钞本和巾箱本)……和《戏文三种》有同样的价值,使我们得以认识戏文的真面目。”[8]在版本分类上,“陆钞本”和“巾箱本”都属于古本系统;而从这两个版本的底本看,它们应当是《琵琶记》在同一时段甚至是同一区域舞台演出的脚本。
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以及时空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观众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反馈他们的审美诉求,而多数戏班往往会根据这些诉求适当地调整演出内容。由于不同观众有着不同的审美诉求,特别是不同地域或不同剧种的观众,其审美诉求更是相差很大。有些观众乐于欣赏戏曲之曲的妙味,有些观众更喜欢戏曲之戏的机趣,对此,各演出团体往往通过增、删曲词或宾白的方式来满足观众的整体需求。如果以这个时段的舞台演出脚本为底本,各版本之间的差异性显然会越来越大,如以古本乃至元本自居的“凌刻本”,便在内容上与“巾箱本”与“陆钞本”差别很大。虽然都有牛太师及从人前往陈留郡旌表蔡伯喈,途中驻跸一处驿站的一出剧情,但“陆钞本”并无“凌刻本”第三十九折内容。另外,为了迎合当时读者,“凌刻本”又补充了原本可能不存在的内容。如“《考试》一折,古本所无。……人既习见,恐反疑失漏者,则附之末帙”[3]328就是如此。即使在宾白方面,“凌刻本”与“陆钞本”之间的也有明显的差异。如在第5出【忒忒令】中,当赵五娘挖苦蔡伯喈“学疏才浅”以及忘记《孝经》《曲礼》时,多数版本均有蔡伯喈自我辩解的两处夹白。“凌刻本”的夹白分别是:“(生白)我学也不疎,才也不浅。”“(生白)那见忘了?”而“陆钞本”则为“(生白)我不曾才短。”“(生白)我不曾忘了。(旦白)你身曾忘了。”虽然“凌刻本”与“陆钞本”的一些宾白基本相同,但“陆钞本”也比“凌刻本”更具口语化的特征,如在第2折【宝鼎现】下面的宾白中,“陆钞本”作“孩儿要与爹妈称庆歇子”,而“凌刻本”则作“孩儿要与爹妈称庆则个”。另外,戏曲虽然是“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9],但多数文人剧作家创作的曲词仍然不免过于典雅,致使文化素养较差的观众无法确切理解大部分曲词的意思。对于这部分观众来说,青阳腔、弋阳腔、太平腔等普遍采用的滚唱等方式就成了不错的选择。所谓滚唱,就是在曲词前后或中间增加一些口语化的韵文或念白,从而使典雅、艰涩的曲词通俗易懂。例如,明代黄文华选辑的《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蔡伯皆中秋赏月》之“【念奴娇序】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生)夫人,可爱甚的儿来?(贴)可爱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全无半点纤凝。正是:月明银汉三千户,人醉金风十二楼。十二栏杆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相公,月明风清,如此良夜,怎不开怀畅饮?正是:西风吹散碧云天,近水楼台得月先。尘世难逢开口笑,良宵莫负遂心年。人生几见此佳景”便是滚唱的一种,显然,如果出版商采用青阳腔、弋阳腔、太平腔等演出本为底本,它们的文本内容必然与以典雅有致的昆曲演出本迥然不同,从而导致这些版本“几于一本一稿”。
和全本戏相比,选本系统的《琵琶记》无疑最具“一本一稿”的特质。由于刊刻于明清时期的各种戏曲选本均为当时流行于舞台上的折子戏选编,而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声腔搬演的折子戏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如果出版商采用不同舞台演出脚本的整理稿为底本,它们的文本内容也因此不同。只要稍加比勘现存各种零出选本所刊载的《琵琶记》,不难发现这些折子戏对原作的改易情况有时比《词坛清玩琵琶记》更甚。除了增、删或改易曲白等细枝末节,《风月锦囊》同样通过整合关目剧情,把42出的全本《琵琶记》缩减为34折的小本戏。《乐府玉树英》本则增加了《书馆托梦》一折,《乐府红珊》《大明天下春》在《赵五娘描画真容》中分别增加了大段的《琵琶词》。另外,为了满足文人受众对曲词的偏嗜,《南北词广韵选》《南音三籁》《词林逸响》等刊刻于明清时期的零出戏曲选本甚至舍弃宾白,只收录曲词。虽然《南北词广韵选》等选本中曲词与《乐府玉树英》等选本内容近乎一致,但前者基本属于零曲清唱的范畴,后者却是曲词与宾白完整的折子戏,因而这两类选本明显呈现了“一本一稿”的特征。即使是同为仅仅收录曲词的《词林逸响》和《南北词广韵选》,前者也因为并未注明各自曲牌的所属宫调,同样较明显地凸显了两者之间“一本一稿”的特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南北词广韵选》和《南音三籁》虽然在曲牌前都标注了所属的宫调名称,而且同一曲牌的曲词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但因为前者既简省了全部折子戏的题名,又在曲牌的数量上与后者并不一致,因而仍未脱离“一本一稿”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折子戏的逐渐繁荣,全本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及以后时代,随着昆曲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逐渐不敌花部地方戏而最终衰落,全本《琵琶记》也因此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舞台空间。于是,受众往往只能通过案头阅读才得以欣赏《琵琶记》的全部剧情。另外,由于当时全本戏舞台演出脚本的匮乏,清代的出版商便不得不从明刊本中选择底本覆刻,这就使清代的各种全本《琵琶记》很少有“一本一稿”的版本形态。虽然毛声山通过系统、缜密的评点,使《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与明代的各种《琵琶记》区别开来,但毛声山的评点本在清代非常流行,映秀堂、天籁堂、书林龙文堂等先后覆刻,在现存清人的11种版本中,评点本占6种,且全为毛声山的评点本。至此,明代习见的“一本一稿”现象近乎终结。不过,全本《琵琶记》“一本一稿”的现象虽然在清代中后期基本终结,但选本系统《琵琶记》却因为其折子戏不断被搬演而不断被“排演和演唱的内行修改”,从而将“一本一稿”的现象一直绵延至今,如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与浙江省文化局戏剧处于1958年编印、现藏浙江图书馆的内部资料《浙江省戏曲传统剧目汇编》(第75集)中,收录了苏剧《琵琶记》的《汤药》《遗嘱》两个折子戏。如果将它们与昆曲等其它声腔的折子戏对比,这两个折子戏依然具有明显的“一本一稿”特质。即使是同为昆曲折子戏,现藏浙江图书馆,由晚清丙子年无名氏抄录的《弥陀寺》,虽然在曲白风格上近似《缀白裘》,但却在内容上与现存所有《琵琶记》的折子戏刻本差别很大,仍然明显地呈现了“一本一稿”的特征。
四、余论:“一本一稿”是多数舞台经典剧作的共同文本特征
陆贻典所说的“一本一稿”现象,不仅明显体现在《琵琶记》文本中,凡是在剧本刊刻之时仍在舞台上风行的其他南戏、杂剧、传奇等经典作品也大多如此。和《琵琶记》一样,这种现象同样是不同时地的出版商采用某一作品不同舞台演出脚本为底本的缘故。另外,从《琵琶记》等作品所呈现的“一本一稿”现象,似乎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的南戏剧本几乎都不是剧作家的原稿,而是后世的舞台演出脚本。这些剧作的版本和发行数量也和它们在当时舞台上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成正比,越是舞台上的经典,其版本和发行数量越多;反之亦然。全本戏的刊刻如此,选本中的折子戏刊刻亦同样如此。最后,现当代同一部当代舞台或影视艺术作品的文本,只要不同出版社采用不同出品方的演出脚本为底本,它们在内容上也往往呈现“一本一稿”的特质。这可能是为什么对于“一本一稿”的刊刻或传抄现象,陆贻典及同时代的学者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后世学者也鲜有探究的最主要原因。或许,类似的现象本来就是一个无需解释的常态。
——《日知录》陈澧批语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