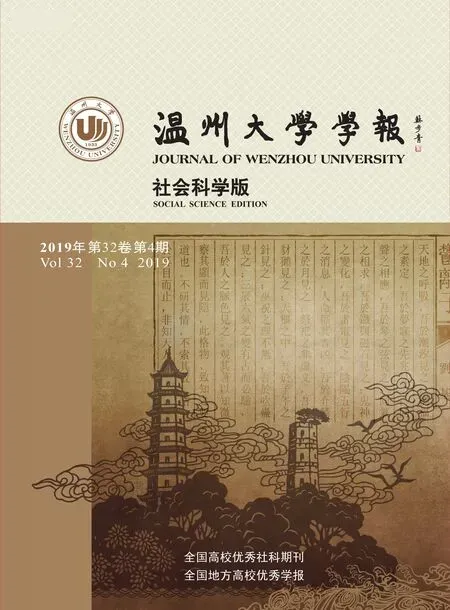乡土文学的新向度:历史大潮下的多视角叙述
——鲁迅、琦君的乡土情怀书写与时代印记
薛熹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还乡”是人类普遍的情感,这种情感会随着时间和现实的更迭而变得愈发强烈,甚至转化为一种对生命的执著。20世纪20年代,家国动荡、黎民颠沛,无论是生于大陆的启蒙者,还是对失去家园而流寓台湾的作家而言,将其内心对故土的愿念化为涓涓文字,这不仅能慰藉个人内心的空寂,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更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
一、情感的纠缠:对乡土世界的现代性建构
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1]“乡土”,是一个对于大多数文学实践者都充满情感的话题。它不只是灵感的家园,更是情感与现实无限纠缠的焦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普通人在异乡的成长经历,总伴随着些不平、疏离和无可奈何。于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故乡风土的怀念,与各种情感相互混合,便产生了各种难以用语言和文章诉说的情愫。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乡土文学”一语最先引入中国文坛始于周作人。他在1910年翻译匈牙利作家育凯摩尔的《黄蔷薇》中写到:“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2]然而,最先把“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看待的,则始于鲁迅。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对“乡土文学”及部分作家做过相关论述: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Brandes G)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3]
在这段论述中,鲁迅并没有详细解释“乡土文学”的定义。但是这些文学实践者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来北京求学或者迫于生计来京谋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描绘了时代大潮下的社会民情,并借此体现了作者对国民性的自觉探索,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废名、台静农等都曾在北京大学读书或旁听。他们以启蒙主义的乡土思想,借由对故乡深深的怀念,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情怀。
情感的纠缠,源于往昔与今日的巨大反差。与清末民初的小说相比,“五四”时期的作家更加突出现代主体性视野,特别是在各种文学的想象中,对乡土中国的想象无疑最能体现现代性话语实践的特征。鲁迅、郭沫若、茅盾、废名、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孙犁等,都深刻地书写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或者进一步探索乡土世界进入现代性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在鲁迅的《故乡》中,叙述者“我”以知识者的身份回到故乡,并通过叙述故乡而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首先,“我”是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眼光观察、评价故乡。在小说中,鲁迅描写闰土月夜手捏一把钢叉刺猹的场面,表现他的聪明伶俐的一面。然而,随着农村社会日益破败,闰土的生活也变得贫乏困顿。多年后,“我”童年的伙伴闰土不仅不能用“平等”的态度与“我”建立关系,且其也失去了表述自我价值的能力。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文学实践者们,内心深知“回到过去”早已成为一种奢望,他们唯有通过描述、批判、反思等方式重构内心的乡土世界,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启蒙主体身份,找寻内心的平衡与慰藉:
《故乡》本来是一篇具有悲剧品格的小说,因为它表现的是故乡的衰败与西瓜土地上银项圈小英雄的毁灭——毁灭于木偶人般的中年农民形象之中。如果说闰土由少年英雄向木偶人的转变是个悲剧,那么由木偶人向小偷的转变则是更深意义上的悲剧。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更深意义上的悲剧存在,“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才那样决绝、悲凉:“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4]
情感的纠缠,根治于理想与现实的分离。在文学创作者眼中,“乡土”往往与诗意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但是物质和诗意的分离,必然导致现实生活与诗意的分离。于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生存,似乎变成了一个被迫远离诗意的过程,即在创作者迫于种种原因选择离开时,“乡土”似乎成为必须舍去的东西,其赋予人的诗意化的生命体验也将无可挽救地沦为越来越遥远而模糊的记忆。文学实践者对都市的描写,经常谈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对都市生活的向往与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经历的留恋与否定。两者孰轻孰重?在他们内心斗争得尤为剧烈。新事物对旧有价值的无情冲刷,使他们必须更细致地去处理传统家园与新生活的矛盾。不难看出,“五四”时期的作家,似乎更能揭示“乡土情结”这种令人留恋并产生悲剧情怀的现代特征与时代风气。他们在反感和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经验虚构了一个“乡土”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里,乡土文学是一种新形式,其负载着作家的内心冲突,反映着“异变”中的乡土世界。他们“恋乡”-“厌乡”-“归乡”-“弃乡”,也代表其心理层面上远离和趋近乡土。由此观之,鲁迅的“离乡”与“还乡”,其实是伴随着作者内心纠缠和陌生感,他转而以一个初见者的身份,观察、描述那些曾十分熟悉的乡土事物,重新使自我与乡土世界建立一个互相对话的关系。
综上所述,鲁迅多站在启蒙立场以批判的眼光打量故乡,但却不缺乏依恋故土的情怀。鲁迅的“乡愁”意识是一种情感的纠缠,即为理想不能实现的人生价值寻找心灵归宿,以及更深层次地审视人的本质意义及终极目的。他从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角度突出了乡土社会的危机,这与家园、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都有密切联系。换言之,当鲁迅的思想状态和现实生活不相协调时,所谓“乌托邦”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种不能实现的思想世界。然而,鲁迅把他的痛苦与他人的喜怒哀乐及现存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起来,在自己生活的框架中显示出来所有不可实现的思想的乌托邦[5]。那么,也可以说,鲁迅笔下的“乡愁”更倾向于精神层面。
二、“乡愁”的温暖: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怀
作家的情感世界、人际关系、物质生活,同乡土、家园不可分割,这使作家对乡土更容易建立完整的价值观念[6]。以台湾的女性文学创作者观之,上世纪5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台湾女作家,多是在40年代末赴台的。当时台湾经济与民生凋敝,依靠写作是无法为生的,因此这些大陆籍文人都为生计而操劳,从事其它行业。虽然未完全弃笔,但是大部分作家视写作为副业[7]。对于那些生于大陆的台湾女作家而言,由于“根”不在台湾,她们便以“外省人”的身份,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丰富的感性来抒发离家漂流的困境,逼真地呈现了她们自身的生活信仰。他们笔下的“乡愁情结”在游子思想的基础上,还折射出一种离别故土的重重忧患,以及面对迁入地复杂人情世故未知的恐慌,更表达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温暖的人文关怀。
每每谈到台湾女作家,总会想到一个名字——琦君。就“乡愁”的抒写来说,琦君笔下故乡风土人情虽不新颖,但表现出的却是纯正的中国式的情感。她从大陆、台湾、美国三地生活过的亲身体验中揭示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及城乡之间的隔阂。如此情况下,最要命的是,她在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对比中,发现人们看不出各自的丑陋和优美之处,便产生了彷徨、矛盾与痛苦的心理,于是,她们便心甘情愿夹杂于两种主流文化的中间,而这种“消极”与“堕落”,只能使她们永远处于无家可归的荒凉之中:
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对长辈杖履追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年老人,第一是身体健康,吃得下,睡得着,做得动,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辈。不然的话,你会感到无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8]
到台湾之初,我化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记得当我拿到银楼去换现款的时候,竟是一点感触也没有,难道是离乱丧亡,已使此心麻木不仁了?[9]
因此,“乡愁文学”虽源于“乡土”题材,但最终分离而出,为大众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时代发展和受众内心寻求的必然体现:
当代台湾乡愁文学的勃兴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由于现实的因素刺激的结果。1949年200多万大陆军民被国民党政权挟往孤岛。这些人背井离乡,痛别亲朋,流落到着陌生而不安的南国一隅。本来,他们忽忽而来,并无长期定居的思想准备,而当朝鲜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又彻底破产。这样,他们梦寐以求的重回故乡的希望也随之幻灭。“老家回去不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无限”的焦灼,使他们普遍患了“怀乡病”。这样乡愁文学便应运而生。它是台湾同胞渴望回归故里,思念落叶归根的强韧观念的一种反应。这种文学对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的心理和困境有重要价值。[10]
过去,人们的关注点大部分停留在作者热情叙事的怀旧情绪和文化认同,但是对作者叙事中包含的女性意识却被忽略了。仔细分析起来,琦君始终以回忆的笔调书写温州的故事,也可以代表从大陆赴台无数人的乡恋情怀。虽然这一类文学的主题大多带着感伤情调和悲剧色彩,但是琦君则将“乡土”中国的人伦道德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动力。这种叙述已不再是简单的倾诉与宣泄,与此相反,更多包含了社会文化、社会阶层与个体身份的转移,以及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心理认同与排斥等诸多可能性。琦君身处于工业化的台湾工商社会,她亲眼目睹了新思想、新道德包括新的人际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性的变异。引人注目的是,她在作品中亦努力表达出了女性自己的人生。面对历史的新陈代谢,琦君看到女性的悲剧常常被女性误解。为了反映这种思想,琦君借助于新旧“女性”的视角来侧面叙述故事,常常由眼前的景联系到故乡的情。琦君作为一个人类命运的探索者,投入故事的方式凸显出女性主体的声音,这不仅加强了叙述的真实度,而且使得其创作更增添了许多温情色彩。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琦君为代表的台湾女作家,虽然没有生活于高度个性化的时代,但她们仍以敏感而多思的个体,从日常生活的体验出发,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中女性“尴尬”的处境与生活的艰难,从而反思在一切权力由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女性被扭曲和践踏的社会根源,凸显了对女性以及普通大众命运深切关怀。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基于性别经验的时代书写
乡土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颇受关注。她们借助女性独有的视角,书写了中国传统女性所经历的种种不公、歧视与苦痛,折射出乡土世界中女性地位的变迁,使其作品拥有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三纲五常”“节烈”“孝道”是早已被制度化的。这在现实生活中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痛苦,甚至剥夺了无数妇女的生命。纵观鲁迅的作品,从其留学归国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之节烈观》起,便表现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创作中,鲁迅聚焦现实人生中女性的受难与死亡,他用血与泪的笔墨再现了女性的悲惨命运,塑造了旧中国的女性形象。《祝福》的祥林嫂、《明天》的单四嫂子、《离婚》的爱姑等,鲁迅笔下的旧中国女性大多丧失了自我独立的思考能力,安于现状。“是一个性别压迫的漫长的社会化过程,致使妇女渐渐丧失了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当这种压迫经过若干代演化最终成为心灵上的桎梏之后,女性精神与心理的畸形,也就不可避免了”[11]。然而在现实中,随着现代化语境的不断延伸,女性作家们开始强调性别平等,表面上亦不再将女性当作“第二性”,但是男权社会下的性别歧视毕竟难以从根源上消除,性别差异本身便是客观事实,它对每名女性的正常生活,甚至命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琦君早年经历过家庭变故与战争带来的伤痛,于是其将奶奶、母亲甚至妻妾们的故事写入自己的作品中。她们虽然对性别的不平意识始终提出疑问,但是无法处理爱情、婚姻等事物,那是一种孤立的抵抗。怨恨归于怨恨,但最终还是依附于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从“五四”到现在,追求妇女解放、女权主义和自由的爱情被视为一种自我独立人格的完成。正如黄子平所言,当异性间的爱情承担着向礼教宣战重大责任时,它便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12],唯独不是爱情本身。于是书写者尽管站在女性的立场,但是并没有把男性改为“他者”的写作意识。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以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能力的评判取代了女性自身的感觉,这就造成了女性身体和价值标准的分裂。通过研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琦君在《橘子红了》一书中,已经敏锐捕捉到了女性价值标准的混乱。作品以16岁的秀娟为视角,讲述了在城里做当官的大伯娶了交际花为二房,从此大妈在乡下守活寡的故事。因为大伯娶的二房无子,一向作为贤妻良母的大妈,自作主张替大伯再娶了比他少18岁的贫家女秀芬作为生育工具。大伯回乡匆匆与秀芬圆房之后,又赶回城里,从此以后秀芬就成了弃妇。最后,秀芬在哀愁与恐慌中小产而死。因为后面也有相关的在琦君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在传统观念与严酷的现实面前日益觉醒,她们逐渐认识到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被统治地位。为了颠覆男性视角的权力话语,建立女性自己的发声方式,作者将清醒后的痛苦与混沌时的安好进行了深刻比对。在琦君笔下,爱情是人生的要义,透过爱情看人生,爱情便不再可靠,也正是在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里,作者挖掘出女性命运的不幸:
“女人家的命就是捏在男人手里,嫁个有良心的男人,命就好,嫁个坏良心的,命就苦。我想你们大户人家的男人总是好的,做小有什么要紧?……因此我只好一心一意地生孩子,等他回来,等孩子长大了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哪里想到胎会掉,他也不再理我了!”[13]
受博爱观念的影响,琦君的作品投射出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女性特有的感知经验。对此,徐学曾给予肯定:“琦君不是哲学家,也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她的人生观,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期中,她受到过中国传统道德的熏陶,也刻下了佛家、基督教‘爱’的哲学的印记。无论她所接受的这些思想是进步或落后的,在她只是一种信仰,其作用只是用来支持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维系一种对人性完美发展的方式追求她的思想资源。”[14]纵观琦君的作品,其女性角色在经历各种风雨之后,明白了所谓的爱情和人生,最终都不过是一场空。所谓情战的胜利,其结果多是沉沦于人生的苦海,淹没了自己的目标与志向,便满足了男性的利己心。对此,鲁迅曾说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5]女人的这种“三性”是被迫的,绝非她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对于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问题,中外许多有识之士进行过深入地研究。在著作《第二性》中,波伏瓦也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6]
在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现实中的女性,面对着生育、家务、劳动、礼教等方面的专制束缚,往往处于自我压抑之中,这意味着女性生命之痛的开始。女性,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17]。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现实生活中,受传统礼教压迫的中国女性总处在纠葛与压抑之中。作为社会个体,她们往往成为单纯的个人化的、欲望化的对象。正因如此,她们的命运更显得悲凉,然而她们却把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和伤痛的责任归于女人本身,并把痛苦不断转移,代代相传,或许这才是琦君所表达的更深层悲剧[18]。
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反思乡土世界,是女性作家对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在唤醒普通妇女女性意识的同时,作者把视角转移到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揭露男性中心意识给女性精神、肉体上来带的伤害。与此同时,借助对乡土社会中男权主义的反向“探索”,她们努力构建新的两性关系。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女性创作中对自我的认同与人道关怀成为其写作的重点所在。对比男权主义为中心的乡土世界,作者对男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通过“主体/他者”与“中心/边缘”相互转换的叙述模式,为乡土、乡愁、乡恋引入了新的情感体验,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