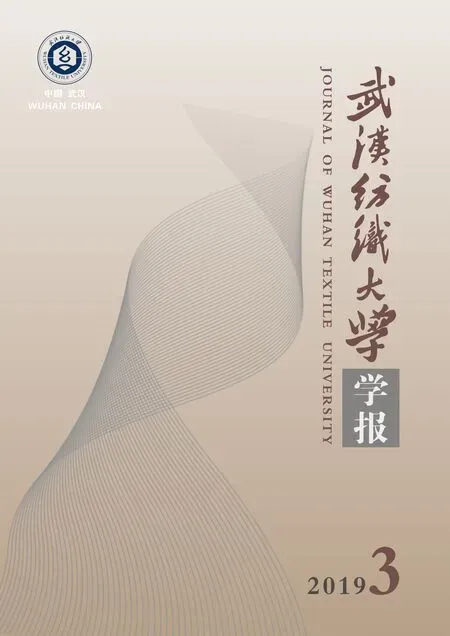明清时期潞绸的特点与“功能性”分析
唐 浩
明清时期潞绸的特点与“功能性”分析
唐 浩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潞绸”作为明清时期纺织业的代表性产品之一,发挥了多重“功能性”作用。首先,潞绸起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衣料的一种,本身便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其次,明清时期,潞绸跟随着潞商的足迹走出潞州,成为了行销广阔地域的“商品”,具有了礼赠资财的功能。最后,潞绸凭借其不断精细化发展趋向,越发深受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群体的喜爱,又成为了征派贡赋与彰显地位的“贡税品”与“奢侈品”,具备了更加多样的“功能性”。
潞绸;功能性;纺织业
“潞绸”,又称“潞䌷”,是晋东南潞州地区所产丝绸的名称,这里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桑树广泛种植,历史上,潞绸曾与杭段与蜀锦同列三大名绸,与二者相比,潞绸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更具开放性特点,原料除了出自本地外,还购自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行销区域更是极为广阔,其产品还拥有手感厚实,物美价廉,结实耐用,轻柔舒适等诸多特征。以潞绸为对象的研究虽已有诸多论著,如朱江琳对其兴衰过程与多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宫廷皇室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并考虑了战乱与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芦苇、杨小明则对潞绸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认为其色彩、样式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尚[2];高春平则是对潞绸在明代的兴盛与管理进行了研究,强调了官府染织局的重要作用[3],但这些论著大多着眼于潞绸本身的兴衰、管理、技艺等方面,而对于超越其本身之外的多重作用和在明清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功能性分析则有待增补。
一、经济层面:“实用品”与“商品”
晋东南地区拥有着适宜耕织的自然条件,民众耕作以食,纺织以衣的生活传统可远溯至秦汉,而到明清之际,则是所产潞绸大规模兴起与大放异彩的一个阶段,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官府为提倡桑麻种植业,规定“栽桑者四年以后有成,始征其租”[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更是下令对山东、山西、河南农户所栽桑枣果树给与减税优待“不论多寡,俱不起科”[5],并规定地方官赴京考察,必须上报劝务农桑的政绩,但此时,潞绸生产仍然还是作为传统耕织经济的补充部分,服务于家户寻常生活,其成色质量在明初都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永乐六年(1408年),沈王朱模就藩潞州,将数千名江南织绸巧匠带到潞州专职从事丝绸生产,随着种植蚕桑面积的扩大,赋税的减免和大量专业化的织户的聚集,潞州地区的丝绸业发展极为迅速,其生产规模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明季长子、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佘张”[6],所产潞绸品质也越加精细化,颜色、纹样、种类更多,舒适度更高,不仅可以做衣物的里、外面料,也可以直接做肚兜,做衫,做袄,做裙,还可以用于巾帽与鞋面等,丰富多彩的样式与鲜亮舒适的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其实用性功能。
同时,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的扩大,潞绸更具有流通与售卖的商品功能,成为了潞泽商人重要的行销货物,跟随潞泽商人的足迹走出了潞州一地。明万历年间,泉州著名文士蔡献臣归乡后,对家乡福建厦门一带的风俗记载道:“时市肆绸叚纱罗绝少,今则苏叚、潞绸、杭货,福机行市无所不有者”[7],表明在明代中后时潞绸甚至已经远销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了与苏、杭丝绸相媲美的衣料,然而,面对潞绸的大规模生产需要,本地生丝原料实已供应不足,“山邑桑茧,丝线取给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8],不仅潞州近邻之河南、河北、山东,甚至远至四川都开始向其供应生丝原料,四川保宁府所产的“阆丝”质地精美,品质极佳,“不仅流通四川省内巴州、剑州等地,还占领了山西丝织业中心潞安的原料供给市场”[9],山西机户、商人将从各地采购而来的大量生丝投入潞绸生产,而再将产出的潞绸销往全国各地,从地域视角上看,整个产销过程极具开放性特征,潞州也一时崛起为北方纺织业中心。
从潞绸本身产品特征来看,色彩上整体以红、绿、青、黄、蓝等亮丽色调为大宗,给人以明亮、畅快的直观感受,但同时也始终保留有黑、白、灰的传统庄重底色,从而将北方浓郁的古朴风格与地域特征蕴含其中。绸料质地手感较蜀锦、杭段更为厚实,而裁剪成衣又美观大方,穿着起来轻柔透气,舒适度极佳,在其绸面上,在力求实用性的基础上,还常常通过不同的织、绣方法来构思出出葫芦纹、寿字纹、锦鲤纹等各种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既简洁实用,又美观大方,更表达传统社会的民众对“福、禄、寿、喜”等美好生活事物的希冀与向往,这些承载着独特地域文化的潞绸在明清之际借助潞商广阔的行销网络“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外夷,号利薮”[10],销往海内外各地,使众多地域的民众得以穿着使用,明清之际,潞绸不仅在衣着服饰,也在经书封面、室内装饰等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了实用性的特征,其作为行销各地的“商品”,实用性功能也在更广泛的地域和用途方面得以进一步发挥。
二、政治性层面:“税贡品”与“赏赐品”
潞绸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发展直接来源于行政性的推动,明初洪武年间,山西便设立了染织局,以采办丝绸,永乐年六年(1408年),朱元璋二十一子朱模就藩潞州,积极组织本地织工与江南征调而来的织匠进行专业化生产,这直接提高了潞绸的品质,为大众广为接受的同时也获得了宫廷统治集团的喜爱,成为了税贡品,明弘治年间,潞州增设染织局,对供应宫廷的潞绸进行直接监。潞绸的行政征派分为常规征派与临时加派两种,常规征派为“十年一派,造绸四千九百七十尺,分为三运,九年解完,每匹价银四两九钱五分零。以十分为率,长治分造六分二厘,高平分造三分八厘,各差官解部交纳”[11],即每十年征派四千九百七十尺布,由长治县、高平县、潞州官衙三地分别以62%、38%和10%的划分织造,并以每匹四两九钱五分的价格征缴,各地机户织完后,由潞州染织局每三年一次解送到京,九年三次才算完成一次征派。清朝对潞绸的征派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这年朝廷“准山西潞绸机户,照明季例,十年一派,三年一解,以九年为始”[12],依然实行三年一解送,九年一周期的征派制度。
除了定期定额的常规性征派之外,临时加派在明万历年之后因为也日渐增多,征缴命令直接来自内廷或者皇帝本人,要求织造的潞绸数量庞大且时间短促。明神宗于“万历三年,征黄绸二千八百四十匹,万历十年,坐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万历十五年,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万历十八年又征黄绸五千匹,四次共派征一万五千余匹”[8],对潞绸持续的加派直接造成了晋省百姓困惫,机户艰殊,然而,减裁征派的请求却仍未得到批准,官府依然动则征数千、万匹之多。宫廷对潞绸“挥之如泥沙”般使用,是造成取之不足的原因,潞绸常被用于宫廷袍服织造,朝臣优待赏赐以及对游牧民族招抚封赏等行政性支出。明中叶,明廷对蒙古俺答部封贡后,宣大总督王崇古在礼宴上“抚赏虏王,及都督指挥大酋长,悉如封贡时,予金色段二匹,潞绸二匹,银花二树,加银台盏一副,大率金段潞绸,百三十匹,银花六十五树,银台盏三十三副,皆仰给三镇协济,抚赏银费凡九百八十八两四分,诸酋快甚”[13],一次性抚赐潞绸一百三十余匹,其中还包括有皇室专用的金色潞绸。清代时,每年中秋前两三天,康熙皇帝常在中南海紫光阁“集上三旗大臣侍卫较射,更设帐殿次第而入,御制诗所谓,队自花间入镳,从柳外分也,高等者,赐蟒缎一匹,内缎三匹,潞绸二匹,羊二只,次等者,蟒缎一匹,内缎二匹,潞绸一匹,羊一只,再次者,内缎一匹,潞绸一匹”[14],可见潞绸与蟒段、内段等发挥了政治性的赏赐品功能。
潞绸与皇室宫廷的紧密联系,能够使其生产规模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拓大,也能使其在一个王朝动荡倾覆时又迅速衰消,挥霍性的行政赏赐支出使得过量急征暴敛持续不断,造成了大量机户生活困苦,整个潞绸行业无法健康发展。伴随着明清两代交替时不断的天灾兵燹,潞州机户零落殆尽,织机骤减,加之过度征派,到了清朝后期,“各机户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奔逃哭,携其赔累簿籍,欲赴京陈告,以艰于路费,中道而阻”[15],机户为往往受朝廷急迫征派的影响,赔累生产,勉强维持,还常常受到各种额外盘剥,苦不堪言,最终广大机户不得不焚烧织机,砸碎户牌,阖家逃亡,在日赔月累之下,潞绸生产逐渐凋零,在清后期实际已难以为继,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请停潞绸疏中写道“晋省常年例解大小潞绸八十匹,生素绢,一千二百匹,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四万张,上项诸色,为物甚菲,而累及官民甚重所役驮载甚多,潞绸并不出于潞安,潞民但能养蚕,不习机杼,向在泽州织办”[16],清末的潞安府虽然还保留着派征潞绸的指派,但早已无法进行实际生产,只得委托在泽州置办,彼时年产数以万匹潞绸的潞州,此时已经变成了不习机杼之地。
三、社会层面:“等级品”与“奢侈品”
明清之际,潞绸作为一种越发精细与高档的手工业品,其制作工艺精巧,产品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配色上拥有有金黄、蛋黄、大紫、真紫、红青、天青、纱绿、油绿、沙蓝、黑色、酱色等超过28种颜色,其染色工艺相当精美,“西北之机,潞最工”[17],凭借其精细奢华特点逐渐在民众生活之中成为了身份地位象征的奢侈品。明定陵考古中发现的万历皇帝“潞绸龙袍”,万历孝靖皇后棺内发现了大红真紫细花潞绸一匹,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康熙皇帝的“黄潞绸里黑狐皮朝褂”、“潞绸舒袖马褂”,雍正皇帝的“黄条行裳”[18]等等,潞绸以其结实耐用又鲜丽明亮的特性深得明清皇室宫廷喜爱,彰显了其奢侈品功能。清代皇室的后宫成员在月俸与用度上都有关于潞绸的严格规定,“皇太后,金二十两,银二千两,潞绸四匹;皇后,银一千两,潞绸四匹;皇贵妃,银八百两,潞绸三匹;贵妃,银六百两,潞绸三匹;妃,银三百两,潞绸二匹;嫔,银二百两,潞绸二匹;常在,银五十两,潞绸一匹;答应,银三十两,潞绸一匹;皇子、福晋、皇子侧室福晋、乳母潞绸各一匹”[19],关于潞绸使用从皇太后至皇子、福晋、乳母都有严明的定例,可以说潞绸用度的多寡成为了后宫品级高低的重要象征。
不仅宫廷皇室喜爱潞绸,世俗间的富家豪室与士绅官宦也喜爱穿着潞绸,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文人书信往来与笔记载录中,也对潞绸来多有提及,明代黄冈人王同轨在赴任江宁县路的上,记载沿路见闻与风俗民风,特地写道:“俗沿朴俭,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不识予所着绒褐潞绸……太史公传楚啙窳偷生而无积聚,无千金之子,亦无冻馁之民,衡实似之宛然”[20],而士绅王维桢在购到一批品相极好的绒绸,甚至致书友人,讨论用潞绸与绒、捐的制衣之法,“此绒颇真,可呼衣工来,令作方袍,用青潞绸缘领及四边,以苏产玉色熟绢为里,则众柔相得,足耐久远,体轻而气温,亦奉身养命之道也”[21],可见对各种绸捐搭配之讲究,而在明人所录杂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一折中,自称山西平阳府人氏的甚舍云“装三十车羊绒潞绸,来这嘉兴府,做些买卖”还在这里看上了名叫李素阑的姑娘,与她母亲讲:“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做茶钱,你若肯将女孩儿嫁与俺,我三十车羊绒潞䌷都与你做财礼钱”[22],在明人杂剧中,潞绸直接发挥了资财的作用。
明清之际,潞绸在民众的寻常生活中,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迎接新生命诞生,到一生婚丧嫁娶,都有潞绸的参与,绸面上织绣的各式纹样与图案则表达了民众对平安幸福、家庭美满的希冀。牡丹花、梅花、兰竹、葫芦等各式纹样搭配大红大绿的亮色调潞绸,多作婚聘、诞子时的欢庆之礼,蕴含了对新婚夫妇与新生命朴实而美好的祝福之情;而“寿”、“万”、“安”等大团纹饰配以黑、紫、灰等庄重色调的潞绸寿衣,则对逝者表达了尊敬与送别之意。潞绸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再仅仅是一件裹身蔽体的普通衣物,还是精神情感的寄托和表达,更在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与人生时节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众情感与生活境况。潞绸在明清之际的整体发展也与当时愈加世俗化的社会文化态势紧密相关,这些涌现在书信见闻、杂剧剧本资料上的潞绸,不仅体现了其在当时作为衣着而盛行一时,也体现了其作为赠礼、婚聘甚至直接充当资财而参与民众生活之中,淋漓地体现了其饱含情感寓意与奢侈品的功能。
四、结语
对明清时期“潞绸”特征与其功能性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其首先作为满足生活需求的实用品所具备实用性功能,随后这一实用品随着鲜亮舒适的品质的提升得以更广泛地应用到衣物里、外面料,或者直接做成衣衫、裙子、鞋面等物件,潞绸为广大民众所喜爱,也成为了潞商销售的主要货物,具备商品性功能。同时,潞绸的发展与明代皇室与行政因素息息相关的,尤其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其生产方式愈加官府化,品质越加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使其本身成为了税贡品与身份等级的象征,潞绸不仅成为了强加在机户身上的一项越加苛重的赋税,也具有了使统治群体与富家豪室彰显尊贵地位的奢侈品功能。对于征派来的潞绸使用,宫廷皇室除了分多寡颁赐不同级别后宫以自用外,还用来赏赐大臣、甚至招抚归附的游牧部族首领,而在民间,拥有葫芦纹、兰竹纹、锦鲤纹等各种美好寓意的潞绸往往用于往来赠礼与婚聘,在特定场合下,潞绸甚至可以直接充当资财来使用。
总之,潞绸这种纺织品作为古代传统手工业产品的重要一员,往往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层面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实用品作用,而更具备商品、税贡品、赏赐品、等级品、奢侈品的广泛意义。这些都是古代传统纺织工艺品在超越其本身意义之外的额外功能,并且连接起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而这也是以“潞绸”为代表的传统手工业品历经时代更迭,能够一代代传承下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认识古代传统纺织工业,不仅要尽可能全面梳理其流传演变特点,更要尽可能多维度地分析其所承担的功能性作用,以“潞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纺织业产品,寄予着世俗大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也承载着了传统纺织业的不息魅力,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潞绸若将这些充满人文情感,美好寓意图案和传统的文化内涵融入现代纺织之中,走文化发展之路,便将能够在当今环境下,不断拓宽潞绸的销路和市场,创造发展历程的新辉煌。
[1] 朱江琳.明清潞绸兴衰始末及其原因分析[J].丝绸,2014,(7):64-69.
[2] 芦苇,杨小明.潞绸的艺术风格及其技术美特征[J].丝绸,2011,(4):44-47.
[3] 高春平.明代潞绸业的兴盛与管理[J].晋中学院学报,2009,(4):19-23.
[4] (明)李东阳.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社,2007.188.
[5] (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3.
[6] (清)张淑渠,姚学甲.乾隆潞安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556.
[7]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507.
[8] 张正明,宋丽莉,张舒.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110.
[9] 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66.
[10](清)杨晙,李中白,周再勋.顺治潞安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551.
[11](清)戴纯,傅德宜.乾隆高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496.
[12](清)蒋良骐撰,鲍思陶,西原点校.东华录[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2005.482.
[13](明)瞿九思.万历武功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544.
[14](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M].丛书集成初编[Z].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27.
[15](清)吴九龄,蔡履豫.长治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347.
[16](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425.
[17](明)徐光启.农政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59.
[18] 宗凤英.故官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一一明清织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19.
[19](清)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491.
[20] (明)王同轨.耳谈类增[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30.
[21](明)王维桢撰.槐野先生存笥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264.
[22](明)臧懋循.元曲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26.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ity of the Silk Produced from Lu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NG 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As a representative product of ancient textile industry, silk of "Lu" played multiple "functional" roles. Firstly, Lu silk originated from people's daily life. As a kind of clothing, it has universal "practicability". Second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 silk followed the footprints of Lu merchants and became a widely marketed "commodity", even in specific occasions, it could be directly used as capital. Finally,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refin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u silk, it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the ruling group and the upper social groups, and had become the tribute tax and luxury goods to collect tribute and highlight the status, with more diverse functions.
crepe; functions; textile industry
唐浩(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区域社会史.
TS941.11
A
2095-414X(2019)03-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