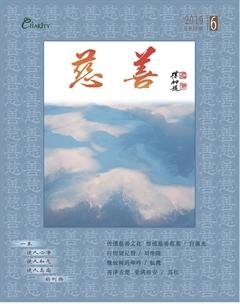陪母亲聊天
张庆安
退休后,得以和母亲“团聚”,聊天成为我们的日常。
年届88岁的母亲,精神矍铄,记忆力特强。虽被幸福生活所陶醉,仍有不称心的事儿。因继父早年先她而去,多年来,辗转于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珠海、安徽之间,忙于给儿女们带孩子、忙家务,终因故土难舍,前些年还是回到这个只有8户人家的巢湖乡下——夏阁镇潘王村安度晚年,孤独寂寞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我虽是母亲的长子,因为生父与母亲性格相左,我与母亲泪眼分离近60年。在我正需要母爱的时候,长辈们告诉我,你3岁(虚岁)的时候就没有了妈妈。没有喝够母亲的乳汁,心有不甘,与母亲有着心照不宣的芥蒂。彼此虽常常默默念叨,却因聚少离多缺乏沟通,而渐渐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但内心似有一股隐蔽的通道勾连胶着,这大概就是基因的融合物化所致。
少小,别人都有妈妈疼爱,过年有新衣、新鞋穿;可我衣衫褴褛,破旧不堪,就是在寒冬腊月里,脚趾头、脚后跟常常裸露在外。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直至参军入伍,一路跌跌撞撞,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花开一春,人活一世,许多东西你可能说不清楚为什么与到底怎么了。然而,人不是因为弄清了一切的奥秘与原委才活下来的,人是因为询问着、体察着、感受着与且信且疑着才享受了生活的真滋味。
走进这个似曾相识的村庄,鲜见儿时的伙伴,村子里多是七老八十的孤男寡女守候在宽敞的房间里与屏幕相视,显得格外的清净与凋零。自从母亲执意要从珠海(二弟家)回到乡下独自生活,在深圳工作的大弟出资把三间老屋修葺一新。添置了电视、冰箱、电风扇,安装了煤气灶、太阳能、自来水等,生活必须一应俱全,就连厕所也改造成冲洗蹲坐。偌大的堂屋墙壁被彩色和黑白相间、千姿百态的照片所霸屏,闲时与儿女子孙对视,那是母亲的小清欢。遇到邻居串门或亲戚来访,母亲总会指点照片,逐一介绍并说上一段故事,显摆中母亲获得满足,绽放灿烂的笑容。同母异父的四个弟妹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而后各奔东西,成家立业。
房屋宽敞,院落整齐,相邻的楼房一家比一家高翘,可鸡鸣狗吠声几乎没有了,偶尔传来几声零星的吠声和鸡鸣声,也少有应和。邻里之间的逼仄巷道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腐枝滥叶,偶尔还能见到阴暗潮湿的地沟里缓慢地攀爬着蜗牛和蚯蚓,一不小心就会踉跄趔趄,不由自主地舞起了芭蕾。人们常说“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不在,只剩归途。”没有什么伤痛是永远的,就像没有永远的爱一样。光阴让人猝不及防,关于父母的故事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记得,越来越少的人提及。
曾经的老屋我儿时偶有光顾,每到吃饭,当母亲把桌上少许的荤菜往我碗里夹时,同母异父的弟妹们會投来异样的眼光。那眨巴的眼睛,似乎在说,你凭什么来我们家把好东西都吃了。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只不过我和她不能天天相守,在一起生活罢了。我也是她的血,也是她的肉,更是融入到她骨头里的牵挂。
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正值困难时期,皮包骨的我孤苦伶仃地七拐八绕,从张华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来到母亲的家。大门敞开,推开虚掩的房门,母亲扎着一个印花头巾坐在床头,单薄的被子里裹着一个婴儿(同母异父的大弟)嗷嗷待哺。母亲看到我一声“乖乖,你是怎么来的?”我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哗哗落下。母亲连忙起身,从床头柜里边拿出一个纸包,一层层打开后用手捏了一小团红糖(她坐月子吃的)放在一个大瓷碗里冲上开水,饥渴难耐的我也顾不得许多,接过滚烫的碗仰头就喝,把我烫得哇哇直叫,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甜蜜回忆”。母爱如水的潜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常常泛起涟漪。
白天,母亲忙家务,我就打下手。与母亲耳鬓厮磨,促膝相视,她脸上纤毫毕现的皱纹,镌刻着岁月的风霜。母亲不识字,更不会写字,可她惊人的记性让我敬佩。比如常联系的几个子女(孙辈)和平时有求的夏阁镇上出租车司机、邻村电工,十五六个手机号码,她会掏出手机——按键139……130……180地拨打。我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聊身边人,聊亲朋好友、侄媳子孙;聊祖辈脉络、前世今生;聊左邻右舍、亲朋姻缘……听她倾诉烦恼,同时也分享她的喜悦。炊烟缭绕,或许来自于她对我的歉疚,不止一次地重复她与父亲的过往,好像这样讲出来让我评判谁是谁非。对他们的事情,我只从邻居和叔叔婶婶们那儿听说过;小时候,父亲偶尔说起都会面带怒色,我只听不做声,只是像梦游一般恍恍惚惚的。
我们母子珍惜时光,形影不离,晚上也同室而卧;在相隔三步之遥的各自床上边说边聊,一串串秘闻轶事,浮沉泛起。说着说着,我由起初的“嗯嗯”作答到进入梦乡的鼾声回应。当我被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吵醒,母亲早已备好了早餐,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呼声好大,全像我的呼声”,真是应了那句“知儿莫如母”的老话。日复一日,漫无边际的聊天中体悟到母爱的温情,那些融入心灵血脉的私语,算是捋清了我们母子的情感脉络。
母亲与父亲的那些事儿,也轮不到晚辈们去评价。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是南京外公家开糖坊雇的长工,大字不识,憨厚老实,平时少言寡语,只会出粗力,且年长母亲9岁。在母亲12岁那年,由外公做主定了亲,由此可见,母亲的婚姻也是迫于压力下的无奈选择。父亲与外公是巢县同乡,父亲来自青龙尖山下的一户贫苦人家,外公外婆早年沿夏阁河挑着货郎担一路讨饭到南京投亲靠友,后来做起了茶食生意。按照当时的习俗,男女定亲,彩礼按照女方年龄一岁一担米,可爷爷张东高家境贫寒,只东拼西凑了九担米,算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温柔贤惠的母亲遵从父命,16岁就嫁给了父亲,17岁早产一个男婴夭折,次年生下了姐姐庆云。五年后的农历二月初五晚上十点多钟,我在南京市珠江路591号的茶食店(一边是酒店,一边是茶食店)降临,外公王明清看是一个大胖小子(九斤半重),欣喜有加。父亲祖上单传,我的降临无疑是张家星丁。满月后,母亲抱着我回到祖籍地张华村的时候,正赶上已过世的奶奶(汤氏)伏山之日,奶奶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到母亲肚里的大头孙子,终因我没这个福气,与奶奶有一面之缘(爷爷在母亲未嫁来之前就已离世)。
母亲虽没有文化,嘴甜心善,能说会道。修长的身材,清纯的相貌,方圆十里算得上出众。有铁姑娘之称的老红旗公社主任、女劳模杨桂芝,对母亲十分器重,有意培养她作为大队妇联主任人选。父亲既要干农活,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对母亲整天忙于外出开会、学习,参加公社和生产大队里的社会事务反感抵触。久而久之,矛盾升级,抽打辱骂成为家常便饭,最终闹得离婚收场。母亲也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颁布)的践行者和获益人。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不幸夭折。父亲与母亲离婚后,为了把我和姐姐抚养成人,终身未娶。70岁那年,他在购买自己寿材的同时,也为母亲准备了一副。农村殡葬改革渐严,父亲就把寿材卖了补贴家用。2006年10月18日清晨,父亲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安然离世,享年84岁。母亲经人介绍嫁给了邻乡烧窑师傅王秀群(继父),先后生下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如今生活都很幸福。父亲生前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小麻将。在一个烟雨朦胧的日子,母亲念及曾经夫妻一场,杵着拐棍来到父亲的坟前,烧(捎)去万千纸钱,这也让我对母亲的敬畏感油然而生。那些丁点儿小事累积的人生,滋味各异,咀嚼不够。岁月如歌,以宽容作曲吧。内心通透干净了,万物柔软温暖。这辈子无论是愉快还是不愉快,发生过的事实已无法改变。
白驹过隙,时光如水。诸多的“昨夜星辰”,浩若银河;或明或暗的星星点点,都是母亲和我心中的软肋;经过岁月的濯洗,那些记忆的底片已渐褪色。
慢慢时间长河,生命不过一瞬。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母亲是生命之源,是遮风挡雨的屋顶,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神性光辉的存在。人生中的那些不幸和遭遇,在母亲面前,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如今与母亲在一起,陪伴对她来说就是最贴心的温暖。两个老屋,一个是我曾经居住的老屋,如今已不复存在;可母亲所住的老屋让我在晚年有了归宿感。
寒冬腊月里,能和母亲靠在山墙跟下晒晒太阳,聊聊家常,充盈于天地之间,内心充实,多么的惬意。母亲养育了我,我陪母亲变老,但愿无愧我心。春风化雨,岁月静好。母亲耄耋,我已年迈。忘记昨天,过好当下,明天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