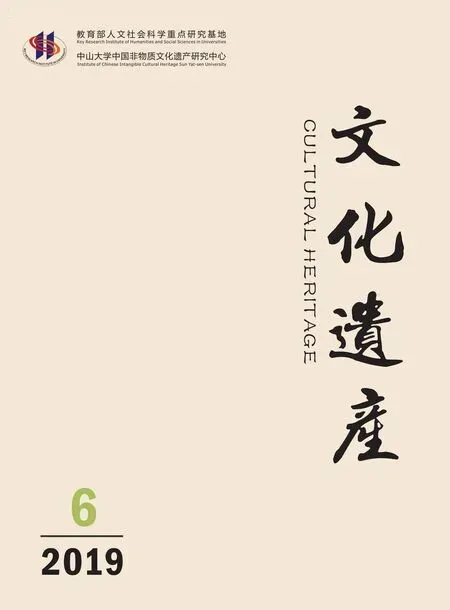上党梆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爱珍访谈录*
姚佳昌
张爱珍简介:女,汉族,1959年出生,山西高平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晋城市上党戏剧研究院副院长。自幼热爱戏曲艺术,13岁考入高平县青年文艺培训班,主攻青衣、小旦。毕业之后,进入剧团,排演新戏《蝶恋花》,并于“文革”之后在晋东南地区首次排演古装戏。对上党梆子进行了唱腔上的有益改革与创新,陆续推出《姐妹易嫁》《皮秀英打虎》等,并在1991年,凭借《杀妻》《两地家书》两部折子戏,荣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其唱腔“甜圆、纯美、如诗、通透”,被广大专家和戏迷亲切的称为“爱珍腔”。演出戏曲的同时积极开展上党梆子的传承工作,于2009年,评选为上党梆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上党梆子,主要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古上党郡地区。清道光末年官方称它为“本地土戏”,民国二十三年(1934)赴省城太原演出,曾叫“上党宫调”,当地群众称“大戏”,1954年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定名为上党梆子(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0年,第95页。。上党梆子在清代中期兴盛,并传播于今山东菏泽和河北永年地区,形成了山东枣梆和永年西调两个姐妹剧种。上党梆子以朝代大戏为主,粗犷豪放为主要特点,融合了“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于2006年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2月8日笔者前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对上党梆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爱珍进行了口述访谈。访谈主要包括了张爱珍的个人从艺史,她对上党梆子的认识以及剧团管理和戏曲传承等方面内容。
一、结缘戏曲,苦练青训班
“文革”期间,上党梆子同样遭遇了摧残,戏曲教育难以正常开展。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地方恢复了戏校,但都以“样板戏”为教材。张爱珍老师的学艺阶段正是戏校刚刚恢复的时期,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她对于上党梆子戏曲艺术的特殊领悟,以下就对张老师的学艺经历以及切身体悟等方面进行请教。
姚佳昌(以下简称姚):张老师好,我老家是长治市的。奶奶是上党梆子戏迷,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对上党梆子也很是喜欢。现在就读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希望通过对您的访谈,了解一下您的从艺经历、剧团管理、戏曲传承等方面的内容。您在十三岁的时候就进入到高平县青年文艺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当时为什么选择进入青训班学习呢?
张爱珍(以下简称张):自己从小就喜欢听歌、哼唱戏词。记得我妈妈曾说过“你看你这个闺女天天嘴里哼唱,长大后去唱戏吧。”她这么随便一说,结果还真说中了。高平在1970年成立青训班,1972年我哥哥冯来生作为高平人民剧团的乐队成员到乡下招生,于是在哥哥的鼓励下报名参加考试。记得当时的考试内容,一个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一个是歌曲《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还有一段阿庆嫂的说白以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然后再看你身段咋样。后来500多个人录取了不到25个,其中只有7个女生。所以说就是这个机会,领进门的就是我哥哥。
姚:您也正好赶上了青训班这个机遇,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全国上下样板戏“一统天下”,对于上党梆子来说,也不例外。当时在青训班学习期间是如何学戏?又是怎样处理传统戏和样板戏之间的关系呢?
张:我们当初学的都是样板戏,传统戏还没有开放。特别是学唱腔的时候,把上世纪50年代,像郭金顺的《徐策跑城》《两狼山》,王东则的《皮秀英打虎》,吴婉芝(2)吴婉芝(1933-1999),女,上党梆子戏曲名家,师从段二淼、郭金顺,其表演以唱功见长。其唱腔古拙中亦有新意,高亢中不乏委婉,如行云流水,刚柔并济,韵味甚浓。广为上党地区人民所喜爱,其优美唱段亦广为传唱,代表剧目为《皮秀英打虎》《秦香莲》等,张爱珍老师是其唯一弟子。的《闯宫》等唱片拿来,反复听,重复唱,当时启蒙的就是这几段,所以说开门的唱腔就是学的上党梆子的传统唱腔。但是古装戏没有开放,你就不敢唱古装戏那个词,还得把那个词改成现代的词。在样板戏流行期间,上党梆子丢失了好多传统,像当时的打击乐,都用京锣、京镲,总的来说得靠近京剧。我们这一代演员在学校学习样板戏,没有系统学习传统的东西,欠缺的也是这个,像唱腔中【四六板】【大板】等,是传统戏开放以后才在剧团系统学习的。当时就请上郭金顺、刘喜科等剧团以前的老演员教我们,所以对传统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认识,化成自己的东西。
姚:当初在青训班您主要是跟从谁学习的?您有拜过师吗?
张:当初青训班总共有十几个老师,有天津京剧团来这里插队的傅凤英老师,她教我们武功。还有武凤英老师,是自己唱腔的启蒙老师,她听吴婉芝老师的唱片,再教给我们,当初都称她为“假婉芝”。所以说我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比较门正,路子比较对。吴婉芝老师的唱腔启蒙,“假婉芝”武凤英老师给我们亲口传唱,这样的话自己没有走弯路。再后来自己又亲自拜吴婉芝老师为师,成了她唯一的弟子。吴婉芝老师对我的要求主要就是认真演戏。演戏要朴实自然、唱腔要注意韵味,把握人物身份、个性。在生活上她关心我比较多,有件事记忆特别深,有一年,她不知从哪听说了我胃不好,便弄上姜配红糖的偏方托人捎到乡下让我服用。吴老师就经常对我讲,你要按自己的理解大胆往前走。
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特别是对于学戏来说,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您能讲讲在青训班学戏的经历吗?
张:我们当初学校是在高平定林寺,那以前是个寺院,环境差。夏天我们就在外边松树下跑圆场练功。到了冬天,就在殿内练功。寺院有好几进院,彩排戏就在最高的一院,那时候开练腿功,身上练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腿肿的厉害,上下台阶都困难,那是比较艰苦的几年。当时老师们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我们练功后,都要进行总结。自己学的比较慢,笨鸟先飞。我比较规矩,不走范,老师教什么,自己就怎么来。青训班期间我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边学习一边演出实践。在练功期间排练一些歌颂那个年代的小节目,那时候就是来了新戏就学,像我们学的《育新人》《审椅子》等,都是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剧目。那时农村都有业余剧团,我们宣传队编上这些节目去农村演出,然后传授给农村大队的演员,那是全国性的活动。
在青训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脚踏实地的能吃得了苦,要把基本功打好。其次就是各位老师都特别关心自己,觉得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培养的对象。但是刚开始自己并不出众,也就是别人有特殊事情,如一部戏分A、B角,我是B角,或者就不是B角。由于A角有特殊情况,因为自己在课下挤时间学会了,到时候救场如救火。记得有一次在高平乡下演出《杜鹃山》,主演病了不能上场,由我顶上女主人公何湘就上场了,一上场老师们认为还挺不错,就开始重点培养自己了。所以说一定要等待机遇,人一生中的机遇擦肩而过,你如果这次把机遇弄丢了,那就永远来不了了。况且我们这是综合性艺术,一个演员遇到给你排一部戏的机会太难得了。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门不成你都做不成。
姚:在毕业期间,正面临着全国戏曲改革,这对于您来说也是很大的机遇与挑战吧?
张:是的,当时毕业后到了高平人民剧团,最幸运的是去北京学习李维康的《蝶恋花》,在这期间李少春的《逼上梁山》,还有《望江亭》《英台抗婚》等几个折子戏也开始上演了,这就面临着古装戏的开放。所以说我们就一边看古装戏,一边看《蝶恋花》的排练、演出。这一年的后半年,又上北京学《闯王旗》,是赵燕侠主演,还有李和曾、袁世海。我看到了京剧演员们排练场上的那种认真。我当时就想,我太幸福了,小时候不知道多会能去北京,想不到现在一年去了两次。
进京学习完《蝶恋花》之后,我们就抓紧排演,这是我毕业后出节目单的第一个戏,当时在高平连演半个月,座无虚席。晋东南地区文化局组织三团一校来看演出,最后晋东南戏校把《蝶恋花》移植走了。那一年我们高平人民剧团在晋东南十分火爆,可以说把好多电影、剧团都比下去了。当时古装戏开放了,因为咱们知道的消息早,就排演《秦香莲》,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在长治莲花池演出。因为古装戏刚开放,人们感觉非常新鲜,莲花池上万人的剧场,一毛钱一票,观众满满的。我们随后还排演了《英台抗婚》《姐妹易嫁》等,当时人民剧团太火爆了,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战功。
二、从观众中走出来的“爱珍腔”
张爱珍老师在上党梆子演出实践中,积极加以有益的探索创新,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唱腔风格,被专家和戏迷亲切的称为“爱珍腔”,广为观众们所喜爱。以下对张老师的艺术风格以及“爱珍腔”的探索过程进行了访谈。
姚:在您的演出实践中,对上党梆子唱腔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创新,从您的《皮秀英打虎》(下称《皮》剧)到《吴汉杀妻》(下称《杀妻》),再到《两地家书》,这三部经典剧目广为流传,您能讲讲这些剧目在唱腔的运用上有哪些独特之处吗?
张:首先《皮》剧,原来就是按恩师吴婉芝老师的原稿全部排练下来的,也不算是很大的改革,基本上还是延续。第二稿是我在演出实践中对声腔的应用,特别是人物的性格表现上做了些变化。其中男女主角谈情说爱的那一段【四六板】“藤萝架上藤花开”就改成【一串铃】(3)【一串铃】,上党梆子曲牌体唱腔。分两种形式,一种为长短句,一种为七字句,适用于武旦。了,以此来表现皮秀英心直口快、活泼开朗的性格。即使有些和老师的唱腔一样,因为理解不同,唱出来肯定有区别。
《杀妻》这个戏从1986年到现在,久演不衰,每个台口都演,而且现在已有四代演员都在传唱,只要是旦角演员能够演的了《杀妻》,就给她奠定了很大的基础。其中“窗前梅树”那一经典唱段,原来是说白,在观众中演出也是很感人。后来导演、音乐设计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把说白改成了唱。之后通过在观众中演出实践,我觉得把这一段改成唱腔,能够更好发挥我的优势,同时丰富人物心理的发展。《杀妻》是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根据人物的个性而设计的,里边几个最经典的叫板,掀起了整个折子戏的高潮。特别是在人物称呼转换的时候,如“夫君那”“驸马”等几个叫板,运用的是花脸的唱法,感觉特别的揪心。“窗前梅树”这一段,前边是【一马三箭】(4)【一马三箭】,又名“幺三五”“一根锤”,上党梆子板腔。该板式唱腔刚劲、稳健,特别是老生、须生、老旦、大花脸行当演唱时更显粗犷、豪放。。我觉得【一马三箭】是上党梆子最美的、最经典的板式,慷慨激昂,把王玉莲那种控诉、委屈、无奈的心情,以及最后成全丈夫那种大义凛然的气度表现的淋漓尽致。之后再转入叫板,对比抒情的“窗前梅树是我友”。在这之后的五十多句吧,如果说都用咱们传统的老剁板,就像“老爹爹且息怒”的唱法一样,也能唱得过去,但是对表现人物来说,她的“三次请求”,从平静到最后的高潮、哭诉,只是传统的剁板唱肯定无法表现。所以我想怎么能够像《洪湖赤卫队》中韩英死的时候“娘……啊……儿死后”的那种感觉。之后冯来生老师,就按着这个感觉,写出来的唱腔,其后吴宝明院长又在一些尾音上进行了修饰,珠联璧合,出来之后,观众们非常喜欢。
姚:我第一次在乡下看您的演出就是《杀妻》,现在仍回味无穷。特别是整部戏的唱腔上,已经形成了属于您自己的风格特征,“爱珍腔”应该也是在那时候形成的吧?
张:是的,是在《杀妻》广为知晓之后,当时有一篇文章是《看爱珍戏,四五夜不睡;听爱珍腔,四五瓶不醉》,好多年轻人连看六七场,有的在剧场就掉泪了。所以说《杀妻》吸引了好多年轻观众,而且是以前不喜欢看戏、不喜欢上党梆子的年轻人。1988年的《两地家书》就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在唱腔的运用以及刻画人物的深度上,比原来讲究多了。当年的马科(5)马科,戏曲导演、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导演,于1988年执导上党梆子《两地家书》,其代表作有《曹操与杨修》等。导演,他强调刻画人物时应该如何更加传情。比如以前排每本戏,有个习惯,对句词只对说白,之后到唱腔部分了,好了,把它跳过去,因为有音乐设计写唱腔,写出来咱们再唱。这个是不科学的,应该是你把句词都朗诵下来,按人物感情把它读好,读出语气的轻重缓急,这样再去唱,那就不一样了。他还强调做“小品”,让演员每天去做“小品”,回忆你从家里边起床以后是怎么来的排练场,回想原来的这些生活“动作”,再去思考如何演戏。有人说演戏都是假的,说你为什么不感人,不感动观众?是因为你表演的都是假的。通过做“小品”这些基本功来练习,出来的人物是活生生的,而且特别的感人,这就是《两地家书》整个音乐唱腔的迷人之处。
1993年的《柴夫人》是对我的唱腔上的又一次提高。1996年还排演了《塞北有个佘赛花》,是我和郭孝明两人主演,整场戏两个人唱,有三百多句唱词,那个也是在“爱珍腔”发展中的又一部作品。特别是之后的演唱会使“爱珍腔”更上一层。2017年4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山西省戏剧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对“爱珍腔”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可以说“爱珍腔”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往前走,也就是走来了30多年吧。
姚:您的“爱珍腔”,有专家认为“有继承,有发展,融清丽于激扬”,您对于戏曲唱腔方面的继承与创新是如何理解呢?
张:创新,我觉的本身就是“老腔新唱,新腔新唱”。“老腔新唱”,比如说我来唱一段《秦香莲》中的【四六板】,我理解的和他们唱的就不一样,主要体现在刻画人物上,我这个人就需要这样行腔。记得有一次在高平演出这部戏,几个乡镇干部看完之后上台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张老师,这唱腔改的真好听。” 我回复说“这是传统”。对于《秦香莲》这部传统戏来说,上党梆子的老艺人也一直在创新,包括吴婉芝老师对于其句词唱法的改革。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中也有创新。声腔三十年一变,你每个人的嗓子,唱法出来就不一样。我觉得有的人说一点不能动,那就把它保存到库房算了,它就成死态的了,有的不能动的就是不能动。现在都有些抠字眼,比如说又一个流行趋势就是讲究方言。地方语咱就是地方语,非要唱成老不唧唧的(指土话),我都觉得难听。有了唱腔的美化,有缩有放,才好听。应该把非遗的东西包装美给了新时代的人去欣赏,那是不是更好?
姚:是的,有继承有创新,才能够更好地弘扬传统戏。作为一名戏曲演员,在您的艺术之路中,您感觉什么是需要坚持的呢?
张:首先你应该爱这个行业。坚持二字,说出来好听,做起来难。那如果说不爱的话,肯定坚持不下来。不管是打把子,还是当宫女,首先要有这份敬业精神,你才能坚持。我觉得心里边应该认定了这份工作,我死活要干它。我觉得有这种毅力的人,才能把上党梆子剧种传承下去。
作为一名演员上舞台要认真,不管什么环境,天阴下雨还是台下只有几个观众,每场戏都应该一样对待,不能说有一场戏马马虎虎演过去,在我这是行不通的,也是我带团所不允许的。如果说舞台上整场演出出现瑕疵,比如音响没放开音或道具误上了或伴奏错了。下来之后,我不管你是多大身份,我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你。另外如果我身体不好,嗓子不好还非得演,戏退不掉,但是唱的达不住自己要求的水平,感觉心里愧对观众,心里难受。所以说干啥都得认真,你如果不认真、不严谨,艺术就要出瑕疵。
姚:这也是您师父吴婉芝老师所教导的。您从县级剧团一路走来,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可以说您是从老百姓中走出来的。
张:是的,我觉得刚毕业之后的实习演出很关键,我十七岁就出名了,当时已经被观众认可,能够担任大戏的主角了。而20岁到30岁这十年的成长很重要。演员没有十年在舞台上滚打,你是没有功力的。必须有十年的时间,四个晚上的戏,是你一个人唱到底的角色,给观众唱十年,这样才比较扎实,才能稍微成熟一点。我觉得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实践,自己就是在观众的口碑中红的,是老百姓捧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什么宣传文章,见到一篇报道自己还嫌不好意思呢。为什么在老百姓心里扎的深,原因就是每年在乡下演出,演出三四百场,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身份。
十年磨一剑,什么东西成功都得有一个时间。对于戏曲来说,你得和老百姓融合,再加上自己的反思,直至观众们喜欢了,也认可了,那么就坚定不移地往下走,这样就形成了精品段子。一个戏排出来之后没有一年多演出实践是不行的,需要和观众们产生共鸣,不断摸索经验。我总觉得艺术无止境,就在这。
三、美不过家乡戏五种声腔
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戏、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从现存舞台题壁可知,至少在十八世纪中叶,上党梆子已经是一个拥有五种声腔的成熟剧种。无论是其声腔类型、剧目种类、音乐特色,还是传承脉络、传播范围等都有其独特性,以下就这些内容对张老师进行了访谈。
姚:有一句话叫做“高不过太行山与天同党,美不过家乡戏五种声腔”?可以谈一下您对于上党梆子五种声腔的认识吗?现在上党梆子的“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还都有保留和传唱吗?
张:“高不过太行山与天同党,美不过家乡戏五种声腔”这一句是吴宝明院长的经典词,这是在我的演唱会上主持人白燕升运用的。提起“昆梆罗卷黄”这五种声腔,不得不说自己的演唱会(6)2010-2012年,上党梆子名家张爱珍演唱会分别在山西晋城、太原、长治、阳城皇城相府、台湾新竹举办,演唱会上的唱段主要有《杀妻》《两地家书》、上党时调《浪子踢球》、传统曲目《杀四门》、上党昆曲《长生殿》、上党二黄《打金枝》、新编现代曲目《李双双》《塞北有个佘赛花》等。,你看为什么演唱会中,一个是我的经典段子,这是必有的,另外是传统戏和现代戏要全,其次是板式上要全,再次是五种声腔要全。当时我就要求这方面的内容,咱们的上党梆子,比如说《杀四门》,那些戏也都快失传了。《杀四门》那段唱是咱们上党梆子打击乐最丰富,最精彩的。另外,我把上党昆曲《长生殿》、上党二黄和反二黄加入。我特别喜欢反二黄,加入《虹霓关》那一段。最后演唱会彩排了总共十段,其中有四段是我以前没有亲自唱过的。之后我就抓紧学习,遵循吴宝明院长所强调的根据塑造的人物个性来演唱。在晋城泽州会堂的演唱会结束后,好多老年观众激动地说,“今晚才尝到了小时候的《杀四门》、上党昆曲《长生殿》的味道。”
姚:您演唱会当时很成功,可以说上党梆子的五种声腔中有些已经失传了,比如说卷戏、罗戏,亟待保护传承。就您所知咱们的上党梆子是否有一个传承谱系?您是第几代传承人?
张:应该是赵清海最早,其次是段二淼、郭金顺、申银洞等,再下来是郝同生、郝聘芝、吴婉芝等,再下来是马正瑞、高玉林等,再下来是我们这代,张保平、吴国华、郭孝明等。我们再下一代就是陈素琴、杜建萍、成静云、索伟琴、张敏丽、宋晋梅等,再下来是李丹、邱亚萍、魏璐颖等,再下来就是高平中专我们培养的这一代。一般一代相隔是10到15年左右的样子。
姚:上党梆子的艺术特色是粗犷豪放的,因为它演出的多为朝代大戏,如《岳家军》《杨家将》等,那还有细腻抒情的地方吗?
张:咱上党梆子演杨家戏、岳家戏多,在咱这个地方没杨家戏,就不过瘾。一个剧团如果没有蟒、靠,就觉得你小家子气。特别是下午场,热闹!上党梆子细腻的,也就是抒情的方面比较少。因为咱们上党梆子中闺门旦、小旦、小生这样的行当比较少,所以这些生旦戏就少,只有青衣、老旦和须生这样的杨家戏。小生、小旦肯定要委婉细腻的多,因为谈情说爱嘛。但是包括《杀妻》《两地家书》中也很少表现谈情说爱的。咱们现在的板式在原来基础上已经发展了很多,包括剁板等好多种,以前也就是两三种。现在可以根据句词的长短,能出来不同的唱腔。根据你的人物,写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唱腔。
姚:上党梆子过去分为州底派和潞府派,州底派主要流行于原泽州府,行腔较稳健、平缓,注重声音的艺术表现力。潞府派主要流行于原潞安府和沁州,行腔高昂而常大起大落,注重情绪的强烈表现,现在这两派还有区分吗?
张:两派之间肯定相互学习,他们的东西在咱们(州底派)里边,咱们的东西他们又吸收上了。通过演员之间相互的串班演出,相互学习,它就有一种融合。另外就是咱们州底派,本身在唱腔的地方语言上就不同,像咱们这儿就分成高平音、阳城音等。都说高平的上党梆子正宗,我觉得主要是在语言上。高平说话位置靠上,鼻音大,唱出来的味道好。你看吴婉芝老师的唱腔就都在鼻音上。大家有时候议论,人家唱的这个味真是好啊,这就是强调的唱腔这个味。再一个唱腔要有个性,包括演员的个性、声音的个性、表现的人物的个性。
姚:上党梆子在清光绪年间传到了山东菏泽和河北永年地区,并发展成为了枣梆和西调两个姐妹剧种,现在咱们相互之间还有交流吗?
张:这些都是过去老艺人逃荒传过去的。应该感谢那些艺人,咱们的地方戏传出去以后,又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发扬光大,我觉得他们为上党剧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以前山东枣梆、永年西调,每年都在咱们这演出。最近几年演员互相往来,交流也增多了。看他们的戏,和咱们一样的地方很多,只是落腔、尾音等,有时候不同。我感觉一是咱们的方言不同,另外就是咱们老艺人,传的时候有可能就唱成这样了。永年西调,那就是咱们给出的孩子。老艺人在其他地方传播的时候,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唱法。咱们上党梆子中的《潘杨讼》,就是移植的人家永年西调的。
姚: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除去唱腔之外,表演动作也是重要的内容。对于上党梆子来说,有哪些讲究的地方呢?
张: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哪样都离不了,当然我是以唱功为主,还有水袖,但比较少。现在好多话剧导演排戏剧,对“手眼身法步”不讲究了。大部分和话剧一样,舞美、灯光,舞台上豪华的不得了,把表演程式的东西都丢失了。一个演员必须打好童子功,必须学开腰腿、拿顶、翻功、把子功、扇子功等。现在有些没有基本功,出来之后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当然用技巧表现人物,但如果为技巧而技巧,离开了人物也不行,应该把技巧很合理的运用到人物中。
姚:上党梆子的音乐也很有特色,包括各类板式、花腔、曲牌等等,其传承和发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张:小时候学谱子,当时的观念就是乐队好好学,演员学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因此演员在这一方面比较欠缺。如果说谱子你都读不准,你也就不懂如何把唱腔唱好,如何唱出感情。所以乐队和演员都应该好好地学习乐理知识。
吴宝明院长的《上党梆子音乐》最近就要出版了,这本书比较全面,包括了上党梆子曲牌等打击乐以及各种唱腔的浪头等,但是咱们戏里边不可能用全了,有些不用的就慢慢丢失了。现在新创剧目的作曲中,吴院长就运用了好多传统音乐。但是咱们年轻人,因为学的少,他老感觉是移植过来的。其实是在上党梆子原有音乐的基础上,把它拆开或者整合而成的,所以还是在传统方面了解的不透彻。另外现在非遗传承人就没有戏曲音乐这一块,可以说演员都是作曲的捧出来的。以前是没有音乐设计,也没有导演,由拉头把的和演员来设计唱腔。现在有了音乐设计,但没有编入非遗传承人当中,全国都没有,就没有设立。我感觉应该设立,戏曲没有音乐不行,演员不靠音乐设计能成功吗?
四、从管理到传承,从未停步
从戏校毕业之后,张爱珍老师分别进入高平和晋城上党梆子剧团工作,先后当任县、市剧团的领导,为扭转剧团的经营状况,她肩挑重任、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在离开剧团之后,又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戏曲传承工作,提携后辈、言传身教,对上党梆子艺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故以下对其剧团管理、传承工作以及对上党梆子未来发展的思考等方面进行了访谈。
姚:在剧团管理方面您曾经大胆创新,特别是您当二团团长(7)考虑到演员个人发展和剧团经营状况等原因,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曾经有过分团和合团的情况,时间分别在1990年和2002年。后就确定了“真正改革、惨淡经营、如履薄冰”的十二字建团方针,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张:说起改革,我够大胆了。因为当初分团时分为第一和第二演出团。分人的时候,比如说两个花脸,就是一家一个,如果是只有一个,就给一团。为什么这样做呢?上级觉得我在县里边当过领导,有经验,不担心。我这里是年轻化,可以到社会上去招聘,但必须保证一团的。所以说当时对我比较严格,给的任务比较艰巨。改革主要是打破原先的工资制度,也就是不管是中专生还是临时工,按打分制来定岗。如果谁不上了,你给谁救场了,那就赚他的一份。所以就有了奖励激励机制,这种机制还是挺好的。但是打破了以前的制度,就需要做一些工作,因为好多人不太情愿,慢慢的大家就理解了。这种机制也为后来合团的改革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姚: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剧团的发展,这也是您对于剧团管理的经验总结,对现今剧团的管理改革仍有很多借鉴意义。我们知道后来在合团之后,您退出剧团,并从那时起开始了上党梆子的传承工作?
张:当时按我的年龄正是唱戏的时候,也是观众希望一直看到你创作新作品的时候。但是合团之后,就出现了对我艺术发展不利的一面。我退下来已经十几年了,你想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因此,说遗憾也算遗憾。遗憾的是自己在舞台上应该展示的时候,不在舞台上,不遗憾的是你能亲自做一些传承工作。这几年,就传承来说,主要是培养杜建萍,把她一步步推到梅花奖的奖台上。在顺其自然能够做什么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工作,思维一直没有停下来。也为观众演出戏曲,因为高平上党梆子青年剧团是我当年创业的地方,是因我而成立的,所以他们叫我,我就过去辅导他们。他们的戏价低,打上我的名就能涨高戏价,演职员就能多发工资。我想这也行,只要我的名字能够给大家带来富裕的收入,这也值得。只是大家想看我的新作品的时候,不好遇到机会了。但也没有什么遗憾,你早点退出舞台,让年轻人展示,这也是咱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上一辈,高玉林老师就是四十多岁退出舞台,把我们捧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捧下一代,这是一个演员的责任。
姚:这十几年您也在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上党梆子这一剧种。特别是在您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的传习工作室?当时为什么要建立传习工作室?传习工作室的主要工作有哪些?
张:为什么要搞传习工作室?其实我原计划在没有平台的时候,就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更好地传承咱们的上党梆子。后来经过各种努力终于建起来自己的戏曲传习工作室,在全省可能也是第一个。这个传习工作室挂牌之后,正好赶上去台湾开演唱会。因为出境的话需要办手续,如没有这个工作室,就没法办理手续,你还去不了台湾。所以说刚成立起来,就做了这件大事。这之后,传习工作室的新闻一播出,高平中专张春生校长就找我谈,想招生办个戏曲班,由我负责戏曲专业教学,这样就和高平中专办了一件大事,培养了一批戏曲后备人才。他们中专六年制,今年(2018)就要毕业了。这一批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班子,女演员小四十名,男演员是27名,乐队38名。我一直想培养一个好乐队,因为当时我团里乐队就是最棒的。由此培养了上党梆子历史上第一代女鼓师、女琴师,而且反响很好,咱们已经连续五年上晋城市春晚。其次是在2016年参与“非遗文化上党梆子”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晋城10余所中小学。在这期间我培养的孩子们积极参与其中,他们演出已经很有经验了。
姚:这也是您在反哺家乡,为上党梆子培养后备人才。除此之外,您还积极培养上党梆子小演员,并且有多人获得小梅花奖,咱们这个小梅花奖也是传习所来培养的吗?
张:小梅花奖是中专和传习所一起培养的。小梅花奖拿了四朵了,计划2018年再拿上一朵,他们的年龄也就到了,因为有年龄限制。所以说这几年也很费心,真的,虽说没有唱戏,我就一直在做这个。为什么两年多我一直没有上台呢?一方面嗓子一直生痰,其次杜建萍去拿梅花奖,还有这批学生费心。所以说,我的身体有些透支了。家里的事务也顾不上照顾,包括孙子也顾不上照看,自己家人帮着承担、付出了很多,家庭成为了自己坚强的后盾。自己一心扑在上党梆子上了,同时又想达到所想要的结果,所以这几年比较辛苦。做这些也就是给上党梆子培养了传承人,作为我一个年龄这么大,话说就是太阳要落山的一个演员,能做的事也就是发挥我最大的余热,从未停步,一直在做。
姚:作为非遗传承人,您在自觉地传承着上党梆子艺术,这也是您文化自觉的表现,由此您身上的责任确实会比较大。
张:对于传承来说,我也是不断思考如何把咱们上党梆子精华的东西运用到所演出的戏曲人物上,让他们更丰富饱满,我感觉这样才有价值。现在,我这个“爱珍腔”基本确立了,但“爱珍腔”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剧种的财富,那徒弟就得把“爱珍腔”传承下去。如果这个徒弟有能力传承下去,他们也可以超越。这不是死的,你只要把这个唱腔把握了,你去运用它,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了才漂亮呢。但是必须遵照四声,不能倒字,吐字就是地方的普通话。其次,对于上党梆子来说现在需要整理改编一些传统剧目,让各个剧团唱,才能传承下去。上党梆子传统剧目有300多,经常唱的只有二三十个。比如有的剧本还需要修改丰富,现在的剧本都是干巴巴的,没有肉,这些需要加强。
姚:为了更好的传承上党梆子和您的“爱珍腔”,您也有正式收过徒弟吗?
张:我正式收的有四个,杜建萍、索伟琴、邱亚萍、魏璐颖,还有几个学生是我内部收的,总共八九个吧。我在收徒的认识上是,徒弟首先具备基本条件,再一个是做人。另外你收上徒弟,老师就有责任对他负责,如何培养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
姚:现在咱们剧团的发展有没有困境,有没有青黄不接的感觉?您感觉咱们上党梆子发展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张:怎么没有,县里边就不行,中层力量太差。包括须生,男角色很缺,小生就更别提了。你要说人才有没有?是有,你看市里边人才济济,但是轮不上唱。我觉得上党梆子的发展还是需要有人才,其次还得让这些人才有平台。现在培养出来了,如何来保护他们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这就需要有个好领导,一个宽宏大量,有文化情怀、远见卓识,并全面考虑剧种未来发展的领导。
姚:上党梆子的传承和发展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各界的共同努力。您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在近几年的看似沉寂中,您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实践。
张:我甚都不关心,就是操心唱戏多,干甚太认真,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的漂亮。现在我觉得,咱做的事无愧于组织的培养就可以了,能做的尽量做,一生想做完是不可能的。只是觉得有时有力出不上,不是很圆满。遗憾的是自己感觉缺一部戏,现在要是有一部新戏,有一个好角色,你看,给观众们过瘾的发挥发挥,那多好!
姚:谢谢张老师接受我的访谈,自己对上党梆子艺术和您的从艺经历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希望上党梆子艺术广为流传,也祝您的艺术之路常青。
后记:拜访当天是2017年农历腊月二十三。上午张爱珍老师还在忙着指导学生,接近中午才得以相见,在她家中访谈近一小时,后被住在同一家属楼的吴宝明夫妇邀请共进午餐,共度小年。餐桌上吴宝明夫妇和张爱珍、张建国夫妇谈及上党梆子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表现出很多忧虑同时又有更多的期盼。期间我给他们敬酒以表谢意,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和睦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饭后,在张爱珍老师家中继续访谈至傍晚时分,张老师在访谈过程中感情投入,情深至极常常心有所动而尽情的回忆往事。上党梆子作为自己的家乡戏,我为有张老师这样的艺人的坚守而感到骄傲,也更愿为其传承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