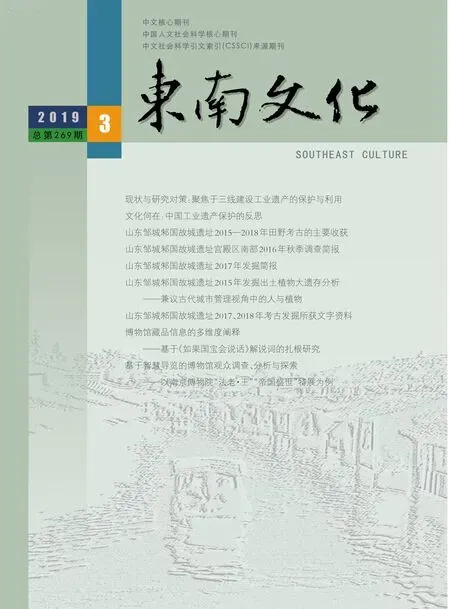陶冶吴越
——简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
张 敏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两周时期的吴国和越国“接土邻境,壤交通属”。吴国的“官工业”为矿冶业,越国的“官工业”为陶瓷业,矿冶业和陶瓷业分别成为吴越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吴越最主要的生业形态。越向吴大量输出陶瓷器以换取本国极度匮乏的铜资源,吴越之间的“资源互动”成为两周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
吴始于周初,终于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历经西周和春秋[1];越亦始于周初,终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杀越王无强,或终于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降越君,历经西周、春秋和战国[2]。
西周时期的吴越都是偏居东南一隅的蕞尔小邦;春秋晚期的吴越都不受周代礼制的羁束而先后称王;春战之际的吴越先后崛起,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而称霸诸侯,成为华夏政治舞台上耀眼的新星。
《荀子·王霸》:“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3]
春秋之初,管仲在齐国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4],垄断了海盐的生产与销售,盐业遂成为齐国的“官工业”[5]。齐国因此成为“春秋首富”,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首霸”,“食盐官营”成为齐国“信立而霸”的经济基础。
春秋时期的“信立而霸”除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需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吴王阖闾和越王句践“信立而霸”的经济基础同样是吴越的“官工业”。
“官工业”即官营手工业。《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6]以为刃,凝土以为器”,“烁金”与“凝土”皆属“百工之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国语·晋语四》:“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7],“工贾不变”与“工商食官”当为春秋时期“官工业”的真实写照[8]。
“官工业”属国家产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构成。通过强权政治将公共资源垄断为国家资源,将手工业者和商人集中起来设官吏统一管理,由政府提供衣食,按照政府的意志、根据政府的需求进行生产和贸易是“官工业”的生产模式;产业规模大、生产地集中、从业人数多、分工细致化是“官工业”的基本特征。
根据考古发现,吴国的“官工业”为矿冶业,吴致力于青铜的开采冶炼,矿冶业成为吴国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吴国最重要的生业形态;越国的“官工业”为陶瓷业,越致力于陶瓷烧造,陶瓷业成为越国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是越国最重要的生业形态。
“鬲”与“鼎”是区分吴越文化最主要的文化遗物,“土墩墓”与“石室土墩墓”是区分吴越文化最重要的文化遗迹。根据吴文化遗址和土墩墓的分布范围推断,吴国的疆域包括苏南茅山以西的宁(南京)镇(镇江)地区和皖南黄山以北的芜(芜湖)铜(铜陵)地区,大致相当于秦鄣郡或西汉丹扬郡的地理空间[9],与矿冶业相关的矿冶遗址、冶铸遗址、聚落遗址、土墩墓、古城址等文化遗存均分布在这一地理空间内,出土的文化遗物中常见青铜鬲或陶鬲[10];根据越文化遗址和石室土墩墓的分布范围推断,越国的疆域包括苏南茅山以东的太湖地区和黄山、天目山以南的钱塘江流域,大致相当于秦汉会稽郡的地理空间[11],与陶瓷业相关的窑址、聚落遗址、石室土墩墓、古城址等文化遗存均分布在这一地理空间内,出土的文化遗物中不见青铜鬲或陶鬲[12]。
由于吴越的生业形态于史无征,对吴越生业形态进行的研究也几近阙如,因此本文主要根据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述的文化现象,谈谈对吴越生业形态的肤浅认知。
一、吴的矿冶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青铜是“祀”与“戎”的物质基础。
皖南的芜铜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蕴藏。《诗·鲁颂·泮水》:“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史记·李斯列传》:“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史记·货殖列传》:“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汉书·地理志上》:“丹扬郡……有铜官。”
西汉时期的芜铜地区属丹扬郡,丹扬郡“有铜官”,因此文献记载的“南金”“江南金锡”和“章山之铜”,皆有可能为皖南地区所产的铜。
(一)矿冶遗址
皖南的铜矿资源分布在中国东部燕山期火山岩浆大爆发后产生的硅卡岩铁铜矿床分布区内,铜矿带主要集中在“下扬子坳陷带”,铜矿多为含铜品位较高、呈巢状或株状分布的“鸡窝矿体型”[14]。
皖南地区经初步考古调查已发现古代矿冶遗址100余处,铜矿遗址分布在贵池、青阳、铜陵、南陵、泾县、繁昌等市县境内,大大小小的中心矿区的分布范围达数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矿冶遗址的分布范围达2000平方公里,并形成规模巨大的铜矿遗址群[15],以南陵的大工山[16]和铜陵的凤凰山[17]一带的矿冶遗址最为集中。
采矿是自地壳内或地表开采矿产资源的技术,两周时期皖南铜矿的开采主要采用“烧爆法”,铜矿矿井的巷道除有木井架外,还有通风和排水设施,多层的采矿平巷交叉分布,而处于不同水平面上的矿井都是独立开掘,矿井的开拓采用了竖井、平巷、斜井联合开拓的地下开采系统,井巷支护均采用木质框架式支撑,根据矿井中发现的大小不一、重量悬殊的平衡石分析,当时可能已使用辘轳一类的提升工具从井下垂直向上提升矿石、废石和积水。
铜矿是铜的硫化物或氧化物与其他矿物组成的集合体,皖南铜矿主要为硫化铜。两周时期铜矿的冶炼主要采用“火法冶炼”,冶炼的方法是先在焙烧炉中用焙烧的方法对铜矿石进行脱硫,然后在鼓风炉中用熔炼的方法将脱硫后的矿石与添加的石灰石、石英石等熔剂物一起加热,通过鼓风至高温使固体矿石熔化为液体金属,通过熔炼使杂质造渣的粗金属分离[18]。
根据南陵、贵池、铜陵、繁昌等地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冰铜锭分析,皖南铜矿是我国最早采用硫化铜矿炼铜的地区;根据发现的焙烧窑遗迹推测,早期的脱硫工艺可能采用“堆烧法”。皖南铜矿已采用鼓风炉炼铜,炉炼的种类有竖炉和地炉;炼铜的燃料最初使用木炭,之后可能使用煤为燃料炼铜[19]。
皖南铜矿出土的开采工具有铜凿、铁斧、铁锄、铁锤、铁錾、铁钻、木桶、木楔、石球、平衡石等;与冶炼相关的遗物有炉壁、炼渣、冰铜锭;生活用器主要有夹砂红陶鬲、印纹硬陶罐、青瓷豆、盘、碗和硬陶钵等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
皖南铜矿的采矿技术包括矿井的选择,巷道的布置、架构、排水、通风、照明和矿石的采掘、破碎、装载、运输、提升、筛选等;皖南铜矿的冶炼技术包括焙烧脱硫、添加辅料、鼓风冶炼、冷却成锭等。铜矿的采冶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含铜率25%~70%、含铁率15%~40%的片状柳叶形冰铜锭是吴国矿冶业的主要产品[20]。
根据出土的文化遗物分析,皖南铜矿的采矿、冶炼始于西周,止于唐宋。西周至春秋时期是皖南铜矿第一次大规模开采、冶炼的时期,因此皖南铜矿第一次大规模的开采、冶炼与吴国的历史相伴,与吴国的建立和灭亡相始终。
铜陵师姑墩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冶铜遗址,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掘确立了安徽长江沿岸地区较完整的夏商至春秋时期的年代框架,出土有矿石、铜块、铅锭、陶范、炉渣、炉壁和小件铜器等[21]。
师姑墩遗址有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早期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期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商时期,晚期遗存的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夏商时期与青铜器铸造相关的文化遗物有矿石、铅块、支座、粘有铜锈的炉壁、炉渣、陶范、石范等,西周时期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铜原料、冶铸设施、冶炼渣和熔炼渣等冶铸废物、浇铸工具、青铜器成品等,涵盖了青铜冶铸的各个环节。
师姑墩遗址的发现,表明皖南地区冶铸青铜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之际,并历经西周至春秋中期。
(二)聚落遗址与土墩墓
皖南地区的聚落遗址主要沿漳河、青弋江、水阳江、姑溪河、慈湖河和长江分布,仅姑溪河流域即发现两周时期的聚落遗址80余处[22]。
皖南除发现大量的矿冶遗址、聚落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土墩墓。土墩墓主要分布于芜铜地区,其中最著名的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南陵千峰山土墩墓群和繁昌万牛山土墩墓群。
千峰山土墩墓群位于南陵的葛林乡,现存墓葬近千座,分布范围达13平方公里;万牛山土墩墓群位于繁昌的平铺、新林两乡,与南陵家发乡的土墩墓群连成一片,现存墓葬数百座,分布范围约6平方公里;而在南陵分布较为集中的23处地点通过遥感调查发现的土墩墓竟多达3029座[23]。
经过考古发掘的有南陵县千峰山[24]、龙头山[25]和繁昌县平铺土墩墓[26]等,随葬器物有印纹硬陶器、青瓷器、青铜器以及采矿、炼铜的生产工具和碎铜块等;此外,繁昌汤家山、孙村、新牌村西周墓还出土鼎、甗、盉、盘、匜、甬钟等青铜器[27]。
皖南的聚落遗址群与土墩墓群不仅与皖南的矿冶业息息相关,而且与皖南铜矿第一次大规模的开采冶炼的年代相始终。
(三)城址
牯牛山古城址位于安徽南陵石铺乡,南北长约900、东西宽约750米,面积近70万平方米,城址四周有古河道环绕,河道宽20~30米,古城址以西20公里即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分布的中心地带,古城四周还分布着密集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
城内有五个高土台,高台内有大范围的红烧土堆积分布,并有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在古城址的西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个面积为100余平方米的小土台。高土台出土了夹砂陶器、泥质陶器、印纹硬陶器、青瓷器、石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物,牯牛山古城始筑于西周,沿用至春秋[28]。
牯牛山古城地处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地带,环境优越。城址四周有古河道环绕,城内河道与城外河道有三处出水口相连,使城内、城外的河道互相贯通,并分别与长江支流漳河、青弋江相通,而青弋江是东通太湖、西连长江的“中江水道”的入江段[29]。
牯牛山古城扼漳河、青弋江水上交通、运输之要冲,控制着原材料和成品的储藏、输入和输出;城内的高土台当为管理机构的建筑基址;在古城址以西20公里即大工山铜矿遗址群的中心地带。牯牛山古城与当时大规模的开采铜矿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经营铜矿开采、冶炼、库存、运输的调度管理中心。
皖南的矿冶遗址群、聚落遗址群和土墩墓群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国矿冶业的兴旺发达;而城的出现不仅表明吴国在矿冶业密集的地区设置了管理机构,也反映了吴国的矿冶业属“官工业”。
矿冶遗址、冶铸遗址、聚落遗址、土墩墓和古城遗址构成了吴国完整的“官工业”体系。
二、越的陶瓷业
瓷器是越人的伟大发明,是越人对华夏文明的巨大贡献,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
浙江是中国最早烧制瓷器的地区,同时也是烧制瓷器的中心。浙江发现的瓷窑160余处,集中分布在于越族群的中心区域,其中尤以东苕溪流域的分布最为密集[31]。
(一)窑址
浙江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可烧制瓷器的高岭土矿床有沉积型、风化残余型、热液改造叠加风化残余型和热液改造型等;在赋存空间上由地表至深部具分带性,即由钙基膨润土→钠钙基膨润土→钠基膨润土→高岭土[32]。
硬陶是古代陶器的一个特殊的品种,硬陶的原料是含铁量很高的粘土,烧成温度达1150~1200℃,胎质多呈紫色、红褐色、灰褐色、黄褐色,敲击有金属声,因器表多拍印几何形纹饰,故又称印纹硬陶;瓷器用高岭土烧成,烧成温度1200℃左右,质地坚硬,胎色灰白,采用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在烧制过程中产生的还原气氛使瓷器呈质地光亮的青绿色釉,故又名青瓷或原始青瓷[33]。硬陶器和青瓷器是越国陶瓷业的主要产品。
窑址主要集中分布于浦阳江流域的萧山[34]和东苕溪流域的德清和湖州,其中以东苕溪流域的窑址分布最为密集、延续时间最长[35]。
东苕溪源出东天目山北部的平顶山南麓,南流折东后与中、北苕溪汇合,然后至湖州与西苕溪汇合后入太湖,东苕溪为浙江北部最重要的通航河流。
东苕溪流域的窑址以德清龙山片区和湖州青山片区的分布最为集中,龙山片区有夏商之际至战国时期窑址145处,青山片区有商代窑址群21处,除少量烧制印纹硬陶器外,大多烧制青瓷器。其中,夏代窑址有湖州瓢山、金龙山、北家山等;商代窑址有德清龙山、湖州瓢山、南山、黄梅山等;西周春秋时期的窑址有德清火烧山;战国时期的窑址有德清亭子桥等[36]。
分布于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和两周时期的越文化都是于越族群创造的文化。东苕溪流域属太湖流域,尽管《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历史文献将越国先君上溯到夏少康庶子无余,然“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37],因此夏商时期东苕溪流域的窑址群属于越族群的窑址群,而西周春秋时期的窑址群属于越族群立国后的窑址群,即越国窑址群。
龙窑为越人首创。东苕溪流域的窑址在夏商时期已出现龙窑雏形,经过西周时期的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已出现十分成熟的龙窑,窑体的改进不仅提高了陶瓷器的产量,也提高了陶瓷器的质量;从西周春秋时期隔烧的托珠,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直筒形、喇叭形、托盘形窑具,烧制工艺日臻成熟[38]。
青瓷器和硬陶器烧制始于夏,商代开始青瓷器和硬陶器的数量明显增多。夏商时期的陶瓷产品主要为日用器皿;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除烧制日用器皿外,还烧制各种仿青铜礼乐器,甚至还烧制陶瓷兵器和陶瓷生产工具。
陶瓷礼乐器往往出土于高等级的越国贵族墓葬,德清亭子桥发现了专门烧制青瓷礼乐器的窑址[39],江苏无锡鸿山[40]、浙江长兴鼻子山[41]和安吉龙山[42]等越国贵族墓葬出土的青瓷礼乐器当为专门的窑址烧制。因此,德清亭子桥一带的窑址已具备雏形“官窑”的性质[43]。
(二)聚落遗址与石室土墩墓
东苕溪流域是马桥文化时期至西周春秋时期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湖州、德清和余杭西南部、长兴东南部的山坡几乎都发现有马桥文化时期至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表明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频繁。
东苕溪中下游是马桥文化时期至西周春秋时期遗址的最密集分布区之一[44],经考古调查发现的遗址有30余处,其中江苏邱城[45],浙江毘山[46]、钱山漾[47]等大型聚落遗址紧邻下菰城东北面分布,下菰城东边开阔的河网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中小型聚落遗址[48]。
东苕溪中下游地区处于太湖平原与莫干山脉的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是先秦时期土墩墓、石室土墩墓最重要的分布区,其数量庞大、分布密集,仅在长兴县的弁山、韦山、小娜山等地发现的土墩墓、石室土墩墓就多达2840座,吕蒙山、乌基山、南皇山、吕山等地也分布着土墩墓群,在长兴鼻子山和磨盘山还发现大型的越国贵族墓葬[49]。
东苕溪流域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群有长兴便山和石狮[50],湖州杨家埠、独山头和堂子山[51],德清塔山、独仓山和南王山[52],安吉三官和笔架山[53]等。这些墓葬的年代有西周、春秋和战国,均为两周时期[54]。墓葬以石室土墩墓为主,长兴便山发掘的37座墓葬中,有34座墓内建有石室;德清独仓山发掘的10座墓葬中,有6座为东西向长条形的石室土墩墓,而无石室的墓葬中,1座有石床,3座有石框。
墓葬的随葬器物主要为罐、瓮、坛、瓿、尊、钵、盂等硬陶器和鼎、簋、尊、豆、盘、瓿、罐、碗、钵、盅、盂等青瓷器,以及少量的鼎、釜、罐、钵等夹砂陶器和罐、盘、盆等泥质陶器。
(三)城址
下菰城遗址位于湖州市南10多公里的道场乡窑头村,地处太湖南岸,西北倚和尚山,东北靠金盖山,面向东南,城南有里江,里江向南数十米即东苕溪。下菰城有内城和外城,平面呈圆角等边三角形,保存基本完好。城墙高约9米,上部宽约5~6、底部宽约30米,外城墙周长1800米;内城位于外城南部偏东处,城墙周长1200米;内城和外城外均有一道宽约30米的护城河。城外的高地上分布着高岭、戈山、东头山、吴十坟墩等商周遗址,与城址有密切的联系。下菰城始建于商代,出土的文化遗物具有马桥文化特征,是一座马桥文化的城址。虽然缺乏历史文献证明于越族群在商时期已建立国家,但下菰城的发现无疑将越人集中管理窑业的历史上溯到商时期。下菰城虽然始建于商时期,但在下菰城内城土城垣中采集的文化遗物中有几何形印纹硬陶片,纹饰有绳纹、长方格纹、方格纹、编织纹、回字纹、曲折纹等;可辨器形有瓶、罐、坛等,与当地商至西周及春秋地层中的遗物无异,因此下菰城可能沿用至春秋时期[55]。
陶瓷器的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烧制工艺大致包括瓷土的开采、舂打、淘洗、练泥、拉坯、修坯、成形、晾坯、素烧、施釉、装窑、烧窑、出窑等,还有烧制之前的燃料储备和烧制成器后的库存、包装、运输等。从开采瓷土到烧制成器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合理的调度和有效的管理,而位于东苕溪畔的下菰城与大规模的陶瓷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为夏商至春秋时期陶瓷业的管理中心。
东苕溪流域的窑址群、聚落遗址群和墓葬群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国陶瓷业的兴旺发达。而城的出现不仅表明越人在陶瓷业密集的地区设置了管理机构,也反映了东苕溪流域的陶瓷业属“官工业”。
东苕溪流域的窑址群、聚落遗址群、墓葬群和古城址构成了越国完整的“官工业”体系。
三、吴越的“资源互动”
吴的“官工业”为铜矿采冶,越的“官工业”为陶瓷烧制,吴越的“官工业”规模宏大,渊源久远,且贯穿吴越文化始终。
吴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越国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吴越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发展本国的传统产业。吴国的铜矿资源和越国的瓷土资源原本都属公共资源,在吴越的强权政治下都成为了国家资源,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吴越在矿冶业密集的区域和陶瓷业密集的区域都筑城设置管理机构,牯牛山古城和下菰城都位于水道交通的要冲,控制着矿冶业和陶瓷业原料到产品的进出和运输,古城的设立在矿冶业和陶瓷业的规划管理、调度运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礼·地官·丱人》:“丱人[56]掌金玉锡石之地”;《周礼·考工记》:“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搏埴之工:陶、瓬。”矿冶业和陶瓷业为吴越的“官工业”,虽然吴国的矿冶业和越国的陶瓷业未必与《周礼》记载的相同,但吴国的矿冶业和越国的陶瓷业当有“丱、筑、冶、凫、栗、段、桃”和“陶、瓬”等专业分工。矿冶业和陶瓷业都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吴国的矿冶业和越国的陶瓷业必然有专业分工,专业分工的细致化必然导致吴越基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57]。
吴国的矿冶产品除用于本国铸造青铜礼器、兵器之外,还流向他国,矿冶业成为吴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金道锡行”的途径除向周王朝纳贡和献金外,诸侯国之间的馈赠、掠夺、贸易皆可成为铜资源流动的途径[58],在这些途径中,贸易似乎成为越国获得铜资源的唯一途径。
越国的陶瓷产品是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这些陶瓷产品除用于本国的日常生活和随葬外,还大量倾销吴国。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已渗透到吴国的各个阶层,其数量已远远超过青铜器,成为吴国炊器之外最主要的生活用器和随葬用器。陶瓷业也因此成为越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印纹硬陶器和青瓷器因具有美观性、实用性和耐用性而受到吴国上下的青睐,但吴国没有陶瓷业。在吴国的疆域内从未发现烧制陶瓷器的窑址,而且吴国遗址或墓葬出土的硬陶器、青瓷器与越国硬陶器、青瓷器的器类、造型、纹饰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吴国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陶瓷器显然来自越国。
吴国矿冶业的主要产品是冰铜锭,越国陶瓷业的主要产品是陶瓷器,越国向吴国输出陶瓷器的目的是换取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冰铜锭。越国的铜资源极度匮乏,疆域内也从未发现过矿冶遗址,但越国却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不仅有著名的铸造工匠欧冶子,还有青铜铸造的“越式鼎”、“王”字矛、鸠杖的杖首和杖镦、句鑃、伎乐铜屋,以及寒光熠熠的“越王句践剑”。根据吴国大量出土的越国烧制的印纹硬陶器和青瓷器推测,越国青铜器的原料可能主要来自吴国。
浙江原始青瓷生产的流布与发展轨迹,与吴越两国的兴衰相一致[59]。《吕氏春秋·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60],《越绝书·纪策考》:“吴越为邻,同俗并土”[61],《越绝书·范伯》:“吴越二邦,同气共俗”[62],吴越接壤,陆路相通;《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山海经·南山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63],苕水注于吴越之间的具区,水路也相通。“接土邻境”是吴越“资源互动”的外因,而“同气共俗”则有可能是吴越“资源互动”的内因。
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述的吴越之间的“资源互动”,是两周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出现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原因是印纹硬陶器和青瓷器的生产已成为越国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向吴国大量输出印纹硬陶器和青瓷器以换取铜原料当属越国的国家行为。
吴越没有货币,也不使用货币,因此吴越之间的贸易当为“以物易物”。江苏金坛鳖墩土墩墓随葬的陶坛中盛有70公斤冰铜块[64],鳖墩附近的土窖和句容庙西土墩墓出土的冰铜块皆重达150余公斤,江苏溧水、丹阳等地的土墩墓中也有类似的冰铜块的出土[65]。显然,将冰铜锭砸成碎块贮藏或随葬已成为两周时期吴国的普遍现象,冰铜块可能充当了“称量货币”的职能。由于历史文献的阙如,吴越之间的贸易途径、贸易流程、等价原则等已不可考。
吴国有着规模宏大的矿冶业,其根据本国的国情大力发展矿冶业,最先掌握了硫化铜的脱硫工艺,开拓了铜矿冶炼的资源空间;越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陶瓷业,其根据本国的国情大力发展陶瓷业。矿冶业和陶瓷业成为吴越的“官工业”,构成吴越最主要的生业形态,为吴越的“信立而霸”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火所以用陶冶,民随国而为之”[66]。陶冶是火的艺术与结晶,陶冶是吴越“随国而为之”的抉择;陶冶构筑了吴越的文明,陶冶铸就了吴越的辉煌。
[1]《史记·吴太伯世家》:“是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越灭吴。”
[2]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3]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七·王霸第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131页。
[4]《管子·海王》《管子·轻重甲》。
[5]《国语·齐语》《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管晏列传》《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
[6]“烁”通“铄”,铄,熔也,烁金即熔金。
[7]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中华书局2002年,第350页。
[8]a.曲英杰:《“工商食官”辨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b.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9]《汉书·地理志上》:“丹扬郡,故鄣郡。……有铜官。”丹扬郡治宛陵(今宣城),领宛陵、於濳、江乘、春谷、秣陵、故鄣、句容、泾、丹阳、石城、胡孰、陵阳、芜湖、黝、溧阳、歙、宣城等十七县。
[10]a.宫希成:《皖南地区土墩墓初步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b.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秦置。”会稽郡治吴(今苏州),领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萧山、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冶、回浦等二十六县。
[12]a.陈元甫:《土墩墓与吴越文化》,《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b.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c.叶文宪:《吴人土墩墓与越人石室土墩墓》,《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d.〔日〕江村知朗:《吴越战争与越文化圈》,林华东、季承人主编《中国柯桥:越国文化高峰论坛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13]《左传》“成公十三年”。
[14]a.陶奎元等:《中国东部燕山期火山—岩浆大爆发》,《矿床地质》1999年第18卷第4期;b.杨兵:《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构成与形成机制》,《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1999年第8卷第5期。
[15]a.魏嵩山:《西汉丹阳铜产地新考》,《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b.郭怀中:《“丹阳铜”产地考略》,《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c.杨立新:《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d.唐杰平:《安徽古代铜矿考古的回顾与思考》,《文物研究》第14辑,黄山书社2005年。
[16]a.汪景辉:《安徽古代铜矿考古调查综述》,《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b.刘平生:《南陵大工山古代矿冶遗址群江木冲冶炼场调查》,《文物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88年;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南陵县古铜矿采冶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2002年第2期。
[17]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10期;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c.张国茂:《安徽铜陵地区古矿冶遗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18]a.李延祥:《从古文献看长江中下游地区火法炼铜技术》,《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4期;b.许书理:《略论中国古代火法炼铜技术》,《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19]a.张敬国等:《贵池东周铜锭的分析研究——中国始用硫化铜的一个线索》,《自然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b.杨立新:《安徽沿江地区的古代铜矿》,《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c.杨立新:《铜陵古代铜业史略》,《文物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1998年。
[20]a.同[19]a;b.刘平生:《安徽南陵大工山古代铜矿遗址发现和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12期;c.秦颖等:《安徽省南陵县江木冲古铜矿冶炼遗物自然科学研究及意义》,《东南文化》2002年第1期。
[21]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6期;b.王开等:《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的相关问题》,《考古》2013年第7期;c.郁永彬等:《皖南地区早期冶铜技术研究的新收获》,《考古》2015年第5期。
[22]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23]宫希成等:《安徽省南陵县千峰山一带土墩墓及石铺塘西古城遗址遥感调查》,《光电子技术与信息》1998年第5期。
[2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年第3期。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南陵龙头山西周土墩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26]杨鸠霞:《安徽省繁昌县平铺土墩墓》,《考古》1990年第2期。
[27]a.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b.谢军:《安徽繁昌新出土的三件铜器》,《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
[28]a.杨则东等:《安徽省南陵县古遗迹遥感调查》,《中国地质》1998年第10期;b.刘树人等:《安徽南陵县土墩墓及古城遗址遥感调查初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环境遥感考古专集》1998年第4期。
[29]《史记·河渠书》:“(中江)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索隐》:“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汉书·地理志》:“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中江水道由东氿、西氿、南溪河、南中河、胥溪、固城湖、水阳江、青弋江沟通而成。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30]a.孙天健:《原始瓷器的发明及其里程碑意义》,《中国陶瓷》2003年第3期;b.郑建明等:《“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纪要》,《文物》2008年第8期;c.“瓷之源”课题组:《原始瓷的起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
[31]a.陈元甫:《浙江出土商周原始瓷概述》,《古越瓷韵——浙江出土商周原始瓷集粹》,文物出版社2010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
[32]a.何英才等:《浙江高岭土(瓷土)矿床成因类型及其应用途径探讨》,《浙江地质》1987年第3卷第2期;b.袁德丰等:《浙江仇山矿区膨润土、高岭土矿石矿物地质特征》,《资源调查与环境》2002年第23卷第3期。
[33]a.罗宏杰等:《试论原始瓷器的定义》,《考古》1998年第7期;b.刘毅:《商周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研究》,《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c.杨冰等:《论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景德镇陶瓷》2016年第6期。
[34]a.王士伦:《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萧山前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5期。
[35]a.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的若干问题》,《文物》1982年第4期;b.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9期;c.潘林荣:《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调查报告》,《东方博物》第四辑,1999年;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e.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f.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1期;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3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
[37]袁康、吴平辑校,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38]郑建明:《夏商周原始瓷略论稿》,文物出版社2015年。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40]a.南京博物院等:《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b.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1]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越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42]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b.同[41]b。
[43]a.陈元甫等:《德清亭子桥战国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方博物》2010年第1期;b.王汇文:《越国原始瓷礼乐器的生产制作工艺探微》,《中国陶瓷》2017年第10期。
[44]祝炜平等:《浙北湖州地区土墩墓遥感影像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27卷第1期。
[45]梅福根:《江苏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4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47]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48]郑建明:《陶瓷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瓷路人生〉编后记》,任世龙著《瓷路人生》,文物出版社2017年。
[49]a.同[41]b;b.李刚:《长兴县土墩墓调查报告》,林华东、季承人主编《中国柯桥:越国文化高峰论坛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50]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便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专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专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51]a.胡继根:《湖州市杨家埠先秦及汉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州妙西独山头土墩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0年第3期;c.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湖州堂子山土墩墓发掘报告》,《东方博物》2004年第2期。
[52]a.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独仓山与南王山》,科学出版社2007年。
[53]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三官土墩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0年第3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54]陈元甫:《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55]a.郑建明:《夏商原始瓷起源的动力因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原始瓷起源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b.陈元甫:《湖州下菰城的初步勘探与探索》,《“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c.劳伯敏:《从下菰城的兴衰看湖州治址的变迁》,《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56]丱,古文矿,“丱人”即“矿人”。
[57]夏毅辉等:《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
[58]a.裘士京:《江南铜材与“金道锡行”初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b.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试析——兼论青铜原料集散中心“繁汤”的形成》,《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59]沈琼华:《原始青瓷与古越文明》,浙江省博物馆编《瓷之源——德清原始瓷窑考古成果暨原始瓷精品展》,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
[60]陈奇猷校译:《吕氏春秋校译·贵直论·知化》,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552页。
[61]东汉·袁康、吴平辑校,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62]东汉·袁康、吴平辑校,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63]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南山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64]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3期。
[65]徐永年:《对吴国的称量货币——青铜块的探讨》,《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
[66]《周礼·夏官·司爟》郑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