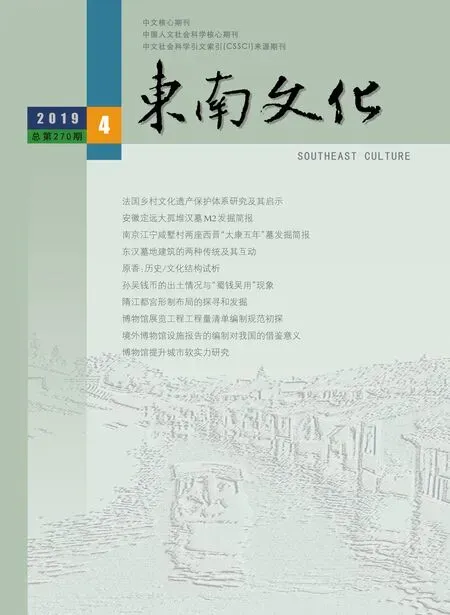隋江都宫形制布局的探寻和发掘
汪 勃 王小迎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2.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苏扬州 225002)
内容提要:从江都兵变相关记载中的隋江都宫的城、城门、殿阁等名称以及叛军搜索皇帝的行进路线等文献资料入手,结合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中与隋江都宫相关的城墙、城门、道路等遗迹以及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相关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对隋江都宫的形制布局略作探讨。研究发现,隋江都宫及东城基本沿袭了南北朝时期广陵城的范围及其主要道路网;隋江都城内包含中轴线在内有3条南北向轴线,或亦有3条东西向轴线;隋江都宫的城门和主要殿阁名称与都城规制关联性较强;隋江都宫的规格甚高,几近于京师;隋唐时期的扬州城是一座都城规格的城市。隋炀帝时期的江都稍具都城形制,隋江都宫作为东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是强化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融的中心。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以下简称“蜀岗古城”)涉及春秋吴邗城、楚汉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唐子城、宋堡城和宝祐城等,隋江都宫的探寻一直都是相关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数十年来在蜀岗古城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一些与隋江都宫相关的遗迹,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也出土了与江都宫相关的墓志文、墓砖、鎏金铜铺首等资料。目前,隋江都宫的面貌虽仍然模糊不清,却依稀渐露端倪。鉴此,管见以为,有必要从江都兵变相关记载中的隋江都宫的城、城门、殿阁等名称以及叛军搜索皇帝的行进路线等文献资料入手,结合相关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收获,从城门和城内道路等迹象入手,由点到线,就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和主要道路等形制布局略作探讨,以便为隋江都宫的探寻和后续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线索和思路。
一、江都兵变记事中的隋江都宫殿阁名称
隋炀帝于大业年间多次到江都,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二年“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六年“三月癸亥,幸江都宫”,七年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十二年七月“甲子,幸江都宫”[1]。隋在扬州以广陵城为基础,营建了江都宫。隋炀帝时期的江都是将东南财物调度至北方的中转站,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隋书》中关于隋江都宫的具体记载较少,除了隋炀帝数下江都之外,还有“俄而勑(张)衡督役江都宮”“(徐)仲宗迁南郡丞,(赵)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使”等。江都兵变相关记事中,留下了一些与隋江都宫形制布局相关的城门、殿阁等名称。
《隋书》中的江都兵变相关记事中,记载有部分与隋江都宫的城、城门、殿阁等相关的名称。如:司马德戡“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屯于东城”;裴虔通“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先开宫门,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擒帝于西阁”;义宁二年(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一日夜,“(唐)奉义主闭城门,乃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钥。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虔通伪曰:‘草坊被烧……’中外隔绝,帝以为然……虔通因自开门,领数百骑,至成象殿……虔通进兵,排左阁,驰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阁。’从往执帝……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因复将入”[2];“宇文化及弑逆之际,(燕王杨)倓觉变,欲入奏,恐露其事,因与梁公萧钜、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为司宫者所遏……”[3];“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箦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稜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4]
《资治通鉴》中的部分相关记载[5],似可补充《隋书》所记。如“是夕,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似表明“殿”为成象殿,“阁”即成象殿之阁;“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此“东门”似为成象殿宫院之东门,而《隋书》中的“奉义主闭城门,乃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钥”的是“城门”;“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武门,叩阁请曰……”,说明皇帝当时在玄武门;“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西阁”,明确说叛军是从玄武门入宫的,而《隋书》中就此并无明确记载;“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涉及隋江都宫的城门、朝堂、宫门、寝殿、西院、流珠堂等名称。
另外,唐临淄县主《与独孤穆冥会诗》记弑炀帝之事,云“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半夜开重城”,是隋炀帝时江都宫被称作“重城”的佐证。
二、隋江都宫形制布局的探寻和发掘
从上述文献可知,隋江都宫为重城,分为宫城、东城,东城为骁果军等扈从所在,宫城为皇帝等所居;从江都兵变开始,到皇帝被弑,再到殡、奉、葬、改葬等隋炀帝葬仪相关过程,涉及到了与隋江都宫相关的宫城、东城、玄武门、芳林门、城门、门、草坊、成象殿、左阁、永巷、西阁、温室、西院、流珠堂等城、城门、殿阁等的名称。宫城有门,夜间上锁以隔绝内外,江都门或为隋江都宫门之名;若是在东城“觉变”,经芳林门侧水窦至玄武门,再“为司宫者所遏”,那么芳林门是外城门还是宫城门、是东门还是北门有待明确。隋江都宫及其宫城、东城的范围界定,玄武门和成象殿的位置关系,宫城内是只有成象殿一座大殿宫院还是如隋洛阳宫乾阳殿之后还有大业殿之类的宫院等问题均尚需思考。
迄今为止,在蜀岗古城考古发掘中找到的隋代相关遗址或遗迹甚少。隋代城墙主要是在城圈的西北角[6],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7]、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8]、蜀岗南城门[9]等三座城门遗址与隋江都宫相关,城内十字街西南隅的东西向道路[10]、南北向和东西向夯土遗迹或与隋代道路相关。以下,从江都兵变相关记事中与隋江都宫相关的名称入手,结合蜀岗古城相关考古发掘结果,试就隋江都宫的形制布局略作探讨。
(一)隋江都宫的宫城和东城
从发生兵乱到隋炀帝被弑、埋葬、改葬的相关历史文献中,涉及到东城、隋江都宫城及隋江都宫城中的温室、成象殿、迷楼等建筑以及雷塘、吴公台等较多与隋江都宫遗址相关的地名、遗迹名等,均与扬州城的关系极为密切。从蜀岗古城相关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汉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唐子城的城圈或相同,城门多为修缮沿用,门道和城内道路也多有层叠现象,因此推测隋江都宫及东城当是基本沿袭之前广陵城的范围和主要道路网。
据《宋书》记载,刘宋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城叛乱,孝武帝命沈庆之率兵讨伐,“于桑里置烽火三所”,“若克外城,举一烽;克内城,举两烽;禽诞,举三烽”。沈庆之率众攻城,“克其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11]。可见刘宋时期的广陵城,有内、外两城。
《与独孤穆冥会诗》中有“半夜开重城”,杜牧《扬州三首》其三中亦有“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关于重城一词,有多种涵义,一指城墙,如李商隐《夕阳楼》诗:“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一指城市,如高骈《寄鄠杜李遂良处士》诗:“小隐堪忘世上情,可能休梦入重城”;一指外城中又有内城的城池形制[12]。从《扬州三首》总体来看,不管杜牧诗中所咏的“两重城”是指隋江都宫城和东城,还是指唐子城内有两重城,其所指均为蜀岗之上的城池,而与蜀岗下的唐罗城并无关系[13],并且“隋罗城”的存在与否尚需商榷[14]。管见以为,隋江都宫的“重城”是指位于蜀岗之上的隋宫城和东城。
从文献记载来看,隋江都宫当有宫城和东城两部分,宫城在西、东城在东。东城,“以在宫城、皇城之东,故曰东城”[15]。《唐两京城坊考》“东都外郭城图”“东都宫城皇城图”中均有“东城”[16],相关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亦曾开展过[17]。
隋唐洛阳东城,始筑于隋大业九年(613年),唐代沿用,位于隋唐洛阳城的中部偏北,宫城、皇城与洛北里坊区之间,“东城的东、南、北三面皆有城门”[18]。换言之,隋东都洛阳宫城与东城之间没有城门,其原因或是隋大业九年之前尚未建东城,即东城是在宫城使用之后才增建的,故而东城与宫城东墙之间没有宫门。隋两京的设计者为宇文恺,隋炀帝下江都沿线建筑也是宇文恺布置的,洛阳有“东城”,隋江都宫“东城”的名称及相对位置,或与隋东都洛阳之“东城”有渊源。至于隋江都宫东城西垣是否与宫城相邻,若相邻则其间是否有宫门等问题都还毫无线索。并且,《资治通鉴》中明确说叛军是从玄武门入宫的,而《隋书》中并未提及此事,那么,叛军从东城进入宫城因何要走玄武门,就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若东城和宫城东垣之间有门,则该门既是城门亦是宫门,当亦未“下钥”,那么从宫城的东侧门进入宫城当最为便利。叛军绕行到宫城北部玄武门入宫的原因,或是如同洛阳,东城西垣上没有与宫城连通之门;或是叛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比从“东华门”等宫城东垣上的“门”距离更短或更为便利;或是东城和成象殿宫院之间,还有如东宫之类的宫院墙;或是东城与宫城东垣并不相邻,而是位于偏北之处……总之,宫城和东城的具体位置关系,宫城和东城之间的连通路径等问题,都还需要细思慎想。
迄今为止,为了探寻隋江都宫的墙垣、建筑基址作过数次努力,然而至今并无重要收获,只是得到了一些线索。
1.宫城墙垣的探寻发掘
笔者基于蜀岗古城考古调查勘探的结果,蠡测过蜀岗古城内各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概况,并制定了相应的考古发掘工作计划。经过7年的发掘,虽然得到了一些与隋江都宫相关的遗迹或线索,但也明白了隋江都宫的探寻工作要比预料中的更为复杂。其原因主要有三:重要位置均被村庄叠压,遗迹面多在今地下水位之下,宋代以来的破坏颇为严重。目前,虽然可以认为在城圈西北角、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等地点发现的隋代遗迹与江都宫相关,但是由于隋代宫城、东城的范围及其与蜀岗古城城圈的关系尚未确定,因此迄今获知的只是与江都宫墙垣相关的线索,而相关遗迹究竟是属于宫城还是外城的问题仍难以判断。
(1)南垣
根据考古勘探结果,推测两条东西向线或与蜀岗古城内墙垣相关,故进行了发掘。
①考古勘探结果,注意到疑似夯土条带迹象ER108-ER107-ER70-ER72-ER73-ER74-ER75(以下勘探迹象均略作编号)[19]东西向分布于堡城西路以南100米,且与东南隅的ER44在东西一线上,因此怀疑其或为一条夯土墙垣,选择布设探沟发掘了其中的ER108、ER107、ER70、ER75。结果表明这些遗迹现象分别为南宋时期的夯土、砌砖、沟等遗存,与南宋之前的遗迹无关[20]。
②在上述夯土条带以南约150米分布有东西向疑似夯土条带迹象ER80-ER81-ER82-ER84,选择在ER82和稍南的ER83的连结位置布设探沟YSA0405T1A进行了发掘。结果在探沟南端发掘到了ER83的北侧边缘,基本判断其为东西向的夯土遗迹。虽然因发掘范围太小,尚缺乏推测相对时代的依据,不过从位于其北侧ER82的时代来看,ER83或与ER82同样为不晚于隋末唐初的夯土遗迹[21]。ER83与ER82的南北向夯土遗迹南端成垂直状连结,南距YSA0404TG4AL3约60米,蠡测或与隋江都宫的南垣相关。
(2)北垣
根据考古勘探结果和蜀岗古城内墙垣的分布情况,由于在城圈西北角(YZG1、YSTG2)、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YSNWM)及其东西两侧的YZG5、YZG3均发现有战国至隋或隋唐时期的遗存,故而在YZG5以东的三条线上开展了发掘,以明确蜀岗古城北城墙西段向东北延伸部分的时代属性以及其与宝祐城北城墙的关系。
①在蜀岗古城北城墙西段、中段及其与宋宝祐城北城墙西段西端连结处进行发掘,结果确认ER94东北现代道路以北的ER59为始筑于汉代的夯土遗迹、更东北的探区B0316内的相关遗存是不晚于杨吴时期的夯土遗迹和开挖于南宋时期的瓮城壕。
②在ER94向东延长线的东西向ER104(宋宝祐城北城墙东段)线上布设探沟进行了发掘,以探寻宝祐城墙垣之下是否还有更早期的墙垣迹象,结果明确了该ER104均为南宋时期夯筑,其内并无更早时期的墙垣遗存,夯土墙体之下地层为汉代文化层。
③在宝祐城北城墙以南约70米的ER8处布设探沟进行发掘,发现有打破生土的基槽迹象,地表上仅残存一层(难以确定是否为夯土遗迹)。遗迹面低于地下水位较多,未能完成发掘。
(3)东垣
为了探寻楚广陵城东西两部分中间隔墙、汉广陵宫城东垣、隋江都宫宫城和东城中间隔墙之所在,在蜀岗古城中部南北向的两条线上布设探沟开展了发掘。
①在宋宝祐城城圈东北角、东城墙、东南角开展了发掘,证明宝祐城东北角、东城墙均为南宋时期始筑,其下地层有汉代堆积;东南角最上层夯筑为南宋时期的。
②在宋宝祐城南城壕以外的其他城壕外围,有半环形围绕宝祐城的土垄,在ER42、ER9、ER63等三处选点布设探沟进行发掘的结果,表明其均为南宋时期的堆筑,与较早期墙垣无关。
(4)西垣
宫城西垣,或与蜀岗古城西城墙及其东侧的两条南北向线相关。关于蜀岗古城西城墙的发掘资料有YZG1、YZG2、YSTG1A︰1[22]等,虽然有隋唐时期城墙遗存,但由于宫城的范围并未确定,故而尚不能将之与宫城西垣等同。
为了探寻汉广陵宫城西垣、隋江都宫城西垣之所在,在南北向的两条线上进行了发掘。
①蜀岗古城西城墙东侧约300米的地点,布方发掘了ER64-ER65-ER68南北一线中的ER64,发掘结果表明,其当为不晚于南宋时期的建筑基址,上限或在六朝时期,在南宋及其后的时代被破坏殆尽。
②在上述南北一线东侧250米左右分布有ER48-ER13-ER50-ER77-ER78-ER82,依据蜀岗古城考古勘探的结果,在ER82和ER83连结处布设探沟(即前述的YSA0405T1A)进行了发掘。结果在ER82西侧探沟内找到了方向358°的南北向夯土遗迹和铺砖面,发掘出来的部分南北长2.35、东西宽0.85米,用砖宽16、厚4.5厘米或宽18、厚7.5厘米,部分砖面上有细绳纹。从铺砖面用砖规格、夯土内出土瓦砾和瓷片来看,夯筑时代或不晚于隋末唐初。南北向夯土迹象和铺砖面遗迹基本与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YSNWM)在南北一线上(门址稍偏西),蠡测其或与隋江都宫西垣或宫院隔墙相关。
2.东城墙垣的探寻发掘
蜀岗古城的东半部分,特别是东南隅地势低下,水位较高。基于考古勘探的结果,在蠡测为东城东南角、北垣的地点开展了探寻发掘,结果亦不理想。
(1)东南拐角
在蜀岗古城内东南隅的ER44东端布方发掘到了上、下两层夯土遗迹,上层的时代不早于晚唐;下层直接夯筑在生土之上,时代不早于隋。下层夯土的发现为探寻隋江都东城提供了线索。不早于晚唐的遗存,说明唐子城可能在东南隅修缮时使用了隋东城东南隅的城墙,而现知的蜀岗古城东南角明确有唐代夯土墙体。因此,蠡测由于前期城垣城壕的存在,特别是隋东城的残存,才形成了唐子城东、北、南三面或有双垣双濠,西面或为单垣(或亦有双濠)。可惜并未在此发现早于隋代的遗迹现象,未能找到探寻邗城和邗沟的线索[23]。
(2)北垣
在ER12一线,选点布设两条南北向探沟进行了发掘,确定均为生土,并且此处生土顶部海拔约为17米,而位于其西北的“北门”第二期城门遗存门道路面海拔约17.65米。因此,基本可以否定之前的勘探结果和相关蠡测。推测宫城北门玄武门若在“北门”以南,则东城北垣或即蜀岗古城北城墙东段。
(二)隋江都宫中轴线及位于其上的城门和宫门
隋江都宫城和东城理当依照规划营建,推测其宫城应有中轴线,主要道路亦应有迹可循。确定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对于探寻江都宫形制布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蜀岗南城门的位置基本确定,然而其向北的延伸情况不明。之前曾推测南城门北侧的堡城南路、雷塘路至宋宝祐城北门一线或亦为隋唐时期城址的中轴线,虽然1978年就在北城墙东段西部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模印有“北门”“北城门”“北门壁”的城砖,但再次探寻并找到“北门”,使得隋唐时期蜀岗城址中轴线最终明确的,是雷塘路东侧约60米的道路YSC0108TG4CL1的偶然发现。
为了验证南朝广陵城、隋江都宫的中轴线位置,还在蜀岗南城门,北门连线的东、西两侧选点进行了发掘,结果并未找到有南宋及其以前的道路迹象。
1.中轴线的探寻与确认
(1)蜀岗南城门
蜀岗南城门(YSNEM)遗迹位于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南端,该门址在南城墙中段中部,是汉晋广陵城南城墙所过之处,亦是南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唐子城、宋代堡城和宝祐城南城墙上的城门。已经考古发掘的是门址的西北部分和门道以南,揭露出了从早至晚的第一至第六期遗存。第一期遗存是城墙而非城门,或为汉代夯土墙体;第二、三、四、五期遗存有门道、柱础坑、散水等遗迹,门道(L3)从上至下可分为A、B、C、D四层,第六期为南宋时期。
其中的第四期遗存的遗迹最为丰富,城门规模最大,由L3B、基槽、加筑夯土、柱础坑、散水等构成。L3B见于L3C以北,路面上有一层含有白石灰膏和黄黏土的薄层,南北长4.2、东西宽2.3米,路面海拔19.5米,北端残存门槛石痕迹。L3B东侧,东西向基槽揭露出来的部分东西长3.85、南北宽0.7米,南北向基槽揭露出来的部分南北长3.55、东西残宽0.6米;L3B西侧,东西向基槽东西残长1.2、南北宽0.65米(西部被踩踏面叠压),南北向基槽揭露出来的部分南北长3.4、东西残宽0.5米。L3B两侧揭露出了南北0.65、东西0.6米的柱础坑17个,东侧11个(南北向6个,最北端的柱础坑以东又有东西向的5个)、西侧6个(南北向4个,南部似还有1个;最北端的柱础坑以西仅揭露出来1个),柱础坑边缘残存含有石灰膏的黄黏土。L3B以东柱础坑北侧用砖瓦砾铺成的散水2东西4、南北2米,顶面海拔19.6米。门道宽约4.15米,方向178°,较之第一期夯土墙体北侧向北伸出4.35米。从该门址遗迹之间的叠压关系,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来看,第四期遗存当与隋江都宫的南城门相关;从既有考古发掘和勘探结果来看,该城门在隋唐时期很可能有三个门道。
(2)雷塘路东侧南北向道路
为了探寻城址内的南北向隔墙,在位于雷塘路东侧、前述ER8以南并与之在南北一线上的ER7处布设探沟发掘,结果并未找到夯土迹象,但偶然发现了道路(YSC0108TG4CL1)遗迹。该道路方向约10°,残存呈西南—东北方向的11道车辙。路面上6道车辙宽0.15~0.35、深0.10~0.20米,路面下5道车辙打破生土,推测其时代或不晚于宋代。从其直接叠压生土、路面下车辙打破生土的情况来看,推测其或与蜀岗古城内南北向的主干道相关。
(3)蜀岗北城门(“北门”)
雷塘路东侧道路YSC0108TG4CL1向北延长线与北城墙东段的交叉点,恰好就在先前找到的有“北门”文字城砖的位置附近,遂决定再次探寻位于北城墙东段西部的北城门。2016年,在1978年发掘区的东侧布设探沟发掘,明确了夯土墙体的沿革,并发现了与城墙呈垂直方向的道路遗迹;2017年全面布方发掘,揭露出了“北门”遗址(YSNEM)。该门址是一座由墩台、门墩、门道、马道等构成的汉—南宋时期的城门遗构,门道内叠压有三期道路(自上而下编号L1—L3),分别属于汉代、六朝时期、南宋时期。
尽管在该城门的门道内并未发现有明确属于隋代的遗存,然而从门道废弃年代不晚于杨吴时期的情况来看,该城门在隋江都宫时期依然使用。结合文献来看,该城门可能不是江都宫城的北门“玄武门”,不过其当与隋江都宫中轴线北端的城门相关。
2.中轴线上的城门、宫门
虽然蜀岗南城门(YSNM)或并非“江都门”,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北门”,YSNEM)或亦非“玄武门”,然而蜀岗南城门、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北门”)位置的确定,以及其间南北向道路的发现,说明蜀岗南城门(YSNM)—雷塘路东侧南北向道路(YSC0108TG4CL1)—“北门”(YSNEM)这条连线很有可能就是隋江都宫的中轴线。
(1)江都门
江都门或亦称“行台门”,抑或与行台门无关。从其名称及“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的记载来看,其是隋江都宫城南门的可能性甚大。蜀岗南城门以南陡然低下,蜀岗古城南城墙呈西南—东北走向,屯于东城的叛军可从东城西进至江都门前,而江都门当在隋江都宫的中轴线上,因此推测江都门或当位于蜀岗南城门以北至成象殿宫院南门之间的中轴线上。
蜀岗古城地面调查工作中,在南城门以北、堡城南路西侧发现有用隋唐时期莲花纹础石立于宅邸冲道路的东南角,据房主介绍其家在修建时地下曾发现较多成排石础。
(2)成象殿宫院的南门和北门
据《说郛》卷一百十上记载:“(大业)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大会设庭燎于江都门朝诸侯。成象殿即隋江都宫正殿,南有成象门,门南即江都门。”[24]《说郛》是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所编纂的文言大丛书,其时代较晚。从文献记载来看,成象殿宫院的东侧门或称“东门”,因此该宫院南侧的宫门有无专有名称尚需确认,或可称作“南门”或“成象门”。
由于推测或与成象殿宫院及其北垣相关的位置处征地未果,故而仅在其北侧、西侧进行了发掘。北侧为间隔很近的两条南北向的排水沟,时代暂定为不晚于南宋;西侧有不晚于南宋、推测为汉晋时期的建筑基址,被南宋时期的东西向水沟破坏殆尽。
综合来看,位于隋江都宫中轴线上的城门、宫门、建筑等,从南向北依次或为:蜀岗南城门—江都门—成象殿宫院南门—成象殿宫院北门—温室—玄武门—蜀岗古城“北门”。至于成象殿宫院北侧是否还有其他位于中轴线上的宫院,目前尚无线索。
从江都事变相关记事的文脉来看,成象殿北门似与玄武门有关。《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迹二》:“隋炀帝宫在县北五里……其宫城东偏门曰芳林,又有元武、元览诸门,皆宫门也。中有成象殿及流珠堂诸处(《舆地纪胜》)。”此处的“元”当为避清圣祖康熙名讳中的“玄”字,故原应为“玄武”“玄览”。谓其“皆宫门也”,似也认为隋江都宫之玄武门并非外城之门。《长安志》“唐禁苑图(内苑附)”和“唐宫城图”中有“元武门”[25],《唐两京城坊考》“东都宫城皇城图”中的隋唐洛阳宫城北有玄武门[26],“元武门”应即“玄武门”,隋江都宫的“元武”门亦即宫城的正北门“玄武门”。
另外,《资治通鉴》中说叛军是从玄武门进入宫城的,而裴虔通搜索皇帝的路线,似有从东向西、从南往北的倾向。那么就需要注意到,若叛军从宫城北门玄武门进入宫城,何以先进入成象殿,然后再反过来向北、向西搜索;若隋炀帝所奔之西阁位于成象殿之前或之后,裴虔通的搜索路线因何绕行作成象殿—左阁—永巷—西阁;若隋炀帝所奔之西阁是玄武门之西阁,那么既然叛军从玄武门进,隋炀帝为何还要奔至此阁,叛军又因何在当时并没有及时发现……诸多问题,不得甚解。叛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再绕行到成象殿东门进入成象殿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然而若叛军从宫城东门进入宫城,则有的问题似乎可以解释。
(三)隋江都宫中轴线上之外的城门、宫墙和宫门
除了中轴线上的城门,江都兵变相关记事中提及的城门或宫门还有芳林门、东门。
1.城门
从蜀岗古城相关考古发掘结果、城门和城内道路分布状况来看,隋江都宫和东城当是以南朝广陵城为基础修缮而成的,城门和城内道路体系或无较大变化。
(1)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
该门址(YSNWM)与十字街西南隅南北向道路(YSA0405TG4CL1)基本在南北一线上,包含不晚于汉代的木构水涵洞、汉至晚唐杨吴时期的陆城门东边壁和水窦、南宋时期的水关和陆城门等八期遗存,从用砖和地层叠压关系判断,第四、第五期遗存属于隋唐时期。
第四期遗存,为陆城门东边壁和内侧填垫夯土。陆城门东边壁,仅存东边壁南端,方向约334°。边壁砌砖部分宽约0.3、残存1.5、可复原残长约5.3米,其内侧填垫夯土带宽约0.45米。用砖有长34、宽16、厚6厘米的,也有长27、宽13或14、厚4厘米的。本期可能基本沿用前期城门,陆城门内口砌砖局部打破前期遗存,并在前期陆城门内口略北处折向东南,相关的夯土墙体亦弧形折向东南,可知本期陆城门内口与前期陆城门的形制不同。
第五期遗存,为陆城门外口东侧的包边砖墙及其东、南内侧的填垫土,砖墙北部有性质不明的侧斜铺砖面。砖墙方向约98°,向北倾斜且有收分,垒砌方法不规律,用黄黏土作黏合剂。存长约1.1、宽0.3米。用砖有长34、宽16、厚6厘米的,也有长27、宽14、厚4厘米或长27、宽13、厚3.5厘米的,其中有残长20、厚4.5厘米的钱纹墓砖一块。
《隋书》和《北史》中均记载道:“宇文化及弒逆之际,(燕王杨)倓觉变,欲入奏,恐露其事,因与梁公萧巨、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卒中恶,命县俄顷,请得面辞,死无所恨。’冀以见帝,为司宫者所遏,竟不得闻。俄而难作,为贼所害,时年十六。”《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中有:“燕王倓觉有变,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人,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意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这两条文献说明,隋江都宫城正北门亦称玄武门,玄武门附近有“芳林门”,芳林门侧有水窦。
从该门址的内涵和蜀岗古城内的河道分布情况来看,流经该门址西侧水窦的河道当从战国楚广陵城时期一直存续到宋宝祐城时期,至今仍然是堡城村向北排水的唯一水口。因此,拙见以为江都城之芳林门位于北城墙西段上的可能性较高。尽管《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一《古迹二》中说“宫城东偏门曰芳林(《舆地纪胜》)。”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芳林”之名,指出其与“华林”有关,最早称作“芳林”,后因避讳齐王曹芳之“芳”字而改称“华林”,北周时期可能复称“芳林”,唐宋时期又恢复了“芳林”园的称谓;曹魏和北魏洛阳城芳(华)林园位于城北,东魏邺南城华林园也位于城北,而南朝建康城的华(芳)林园则位于城东偏北的位置;隋继北周而兴,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芳林门位于玄武门之西的北城墙上,隋江都宫城的“芳林门”可能位于北城墙[27]。由此推测,隋江都宫应与隋大兴城有较多的一致性,或不会有较多的建康城因素。并且,无论隋江都宫的芳林门是在北城墙还是东城墙上,“芳林门”的名称都表明隋江都宫是具有都城规格的宫城。
《资治通鉴》中记述叛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说明玄武门以北地带不在宫城内(或属于东城)、玄武门或在蜀岗古城“北门”以南的宫城中轴线上(即“北门”并非玄武门)。并且,燕王倓从“芳林门”入城之后至玄武门被“遏”,若《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所说“宫城东偏门曰芳林(《舆地纪胜》)”无误,宫城东垣上就至少有两座宫门,“芳林门”或在“东华门”以北的宫城东墙上。也就是说,杨倓从芳林门侧水窦先进入了宫城,在玄武门以南的成象殿宫院未找到皇帝,再向北到玄武门才被阻止,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并且,若杨倓是从东城出发,经“宫城东偏门”侧的水窦才进入了宫城,则说明宫城东墙的东侧就是东城,且芳林门此时已被叛军控制,那么叛军因何不从已经掌控的宫城东侧偏门芳林门入宫,而一定要绕行到玄武门去,就依然是个问题,除非明确知道皇帝在玄武门一带。然而,熟知宫内情况的裴虔通却首先是在成象殿宫院去搜寻皇帝,然后才向北搜索,似乎亦有不合情理之处。总之,不管隋炀帝在江都兵变之前是在成象殿宫院还是玄武门一带,芳林门是宫城东偏门的说法还需要商榷。
(2)其他城门
如上所述,隋江都宫是有中轴线的。而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又可以观察到各有一条南北向的轴线。西侧轴线的北端已经证明是有城门的,而南城墙西段上恰好又有与之南北对应的豁口(俗称“梁家楼”,包含有用砖甃城的萧梁之“梁”字);东侧轴线的北端(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虽然尚未找到城门迹象,但是此处俗称“迎淮大道”,而与之对应的南城墙东段上(汉广陵王墓博物馆东侧)亦有豁口,并且其间现在仍有道路相通。管见以为,诸多“巧合”或可为相关城门、城内南北向轴线的探寻提供线索。
为了探寻中轴线东侧轴线的南端、或隋江都宫城东南城角的位置,在推定为南城墙东段的豁口以东北侧的东、西两个区域布设探沟进行了发掘(即YSD1005T1D、YSD1104TG2F—YSD1104TG4F)。在东部发掘区找到了不晚于唐代的壕沟1条,因发掘区域所限,壕沟的宽度、方向以及是否有城墙等均未能清楚,尚待今后解明。在西部发掘区内找到了不晚于唐代的存深11.15、口宽1.2、底宽约1米的水井一口,井口海拔19米;未发现东部发掘区的壕沟,推测壕沟向西延伸的部分应该在西部发掘区以北,故亦有待今后发掘;出土瓦当、板瓦等建筑构件较多,或与不晚于唐代的城门相关;还发现有早于唐代的建筑基槽,槽内所填建筑构件多为汉晋时期的。
至于就城圈上西城门、东城门的推测,虽然现今地表上似仍可见相关迹象,然而由于尚未开展相应的考古发掘来验证,在此不再探讨。
2.其他宫门
《资治通鉴》中说裴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推测此“东门”为成象殿宫院之东门的可能性较大。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道:“(隋炀帝)宫城东偏门曰芳林,又有元武、元览诸门,皆宫门也(《舆地纪胜》)。”如上所述,“元览”或原为“玄览”[28],然隋唐两京未见有“元览门”或者“玄览门”,仅《长安志》“唐大明宫图东内苑附”北墙上的东部有“元化门”,若隋江都宫确有称作“元览”之宫门,或可由此蠡测其为北宫门东侧的宫门。
另外,今堡城西路通过蜀岗古城西城墙的豁口俗称“西华门”,其名称或与京师八门之“西华门”[29]相关;且有“西华门”则当有“东华门”,“西华门”“东华门”应与宫城东、西两侧的宫门相关。隋江都宫西华门的位置,推测位于该豁口东侧堡城西路上的可能性较大。
(四)隋江都宫内城门之外的主要建筑物
叛军弑君所经路线:东城、宫门、成象殿、左阁、永巷、西阁。《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说隋江都宫内有水精殿(隋帝于江都宫水精殿,令宫人戴通天百叶冠子插瑟瑟钿朵,皆垂珠翠,披紫罗帔,把半月雉扇子,靸瑞鸠头履子,谓之“仙飞”)、西阁、彭城阁(旧为彭城村,炀帝因以名阁。先是开皇末有“泥彭城口”之谣,宇文化及作乱,帝果遇害于是阁。《隋书》言“温室”,或阁内有温室也),成象殿南门为成象门,再南有江都门[30]。
另据《嘉庆一统志》:“江苏省扬州府古迹:临江宫在江都县南二十里,隋大业七年,炀帝升钓台临扬子津,大燕百僚,寻建临江宫于此。显福宫在甘泉县东北,隋城外离宫……江都宫在甘泉县西七里,故广陵城内。中有成象殿,水精殿及流珠堂,皆隋炀帝建……十宫在甘泉县北五里,隋炀帝建。《寰宇记》:十宫在江都县北五里,长阜苑内,依林傍涧,高跨冈阜,随城形置焉。曰归雁、回流、九里、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31]
从相关文献中均提及成象殿之名来看,成象殿为江都宫中最为重要的正殿,围绕成象殿的有左阁、永巷、西阁、温室、西院、流珠堂等。
1.成象殿
所谓成象,据《易·系辞上》:“在天曰成象,在地曰成形”,韩康伯注:“象况日月星辰。”孔颖达疏:“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能用代表日月星辰的名称作为宫殿之名,当然应与天子有关。相关文献中“江都宫”“宫城”“成象殿”等名称的使用、“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32]的规定,都反映出隋江都宫是座规格甚高,近乎都城级的行都。成象殿作为隋江都宫正殿,当东西向横亘在中轴线之上,推测其或位于堡城村十字街交汇口略偏东北之处。
成象殿北侧是否还有其他宫院的问题,尚缺乏用于探讨的必需资料。叛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到进入成象殿之间缺乏记载。不过,从蜀岗古城的中轴线长度即南北向空间来看,推测成象殿之后或还有宫院,若与水精殿相关或可暂称作水精宫院。
2.成象殿周边建筑物
主要有左阁、永巷、西阁、温室、西院、流珠堂等名称。从相关记载来看,搜索皇帝的领头人是熟知宫内情况的裴虔通,其搜索前进的路线较为清楚,因此可以基本排除多行人到处搜索的可能性。换言之,从裴虔通的行进路线上,可以看到隋江都宫核心地带的面貌。
裴虔通在成象殿未找到皇帝,遂到“左阁”搜索。按照中国古代前南后北、左东右西[33]的方位概念,左阁或即成象殿东侧之阁。
裴虔通在左阁仍未见到皇帝,遂“驰入永巷”。西晋左思《魏都赋》中有“于后则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推测永巷当在成象殿之北,且或与左阁连通。
在永巷一带,有“美人”告知裴虔通,皇帝“在西阁”。“西阁”是玄武门之阁,还是成象殿后之殿阁,还是成象殿前右(西)侧之阁,尚需探讨。若“左阁”为成象殿东侧之阁名,那么成象殿西侧之阁名或可作“右阁”。从左阁—永巷—西阁的路线来看,西阁在成象殿以北之西侧的可能性较大,此亦合左东右西之理;或可认为“西阁”与“右阁”并非一阁,蠡测“西阁”或为成象殿后面(北侧)西侧之阁名。
隋炀帝“崩于温室”。关于温室,《魏都赋》中亦有“丹青焕炳,特有温室”之句,“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中有温室[34]。从曹魏邺城宫中温室的位置来看,隋江都宫中的温室或在成象殿与其后宫殿的隔墙中部一带。
“流珠堂”之名,史籍和隋炀帝墓志文中均有之。炀帝崩于温室,流珠堂在西院,推测西院或在温室之西,或为成象殿后(北)侧宫院的西侧院落。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提到的隋江都宫水精殿之所在,尚毫无线索,不过,若《嘉庆一统志》所载有源,按照其记载的成象殿、水精殿、温室的顺序,水精殿或为仅次于成象殿的宫殿。
(五)隋江都宫内中轴线以外的其他主要道路或轴线
从蜀岗古城的范围、中轴线位置未发生变化等情况综合来看,隋江都宫城内的主要道路体系或亦与南朝广陵城的主要道路近似。从隋江都宫城门、城内道路等相关遗迹观察其主要道路或轴线的分布情况,可知隋江都宫城的中轴线是基本明确的,中轴线西侧的南北向轴线似隐似现,并且这两条轴线与蜀岗古城范围内的地貌地势也是较为一致的。虽然城址东部的面貌分析尚缺乏有力的线索,但综合地势观察来看,蠡测东部或亦有一条南北向轴线,隋江都宫或有包含中轴线在内的三条南北向轴线。至于隋江都宫的东西向轴线,管见以为,在城址内的中部、南部各有一条,或均不在东西一线上,虽不甚清晰,然或可成立;蠡测北部或还有一条东西向轴线,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继续探寻。上述六条轴线或以宫城为中心分布,至于其与蜀岗古城城圈的关系,尚需通过考古发掘来明确。
推测或与隋江都宫相关的道路,除了前述中轴线上的YSC0108TG4CL1之外,还有位于十字街西南隅的两条道路。
1.十字街西南隅南北向道路
编号YSA0405TG4CL1,存厚0.3~0.45米,残存多道车辙,路面宽度当大于揭露出来的7.5米。揭露出来的路面时代为南宋时期,其向北的延长线与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YSNWM)中南宋晚期柱排、汉—唐门道东边壁的连线角度分别为355°、357°,与宝祐城东城墙的偏角较为接近。推测其下或附近可能有通往YSNWM、与YSA0404TG4AL3向西的延长线形成十字路口的更早时期的道路遗迹。另外,该道路西侧20余米即上述ER82处的南北向夯土遗迹,其或与宫城西墙内(东)侧的道路相关。
2.十字街西南隅东西向道路
编号YSA0404TG4AL1—L3,为叠压着的上、中、下三层道路(从上至下分别编为L1、L2、L3)。其中L3为砖铺道路,方向87°,揭露出来的部分西高东低倾斜约5°。砖铺道路,宽2.58米,由路面和路牙组成。路面规整,宽2.33米,用边长33、厚7.5厘米的素面方砖平铺而成,东西向七排砖,南北向砖缝错缝;路牙宽0.125米,用长35、宽18、厚6厘米的两排侧立条砖错缝砌成;砖之间的黏合剂均为黄黏土。素面方砖多已残碎,个别铺砖上似有文字。从地层关系、道路用砖和铺砌规整的情况来看,L3铺砌的年代当在隋唐时期,其或与大型建筑附近的道路相关,亦或与江都门南侧的东西向道路相关。
(六)隋江都宫周边的重要遗址或名称
隋炀帝《泛龙舟》诗中有:“舳舮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明确说明了“扬州”位于淮南、江北、海西。与扬州相关的诗词很多,与隋江都宫周边离宫别院相关的文字也很多,《嘉靖惟扬志》“隋唐扬州图”中有“隋炀帝陵”“九曲池”“雷陂”等。另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江都有显阳宫[35];城东茱萸湾有北宫(后改为山光寺)、城外(东)有显福宫;城西长阜苑内有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大雷宫、小雷宫、春草宫、九华宫、光汾宫等九宫,或加枫林宫为十宫;城西南或有萤苑,九曲池上有木兰亭;再往西北或在大仪乡有上林苑;长江北岸边的杨子津有临江宫(扬子宫),宫中有凝晖殿、元珠阁[36]。以下,仅列举与隋江都宫关系较深的隋炀帝墓、栖灵塔。
1.扬州曹庄隋炀帝墓
隋炀帝墓与隋江都宫相关的地名,有与蜀岗古城西南角相关的迷楼及其西侧的吴公台、雷塘等地名。《嘉靖惟扬志》“隋唐扬州图”[37]中的“炀帝陵”位于“九曲池”的西北、“雷陂”的西侧,相对位置接近于曹庄隋炀帝墓之所在。似乎说明直至明代,隋炀帝陵的位置认知并未错误,而是因为清代阮元的错误考证才出现了隋炀帝陵位置的错误。
(1)吴公台
刘宋沈庆之为平定竟陵王刘诞之反叛而在广陵城外筑台,后来南陈吴明彻围攻北齐敬子猷增筑此台以射城内,故名“吴公台”。《资治通鉴》中有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的记载,陈稜葬隋炀帝当为旧臣葬旧主之行为。
从广陵城城圈及其周边地势来看,北城墙一线较之更北侧地势明显高起,东城墙外侧的城壕较宽,蜀岗南缘的高地被称作“峰”,西城墙外最近的高地就是北宋欧阳修所建之平山堂、南宋平山堂城及其西侧的大明寺所在之地。因此,推测吴公台可能位于蜀岗西峰附近,相关研究也可为楚汉六朝广陵城南城墙位置的探寻或确认提供重要的线索。
(2)雷塘和迷楼
雷塘,又称雷陂,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扬州历史沿革较长的地名之一,涉及扬州的历史文献中多见雷塘之名。《汉书》中就说有“(江都王)建游章台宫……后游雷波(陂)”[38];《扬州水道记》十张附图中从“图一吴沟通江淮图”至“图八宋湖东接筑长堤图”[39],雷塘皆为广陵地区北部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地名。
唐代杜牧《扬州三首》其一中有“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宋代曹勋《迷楼歌》中有:“炀帝爱迷楼,死葬迷楼北。”从诗文来看,隋炀帝葬于雷塘,其位置与迷楼位置相关。关于迷楼的位置,基本认为在蜀岗古城西南角或其附近。因此,唐、宋时期诗文中隋炀帝墓与迷楼相关的诗句,说明隋炀帝墓与隋江都宫的位置关系是陵在城的西或西南方,这与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与隋江都宫的位置关系是一致的。换言之,隋江都宫之西或西南方或也有与雷塘相关之地名,这与曹庄隋炀帝墓附近有“西雷塘”之俗称不谋而合。文献记载中雷塘有上、中、下之分,均位于蜀岗古城以北,清代阮元所定之位于蜀岗古城以北的雷塘(今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雷塘北侧)隋炀帝陵,基本可以说是因雷塘之地名及古冢位置之巧合而讹成。
(3)出土遗物与隋江都宫的关系
扬州曹庄隋唐砖室墓包含三座墓葬,其中M1为隋炀帝墓,M2为萧后墓,M3时代接近于萧后墓[40]。曹庄M1用砖为南朝墓砖和隋江都宫用城砖,墓葬形制、砌法,与扬州南朝时期墓葬的共性较多;曹庄M2的平面形状呈腰鼓形,为扬州初唐时期的墓葬形制,其用砖规格、装饰、烧制等带有扬州地区初唐至中唐时期砖的特点[41]。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用砖资料,与扬州城遗址用砖可互证,说明对遗址中出土砖的时代判断是基本可信的,蜀岗城圈西北角内侧的楔形砖确为隋代城砖。
曹庄M1的形制、用砖等表现出较多的南北朝时期特点,与唐代墓制差异较大,而“隋炀帝墓志”文中却明确有贞观年号;并且,曹庄M1距离蜀岗古城西城墙一公里余。究其原因,管见以为,扬州曹庄隋炀帝墓很可能就是陈稜下葬隋炀帝之地,亦即是杜牧所说的“雷塘土”之地,贞观时期只是将萧后合葬至此。
另外,扬州曹庄隋炀帝墓出土有4件直径达26厘米的鎏金铜铺首,其尺寸与西安大明宫出土铜铺首[42]相近。鎏金铜铺首很大,其制作工艺精致,流程相当复杂,并非短时期内即能制作出来。萧后与宫人殡炀帝时,撤漆床板为小棺,当并未使用此等铺首;陈稜葬炀帝时,虽为旧臣葬旧主,但此时专门制作如此规格的鎏金铜铺首去装设于棺椁上的可能性较小;唐武德或贞观时期的葬或合葬,制作隋炀帝专用棺椁的可能性亦不大。因此,该鎏金铜铺首是否与隋江都宫之物相关,是否为唐初改葬所制[43],都依然还是需要探讨研究的问题。
2.诗文志书中提及的建筑物
(1)栖灵塔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于大明寺内建栖灵塔,塔高九层,雄踞蜀冈,塔内供奉佛骨,谓之佛祖即在此处。本焚僧大觉遗灵之言,故称“栖灵塔”。与栖灵塔相关的诗有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白居易《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等。栖灵塔位于隋江都宫西南角西侧,从其上可俯瞰隋江都宫,其位置所在是蜀岗古城外围最高之处。
(2)九曲池
《嘉靖惟扬志》“隋唐扬州图”中有“九曲池”,其当与从西向东流来的浊河相关,亦当与蜀岗古城南城壕相关。从长江北岸线逐渐由蜀岗南缘向南退至今之江线来看,早期的九曲池甚至可能与长江漫滩、邗沟等相关。随着隋唐时期城市向南发展,池水面逐渐缩小,《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中宋宝祐城东南拐角外侧的德胜湖或亦与之相关。
三、结语
从蜀岗古城相关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汉唐时期的城圈(包含汉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唐子城等时期)或相同,城门和城内道路也多见沿用或层叠的现象,因此推测隋江都宫及东城当是基本沿袭了之前广陵城的范围和主要道路网。
与隋江都宫相关的都宫、东城、成象殿、温室、永巷、玄武门、芳林门、江都门、行台门等名称,都说明隋江都宫城门和主要殿阁名称与都城规制关联性较强;“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的规定,则说明隋江都宫的规格甚高;曹庄隋炀帝墓的发现,使得扬州因有了帝陵而俨然都城形制;另据文献记载,隋江都除了江都宫之外,还有隋十宫、临江宫等宫苑,虽然时日不长,但隋江都宫亦曾一度达到行都的规模。这些,都说明隋江都宫的规模远非一般地方城市所能比拟,虽然最多只能算是一座“行都”,然而在当时是一座都城级的城市。
隋江都宫使用时期,隋炀帝除了继续开邗沟通淮南运河之外,还开掘沟,将扬州向东至如皋蟠溪的运盐河再向东延伸到了如东[44],使得扬州成为运河咽颐之地,确立了南北朝以来广陵地区作为“四会五达之庄”[45]的地位。隋炀帝时期的江都宫,作为东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成为强化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融的中心。
[1]唐·魏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65、75、90页。
[2]同[1],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第1888—1889页。
[3]a.同[1],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四,第1438页;b.唐·李延寿:《北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2475页。
[4]同[1],卷四《炀帝纪下》,第93—94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776—5782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3—27页。
[7]汪勃、王睿、王小迎:《扬州蜀岗古城址的木构及其他遗存——从一个地点的考古发掘认识扬州城的1700年历史》,《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27日第4版专题。
[8]国家文物局主编:《2017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13—117页。
[9]2011年的蜀岗南城门遗址南缘的发掘结果,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6—89页;蜀岗南城门西北隅的发掘结果,参见《蜀岗古城遗址南门考古重大发现》,《扬州晚报》12月9日A5版。由于整个扬州城遗址的南城门不止一座,而蜀岗古城或仅有一座南城门,故定名为“蜀岗南城门遗址”;并且,由于该城门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不尽相同,文献中又有“南门”之名,因此本文中“南城门”的内涵包括不同时期的该城门,而“南门”一名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称谓。此定名方式,亦适用于“北城门”“北门”。
[10]位于十字街西南隅的东西向道路遗迹的发掘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三处道路遗迹发掘简报》,《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
[11]a.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十九《文五王竟陵王诞》,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4—2036页;b.唐·李延寿:《南史》卷十四《竟陵王诞》,中华书局1975年,第397—399页。
[12]关于南北朝以后内外城形制,郭湖生《子城制度》一文收集了极为全面的文献资料,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五十七册(1985年3月),后收入《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增订再版,台北空间出版社2003年,第145—164页)。
[13]余国江:《扬州读史小札》,扬州博物馆编《江淮文化论丛》(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14]a.汪勃:《隋江都与隋炀帝墓砖》,《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3页;b.汪勃:《扬州城的沿革发展及其城市文化》,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9—537页。
[15]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页。
[16]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25页。
[17]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18]霍宏伟:《隋唐洛阳东城形制布局的演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10月,第115—126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图一一、插页附图。以下与勘探迹象相关的部分均出自该报告,不再注释。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西南隅勘探夯土迹象的发掘》,《扬州文物考古》待刊。
[21]汪勃、王小迎、王睿、束家平、池军、张富泉:《扬州市蜀岗古城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17—118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扬州市蜀岗古代城址西城壕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9期。
[23]汪勃:《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1999~2015年)》,《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59页。
[24]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75页。
[25]宋·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296—297页“唐禁苑图”,第300—301页“唐宫城图”。
[26]同[16],第25页。
[27]汪勃:《汉代有无华林园及天泉池考——史籍中所见芳(华)林园及天渊(泉)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5—256页。
[28]明·张居正《七贤咏》(《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5页)序中有:“虽不敢谓独契古心,庶亦不移流俗,亦冀元览达观君子,有以明余之志焉。”清·蒋士铨《桂林霜·叛噬》(《蒋士铨戏曲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04页)中有:“你逆天悖主公然敢,更说甚苍苍元览。”
[29]明·刘若愚《酌中志·大内规制纪略》:“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南二重曰端门,三重曰午门;魏闕两分,曰左掖门、右掖门;转而向东,曰东华门,向西曰西华门,向北曰元武门。此内围之八门也。”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页。
[30]清·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等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一江都县》、《古迹二甘泉县》),广陵书社2006年,第474—512页。
[31]清·穆彰阿等纂修:《嘉庆一统志表》,商务印书馆1935年。
[32]同[1],卷三《炀帝纪上》,大业六年六月甲寅,第75页。
[33]汪勃:《四神的方位及其首尾方向》,《碑林集刊》第7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四神图的位置原则上均遵从“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即“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这一古代的方位概念。
[34]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及图下文字说明之“14.温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5]“显阳宫”的名称,或与汉广陵王显阳殿相关,所在位置不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476页有:“显阳殿汉厉王胥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八子随左右,等鼓瑟歌舞。”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第2762页,卷六十三《广陵厉王胥传》,有广陵王刘胥“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的记载。
[36]a.同[30];b.唐·杜宝《大业杂记》:“(大业二年)二月,大驾出杨子,幸临江宫,大会,赐百僚赤钱于凝晖殿蒲戏为乐。”
[37]明·朱怀干修、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广陵书社2013年,卷之一郡邑古今图“古扬州图”“隋唐扬州图”。
[38]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三《江都易王非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4、2415页。
[39]清·刘文淇:《扬州水道记》(扬州地方文献丛书)序后插页图一至图十,广陵书社2011年。原著所附之图的图名中均无“附”字,为了简单明了地表示其是《扬州水道记》所附之图并避免误解,本文中在原图号之前冠以“附”字。
[40]扬州曹庄M1、M2的资料,参见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曹庄M3为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41]汪勃:《隋江都与隋炀帝墓砖》,洪军主编《隋炀帝与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第26—35页。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
[43]余国江认为:“隋炀帝墓中出土的鎏金铜铺首与江都宫有关的可能性很小”,“这种大型鎏金铜铺首正与隋炀帝帝王的身份相吻合,应该是唐初改葬时制作的。”余国江:《隋炀帝墓出土鎏金铜铺首小识》,《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4期。
[44]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开成三年,838年)七月十八日条记载:“掘沟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
[45]《四部备要·集部》,汉魏六朝别集,鲍氏集,卷一,芜城赋,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鲍照(414—466年)登劫后之广陵城,有感而作《芜城赋》,其中有“重关复江之隩,四会五达之庄”之句,广陵城在汉六朝时期的交通体系中已逐步成为“四会五达之庄”,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而确立了扬州城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