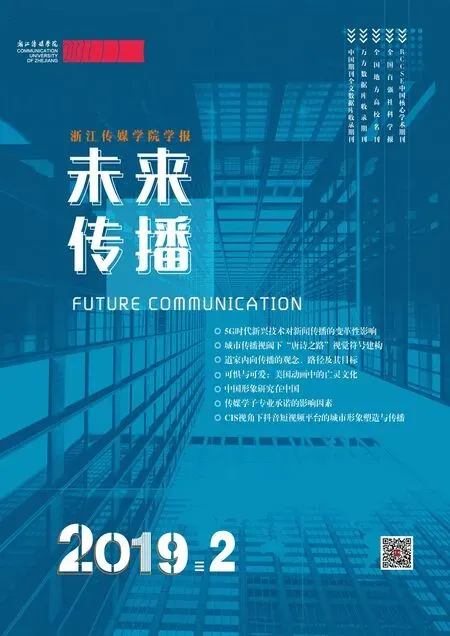“丝绸之路影视桥”的平等传播姿态
——一种电视节目模式“共造”的机遇
陶 冶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战略意义重大。有许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文化先行,以实现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发挥文化的先行优势,通过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大力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是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与策略”[1]。亦有学者认为古丝绸之路的建设“便有着文化先行的成功经验”[2],甚至举出了张骞通西域与郑和下西洋的例子。2014年,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工作的配套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2014—2020年规划》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提出。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我们制作、翻译了一批优秀的节目,开拓了新的传播渠道,开展了中阿广播电视节目交流项目,甚至培养了一大批固定的海外观众群体。然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丝绸之路影视桥”的建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心相通”,显然还有着更巨大的拓展空间。
另一方面,广播影视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中扮演了“战略解读者、政策践行者和文化传播者”[3]三种角色,不仅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广播影视在“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中的作用。其中,广播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国均是传播力最广的大众通俗文艺形式,尤其是欧美国家近年来对世界各国广泛输出的电视节目模式,极大地改变了输入地电视节目内容的面貌,同时也使得韩国、日本等电视节目模式输出的后起之秀在经济上获益,并进一步提升了各自的国家形象。2013年起,我国电视荧屏上充满了《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X音素》(X Factor)、《舞林争霸》(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Stars)、《急速前进》(The Amazing Race)等各类节目模式的中国版。那么,通过“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建设的契机,是否可以推动我国电视节目模式创新进而“走出去”呢?
一、“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再造”的陷阱
众所周知,在远早于“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开始建设之前,电视节目模式作为文化产品的交易活动便长期存在。根据著名节目公司Granada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其实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模式输入市场,英国则是最大的节目模式出口国,占据了所有模式节目播出时间的45%。[4]表面上看,是英国、荷兰、瑞典等输出节目模式给美国,其实,任何企图向全球市场推广的节目模式必然要接受美国收视市场的检验。换言之,各国研发的电视节目模式必须在美国市场上经过一次“美国化”的意识形态改造,方才具备向世界各地销售的政治许可。伦敦城市大学教授滕斯拖尔(Jeremy Tunstall)将这套节目模式交易体系命名为“盎格鲁—美利坚”体系。[5]这一概念于1999年一经提出,便成为英美两国电视研究学界的共识。在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建立了一整套以BBC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模式,而西岸的美国则建立了一套完全基于商业自主的广电模式。滕斯拖尔却认为这两种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政体,而是一个市场”。[5](50)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和欧洲已经完全占据了WTO、IMF和世界银行的全部主导权,而这一切正是以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并因此推动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6]而建构的。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范畴内,“盎格鲁—美利坚”体系表面上依然是一种在WTO框架下运行的商业交易体系,哪怕是接受方的观众发现这一体系带来的节目是异质文化的“他者”,也很难确认这个“他者”到底是谁——特别是面对以荷兰、瑞典、以色列为代表的诸多欧洲国家研发的节目模式的时候。但是,经济的检验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改造一并进入了“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从而使接受方的受众主观上产生对英美文化的接受——如不经特别说明,绝大多数接受方的受众均认为《XX好声音》或者《幸存者》这些节目来自英国和美国,而完全不知其原创国其实是荷兰和瑞典。另一方面,电视节目表面上存在作为文化“产品”来进行交易的经济属性,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其作为“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故而输入国不可避免会带有警惕,并在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的时候设置意识形态的把关人,此时通过WTO的体系打着贸易平等的旗号就成为了突破这道屏障的利剑。
就节目模式本身而言,其核心的概念是“再造”(Reproduce)——正如以色列学者波登(Jérme Bourdon)所认为的那样,“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是一种“硬拷贝”且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对其的一种“离散的适配性”[7]。换言之,这种“再造”具备插即用的特性。如果我们将内容与形式拆分开来的话就会发现,本土内容其实已然包裹在一种意识形态上高度“美国化”的形式中。比如,我国引进节目模式的《中国好声音》,其原版中椅子背后听着歌声选学员的明星歌手被称为“coach”即教练,而随着节目的深入是四个“教练”带着自己的“队员”与其他对手进行比赛。但是经由中国创作者本土化再造后,“教练”被改称为“导师”,“队员”也成了“学员”,这恰恰是因为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对一夜成名存在着普遍的不认同,同时又强调在“成才”的道路上“导师”的指导与帮助,讨论的是中国的话题,唱的主要是中国歌曲。当我们抛开这一切本土化再造的内容后,惊讶地发现其被内容所掩盖的形式依然是宣扬一夜成名的“美国化”意识形态,而版权方对于这种核心意识形态的捍卫更是要通过派出“飞行制片人”来予以监督的。因此,该体系对于节目内容创作权就可以有相当大程度的让渡,而本土化的“再造”则以对接受方“表面上”的“充分尊重”与“平等传播姿态”来呈现。经历本土“再造”的电视节目模式下每一个节目参与者都是本土的主持人、本土的明星,讨论的也都是本土的话题,这便会使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本土性”的认知偏差与文本误读。
表面上这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达成的“双赢”局面,本土的“自我”在“他者”的“模式”里得到了张扬,并为本土观众创作了许多喜闻乐见的节目。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传播策略,以至于在“异质”与“本土”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也照样播出着《沙特好声音》《卡塔尔达人秀》这样的节目。[8]这种看似平等的传播姿态表面上是让渡“内容”的创作权,但却通过版权的方式极尽所能地扩大“形式”的外延,以取得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这种平等传播姿态的“假面”下,是“盎格鲁—美利坚”体系高高在上且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
二、“丝绸之路影视桥”:借鉴的困境
在此,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盎格鲁—美利坚”体系能够进行如此“伪平等”的传播,其前提还在于这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系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将古代丝绸之路视为全球化1.0形态,而将当前以全球贸易、投资扩张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视作2.0形态,同时,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建构全球化3.0形态充满了期许。[6](10)“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一种包容性的全球化,是一种沿线各国老百姓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全球化,是一种“南南合作”而实现共赢的全球化,因而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式全球化”[9]。相较于起源自大航海时代而建立的以殖民体系为核心的全球化2.0形态,“一带一路”战略所建构的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共同复兴,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而串联四大文明,推动与我们一样历史上曾经十分繁荣的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因此,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文化先行”与“民心相通”便显得任重道远,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进步超越文明优越感”[9](11)的文明融通机制。
对于“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而言,且不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宗教、民族习惯的不同,即便我们依然按照全球化2.0形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该问题,所做出的一切都将不过是对“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的拙劣模仿,并会遭到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留情的惩罚。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文化先行”的策略无可厚非,并且“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本身也是“文化先行”的一部分,而“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建设原则本身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所秉持的价值观,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文化先行”?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更加应该强调“平等的传播姿态”[10]。同时,作为“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先期的理论准备,我国学术界一直在强调立足沿线各国的国情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然而,沿线各国国情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宗教信仰天差地别,如果一一满足则会加剧“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创作难度并付出高额的创作成本。那么“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看似平等”的传播姿态是否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呢?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这种“伪平等传播姿态”——对内容创作权的让渡,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是WTO框架下的一种惟利是图而挣取版权费的节目交易体系,接受方则因为与直接引进节目不同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再造权。殊不知在这种模式交易为主体的体系中,“内容”只是节目模式的枝节,而“形式”被经过各种商业测算和市场检验为“模式”才是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根本内核。并且,这种方式成立的前提是英美国家对WTO领导权的控制,如果失去了经济全球化的法律保障,交易都可能不复存在,又谈何“传播姿态”呢?而“丝绸之路影视桥”本来就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先行”者,又何来这套完整的经济基础设施呢?
其次,我们抛开再造的内容“幻像”反观近年来充斥世界各国荧屏的各类引进节目模式的电视栏目,会发现一些其模式中无法去除的原生规则,比如许多“类比赛”的电视节目——无论是竞演类的节目如《XX偶像》,亦或是野外生存竞技类的节目如《幸存者》——往往都会将参与者分组,在小组中强加入所谓的“同学”感情,然后随着比赛环节的推进让他们自相残杀,甚至还要极度残忍地让“导师”在两位“学员”中选择其中一位“生还者”。这些比赛环节绝不是崇尚和谐、包容的沿线文明所鼓励的意识形态,即便本土观众从本土创作者和表演者所提供的“内容”中不知不觉地对“模式”中提供的价值观产生认同,也不可避免会带来“文明的冲突”。沿线各国本身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一定程度上存有疑虑甚至戒心,[11]在传播姿态上稍有不慎,后果难以设想。
再者,我们自主的电视节目模式尚处在引进、消化与吸收阶段,真正意义上自主研发的电视节目模式少之又少,即便有,也主要是像《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那样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的节目。这一类的节目尚未提炼出节目模式,更无法提供他国进行再造——我们很难想象,如若这些在中国国内有着非常高评价的电视节目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再造”出“《哈萨克斯坦诗词大会》”或“《阿拉伯文听写大会》”之类的节目,这样的“再造”对“一带一路”战略所期望实现的“民心相通”又有多大程度的支持作用呢?对文明的融通是否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三、平等传播姿态:“共造”的可能
时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强调:“‘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需要我们逐渐探索出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3]“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伪平等传播姿态”与我们对“一带一路”战略所期望的文明的融通显然有着较大的差距。中国人民大学的陈阳教授曾在2009年便极为敏锐地发现了电视节目模式全球流动中的这种“文化混杂”与“本土改造”,并对“文化混杂”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担忧。[12]尤其是其包裹在让渡内容再造权的外壳下,坚定的意识形态模式内核在根本上与“丝绸之路影视桥”的精神内涵不一致。然而,从微观的技术层面来看,让渡本土内容再造权确实是值得我们在建构自身节目模式创新时需要高度重视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拿出真正的“平等的传播姿态”来实现与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呢?我们能否打造一系列“中国形式”的电视节目模式从而让沿线各国来“再造”本土化的节目呢?我们能否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乃至共赢共荣的“中国梦”直接融入电视节目模式,从而让沿线各国的观众在从他们本土表演者的脸上看到这种价值观呢?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乃至我国已开发的电视节目模式的“家底”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借鉴“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核心创作理念——让渡“再造”权。故而,我们认为应该欢迎沿线各国的创作团队一起加入到电视节目模式研发的前端,将“再造”(Reproduce)改变为“共造”(Coproduce),进而从根本上打破“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意识形态内核,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实现对文明的共同进步,从而超越全球化2.0的西方中心主义藩篱。
这种“共造”必须是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识,由各国创作团队集体打造的“形式”(节目模式),然后再由各国根据自身具体实际来进行本土化的内容生产。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再造”本质上是一种“我设计好游戏规则,你负责带着你们家里人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玩游戏”的过程;而“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中的“共造”则是“我们一起来设计游戏规则,然后各家玩出各家特色”的系统。对于捍卫贸易自由化的我国而言,将我们与沿线各国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平等、公正、友善”——以“共造”的方式内化为其中的节目模式,并像其他原创节目模式一样经受住市场的检验,便一定可以通过“丝绸之路影视桥”将这种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
“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中贯彻的“美国化”意识形态具备一种随时可切换的动态性——美国最初是殖民地,因此其意识形态中具备第三世界殖民地斗争的“解放性”;之后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拓荒努力而具备逻辑自洽的“开拓性”;同时又是现代科技的领导者,这便使其又具备了无可争辩的“现代性”,那么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或曰各电视节目收视市场,“解放性”+“开拓性”+“现代性”的动态平衡总能找到与当地观众“适配”的意识形态接口。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强的文化自信来面对“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尽管横亘在面前的“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已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观念统治了全球,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或多或少地呈现出“逆全球化”的态度。若以“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平等传播姿态,在充分尊重沿线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前提下建构节目模式的“共造”权,则对“民心相通”起到极大的建设性作用。
同时,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讲好中国故事”而言,“丝绸之路影视桥”的“共造”体系可以发挥沿线国家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一种单向的传播成为一种双向乃至多维互动的关系,并将这种互动上升为“文明的互鉴”与“文明的共同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友善”具备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传播的共同价值——作为今天贸易孤立主义思潮中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我们热爱自由;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者,我们自始至终平等对待沿线各国,并期望所有国家能够共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作为单边主义贸易壁垒的受害者,我们捍卫公平的决心一以贯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一贯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并将这种友善的外交风范推广到全世界。而如上的共同价值一样可以实现动态平衡的适配。
“丝绸之路影视桥”的“共造”体系要求我们在节目模式研发的时候必须守住意识形态的底线,坚决与“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零和博弈”的竞争性价值观切割开来,强调今天现代化中国互利共赢与和平友善的价值观。同时,我们可以拿出在中国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与沿线各国创作团队一齐来探讨,如何将这些节目“共造”成沿线各国观众都喜闻乐见的节目模式。笔者以为,我国原创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具备这种模式“共造”的潜力。沿线各国几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灿烂的文化,至少在内容层面具备了各国对该节目进行本国再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各国博物馆本身具备文化交流的功能,因而在“国宝”交流过程中就具备基于“形式”的情感表达——互相尊重彼此历史,互相尊重彼此文化,中国的平等友好与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可以在与沿线各国共造节目模式的时候贯穿始终。这种共同价值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广泛传播就具备很强的可行性,同时也赋予了沿线各国较高的创作参与性。
四、结 语
至此,我们不难意识到,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的形态中,“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本质上是这一形态作用于电视节目模式交流(交易)的呈现形式。若不是冷战结束,也不会出现“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至少当时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苏维埃体系”[13]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节目交流体系。换言之,“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电视节目交流的当然体系。
也因此,我们认为“丝绸之路影视桥”完全具备成为这个世界上另一种节目模式交流体系的可能性。这种依托于全球化3.0形态的电视节目模式交流体系本身就是不断自我建构、不断完善的动态演进体。它要求我们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融入其中的电视节目模式。这不仅是为了展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完全平等的传播姿态让沿线各国参与进来。此时,基于“丝绸之路影视桥”研发的电视节目模式便是我们“搭的桥”,而沿线各国通过“共造”创作的内容则是大家一齐“铺的路”。今天,我国电视荧屏上热播的《中国好声音(新歌声)》《急速前进》《奔跑吧!兄弟》《中国达人秀》等等可以视为“分享红利”阶段,而我们自身能够研发出立足自身市场的《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则可以视为“红利互动”的开始,那么“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建设或者说以《国家宝藏》(《一本好书》部分具备)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节目模式研发就应该为“给予世界更多红利”的布局。这里要提醒的是,在“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共造”语境中,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刻意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容模式,因为我们日常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往往指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恰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反而使得接受方对于节目内容的前理解存在较大的隔阂。换句话说,如果试图传播中国文化则必定会在“内容”上反复着力,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形式”(节目模式)的重要性。
当我们回首“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的传播策略时,对“形式”和“内容”的对立性传统认知就十分值得重新审视。而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内容直接可以内化于电视节目模式这一“形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不是“让渡”创作权,而是邀请沿线各国广泛地参与创作,以实现沿线各国的“万众创新”,进而实现文明的共同进步。故而,在“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内容再造权不是像“盎格鲁—美利坚”体系那样“让渡”出来的,而是从根本上基于对接收方本土文化甚至文明的尊重而共同参与出来的。换言之,如果本土“再造”是“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共造”就是“丝绸之路影视桥”的根本表现。与此共生的不仅是“平等的传播姿态”,还有着“互利共赢的经济姿态”,以及“共荣共进的文明姿态”。当经济上的连通使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共同价值的传播姿态便会在此氛围中呈现得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