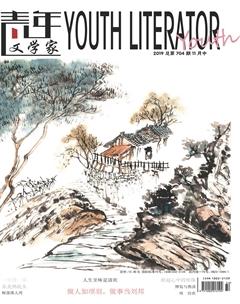略论十到十二世纪女真与党项的“髡发”习俗
王砚淇
摘 要:在十到十二世纪,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北方族群的发型发式虽各自仍有差异,但几乎都具有了“髡发”这一基本特征。西夏、金国在各自的政治目的下,为推广髡发发式,不惜采取行政手段强迫本族或他族。在传统社会中,影响某种发型发式形成和流行的,除传统性、宗教性因素外,政治性因素也不得不视作重要的一方面。
关键词:发型;女真;西夏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2--02
古代中国北方各族群的发型发式各异,有“结发”、“拖发”、“椎髻”、“披发”、“断发”、“剪发”、“绳发”、“索头”、“髡发”等等。这些发型发式存在两个基本区别:蓄留全发和剃发。蓄留全发是指对头发剪剃一少部分,留有一大部分,任其自然生长,但可以结辫,例如“拖发”、“椎髻”、“披发”等等;而剃发则是剔除大多数头发,往往表现为短发、寸头乃至秃发,比如“断发”、“髡发”等。
髡发,是指剔除部分或者全部头发的发式,留有的头发可以结辫或者自然披散。从辽庆陵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水月观音》等考古资料来看,在十到十二世纪,北族的发型发式虽各自仍有差异,但几乎都具有了“髡发”这一基本特征,活跃的代表即是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
在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中也详细描摹到金人的发式发型,图中一共有十二个人,其中在整个队伍后半段的胡人官员的发型特点最为突出:前额头发剃除,后面头发留长,辫成两个细长的辫子,这是十到十二世纪女真族人的典型发行之一。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关于北方民族多髡发的原因主要包含信仰和现实两个方面。首先,不少民族都就将头发被视作人的灵魂寄所,弗雷泽《金枝》一书中认为:“原始人相信自己人体各个部分同自己有染触关系,即使那个部分已从身上脱离出来,这种染触关系依然存在,”[1]虽然不存有全部头发,但头发依旧被看作身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可以具体表现在清宫档案记载:“有跟随将军明瑞之蓝翎侍卫三保家人书克翁,将明瑞身躯掩埋,将发辫、扳指、带子带出,并将总督印信令三保等赍送永昌,给予驿马赴京,恭候皇上询问。”[2]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人心中,发辫是人灵魂的象征之一,不可忽略,而髡发恰恰可以留有头发,满足人体的精神需求;其次,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常年以打猎为生,避免不了与野兽的搏击,而髡发的发量少,发辫轻,有利于打猎,髡发轻快、方便、实用。
在十到十二世纪,髡发大都剔除头顶头发,但具体形态又有所不同,形式多样。《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男子辫发垂后,耳饰金环后颅留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3]女真族髡发多为剔除头上其他部位头发然后蓄留颅后头发,结成下垂发辫。女真发式虽亦为髡发,却与契丹发型发式颇有不同。 而北宋曾巩《隆平集》书:“(西夏)文人服靴笏幞头,武臣金帖镂冠,衣绯衣,金银黑束带,配蹀躞,穿靴,余皆秃发,耳垂环。”[4]与女真發式又有所不同。
西夏人以髡发发式为主的原因,与西夏的“秃发令”有莫大的关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命令其属下臣民秃发,称为“秃发令”。《续资治通鉴长篇》即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5],可见这一政令实行之严苛与急促。然而,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大都为羌人后裔,或羌化严重的鲜卑后裔,在元昊“秃发令”前,其普遍的发型发式也为羌人常见的披发,这一点当是确实无疑。[6]依据一些学者的说法,秃发是恢复了拓拔鲜卑的“旧俗”。[7]然而,且不论元昊所部是否为拓拔鲜卑之后,拓拔鲜卑的“索头”是一种蓄留全发的发式。[8]因此,元昊下令秃发,不应当是模仿鲜卑发式,依据传世画作以及考古资料来看,其秃发样式更像是模仿契丹髡发。元昊自认为拓跋鲜卑之后,《宋史》载其向宋廷上表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9]然而,北魏拓跋鲜卑的发型发式本为披发(索头),元昊却下令秃发,其发型发式又颇类契丹,这很可能说明元昊一方面自认为自己是鲜卑之后,然而关于鲜卑旧俗却知之甚少,遂模仿当时较为常见的、象征北族胡人的契丹式的髡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元昊自觉为拓跋鲜卑之后,却对契丹式的发型发式生了某种“认同感”,并不惜用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之——这一现象可以贴切地反映一种发式形成的背后,种种政治话语的交互和错位。到哲宗时期,“环庆路熟户捉生伪冒、改名、剃发、穿耳、戴环、诈作诱到西界大小首领”[10],说明起码到哲宗时期,西夏人秃发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西夏人将秃发这一习俗一直保留下来,而并非只是慑于元昊一时之威,或许可以说明这种认同似乎相当普遍。
同元昊一般采用行政手段推行髡发的,还有金的“剃发令”。其立意缘由则是出于对汉文化的警惕之心和对汉人忠诚的考验,亦方便女真统治者在战争状态下划分宋金阵营,区分敌我。早在天会四年(1126年),金政权即下令所征服地区的汉人“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11],天会七年,又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杀之”[12],《德安守御录》记载:“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称是单州团练使、郢州钤辖孔彦舟,在黄州麻城县作过。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贼至黄州,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13]按建炎三年,距离孔彦舟叛走伪齐、投降金朝尚有四年之久,这时其流寇部队采用女真发式,可能是出于借金人之名威吓南宋军,方便其南下劫掠的军事目的,这是金国影响力的绝好体现。再加上金国境内实行的诸如“剃发令”一类的行政措施,其风俗文化对其他北方民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到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为止,剃发令一直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剃发令中,不仅要求汉人剃发,并且要“如式”,说明女真人的髡发与契丹发型多样的髡发不同,具有一定范式。到金末,“今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14],说明女真式的既髡且辫发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
综上所述,十到十二世纪,以女真、西夏为代表的各民族髡发发式的形成,有民族性因素,还有政治性因素。发型发式作为传统社会中“风俗”的重要部分,推动其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值得今日史家深入研究。
注释:
[1]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46页
[2]军机档,40302423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转引自吴美凤:《“顶上风云”:满人髡发源起》,《满语研究》,2013年2期,第65页。
[3]《三朝北盟会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4]曾巩《隆平集》卷十二。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中华书局,1993年,第2705页。
[6]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7]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页;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8]详见李志敏:《索头为既辫且髡发式说辨误》,《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景永时:《关于西夏秃发令及发式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9]《宋史》卷485,《夏国传》,中华书局,1985,第13995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日丙午条,中华书局,1993年,第12187页。
[11]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6页。
[12]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页。
[13]《守城录》卷4,(宋)陈规、汤璹《德安守御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4]《金史》卷35,《礼志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