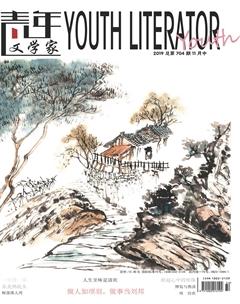论“山珍三部”生态书写的空间叙事
摘 要:阿来的生态写作具有空间意识嘉绒藏区空间书写在其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阿来山珍三部为例从其空间叙述特色及策略角度揭示阿来的生态和文化批判归旨,展现消费社会藏区地域下现代性反思,以及对人类生态愿望和生存理想的追求。
关键词:空间叙事;山珍三部;生态书写;文化反思
作者简介:刘利娟(1995-),女,汉,湖北人,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2-0-02
阿来生态写作初步具备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即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以对生命价值形态的审美观照为本,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出生于阿坝 州马尔康县的阿来,嘉绒藏地是其创作的来源,“藏地空间”自然是阿来生态小说的主要观照对象。阿来曾肯定:“我一直认为中国小说的空间感比较差,这也是中外小说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而我希望自己的小說中有空间的质感。”[6]2015年藏族作家阿来连续发表了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三部作品,结集出版总名为《山珍三部》。三部作品皆以青藏高原物产作为小说的逻辑起点,通过儿童、老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反映高原地区的生态窘局。
空间叙事在阿来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与文学的联系得益于空间诗学创始人巴什拉的著作《空间的诗学》与新文化地理学代表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巴什拉从诗歌作品出发,对诸如家宅、箱子、抽屉、鸟巢等空间形式做了形而上的思考,而克朗则揭示了地理、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空间叙事视角下的阿来小说研究试图多维度的还原藏族村落的地理、生态与文化内涵,对于发掘生态小说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回归与继承,具有重要意义。
一、藏地空间生态书写
在分析莫言小说创作特质时,曾被使用“在地性”的概念,即他始终脚踏实地站在他的高密乡。这种创作特质在阿来小说叙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川西嘉绒藏区是一个汉藏交织的区域,它既具有一般乡土特征,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土地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地空间往往存在着农村自古以来的“地母情结”。传统农耕社会,农民把土地视为母亲,表现出人们对大地的极大依赖。受汉文化影响,嘉绒藏族是一个“对土地的倚重大于对草原的依恋”的民族,自古以农耕为主的土地空间成为乡村近乎神性一般存在。其表现在:
首先,一旦天灾人祸便导致土地颗粒无收,农民就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民不聊生。《蘑菇圈》中因“山上的原始森林被森林工业局的工人几乎砍伐殆尽,剩下的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1],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导致河流干涸使得机村村民的生存受到严峻的挑战,犹如世界末日般给饥饿折磨的农民带来生存压力。《三只虫草》里原居民“一家人的柴火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1]《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的父亲作为周围几个村子里唯一的木匠,靠着自己传统的伐木手艺为生,藏区居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土地是他们生活来源。
其次,藏区地理位置多处高山峡谷,大漠纵横、河流密集的边缘区域,藏族与自然密不可分的联系,造就了其自然的信仰。从阿来的作品里,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蘑菇圈》中关于雪山之神阿吾塔毗的传说,具有神性色彩;《三只虫草》中虫草季开启前,藏族人民也都有例行的仪式,“喇嘛坐在上首,击鼓诵经。男人们在祭台上点燃了柏枝,芬芳的青烟直上蓝天。”[1]在《河上柏影》里,对藏族传统丧葬方式——天葬,有所描述,天葬核心是灵魂不灭和轮回往复,无不渗透着对信仰的坚守与神灵的敬畏。
再次,“山珍三部”均各自以高原植物“松茸”、“虫草”、“岷江柏”为叙述焦点,作品处处散发着隐喻与象征的意味,透露深刻的文化内涵。意象主义诗人庞德曾说: “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3],是一种“各自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3]在藏区,松茸与虫草的采集由来已久,依循松茸与虫草等名贵药材的采集而构建的“虫草社会”,代表着藏族原始文化,绵延出历史悠久的采集文化。三种意象共同隐喻着一种“原始生态文化”,也象征着人类以及其他自然生物的命运多舛。“山”是原始生态文化,“珍”即物的奇珍、人品质的珍贵。三种中心意象隐喻并暗示时代变迁给人类、原始文化乃至自然生态带来遭际,以期在历史的进程中找回人性与生态的栖息之地。
二、空间时间化与历史叙事
时间与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相互交织,但受历史决定论影响,后者常常被忽略。空间时间化是指通过空间来呈现时间的变化,具体到小说创造中,是指故事情节铺展在同时并置在空间场景中,小说中的时间被空间的紧张、压迫、变化所抽空,强调空间对于历史的回应。巴什拉认为“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便是空间的作用。”[4]约瑟夫·弗兰克认为空间形式论最终强调的是文学叙事中的时间关系;巴赫金更是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诸形式》中指出:“空间也是有负载的,能回应时间、情节和历史的律动。”、“空间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4]由此可见,对某一特定的空间形式或结构的观照可以获得其背负的历史密码。
“山珍三部”皆以藏区历史文化变迁为语境,又借以“空间”叙述历史的记忆,具有显著的历史叙事特征。《蘑菇圈》中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机村”这一固定空间中展现。全篇以机村植物“蘑菇圈”为横断面,表现了从建国之初到现在,特别是几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合作社时期、大跃进时期、四清运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当下的商品经济时期藏区嬗变的历史。小说始于蘑菇又终于蘑菇,“蘑菇圈”可以看作藏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缩影;《三只虫草》中作者以儿童桑吉“逃学离校-返校-离校上城-返校”为叙事模式,校园、乡镇、县城皆为叙事空间,通过空间的描写记叙着桑吉的成长。《河上柏影》中王泽周时隔多年回到家乡:
“两个小时后,王泽周和多吉已经出了县城,站在那座花岗石丘前。河流还是原来的样子,河道中乱石狰狞,参差的巨石间,波浪激烈……村子也还是一模一样。如果有某种变化,就是村子似乎比过去更安静了。”[2]
可见,空间被时间化了,空间的表现形态往往是静止,而历史的动荡往往根植于这一看似毫无变化的空间场景中。也就是说,空间的静止状态并没有违背时间动态发展的规律,而是以一种相对静止的表征形态回应着时间的流逝。
此外,承载历史记忆的空间不仅回应着历史也面向着现实。文本中空间时间化隐含着的是当今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有关空间的历史——也就是权力的历史。”[5]
乡村城市化往往表现为城市资本与乡村权利结盟,使乡村本土失去自主性,沦为商业资本的附属。《蘑菇圈》主要关注城市资本对乡村主体的掠夺,丹雅的公司策划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的项目,表面上是为了保护野生植物,实质上是城市商业资本向乡村的流动的旗号,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乡村土地使用权,垄断区域性的松茸市场。城市资本的来袭不是出于启蒙或者为乡村某福利,而是商业追逐的利益化。《三只虫草》中调研员利用儿童桑吉千辛万苦挖来的虫草,以作为其抵达权势高点的工具;《河上柏影》中旅游局副县长贡布丹增利用特权以白云寺作为重点开发的旅游资源,一味搬演并渲染宗教性故事,拼命搜寻游客浅陋的兴奋点来获得商业利润。城市资本重塑乡土空间后,乡村主体性身份受到了冲击;城市资本与乡村政治权力结盟后,重构起乡村权力控制的等级秩序。
寺庙与宗教的神权逐渐淡化,信仰变成被掏空了精神的符码化存在。阿来笔下,大量普通僧人跌入凡尘。喇嘛按照传统在虫草季“摇铃击鼓,大作其法”[1],索取虫草作为报偿,却不再满足于化缘及供养:“山中的宝物眼见得越来越少,山神一年年越发不高兴了,我们要比往年多费好几倍的力气,才能安抚住他老人家不要动怒。”[1] 这完全是世俗之表态。物产与物欲之间的冲突侵袭着传统的藏地空间,也瓦解着传统文化信仰。
三、生态追求与文化反思
“生态文学里的空间叙事关注的是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生存空间焦虑,它不仅体现出对空间设计的焦虑,还包含了生态立场下关于人类精神空间的省思。” [7]文学中的空间具有叙事功能,阿来生态小说藏地空间叙事以点带面独照了现实,展现阿来“回归与节制”的原乡生态追求与文化反思。传统的藏地空间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態维持着乡村的农业生产,土地没有被污染,人心没有变异化。淳朴的乡下人仍然对乡土地域保持着传统的敬畏,臧地是田园牧歌的象征,是诗人或哲学家那里的神秘主义诗学。
商业资本的入侵,土地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所拥有的光环黯然失色。在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中给每个小说都安排了一位生态的守护者他们保存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以悲剧者的姿态抵抗着时代大潮 同时也召唤着同道者。《蘑菇圈》以斯炯为代表的老妪,用其一生守护着蘑菇圈、守护着即将消亡的自然神性与人性的本真;《三只虫草》以儿童桑吉的视角审视高原物象,三只虫草的漂流之旅预示着桑吉那未知的命运;《河上柏树》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王泽周面对城市化对质朴乡野的强烈冲击束手无策更多地带有生态的反思的意味。由儿童、成人、老人形成“山珍三部”的代际书写,皆是奇妙的生命的历程,皆是对生态文化反思的故事,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完整地构成一幅藏乡风俗画。
阿来生态小说寻求藏地原住居民朴质可贵的人性之美、天然的生命意识及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态理想。正如他在书序所说“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向着贪婪与罪行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2]以诠释其“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2]的写作要旨。
参考文献:
[1]阿来.蘑菇圈[M].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2]阿来.河上柏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汪耀进.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丛·意象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4]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蒋楚婷.阿来:文学是一种沟通的工具[N].文汇读书周报,2009(09).
[7]林岚.阿来小说中的乡土空间叙事[D].贵州民族大学,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