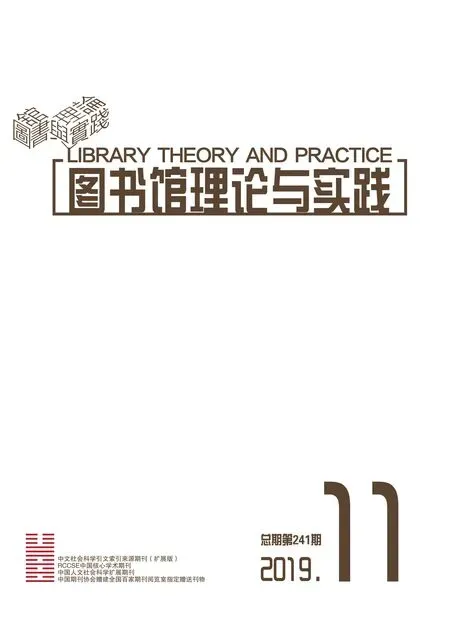周必大日记的版本及价值考论
代天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周必大全集》中收有周必大日记八部,“按时间顺序,依次为《亲征录》《龙飞录》《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乾道庚寅奏事录》《南归录》及《思陵录》”,[1]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此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点。虽然《周必大全集》已经出版,但周必大日记的版本问题却一直未有定论。因此,本文对周必大日记宋本的刊刻问题以及宋元之交的单行本进行考论,并说明其价值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策略,以便研究者使用。
一、周必大日记初刻本的刊刻问题
周必大全集由其子周纶初刻于开禧二年(1206),但周必大日记是否在开禧二年刊刻则有疑问。顾广圻认为《杂著述》(包括周必大的日记) 在开禧二年便刊刻,[2]569-570但王聪聪、闫建飞批评顾广圻的看法,认为没有刊刻。[3]闫建飞等人的依据是,周必大子周纶跋云:“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与先友免解进士曾无疑三异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进士许志伯凌、乡贡进士彭清卿叔夏、罗次召克宣相与覆校,敬锓木以传。惟日记自绍兴戊寅至嘉泰甲子,纪录颇详,而《书稿》尤多,皆未容尽刻。实藏惟谨,当俟他日。开禧丙寅中秋,嗣子纶谨书。”[4]96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周益公集》 二百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丞相益文忠公庐陵周必大子充撰。一字洪道。其家既刊《六一集》,故此集编次一切视其凡目。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郑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5]785因为其中有“未容尽刻”及“未刊”二字,因此闫建飞等人认为周纶初刻本没有周必大日记,而陈振孙又云“郑子敬守吉”时“募工人印得之”,故而认为《思陵录》是郑子敬知吉州时刊刻,而郑子敬知吉州在嘉定十年(1217)至十一年(1218)七月十九之间,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周必大日记初次刊刻的时间。
顾广圻《思适斋集·周益文忠公集跋》云:
首列《周益文忠公文集》总目,凡《省斋文稿》三十卷、《平园续稿》 三十九卷、《玉堂类稿》 十三卷、《政府应制稿》一卷、《历官表奏》五卷、《奏议》十二卷、《奉诏录》 四卷、《杂著述》 七卷、《书稿》十四卷,共百二十五卷,又《附录》 五卷、《年谱》一卷。总目末有开禧丙寅嗣子纶所书,言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与曾三异纂集,又得许凌、彭叔夏、罗克宣校正,惟日记纪录颇详,而《书稿》尤多,皆未容尽刻。据此,则开禧刻本止有此数矣。今外间抄本称《周益公大全集》 共二百卷,而名目卷第、多寡先后无一相同,盖出于后来刻本,未详何人所重编校也。此本旧钞,有真定梁焦林相国名印,尚是文忠家刊,洵可宝也。今藏阳城张古余观察与古楼。道光四年六月,出以相示,为考覈而书于帙端。[2]569-570
陈振孙已言“《周益公集》二百卷”,而周纶所言“未容尽刻”者之总数亦不过二十余卷,流传者至少有一百七十卷,绝不止百二十五卷。陈振孙云其印得之本“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顾广圻云“《奉诏录》四卷、《杂著述》七卷”,亦是十一卷,可见闫建飞等人认为初次未刊刻的部分亦在顾广圻所见之本中,且卷数完备,则“开禧刻本止有此数”必属误判。《省斋文稿》《平园续稿》今存明清全本皆是四十卷,可见文中所列总目乃残缺之后依所存者加录,并非原本如此。而“今外间抄本称《周益公大全集》 共二百卷,而名目卷第、多寡先后无一相同,盖出于后来刻本,未详何人所重编校也”,据记载及现存抄本刻本,自周纶刊刻后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方有刊刻,在顾广圻之前并无其他刻本。[3]顾广圻所见旧钞“尚是文忠家刊”,即此本为影宋本,其中存《杂著述》七卷,就说明周必大日记在开禧二年便已刊刻,只是流传既久有所散佚。
王聪聪、闫建飞其实是误读了周纶跋与《直斋书录解题》。周纶云“纪录颇详,而《书稿》 尤多,皆未容尽刻”,“未容尽刻”并非是未刊刻,而是部分未刊刻的意思,也就是说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刊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 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郑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所谓“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即已经刊刻而由于其多及时事,遂以“未刊”为借口,秘不示人,人莫之见。“郑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印得”二字表明已有刊本,郑子敬只是招募工人摹印而已,并非刊刻。“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即陈振孙所藏周必大全集没有日记部分,他遂从郑子敬印得之本抄录补全,然因时间已久,书板有损,故印本“犹漫其数十处”,若是郑子敬新刻,不至于“犹漫其数十处”。陈振孙言“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 凡十一卷”托言未刊,则陈振孙所藏之本已经有周纶“未容尽刻”的《书稿》(今有十五卷),说明《书稿》 已经刊刻,这就更能证明“未容尽刻”是周纶秘不示人的托词。综上,周必大日记在开禧二年已经刊刻。
二、宋末元初存在周必大日记的别本
生活在宋元之际的周密曾看过周必大的日记,其《癸辛杂志》“孝宗行三年丧”条云:“李氏《杂记》尝书其事,甚略,今摭当时始末于此,以益《国史》之未备云。”[6]50-51李氏《杂记》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周密认为李氏所书甚略,因此摭当时始末益国史之未备,其所采之文即出自周必大《思陵录》(见下表)。
上表可以直观地看出《癸辛杂志》“孝宗行三年丧”摘自《思陵录》,它的存在就证明周密确实看过周必大日记。《思陵录》中有几处称“予曰”的地方,《癸辛杂志》 则称“必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作“王淮等”,就说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录应不出自周必大日记,而是别有来源。这个事实说明周密看过周必大日记。
周密看过周必大日记不足为奇,但周密记录下了几条出自周必大日记却不见于今传本的信息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云: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飢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寃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鄕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周必大)、王季海(王淮)日记。而朱门诸贤所着《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7]323
虽然此桩公案是非难论,但陈亮淳熙十年(1183)秋传信朱熹言及此事,云唐仲友怀疑陈亮从中挑拨,并因此辩白,[8]证明周密所记有其可靠来源,并非陈伯玉或周密本人捏造。周密言“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而于文中注明“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说明此说在周密记录之前并非仅口耳相传,而是见诸文献,即周必大、王淮之日记,只是王淮日记不传,而今传本周必大日记未见记载。

表“孝宗行三年丧”记录文字对比
周密言周必大日记所记之事不见于今传本周必大日记并不是孤例。“陶裴双缢”条云:“丙申嵗九月九日,纪家桥河北茶肆陶氏女与裴叔咏第六子合著衣裳,投双缳于梁间,且先设二神位,仍题自己及此妇姓名,炷香然烛,酒果羮饭,烛然未及寸而殂矣。尝记淳熙间王氏子与陶女名师儿,共溺西湖,有人作长桥月短桥月,正其事也,至载之周平园日记。”[6]222-223“髯阉”条又云:“周益公日记云:‘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6]255如果说“朱唐交奏本末”有道听途说之嫌,此两条则皆注明出自周必大日记,无可怀疑。两事皆不见与于今传本周必大日记,这证明在宋元之际,周必大日记存在一个与今传本内容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的存在,证明今传本周必大日记不是内容最全之本,而是一个删改本。
周必大日记已经刊刻,而周纶等之所以秘而不出,陈振孙一语道破:以其多及时事。两宋常因政治变动而对《国史》《实录》 等官史屡加修改,甚至有“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变”的说法。[9]23政治变动不仅影响到史书的修纂,对个人创作也有相当影响,特别是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发生后,政治人物的创作都或多或少的自觉的受到“规范”。除了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自我抑制之外,还有另一个方式,就是对已有的著述进行修改,关于这一点,顾宏义先生研究《曾布日录》 的结论无疑对此有重要启发。《曾布日录》“记在政府奏对施行及宫禁朝廷事”,顾宏义先生云:“《曾布日录》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因曾布编修《日录》,本出于政治考虑,且又编订于其罢相以后的徽宗时,故其为自身利益计,自是时做删润、曲笔。有人曾问朱熹道:‘若据布所记,则元符间何为与章子厚在政府而能两立?’朱熹答到:‘便是恐不可全信。’”[9]251
曾布的记载“多有日后修订讳饰的文字”,[9]255《哲宗实录》由蔡京主持,突出了其弟蔡卞的“册立”之功,而曾布为了彰显自己的拥立大勋,向徽宗邀宠,便针对《哲宗实录》对已经写成的《日录》进行修改,削弱蔡卞、向太后在册立上的作用。[9]252-257除了自我修改外,其子曾纡将《日录》中“绍圣以来有奏对要语”抽出与熙宁间事合为《三朝正论》,以此得到高宗的夸奖。[9]250为了广其流传,亦曾有选择的刊行,朱熹曾说:“《曾子宣手记》,被曾拣出好的印行。某于刘共父家借得全书看,其间邪恶之论甚多。”[9]250《曾布日录》 的面貌因为政治而几经改变,同理,周必大日记多及时事而且可能还有突出自我的因素,所以刊本内容与别本相较,有所删节,这大概是周纶“未容尽刻”的真正含义。
三、周必大日记的价值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周必大日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比如《思陵录》。今天我们见到的《思陵录》 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日常行事的记录,二是一些重要文件。重要文件首先是申状、供状。第一份赵实关于医治高宗的供状,此供状详细讲述了高宗病危、医官刘确、王泾、马希古、汤公才等看脉、进药的全部过程。其二是关于放逐高宗后宫人员的申状,此状详细记载了高宗去世后被放逐出宫的人员名单。其三是修建高宗陵墓及慈福宫的档案,这两份档案在《思陵录》中是依原式录入的。这些文件均附录在事件发生当日之后。除了完整的申状、供状,还有一些短小的内批与御笔。比如:
丁丑。延和起居毕,奏事。同王相、萧参谢许辞免支赐。上曰:“勉从卿等所请。”……内批付三省、枢密院:“朕祈请皇太后还内者数四,未蒙俞允。今早复申恳切再请,恭奉皇太后圣旨:‘先帝享天下之养,优游二十余年,升遐此宫,何忍遽然迁去。今几筵复奉安于此,倘欲还内,当俟终制。’百官宜敬悉皇太后圣意。”[10]1655
这一日是宰执率领群臣朝于延和殿,然后奏事,接着是王淮、萧遂谢许辞免支赐及孝宗对此行为的回应。《思陵录》的记载是以孝宗的问、宣谕与以宰执为中心的群臣的“奏对”展开的,记载奏事过程中相关人员的言语行事。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九章考证王淮罢相始末时基本依靠《思陵录》,说道“现存史传中关于王淮去位的记载都极简略,不足为重建此事的根据。但是我们的运气特别的好,周必大的《思陵录》竟提供了第一手的内幕材料”。[11]485平田茂树《从周必大〈思陵录〉〈奉诏录〉考察南宋初期的政治结构》对《思陵录》的价值又有创造性发现。他认为《思陵录》是“考察南宋初期政治的绝好史料”,[12]234并且认为“在礼制研究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12]265《思陵录》 还是考察孝宗后期宋金外交状况的绝好史料。许浩然《从周必大〈思陵录〉看淳熙十四年宋金外交之隐秘》考察了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孝宗以守丧为由拒绝接见金使的深层原因及孝宗的行事风格、政治心态。[13]《思陵录》中还保存了两份特殊档案:慈福宫与永思陵建造的工程档案。这两份档案对探索北内建筑与南宋皇陵建制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一点很早就被建筑史领域的研究者认识。李若水《南宋临安城北内慈福宫建筑组群复原初探——兼论南宋宫殿中的朵殿、挟屋和隔门配置》利用《思陵录》讨论了北内格局和慈福宫建筑原状,并对南宋宫殿中的“朵殿”“挟屋”及隔门的设置进行了探讨。[14]孟凡人《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布局》以《思陵录》为中心,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所绘制的《宋永思陵上宫龟头殿复原想象剖面图》《南宋永思陵石藏子复原想象图》 分析了永思陵攒宫的形制和结构,并绘制出永思陵下宫平面示意图。[15]对《思陵录》的进一步运用,也昭示着《思陵录》的价值。
我们在研究时,要注意周必大日记被删改的情况。黄丕烈校《思陵录》,云:“校周益公全集及此种,因忆藏旧有抄本无‘周某集卷第几’字样,或岀于专本,遂取此本讐于所校本上,用朱笔,故此本闲有朱笔抺者,皆因彼以知此之误也。用乁者,据彼所有以知此所脱也,不尽据彼校此者,留此本面目尔。”[16]20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卷二十四史部亦著录此本,并录黄丕烈跋语。黄丕烈据单行本改正总集本,又云“不尽据彼校此者,留此本面目尔”,则单行本与总集本内容有差异较大,不可校改,然究竟有何差异,因单行本失传,今日已不得而知,但这提醒我们要注意周必大日记被删改的情况。我们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八日《奏孙绍远差除赈籴减价三事并跋》与《思陵录》记载虽大致相同,但有小异,如下:
《思陵录》:乙亥(八日)。五更(鼓),带御器械邓从训来两传旨云:“驾即今过宫供侍汤药,更不还内。令一面降指挥召草泽,所有大内行宫合差官及服制并差三卫兵将廵警弹压之类,宜子细理会。”予因附奏:“万一太上不讳,合差金国告哀使。”又令附奏三事:一、昨日已议定广西漕臣孙绍远移湖北运判,替周颉,恐叶大未能便到,则广西全无监司,欲便降指挥,除孙绍远替周颉而令候叶大亷到任;一、韩彦质再乞赈粜米,本俟月半取旨,今欲更借与五万石;一、赈粜米虽令平价,缘无钱数(类),莫知所从,今欲令依时直,减四分之一,将来必不亏丰储元籴之数。又礼部、太常寺申车驾频数往来徳寿宫,欲乞措置复道。予令邓携以进呈,若许如此,则令内修内司同临安府措置。既至待漏院,邓御带复来云:“三事甚好,并已批依,丞相(然相公) 思虑无不允当,复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谕丞相,凡百更頼子细理会,恐官家忧恼中多有颠错。”[10]1617-1718
《奉诏录·奏孙绍远差除赈籴减价三事并跋》:一、昨日已议定除孙绍远作湖北运判,替周颉,恐离任则广西都无监司,欲降指挥候叶大亷到日离任。一、比韩彦质再乞米往诸县赈籴,初俟月半后取旨,今欲凖备应副五万石,依例拘收价钱。一、昨令平价籴米,缘未曾定钱数,恐増损不定,今欲令比市价四分减一,髙下随时,旬日一申,比之丰储仓元籴之价,决可及数。奉御笔批依。
(跋) 十月七日晚,太上腹疾过度,势益殆。八日五更,带御器械邓从训来两传旨云:“驾今即过徳寿宫供侍汤药,更不还内。可一面降指挥召草泽,所有大内及行宫合差官并差三衙兵将廵警弹压之类,宜子细理会。”因附奏礼部太常寺申乞置复道,频数往来,若许之,则欲令临安府同修内司措置。此外别有三事。昨日已除叶大亷广西漕运见阙,赵伯逿虽除提刑,尚在泉州。孙绍远正与詹仪之交争,忽闻冲罢,必以为疑。又此间诸县赈籴米,恐或不继,且未曾定价。皆目前急务,恐太上弥留中,无由禀旨,乃秉烛忽遽具奏,令从训进呈。暨至待漏院,从训复来传旨云:“三事甚好,并已批依,丞相思虑无不当,复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谕,凡百更頼子细理会,恐官家忧恼中多有颠错。”臣某谨记。[10]1436
跋语属于周必大追记,内容与日记相同的部分应是从日记中抄出。《思陵录》与跋语的内容相比,缺少的重要信息是“孙绍远正与詹仪之交争,忽闻冲罢,必以为疑”这一涉及政治斗争的事实,多的是“予因附奏:‘万一太上不讳,合差金国告哀使。’”乞置复道乃礼部太常寺申,周必大附奏三事,因此邓从训奏报返回后,云“三事甚好,并已批依”,对复道事亦加以回应,说“事不可行”,跋语与《思陵录》一致。如果加请差金国告哀使事,周必大实际附奏四事,但邓从训返回的话语中没有对此加以回应,亦只云三事,而且周必大不能预知高宗的病情,他贸然说出差金国告哀使事,如果高宗痊愈,其罪名不小,说明《思陵录》中差金国告哀使事应是后来所加,目的不过是为周必大增光。从另一面看,这则跋语和上文记录孝宗服三年丧事也可以说明:虽然《思陵录》的记载与其他记录有一定偏差,但大致的事实是基本可靠的。
为了更好地解决周必大日记及其相关问题,我们需要将周必大日记与其他材料参悟使用。比如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周必大援引朱熹入朝,而朱熹遭到弹劾,初四日周必大参与议事,此日周必大将孝宗要求朱熹入对的意愿传与朱熹,但是这在日记中没有记录。[17]896-897十一日,周必大又参与讨论林栗对朱熹的弹劾,且援助朱熹,日记不仅没有记载,连日期都未留存。[17]902-903此月缺略甚多,我们可以用相关书籍补出,以便我们研究日记所记录时间段的历史及缺略的原因。又比如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二十日,《思陵录》记录孝宗内批付三省、枢密院。我们可以根据周必大自己的记录补全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据《奉诏录》,孝宗四月十八日下《布素终制御笔》,要求王淮、周必大等润色,周必大执笔改进稿同日奏上,云:“朕昨降指挥,欲縗絰三年,缘羣臣屡请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视事延和,俟祔庙毕,别议再稽礼典,心实未安,服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10]1444孝宗又下御笔认为改进稿没有对之前“俟过祔庙勉从所请之诏”做出回应,斥责王淮、周必大,执笔回奏承认错误并重新改进,云:“朕昨降指挥,欲縗絰三年。缘羣臣屡请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视事延和,虽有俟过祔庙勉从所请之诏,然稽诸礼典,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10]1445周必大于改进稿后记录道:“二十日批出,改‘易服御殿’为‘御殿易服’,‘姑’以为‘故’,以‘延和’为‘内殿’。”[10]1445周必大日记只记录了内批的结果,并没有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然而这恰恰是研究《思陵录》不可缺少的方面。因此,要完全解决《思陵录》 的问题,必须将《思陵录》 与相关材料参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