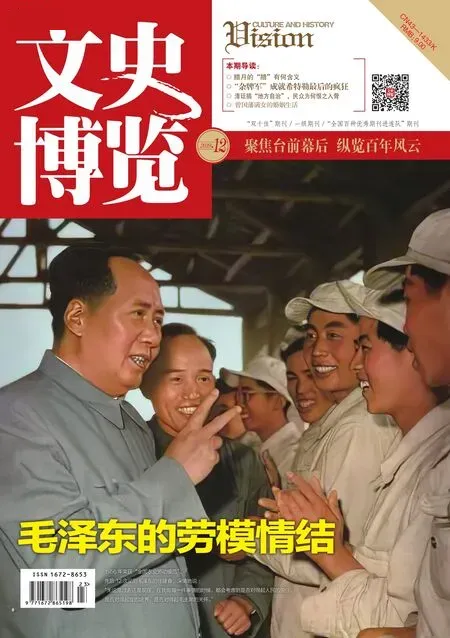那些年买小鸡,很少给现钱
记得小时候,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都要养几只、十几只,甚至二十多只小鸡,而且养的大都是母鸡,所谓“鸡屁股银行”是也。因为这些母鸡下的蛋不但能解决一年油盐酱醋茶的费用,还能把孩子上学的学费解决掉。
那时养鸡,一般都不是自家孵化,而是在早春时节买人家的小鸡来喂养。说是买,但很少有给现钱的,大都是赊,就连挑担卖小鸡的,一般也不喊“买小鸡”,都是喊“赊小鸡”了。
之所以“赊”,是因为那时候农民一年到头手头上都不宽裕,过年时已经花了不少钱,早春时还要把主要资金用在农业生产上,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钱来买小鸡了,所以买卖双方约定俗成,一般不现金交易,而是先赊欠着,等赊欠的小鸡长大,农户到深秋或初冬卖了成鸡或者鸡蛋,有了钱再结账。同时,这个时候,秋收一毕,生产队也开始分钱了,与早春相比,农户的手头上宽裕多了,这个时候赊卖小鸡的人拿着账本到各村各户收账,都能收到钱了。
父亲的干儿子松山哥当时所处的大队有炕房,大集体时,生产队的炕房,一次孵化小鸡一般是五六千只,到了松山哥的父亲大老李自己单干时,一般是2000只。每次孵化时间相隔6天,上一次孵化没有卖完的小鸡,就混入下一次继续卖,所以精明的妇女在拣鸡雏时,一般不要大个的,因为在她们的心目中,那都是上一次拣剩下的,是次品。
1967年的秋天,刚读初中二年级的松山哥就辍学了,回村的第二天,他就参加了大队的“赊小鸡”队伍,与一个成年人一起,挑着扁担走四乡八里“赊小鸡”去了。他用的那根扁担我见过,“上弯扁担”两头翘,两边担的箩筐底部是有四个撑子的方形木托。开始他跟在大人的身后喊不出口,后来慢慢习惯了,竟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赊小鸡”专业户,一直到1990年以后,他还卖着小鸡。
至今松山哥还清楚地记得,用扁担挑着小鸡卖时,最多只能挑100多只。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开始用自行车载着两个座筐叫卖了,一次能载300多只;1990年以后,骑着摩托车叫卖,两边的筐笼上又各加一层,一次能带500多只了。再以后,农村人口减少,粮田也减少,大家感到喂鸡费事费时,散养鸡的农户越来越少,赊小鸡的也慢慢消失了。
谈起这些,我和松山哥还都能回忆起当年的小鸡价格、赊小鸡记账的情景、妇女挑拣小鸡时的神态以及孩子们跟着瞎跑的热闹劲。松山哥说,他辍学之前,也经常在他学校所在的村子里帮人家记账,他说他记的最早一笔账是1961年农历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到邻村的同学家里玩,遇到卖小鸡的老头不会记账,赊了20只小鸡的大婶也不识字,于是就让他代笔了。当时一只小鸡付现钱是两毛,赊账就是两毛五,20只小鸡是五块钱,他记好后,把账本和圆珠笔交给卖鸡人时,还得到了大家的夸赞。
这个感受我也有过,我也是上小学时就帮人家记小鸡账了,记忆中那时候人们特别守信,不论是卖鸡人自己记,还是买鸡人记,抑或是找第三方代笔,从没有出过差错,更没有“老赖”出现。记得有一年来我们村里收小鸡账的人,由于账本破损严重,账本上只能看清村庄的名字,户主、数量、价格都模糊不清,但收账人一到村里,几个妇女汇集一起,互相回忆一下,大家都分文不少地把钱付给卖鸡人。
我之所以给他们记的账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好事,是因为我喜欢看小鸡,每当卖鸡人把箩筐放在村中最热闹的地方,拿出一截茓子(方言,做囤用的狭长的粗席子)头圈好,把一只只小鸡放到里面时,那毛绒绒、全身嫩黄,连嘴和爪子都是黄色的小鸡煞是可爱,它们叽叽喳喳、你挤我我挤你、瞪着眼睛的神态,总吸引着孩子们久久不愿离去。
特别是碰到大人们挑拣小鸡的时候,我们更是殷勤之至,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卖鸡人才舍得让我们摸一下小鸡。松山哥说,那些挑拣小鸡的婶子大娘,挑起鸡来可仔细了,首先是看小鸡是多是少,是头茬鸡还是二茬鸡,抑或是垫窝子鸡,头茬鸡二茬鸡还好,垫窝子鸡她们绝对不要,哪怕非常便宜;其次是看小鸡旺相不旺相,有没有精神头,生命力强不强;再就是看小鸡有没有“闪铺”症状,就是在炕房里有没有感冒过,如果感冒过,小鸡屁股上就会挂点粪便……回忆起这些事来,松山哥脸上还是溢满荣光。
如今“赊小鸡”的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那种朴实守信的生活态度,还是让人非常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