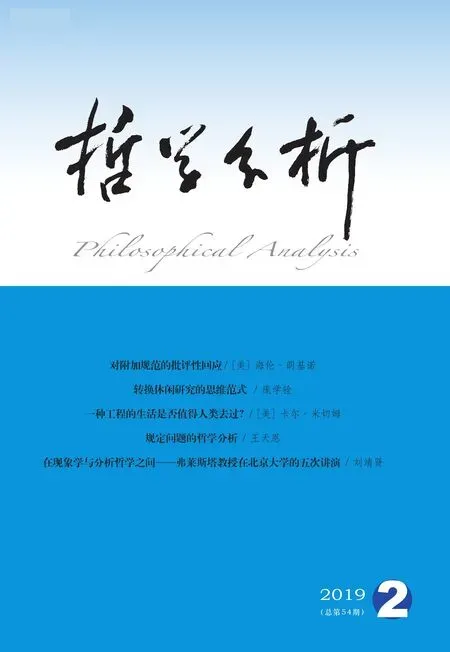规定问题的哲学分析
王天恩
现代科学和哲学中描述(description)问题的全面凸显和深入研究,使作为描述前提的规定(stipulation)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a王天思:《描述和规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而在当代信息文明的实践层面,大数据基础上的创构,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则使规定浮出水面,使在先规定的研究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语言学中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stipulationism)和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到哲学中的规定主义(stipulationism)和描述主义,从规范人类行为的外在法规到与事物“本质”相联系的内在规定性,规定问题的研究既涉及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逻辑学和美学,又涉及语言学、心理学、法学,甚至政治学。这一特点决定了规定问题的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涉及对于真、善、美共同哲学基础的探索。
作为人类(目前为止只有人类)为认识对象所作的关于量和质、方式、方法和模式等的规范性设定,规定注定具有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关于规定的研究,人们可以在语言学和哲学中感受到一种共有的张力。语言学和哲学研究中由“规定主义”和“描述主义”构成的张力机制,使规定问题得以从思想深处凸 显。
一、语言学中的规定主义致思
在语言学中,规定主义不仅有“prescriptivism”,还有“stipulationism”意义上的,只是“stipulationism”的使用频率远不如“prescriptivism”高。语言学中的stipulationism受到越来越多挑战,以至于早在20世纪80年代,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兴起就被认为“为规定主义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aBrian MacWhinney, Language Emergence in An Integrated View of Language Development—Papers in Honor of Henning Wode, edited by P. Burmeister, T. Piske, and A. Rohde, Trier: Wissenshaftliche Verlag, 2002, p.17.。之后“形式语言理论也开始远离规定主义”bN.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而“从历史发展看,突生论(emergentism)是作为对规定主义的反叛开始的”cBrian MacWhinney, Language Emergence, p.18.。与“stipulationism”不同,辞典编纂的规范主义和规范语法则在语言学研究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
在语言学研究中,辞典编纂的规范主义和规范语法虽然分别有被辞典编纂的描述主义和描述语法淹没的现象,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语言学中关于规定问题研究的式微,而且相反,语言学中关于规定问题的研究,事实上正是在与规定主义和描述主义、规定语法和描述语法所构成的张力中得以更深入系统。
一些辞典编纂的规范主义代表人物被看作语言上的保守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语言是活的;与语言的使用性相比,语言的规范性不仅在关系上位居次要,而且二者的权重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语言的规范从属于语言的使用,因为语言的规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语言的使用服务的。在规范语法和描述语法中,这一点有更具生命特征的展开。
语言是活生生的,是在人们使用中的生命体。因此语言规范不是依据某个一成不变、具有本质特质的既定标准而存在,而与人们使用语言的需要和使用的具体情景密切相关。因而,语言的规则和使用规范本身不是一个枯死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的过程。规定主义辞典编纂原则似乎完全是一个僵死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反映了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语言是最讲究规范的,没有规范的语言不能成其为语言,因为它不能使用,达不到使用语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语言来说,最根本的是使用。正如不会投入使用或没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具,不会进入使用的语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因此,语言的规范性是为语言的使用服务的,从属于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的需要。由于人们使用语言的需要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语言本身也在随之不断变化发展。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规范也在不断变化。作为语言的关键要素,语言规范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而不是某种与具体使用无关的标准,也不存在一种关于语言规范的无条件客观标准。要把握语言这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就必须把握语言不断演变的规范,这就必须客观地描述不断变化的语言,其中就包括对语言使用规范本身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描述主义更好地体现了语言规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即语言——包括其规范——的约定俗成性质。
英语词典编纂虽然经历了一个从以规定主义为原则到以描述主义为主流的过程,其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但规定主义始终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只是规范从强制性转向指导性。发展到当代,作为两种在理论上曾经完全对立的观点,规定主义和描述主义呈现出两相结合的总趋势。这种结合趋势,在语法理论研究中如出一辙。
规定语法明确规定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以固定不变的标准把语言当木乃伊了;而语言是活的,语言的生命就是语言的使用。英语的规定语法最早根据拉丁语法建立,但随着英语的发展,日渐与实际使用中的英语拉开距离。特别突出的是,一方面是实际使用中的英语,另一方面则是规定语法为口语的习惯用法。后者所规定的条条框框,与前者越来越不相符合。描述语法则着眼于描述语言实际使用的方式,更注重语言的约定俗成本性,注重语言应当如何使用,而不是把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定看作不可移易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个外在的固定标准可以脱离语言本身活生生的使用。
由于把语法看作语言使用者广泛默认的结果,描述语法更关注语言的变化及其文化语境的时代性。但也正是由于语境及其时代性,脱离习得语言环境的外语学习晓示了描述语法的局限性。当人们的语言习得脱离语言使用的文化语境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抽取该语言的截面,把它制作成一个干枯的标本,供外语学习之用;不这样做,人们就没有办法或难以脱离语言环境学习一门外语。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的描述主义弊大于利,甚至不可行。
作为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语法具有很强的“规定性”,但语法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性的标准。正是语言重在使用,从而使语言或语法的“本质”概念失去了意义。这也正是在感性实践中,“本质”概念失去原本意义的根本原因。语法就是语言的实际用法,一切取决于语言实际使用中使用者的需要及其语境。正是语法,以一种最为平常的方式标示着本质主义的症结所在;正是实践使用,使“本质”概念从本体意义回归到描述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也许是标明本质主义臆造性的最好例证。这也是维特根斯坦那么热衷于语言游戏研究的内在原因。
语法必须具有相对规范因而是相对稳定的,但语法本身不是语言的标准。语言的标准是生活实践,是语言的实际使用需要。因为,正是人的生活需要语言,而语言的使用需要语法,而不是相反。语法如同交通规则,也像交通规则一样决定于交通的实际需要——当然归根结底是人的需要。人的语言是供人使用的,而不是相反。
与规定语法一样,辞典编纂的规定主义把语言规范绝对化,坚持说法和写法非“对”即“错”的固化标准,将语言因时代变化而突破既定规范的现象看作语言的退化。这种主张甚至推动成立专门组织“照看语言”,以遏制语言的变化,从而日渐走向保守。
描述语法立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因而反映了时代性,关注语言的变化发展。这种语法理论的一个主要根据,就是历史上是错误的语法,可以由于语言的现实发展变成新的语法现象。在语言的使用中,语法变异就像某些生物变异,它正是语言发展的契机,不能等同于语法错误,比如“很中国”和“百分百”等。社会发展速度越快,语法变异发生的频度就越高。在信息文明时代,语法的变异甚至成了网络语言的标志性特征。一些网络语言虽然明显具有不受传统语法制约的随意性,但由于得到网民的普遍认同,就融入了网络语法规则。在语言环境中,由于文字作为即时交流的工具,中文语言的变化就受文字拼音的极大影响。“神马是浮云”,如果脱离网络时代,只能往文学性描述理解;而从网络语言活生生的使用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它与时代相契合的奇妙使用效果。而规定语法则阐明了一种语言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规则的根据,这是有效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础。所以,人们强调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应当以规定语法为基础。但是,规定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如果句子“被和谐了”很常用,从描述语法看,其存在就是自然的,而从规定语法看则会被认为语法蹩脚,应当改为“出于和谐考虑被……”了。这里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主要在于语言必须有规范(约定)的一面和俗成的一面。也就是说,语言归根结底是用来使用的,只有使用中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因而语言是与其使用分不开的。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进展,同时也是推进哲学研究的重要契机。
语言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产物,又隐含着人类认识形成及其性质的密码。描述和规范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形式方面。事实上,不仅在语言形式中,在经验科学中——即使在人们心目中最具客观性的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
二、科学研究中的规定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必须作出某些规定;所有的法律和规范都是建立在这种规定基础之上的规则的典型形式。但规定并不仅限于社会生活领域,即使在对于自然的描述中,规定也都无所不在。如果这一点在经典科学中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那么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则再清楚不过了。
在牛顿力学中,不仅有一个一个似乎与外部客观存在一一对应的概念及其所构成的体系,而且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伽利略坐标”和“万有引力”等。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伽利略坐标”没有一个对应的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根据建立经典物理学理论需要设立的一个规定。而一些看上去并不那么特殊,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高度契合、似乎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概念,实质上也是规定,典型的如“波动”和“粒子”等。而在量子领域,则完全不像我们的经典想象,一些基本概念的主观规定性质暴露无遗。正是量子力学,使规定问题在现代科学中得以集中凸显。深入考察量子理论基本概念的规定性质,是规定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
在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中,相对于经典物理学,物理学家们遇到了空前的理解困难。早在1926年,量子力学的数学表达形式就已经基本完成。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十分成功地表达了微观领域的复杂关系,可是与以往的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实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正如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谈到当时的感觉时所说的,量子力学“显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对它的正确性确实不能有进一步的怀疑。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对这种量子力学应该如何进行解释,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其内容”aWerner Heisenberg, Encounters With Einst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2.。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狄拉克(Paul Adrie Maurice Dirac)也曾回忆道:“我们虽然有了涉及这些非对易量的方程,但在当初,我们没有对于这些方程的一般解释,对于一个物理理论来说,那确实是一种奇异的情势。”bP. A. M. Dirac, Directions in Physics, John Wiley, 1978, p.7.面对这种不能有直观理解的理论体系,物理学家们不能不感到不安。即使一些现代物理学家也仍然有同样的感觉,巴瑟尔·希勒(Basil Hiley)就曾写道:“我已经被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培养成才,我觉得直观总是具有极大帮助。但当我考察量子力学时,我发现它完全是非直观的。我们只有一种规定——一组规则:我们有一个波函数,它被假定描述了系统的状态;我们有一个算符,它可以运用于这个波函数及我们从中得到一定具有预示性的实验数据。但这对于我理解——譬如说双缝实验并无帮助。当穿过狭缝时,电子到底在干什么?它是穿过一道缝,还是穿过两道?这些问题对于力图获得一种什么正在实际发生着的感觉,是极为重要的。”aP.C.W. Davies, Julian Brown, The Ghost in the Atom: A Discussion of the Mysteries of Quantum Phys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6.这里所涉及的,就是规定和规定问题。
现代科学越来越不容置疑地表明,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们所建立的关于自然的科学理论,并不是客观实在的镜式反映,而只是对它的描述。那些沉湎于描述的科学家,始终把对自然的描述当作自然本身的性质或对自然的纯客观认识。人们谈论着、描述着世界,而没有注意到描述者,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着一种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努力。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似乎与此不同,他们所面对的是宏观事物,好像不存在描述与解释分离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描述似乎是不重要的,正像在经典物理学中那样,人们所要关注的似乎只是理解或解释(interpretation)问题。其实,那只不过是多了一层“建筑”,或者说更隐蔽些而已。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文本就是描述的结果,就是一种描述。在那里同样存在着描述问题。而且,人类认识越是深入,描述问题越是明显和突出。只是在人文世界和宏观领域,由于更深地卷入人类学特性,描述问题进一步渗透进规定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描述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规定问题,这是关于规定研究的内容。关于规定的哲学研究更深地涉入人类学特性,它是在人文世界和宏观领域描述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描述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语言表达式的分析,但其根本任务则是对我们描述的探究。而描述的规定基础问题,则典型地表现在当代自然科学前沿。
在当代基础科学发展的前沿,我们可以最为典型地看到描述和实在这两种不同致思的微妙而富有深意的交织。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就是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虚时间”概念的提出和在宇宙描述中的运用。
虚时间听起来的确有点像科学幻想,但作为一个很好定义的数学概念,它就是用虚数度量的时间。虚数是数学上和实数对应的数,它对应于一根垂直线上的位置:零在中点,正虚数画在上头,而负虚数画在下面。这样虚数可被认为是与通常的实数夹直角的新型的数。事实上,在对宇宙的描述中,虚数的引入本身更意味深远。
由于虚数“是一种数学的构造物,不需要本体的实现;人们不能有虚数个橘子或者虚数的信用卡账单”。从实在论角度看,“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意味着虚数只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然而从霍金的哲学立场看,“人们不能确定何为真实。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去找哪种数学模型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由于人们发现牵涉到虚时间的一种数学模型不仅预言了我们已经观测到的效应,而且预言了我们尚未能观测到但因为其他原因仍然坚信的效应,霍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那么何为实何为虚呢?这个差异是否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a史蒂芬·霍金:《果壳中的宇宙》,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9页。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对宇宙的描述本身,而且涉及规定的基本问题。虚时间概念本身,再好不过地表明描述和实在的关系。正因为其“虚”,虚时间使我们看到描述和描述对象本身的不同。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霍金通过自己的工作所得出的一些观念意义重 大。
霍金自称实证主义者,他同意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个数学模型,它描述和整理我们所进行的观测。一个好的理论可以在一些简单假设的基础上描述大范围内的现象。并且作出能被检验的确定的预言。如果预言和观测相一致,则该理论成立,尽管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观测和预言相抵触,人们就必须将该理论抛弃或加以修正。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说时间究竟为何物,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将所发现的现象描述成时间的一种非常好的数学模型并且说明它能预言什么。b同上书,第31—32页。然而,霍金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证主义者,他在建构自己的宇宙理论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关于描述和规定的思 想。
霍金认为,我们不能询问一个理论是否反映实在,因为我们没有独立于理论的方法来确定什么是实在的。甚至在我们周围被看作显然是实在的物体,也不过是在我们头脑中建立的一个模型。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有几种对于宇宙的不同描述,所有这些理论都预言同样的观察。我们不能说一种描述比另外一种更实在,只是对一种特定情形来说,某种描述更方便。所以一个科学理论网络中的所有理论都处于类似地位。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声称比其余的更实在。即使时空及其维度,也不是绝对独立于理论的量,而只是依赖特殊的数学模型导出的概念。这样一来,什么是实在的呢?根据实证主义哲学,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不存在独立于模型的实在性的检验,或者说什么是宇宙的真正维数是没有意义的,在宇宙理论中,四维和五维的描述是等效的。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世界中,我们对这些自以为一清二楚,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也许只不过是柏拉图“洞穴”中,闪烁篝火对面我们在墙上的投影而已。面对那个“膜的新奇世界”,“我们不能问什么才是实体,是膜还是泡泡?两者都是描述观测的数学模型。我们可以随便使用这两个模型,哪个方便就使用哪个”a史蒂芬·霍金:《果壳中的宇宙》,第198页。。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应当是对真理的否定,而是关于真理问题的更真实阐述。这种阐述之所以更真实,就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量子力学规定性质认识的基础上。无论语言学还是科学中的规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哲学意蕴,都与哲学研究中的规定问题联系在一起。
三、哲学研究中的规定问题
在哲学中,规定主义(stipulationism)与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密切相关。约定主义尽管受到诸多批评,但以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为代表的“约定论”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始终给我们以不能摆脱的影响。
彭加勒认为,几何学中的基本命题,包括欧几里得公设,都不过是些公约。因此问它们的真假是不合理的,问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像问米达制是真的还是假的。彭加勒的这一观点,并不像有些理解那么简单,他在两方面作了重要解释。一方面,“这些公约是便利的,而这是若干实验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这种公约并非绝对任意的;它不是由我们的私意而出;我们采用它,因为有些实验向我们指出它是便利的”。正因为如此,他甚至批评有些哲学家把全部科学看作原理,从而把全部科学看作公约。彭加勒认为这种观点是唯名主义的,“这种荒谬的学说”“不值一谈”。b彭加勒:《科学和假设》,叶蕴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7—98页。因此,对于约定主义观点,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简单对 待。
即使我们忽视甚至反对约定主义,但无论如何不能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约定论特征视而不见。约定论观点中很多重要约定的假设性质及其试图在经验论与先验论之间作出新的探索,都表明约定论与预设理论的内在关联。正是从规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吸取约定论的合理因素到深化规定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
约定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某些事实是能动者(agent)建构的,而叙述它们的句子也是这种行为使其为真”c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 in Lorenzo Magnani,Walter Carnielli, and Claudio Pizzi (eds.), Model-Based Reaso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pringer-Verlag Berlin and Heidelberg GmbH & Co. K, 2010, p. 24.。而且,科学理论中的很多内容都具有约定的性质。
哲学中的“规定主义”具有与约定主义相似的一面,认为“某些对象和某些事态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创设的,而涉及其创设的是它们被想出来(being thought up)。同样,规定设定了对象和事态在这样的方式中被想出来——使表达它们的句子为真。”更简要地说,规定主义“认为某些事实是被建构的,而且一些关于它们的陈述是能动者的语言行为使其为真”a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 这既与真理问题密切相关,又在一个不同角度涉及实在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伍兹(John Woods)的“真理的规定性 (stipulationist)理论”就试图“在抽象领域发展一种反实在论,在这种抽象领域的核心保留反实在论倾向”bA. D. Irvine, John Woods,“Paradox and Paraconsistency: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bstract Sciences (book review)”, Studia Logica, Vol. 85, Issue 3, 2007, pp. 425—428.。规定主义认为一些事实是被建构的,而关于它们的一些陈述的真则是能动者的语言行为使然,这就无疑脱离了规定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根据。这是规定主义既具有重要思辨张力,同时又面临诸多挑战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规定的客观根据问题在给规定主义带来严重挑战的同时,又使规定本身的研究蕴含着重要契机。一方面,在哲学中,人们认为规定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是富有成果的,但是规定主义未必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规定主义者必须解释,这种关于对象的方法论迷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果”,由于规定主义“以对象为中心的思想只是解释学的”,让人们担忧规定主义者“不能作出解释”cJody Azzouni, “Proof and Ontology in Euclidean Mathematics”, in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edited by Tinne Hoff Kjeldsen, Stig Andur Pedersen, and Lise Mariane Sonne-Hansen, Denmark: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04, p. 120.。这种担忧肯定不无根据,而规定主义在客观根据方面的不足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规定本身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在哲学特别是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基础中,规定主义仍然是强大的张力来源;甚至在经验科学中,规定问题亦日渐凸显。
随着哲学的发展,规定的特殊地位早在近代就已露端倪,“对于康德来说,规定是综合,就是新概念的创设”。这里可以看到规定问题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规定与综合密切相关。“分析和规定的区别大致相当于康德的分析与综合对比。康德认为,分析的任务是使概念清晰,综合的任务是创设明确的概念,那就是构造概念。”d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 Topoi( 2012) 31:121,C134.这已经是对规定的直白说明了,只是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定性质,从而还没有更强有力的支撑,关于规定问题的研究条件还不成熟,以致数学和逻辑早已天然表露出来的规定性质,也被掩映在“先验”或“先天”的迷雾之 中。
事实上,数学的规定性质最为明显,而且最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规定在近代哲学中历史悠久,而且很久以来在数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a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而“对于罗素而言,规定是数学定义,这使事物为真而没有产生由以说明如何为真的概念”bBertrand Russell,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 p. 27.。由于规定的约定性质,人们很难想象,规定怎么能支撑起精确的数学。因而“规定主义”就时而被当作存在问题的标志。乔纳森·卡斯汀(Jonathan Kastin)就被贴上“数学规定主义”的标签。cJody Azzouni,“Proof and Ontology in Euclidean Mathematics”.直到现代人们才认识到,虽然规定随约而变,却并不影响它们作为理论的基础。“正像康德所说,规定是数学的股票和贸易(stock and trade)。但它也在所有基于模型的科学中稳定地工作。”d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而变动不居的规定成了基础,这正是规定在人类认识中起作用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数学和逻辑都具有规定的性质。
与数学相似,逻辑也具有明显的规定性质。“一个虚无主义的早期预示是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按照它的观点,逻辑既是规定性的(stipulationist),又是与人的意识无关的事物的先在事实(unattended by antecedent facts of the matter)。对于卡尔纳普来说,逻辑是你所做成的东西。”eIbid.事实上,不仅数学和逻辑,也不仅在语言学和科学中,在哲学中,规定问题的研究早就开始了。在约定论(conventionalism)和预设理论(theory of presupposition)中,在当代哲学前沿,这种研究由于涉及对象的内容而事实上转向规定问题的哲学研究。因而,规定问题的研究将涉及规则和规律的共同哲学基础。在我们的认识中,规则和规律似乎是泾渭分明的。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游戏都必须有规则,规则赋予游戏以意义。“要获得一种意义也必须用公约”,而公约就是典型的规定。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定基础之上。事实上,所有理论基石都具有规定的性质。“蒯因(Quine)说理论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概念化;爱丁顿(Edington)说它们‘是预先商定的工作’。”fIbid.而哲学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认为“分析是哲学的范围,综合则是数学的领域”,只是因为从分析哲学的传统把哲学看作只是分析。只要承认“解释和理性重建是二者的结合,只是解释更多的在于分析而理性重建则更倾向于规定”gIbid.,哲学基石的规定性质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所有理论基石都具有规定的性质,正是规定对于科学和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所有理论都是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体系,我们必须在规定的基础上作出解释;而在解释的基础上,我们又可以作出更新的规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如奎因的著名妙语:一个人的解释,是另一个人的规定”a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解释和规定建立起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进行着“人类的伟大创造” (爱因斯坦语)。只是我们必须在基于规定建构起来的空间中,将真理问题落到一个更真实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定回答这一问题:‘那么,怎样使它们为真的?’答案是,他们被理论家规定为真”,也就是说,“由此引起的关键问题是:理论家的规定——他的如是说——何以可能产生真理?”b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在这里,问题本身就是深化研究的“端口”。而这一问题的解答,却正是在规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真理问题本身探索的深入,无论在科学还是哲学中都是如此。哲学基石的规定性质自不待言,科学基石的规定性质也正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而规定问题就成了哲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内容。
霍金关于前沿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索,表明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巨人,而且像爱因斯坦和波尔他们一样,也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至少就其所涉及的描述和规定问题而言是如此。从规定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实在”作为一个规定来考察,把关于实在的规定提到一个比“关于实在是什么”的问题更具前提性的地位。甚至“实在是什么”的问题本身,也可以改写成更有效的“我们关于‘实在’的规定意味着什么”的问 题。
在关于规定研究的哲学前沿,当塞尔孟(Nathan Salmon)说我们的规定和形而上学的规定是两种不同的规定(decides)cNathan Salmon, “Trans-World Identification and Stipula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84, 1996, pp. 203—223.时,其实就把形而上学看作与我们的认识无关的外在于我们认识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的规定和形而上学的规定是同样的一个规定,因为即使形而上学本身也建立在我们规定的基础之上。因而,与我们相关的法规(legislation)和形而上学的法则(law)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在计算机科学中,我们则可以看到一种与规定更为密切相关的情形。规定语法有一套语法规则规范语言,而描述语法则详尽、完整地描述语法结构的规律。在数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中,所使用的形式语言的语法是描述语法,而自然语言的语法则往往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规定性。在这些领域,规律和规则相互交织,甚至可以通用。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对象的存在方式与我们作为特定宏观主体的人类学特性密不可分,与我们的思维规定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在提示着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关于规定问题的哲学研究。
关于规定问题的当代哲学研究,弗雷格的探索是深层启动,维特根斯坦的奇特命题是规定问题研究的重要启示,之后才有了克里普克的逻辑展开和规定问题研究的当前进展。规定问题的当前研究,首先是在规定的使用中研究规定问题。在使用中探究规定,正是规定问题研究本身能具有的基本特点,也是不同于传统哲学范式的重要特色;其次是在专名研究中涉及规定的形成机制,弗雷格和克里普克关于专名和通名的研究,蕴含着关于规定形成机制的重要思想萌芽;再次是在悖论消解中研究规定;最后是在逻辑和经验间探索规定与真以及先验性问题。
四、结 语
关于规定问题的哲学分析表明,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开启的信息文明的到来,关于规定的反思日益凸显,规定论研究呼之欲出。
规定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规定的形成、规定的性质、规定的发展和层次、规定的合理性和合理化等。规定形成不仅具有特定的客观根据,而且与主观需要密切相关;规定具有实践性、相对性、主体间性、规约性、抽象性和人类学特性。规定的类型主要包括有限规定和无限规定、相对规定和绝对规定、具体规定和抽象规定、知性规定和理性规定、经验规定和逻辑规定、定性规定和定量规定等。既存规定的突破把描述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意味着规定的发展。规定的层次呈现出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的系列:涉及否定概念的规定、涉及思维边界的规定以及涉及活动前提的规定和涉及理性本身的规定。规定的合理性包括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规定的合理化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具有以人类实践需要为转移的性质。在规定的合理性发展和合理化过程中,规定批判居有重要地位,涉及规定的反思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