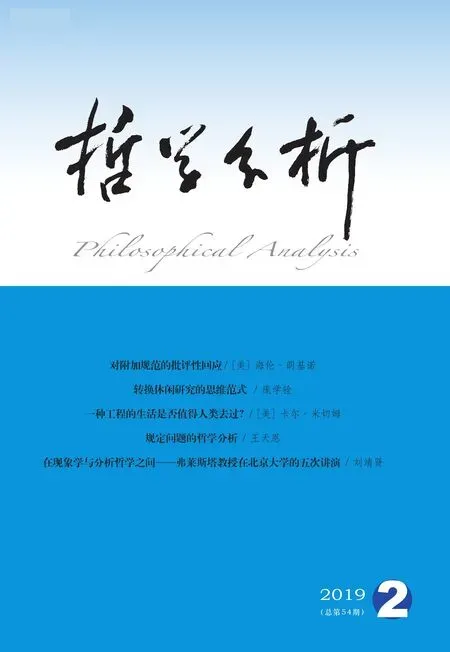一种工程的生活是否值得人类去过?a
[美]卡尔·米切姆/文
黄晓伟/译
作为工程的哲学人类学的尝试,本文致力于思考工程的生活方式(engineering way of life)和工程化的生活方式(engineered way of life)。b“工程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生活方式 ,而“工程化的生活方式”指的是非工程师所处的、已被工程化了的生活方式。——译者这一研究兼收并蓄了多种思想资源,因而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与其说这是一篇完全成形的正式议论文,不如说更像一篇非正式的论说文。
一、作为独特生活方式的工程
通过将工程生活设为哲学人类学的一个主题,笔者想要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工程不仅是一项专业性的活动,还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 式。
工程师们已经以各种方式为这一论点作过辩护,但有时却适得其反。在《论方法:指导工程师的问题解决之道》 (2003)一书中,美国核工程哲学家比利·科恩(Billy V. Koen)提供了一个迄今推理最为严谨的版本。
对科恩而言,工程的在世方式——通过他称之为解决问题的工程学启发式方法a启发式方法(heuristic),又译为“探索法”,其特点是在有限的问题域内,利用过去的经验规则进行试错,选择可能有效的方法,而非以确定步骤系统地去寻求答案。——译者——既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一直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它与我们的人类学起源是同期出现的。“人成之为人意味着成为一名工程师” (To be human is to be an engineer)bBilly V. Koen, Discussion of the Method: Conducting the Engineer’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相比过去,如今的工程只是更加具有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获得部分地借助了科恩自己的笛卡尔式论述。
但这肯定是概念上的夸大其词了。工程自有其历史。工程自身的起源是有别于原始人的。尽管人类生活可能起初就依赖技艺,但并不总是依赖工程。“工程”这一术语是在特定时间(大约公元1500年)才出现的,指涉一种特殊的技艺,其建造过程是如此之新,以至于需要命名一个新词。
作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c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British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成立于1818年,1828年获颁英国皇室的特许状。——译者的首任主席,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1757—1834)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一名学徒期满的石匠开始干起,在他近三十岁时,技能已经变得足够娴熟,转而自称是一名建筑师。正是作为一名建筑师,他设计的房屋和教堂才被建筑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 Nikolaus Pevsner)赞许为“非凡的设计,内外都极为庄重”dNikolaus Pevsner, The Buildings of England: Shropshire,revised by John New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62.。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特尔福德又一次做出了转变,开始自称为一名工程师。显然,他认识到工程是与建筑殊为不同的事物。土木工程师学会申请皇家特许状时,由特尔福德起草、提交给乔治四世(King George IV,1820—1830年在位)的定义已经很标准了:“土木工程是引导自然界的伟大力量之源服务于人类使用和便利的艺术;其作为自然哲学最重要原则的实际运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预期,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ahttps://www.ice.org.uk/about-ice/who-runs-ice/royal-charter.
这里提到了培根,表明工程师们认为自己在人类活动中引入了新生事物。短语“使用和便利”也蕴含此意,这条价值标准是由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提出的一个专业术语。事实上,休谟与特尔福德两人的生平是存在交集的。
在阐述土木工程的内涵时,这一经典定义继续写道:“土木工程最重要的目标是改善国家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既包括国际贸易方面,也包括国内贸易方面。”这就将工程看作一种脱域的或者去属地化的建造活动,从而与属地性的建筑居所有效地区分开来。譬如,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强调了市政空间的设计与构造,这些空间培育和支撑了家庭生活、政治话语、宗教崇拜以及审美乐趣。bMarcus Vitruvius Pollio, 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translated by Morris H. Morg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0.然而,该书只字未提那些能够提升经济生产效率或交通及通信方式的设计与构造。事实上,恰恰是当特尔福德成为英格兰运河运输系统的建造大师时,他开始自称为一名工程师。
此外,正是在特尔福德这一代人时,工程与其军事起源渐行渐远了。由于不再受制于军队权威的等级制度,民用(即非军事领域的)工程师转而投至新的工业领袖麾下。因此,与当今世界的情形一样,工程领域在文化意义上被资本主义殖民化了。这种去属地化的设计和构造极易受这种殖民化的影响。
二、工程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日常事务
笔者的第二个论点与工程的哲学人类学有关,即工程的这种独特生活方式正在影响着日常事务。正如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被殖民者反而将殖民者殖民化了。工程将商业资本主义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将投资银行业务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这也被称为金融工程)。如今,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平台资本主义。c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 Polity, 2016.
通过将工程生活设定为哲学人类学的一个主题,笔者希望凸显为主题的不仅是工程师成之为工程师的生活,还有我们所有人——工程师与非工程师——日益参与其中的生活方式。这里讨论的“参与”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方面,当然,所有工程师和非工程师的生活都越来越依赖工程成就。正如科恩所说:“环顾一下你现在所处的房间。你发现什么东西不是由工程师开发、生产或交付的呢?”dBilly V. Koen, Discussion of the Method: Conducting the Engineer’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那些遵循胡塞尔路径的现象学家,如帕特里克 · 海兰(Patrick Heelan),所谓的充满直线和几何视角的“木匠化世界” (carpentered world)aPatrick A. Heelan, Space-Percep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172.,现在完全可以描述为充满便利的公用设施的“工程化世界” (engineered world)。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工程师们探索性地设计了各类公用设施,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渗透并且日渐影响着非工程师们的生活。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工程师,还关注我们所有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工程化的世界以及工程的世界之中,并深受工程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都是工程师呢?作为一门独特的职业,工程所表现出的一些关键特征既超出了工程师作为问题解决者的自我认同,也超出了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侧重制造与设计的自我认同——为追求人类的“使用和便利”,这种制造与设计极大地依赖科学知识。科恩所说的“工程学启发式方法”准确地捕捉到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科恩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启发式方法是在解决问题时能提供可信的辅助手段或思考方向的任何方法,但说到底缺少充分而正当的论据,结果也可能出错。”bBilly V. Koen, Discussion of the Method: Conducting the Engineer’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 p.28.工程师们局促不安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非工程师在何种程度上也开始以这种方式思考自己的生活。生活在发达的技科学社会(technoscientific society)中的我们——无论工程师,还是非工程师——都倾向于从问题导向来看待生活,然后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可信的辅助手段或思考方向”,同时承认“[这些辅助手段]说到底缺少充分而正当的论据,结果也可能出错”。我们对于这些辅助手段的承诺和运用是一种意志坚定的决断行为。
我们谈论越来越多的不仅有设计出来的结构、产品和流程,还包括商业计划、经济与政治政策以及生活方式。作为个体,我们会思考如何营造我们的生活以满足那些清晰界定的目标,如何凭借我们科学地发现的自然资源,自觉确保我们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如何从生理上和心理上盘点我们的个人资源,以便更好地经营我们作为工人、企业家、运动员等角色的生 涯。
父母们在不久之前试图规划他们自己的婚姻,以及他们子女的生活,并催促子女们在性格养成阶段就承担起自我规划的任务。学生们规划他们的教育经历,并经常将他们的人际关系(包括他们的友谊)看作需要用启发式方法加以分解的难题。在脸谱网(Facebook)上的自我推销只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表现罢了。解决问题的启发式方法在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它通常是以类似工程学的术语“使用和便利的投入/产出效率”来衡量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规划我们自己的死亡。人类作为赛博格(cyborgs)不只是控制论(cybern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s)的杂合体a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 Routledge, 1991,pp. 149—181.,也是我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杂合体。这意味着,对有着多重表现的工程生活方式进行哲学上的批判性反思无疑是恰当 的。
笔者的观点是,职业工程师的生活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是密切关联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要经历的世界正在逐步地为工程师所设计、建造、运营、维护与创新。工程伦理学不再只是服务于工程师。而笔者的问题是,在最深层和最深刻的意义上,工程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三、工程的生活方式应该被审视
第三个论点是,就像任何生活方式一样,这种工程的生活方式也应该被审视。值得注意的是,科恩在关于工程学方法的笛卡尔式论述中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本文的标题显然暗示了一种非笛卡尔式的不同研究进路。这来自《申辩篇》中的一个著名段落,苏格拉底宣称“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人类去过” (38a)。《克力同篇》对此作了补充,人类不应该只是活着,还要活得幸福(48b)。bPlato, The 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 (Third edition),translated by G. M. A. Grube, Indian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39, p.48.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工程能够或不能增进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呢?对于工程师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活得幸福 呢?
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工匠或实物制造者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曾在《申辩篇》中称赞他们比政客或诗人更睿智。在苏格拉底看来,工匠未曾接受错误的意识。与工程师类似,工匠们确实知道如何造物,而这与(用辞令操纵他人的)政客或(为诸神所支配的)诗人大相径庭。尽管这对于理解人成之为人的意义并非最基础的知识,但却是真实的知识。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5章中,亚里士多德重拾人成之为人的意义这一议题。他观察发现,多数人通过身体上的享乐来寻求善或幸福,但另外两种生活方式也显而易见:政治的生活和理论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并非人类独有,这是一种与动物共有的生活方式。由于政治生活是依赖他人的,需要追求荣耀或尊严,所以它缺少了自主的东西。因此,更为高尚的生活是追求理论的、沉思的或思辨的知识。c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translated by Roger Cris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6—7.
不过,这里用“理论的”“沉思的”“思辨的”等词汇来描述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可能会产生误导。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思辨知识是由我们观察某些重要事物时所产生的那种认识构成的,它很容易单纯满足这种认识,倾向于依赖经验,并从经验中获得智识上的愉悦。思辨知识具有审美体验的特征,既能自我验证,又内在平静。
那么,工程在何种情形上适用于这种分类呢?显然,苏格拉底力求尊重制作和建造的生活方式(即工匠的生活方式),难道推崇思辨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忽视这种生活方式吗?或者说,亚里士多德讨论“技艺”和“创制”的观点能够提供弥补这一空白吗?
除古希腊哲学的视角外,我们能注意到,现代科学研究的生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并富于理智之美。尽管这种观点也受到批评,但科学家们自己无论是作为已有知识的学习者,还是作为推进知识生产及其边界的研究者,在理解世界的本质方面似乎通常会深感满足。当笔者第一次学会如何证明勾股定理时,那时经历的兴奋感与满足感从未离我远去;同时,从化学合成、演化生物学、高能核物理学以及太空探测器获得的启示,都会让我旋即着迷、内心充实而平静。当然,正如唐·伊德(Don Ihde)等人经常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严重依赖技术仪器。aDon Ihde, Expanding Hermeneutics: 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值得深思的是,伊德并不将其称为工程仪器,但我觉得最好这样称呼。理论认识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加依赖技术工程,其方式是亚里士多德远未预料到的。
亚里士多德对三种生活方式的分析还有其他的局限性。也就是说,除了他的三分法外,还有其他与思考工程相关的生活方式,所缺失的就是那些有关宗教的生活方式。达摩禅法与道教教义阐发了一种与宇宙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而亚伯拉罕诸教b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指的是信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称之为易卜拉欣)。据《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是诺亚的长子闪的后代。——译者的生活方式以顺服神启(divine revelation)为特征。培根认为,神启为人类成为工程师创造了条件,这在讨论创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时得到了确认。如前所述,“使用和便利”这一术语就从休谟(培根的追随者之一)那里吸收而来,并用来界定“土木工 程”。
最后,现代社会越来越将制造活动视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独特之处。康德主张,人类经验是由统觉的先天形式建构起来的,即人类是世间理念的建构者。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现象学是通过奴隶而非主人实现进步的。马克思甚至更详尽地发展出一种工具人(homo faber)假设的人类学。为此,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提供了一种广泛而详细的论证。aArnold Gehlen, Man: His Nature and Place in the World,translated by Clare McMillan and Karl Pille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最近,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hard Stiegler)借鉴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深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将如下理念置于其哲学人类学的核心,即人类之为制造者,是凭借他们的制造活动而创造了自身。bBernh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Vol. I: The Fault of Epimetheus,translated by George Collins and Richard Beardswort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由此,世界因其基础设施、建筑物、消费用品等逐渐变成了一个工程化的产物,在环境、医疗、社会乃至基因等方面也逐渐被工程化了。但我们应该追问,这种在世方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真正的在世方式?当今的工程经验与工程化经验之间的悖论之一业已表明,提出这一问题仍然是合理的。就是说,借助工程的伟力,一方面,我们经常渴望通过创新使自身(在财务、社会方面,甚至是物质和环境方面)变得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渴望能够保持我们在环境、文化、宗教、政治方面的现有状 态。
我们今天的处境不过是贯穿于西方传统及其基督教遗产中的另一个悖论在当代的回响。一方面,基督徒宣称对天堂的信仰,相信死后的生活会优于我们在此岸世界的际遇。另一方面,并没有哪种文化真的变成了梦魇,去阻碍人们更加努力地在此岸世界存续。当然,解决这一悖论的意识形态思路是,相信上帝命令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创世纪》1:28)。看起来,这一观念的世俗版本就是创新,无所畏惧地创新,并且生活在无尽的创造性破坏之中,从而在持续地自我破坏的世界中绝望地保存我们自身。
既然笔者已经确定有必要审视工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必要重申苏格拉底在其中的自我反省,那么,这种审视事实上又能表明什么呢? 笔者的这三个论点只不过是为进行反省所作的准备。进行自我反省并不容易,就像实际行动或工程创新一样困难,甚至更难。 更深层次的无所畏惧不是创新本身,而是对创新的反省。
从哲学上对我们工程的生活与工程化的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主要有两种形式:从外部看,非工程师们已经用“社会正义”的话语去评估这种生活方式;从内部看,工程师们的反思则大多采取辩护性的论述。如前所述,科恩的思想在哲学意义上是最为精巧的论述之一。塞缪尔·弗洛曼(Samuel C. Florman)对“工程的存在乐趣”cSamuel C. Florman, The Existential Pleasure of Engineering (Second edition),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Inc., 1996.的辩护则是另一种论述。不过,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对工程的苏格拉底式质疑会把工程当作新轴心时代的平台。aCarl Mitcham, “The True Grand Challenge for Engineering: Self-Knowledge”, Issues in Science & Technology Vol.31, No.1, 2014, pp.19—22.最后,我将以一个简要的建议作结:经过审视的工程将如何导向一种新轴心时代的工程——也可以称作工程2.0。
轴心时代是什么呢?公元前 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或轴心时代。在世界历史的这一时代,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中国的老子和孔子、以色列的希伯来先知以及希腊的苏格拉底等思想家们,彼此独立地就人间世事提出了新的疑问:人成之为人的正当方式是什么? 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轴心时代之前,人类不加质疑就接受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已经社会化了的身份和精神生活。部落、种姓、性别角色、阶级和宗教信仰都被当作注定的加以接受。当地主的父母,子女也是地主,做工匠的父母,子女也是工匠,而买卖人的父母,子女也做买卖。地主的子女会像地主一样思考,工匠的子女会像工匠一样思考,买卖人的子女则像买卖人一样思考。精神生活与肉身一样,都是遗传下来的。文化上的遗产进而补充了基因上的遗传。
在这个固化的世界中,释迦牟尼佛主张摆脱那些被业已接受的东西,苏格拉底则质疑那些人们普遍相信的东西——这两种情形都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未必要接受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而是能比过去更加深入地思考他们是谁以及想成为何种人。孔子要求他的弟子们反思,周朝颁布的传统与礼仪是否并不比他所处时代的传统与礼仪更为优越。老子质疑文明与道的关系。希伯来先知耶利米(Jeremiah)敦促他的犹太同胞们思考,他们是否真的在遵守他们生来即订下的圣约。这些轴心时代的宗师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勉励我们去追问“我们究竟想成为何种人”,并逐渐成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受给定身份支配的自我。难道我们现在不应该把这种思维方式同样运用到工程的生活方式上吗?
但更重要的是,工程正在将我们所有人——工程师和非工程师带入一个新轴心时代。在新轴心时代中,由于工程的伟力,我们意识到我们未必要接受我们生来所处的外部世界。地球正在变成人工的产物。与原初的轴心时代使人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固化相映照,新轴心时代将使人们的外部世界不再固化。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轴心时代,这勉励我们去追问:塑造世界的正当方式是什么?工程生活方式的意义是什么?——这不仅是对工程师而言,还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为工程的在世方式有所贡献并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
在就任美国国务卿前,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Mobil)的首席执行官,他曾经宣称气候变化是一个“土木工程问题”bhttps://www.cfr.org/event/ceo-speaker-series-conversation-rex-w-tillerson.。我认为他是正确的,尽管或许不完全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气候变化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是一个因工程而产生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能单纯再用同样的工程手段加以应对。我们需要一种新轴心时代的工程去提出大问题。我们需要从土木工程1.0转变成土木工程2.0。
当然,有关新轴心时代的另一个术语是工程师和科学家所描述的“人类纪”(Anthropocene)aPaul Crutzen and Eugene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Vol.41, 2000, p.17.。荷兰工程师和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已经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激发我们认识到人类对世界的影响方面,他举足轻重——这个世界不仅包括我们人类,还包括地球上所有现存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是被动地认识这个世界。人类纪促使人们去追问:我们想要塑造出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就需要一种超越工程伦理学的工程伦理学。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效法其比利时同事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将此称为宇宙政治学(cosmopolitics)——这种政治学不仅考虑到人类及其使用和便利,或者其安全、健康和福祉,而且包括所有行动者的存在。bIsabelle Stengers, Cosmopolitics, Vol.I & II,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Bruno Latour, “Whose Cosmos, Which Cosmopolitics?”, Common Knowledge, Vol.10,No.3, 2004, pp.450—462.新轴心时代的工程伦理学需要从大处着眼,真正的大处,并且要考虑地球应该是怎样的。
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对人类而言是可能的吗?要问“一种工程的生活是否值得人类去过”,还必须要问“这种生活是否真的可能长期存在”。它有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但要对我们正在有意或无意构建的复杂世界进行长期的工程管理,也许超出了我们的系统工程能力。从一种苏格拉底的视角去质疑这些能力,至少是合乎情理的。在笔者看来,发端于苏格拉底的工程哲学应该欣然接受这种质疑。一种工程的生活是否值得人类去过?我无从知晓。但至少我知道我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