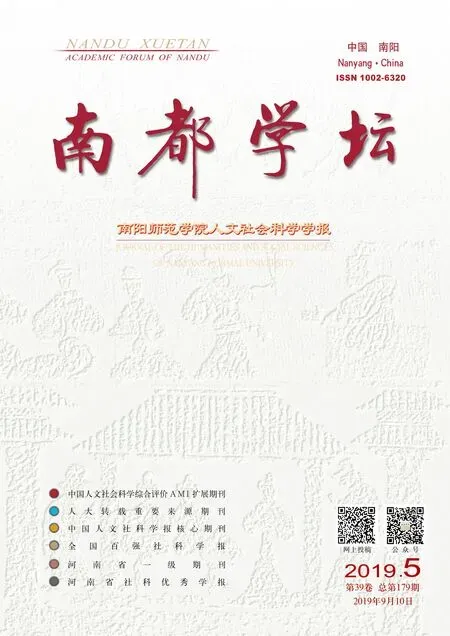我国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及防范路径
丁 新 正
(重庆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党自上而下正在分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体到扶贫工作,就是要在脱贫攻坚中坚定理想信念,咬定目标,苦干实干,要在脱贫攻坚中坚持利民惠民,以人民为中心,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遏制我国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我国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中相当数量的案件发生在区县部门、乡镇(街道)和农村基层组织,在我国基层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其他职务违法犯罪相比,其主要发生的领域、环节和地区有其特殊规律。以我国部分省份的区县基层为例,自“十二五”期间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由于扶贫投入加大,部门和基层权力增大,纪检监察、司法检察相对滞后,相继发生了区县、乡镇(街道)、村组(居委会)扶贫系统干部挪用、贪污、套取、截留、侵吞扶贫资金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同时,群众涉及扶贫的信访件数量上升较快[1]。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我国脱贫攻坚、消除贫困的进程,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部分区县的个案分析,检讨近年来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情况,准确把握其违法犯罪的基本概况、趋势及其种类,进而分析把握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综合施策、有效防范基层职务扶贫领域违法犯罪的路径:一是把握一个特点(规律);二是把好两个关口;三是处理好三个关系;四是建立一套完善的防控预警机制。
二、学界和实务界对扶贫领域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一)国外的研究和探讨
国外对于扶贫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入手的,研究和实务操作起步较早,但多数研究集中于贫困理论和贫困人群、贫困现象的本身,对于扶贫职务犯罪问题没有重点涉及。如,世界银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就给出了“贫困”的定义,之后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到21世纪初世界银行2001年发表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把“贫困”的含义修定为缺乏摆脱贫困的能力,即“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困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的影响力”[2],即既需要物质扶贫,又需要权利扶贫。这给我们研究探讨我国扶贫领域违法犯罪问题拓展了思路:既要重视研究探讨在物质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又要重视权利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
另外,一些国家的扶贫经验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如,美国通过立法把扶贫开发项目以扶贫法案的方式确定下来,依法规制国家财政主管的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直接救济和非营利性机构对贫困人口的援助,这样有利于依法治理在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
(二)国内的研究和探讨
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扶贫脱贫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关于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日益活跃。
关于扶贫领域违法犯罪的概况,学者们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陈文权、唐述英等认为在扶贫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当前扶贫领域腐败分子在高压下仍不收手,反腐形势仍然严峻,而且乡村“小官”是扶贫领域腐败的绝对主体且手段老练[3]。陈学敏则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典型案例,发现了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诸多特点,如犯罪主体集中,涉嫌罪名集中,涉嫌的环节集中,窝串案多,共同犯罪案件占较大的比例,“拔出萝卜带出泥”现象突出,个人受贿与单位受贿交织[4]。
关于基层扶贫领域违法犯罪频发的成因,学者也有如下观点:霍亚鹏、白洁认为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第二,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第三,资金来源渠道分散、实施项目繁杂、使用面积广,监管难度大;第四,监管虚位,涉农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监管;第五,资金使用情况不公开不透明[5]。陈文权在《扶贫领域腐败的精准治理对策》一文中也对扶贫领域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涉案人员用权任性,私欲膨胀;扶贫监管存在盲区,让人有机可乘;扶贫腐败的违法违纪成本低。此外,刘振杰的专著《个人资产账户与贫困治理》在分析反贫困战略及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提出我国现行的救助体制很容易滋生腐败的观点[6]。
关于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学者同样提出了一些预防建议和对策。如,王雷在《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之浅见》一文中就提出几点预防建议:一是检察机关要有所作为,要在大框架下加强组织领导,要调研摸底做好事前预防,加强人员监控,做好事前预防;二是乡镇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各负其责,在强化自身监督的同时加强监管;三是个人要加强综合修养[7]。徐春霞在《扶贫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中认为要加强监管力度,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8]。刘翔和李讯华在《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查办问题研究》一文从侦查的角度提出了建议:第一,联合多方力量形成打击合力;第二,充分利用信息开展精细化初查;第三,多方面推广专业化办案机制,细化侦查人员分类,培养专业的刑事检查人员;第四,构建典型案例示范平台[9]。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动作为,领导带头、有关部门积极参与,曹建明检察长提出“各级检察机关要立足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基本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工作”“要突出重点、盯住基层”的办案要求[10]。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与国家扶贫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方案》[11]。
总的来看,目前大多研究从比较宏观的国家层面探讨我国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而对绝大多数发生在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进行专题研究尚为欠缺。
三、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基本概况和特点
(一)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基本概况
1.在案发领域和环节方面。从近年来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查办的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类型表明,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教育扶贫、搬迁扶贫、医疗卫生扶贫、低保兜底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以及扶贫资金分配、发放管理、项目申报、审核审批、项目实施、检查验收等重点环节。以中西部地区的湖南、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甘肃、广西、青海为例,在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祁连山等连片贫困地区以及国家级贫困区县和省(市、自治区)级贫困区县表现尤其突出。以重庆为例,涉及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区域分别如下:区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教育扶贫、搬迁扶贫、医疗卫生扶贫、低保兜底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项目申报审核审批以及实施、验收,扶贫资金发放、分配等重点环节;围绕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等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和2个市级贫困区县等重点区域。
2.在案发主体方面。以两大类人员最为突出,一类是区县相关扶贫部门的干部,如扶贫、民政、慈善福利机构等部门的人员。另一类是乡镇(街道)站所、村级“两委”成员等涉农领域工作人员。他们或直接负责支农惠农资金、项目,或负责工程项目申报,配合乡镇(街道)站、所人员发放惠农补贴和协助工程建设。
3.利益被损害人的类型。利益被损害人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居民和城乡残疾人、五保户群体。他们很多人文化水平有限,社会交往范围狭窄,对相关政策和规定在乡村的操作程序和落实难以知晓细节,加之权利意识淡薄、维权能力弱,容易成为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侵害群体[12]。
(二)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特点
1.违法犯罪在环节上高度一致且比较集中。主要体现在三个环节:一是侵占私分、贪污挪用,或失职渎职、违规操作,致使资金跑冒滴漏、虚报冒领等环节;二是扶贫、救灾、农民工培训、农业政策性保险等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管理、验收等环节;三是对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棚补贴、规模化养殖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环节。
2.基层“蝇贪”现象突出。特别是在基层涉农惠农扶贫领域,基层乡镇(街道)、站、所和村(社区)职务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涉案人员包括乡镇(街道)、站、所的工作人员和村(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居委会)主任、会计、出纳和村民小组组长;另外,也不乏部分区县扶贫、惠农等职能部门科级及以下干部。这些人级别不高但均实权在握,小官“蝇贪”现象比较严重[13]。
3.“抱团”作案、“团伙”腐败现象严重。近年来,从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检察机关所查办的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抱团”作案、“团伙”腐败现象严重,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突破一案、带出一串,而且相互勾结、团伙作案有蔓延之势。根据中纪委通报和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官网“风正巴渝”披露的案例,重庆2016年下半年处理的两起窝案涉及的7名村干部无不是“抱团”作案、“团伙”腐败。该市江津区石门镇李家村村委会原主任杨炯贵、原出纳曹辉箱、原会计程从海、原综治专干周黎勇私分村集体资金等问题,4人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开发票、虚列支出等方式私分集体资金[14]。
四、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成因
当前,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处于高发态势,从社会根源上来看,主要是基层没有形成良性治理机制,特别是社区和乡村良性治理机制的缺失;加之治理资源的投入不足,为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机会;从监督机制方面来看,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增大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管理权限的扩大,对扶贫领域的权力监督机制没有跟上。具体来看,原因如下。
(一)违法犯罪的基层扶贫干部宗旨意识不强,担当精神有所欠缺
基层扶贫干部很辛苦,压力大责任重,具有宗旨意识是精神支柱和立身之本,也是基层扶贫干部负责担当精神的前提。树立宗旨意识,转变思想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是做好扶贫工作的关键。违法犯罪的基层扶贫干部往往由于宗旨意识不强,导致不作为、缺乏担当精神。
(二)规章制度不严,监管流于形式
一方面,规章制度存在漏洞,扶贫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透明度低,而且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很大,缺乏严格的约束制度,导致扶贫专款被贪污、挪用。另一方面,一些乡镇(街道)、村组(社区)管理松懈。一些农村基层组织没有严格的规则可循,账目不清,单据、凭证不完整,或为躲避监督设立小金库。在区县扶贫救济、涉农等20多个职能部门中,发改委、金融、农业和民政等部门只注重扶贫资金的划拨,忽视监督申报和使用资金。一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深入了解群众意见,工作流于形式。
从各地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看,当前,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不规范,没有按要求建立详细的贫困户花名册和统一费用发放票据,没有及时将费用发放原始票据按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统一进行账务管理,一些村镇干部抓住漏洞,相互勾结,以“合法”形式挪用公款,假公济私,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贪污渎职问题突出的情况[15]。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围绕阳光扶贫、廉洁扶贫相继制定出台了全面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意见和制度,对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扶贫资金量大、面广、点多、线长,监管难度依然很大,扶贫资金闲置、“项目趴窝”等问题依然突出。
(三)涉案乡镇(街道)、村组(社区)财务大多不公开
涉案乡镇(街道)、村组(社区)普遍存在财务不公开、暗箱操作等现象,特别是在征地补偿、移民搬迁、惠民资金管理发放等环节问题比较严重。
以国家惠农惠牧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资金、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的审批拨付为例,款项一旦打入村镇账户后,区县政府部门便难以有效监管,从而导致村镇干部容易与会计合谋挪用、私分、贪污。再以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农地入股公司为例。如何使土地入股的农业企业与城镇的工业企业一样,形成信息充分而透明的财务制度、规范的管理制衡框架与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应的财务会计规则行事,保障公司财务透明度,是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16],也即如何保障以农地入股的公司财务透明度,防止入股公司的财物被挪用、私分、贪污以及被强者通吃,是农地流转合法运行、遏制违法犯罪、真正助推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
这些案例说明,镇(街道)、村组(社区)等基层权力集中、监督相对弱化,加之财务大多不公开,使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
五、如何精准施策、有效遏制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
(一)把握我国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特点规律, 开展区域性、行业性专项预防
1.完善和规范派驻乡镇的纪检监察室和司法检察室,强化组织建设,发挥党和国家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检察的末梢作用。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对扶贫领域“微腐败”进行两批次的“五个一”专项整治,把“反腐红利”化为“民生红利”。继2018年开展“一盏灯、一栋房、一张床、一口井、一条路”等“五个一”专项整治之后,2019年又开展“一块地、一棵树、一枚章、一张卡、一封信”等新的“五个一”专项整治[17],让广大村民直观地感受到国家扶贫领域反腐的决心、增强村民脱贫的信心、让村民得到实惠,赢得村民真心称赞。
2.强化内外联动,加强纪检监察、司法检察、行政审计的沟通机制,定期开展与扶贫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和信息互换,及时受理、收集、保存、固定证据,收集线索、总结经验,不断提升综合施策、遏制基层扶贫领域违法犯罪的能力。
3.要把对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预防与我国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工作联系起来,精准打击具有黑恶背景的职务违法犯罪。针对我国区县乡镇面积广大、情况复杂,特别是当前一些农村基层组织“黑社会化”蔓延的问题,因地制宜、多管齐下,重点打击镇(街)、村(居)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近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督导甘肃省工作,中央督导组入驻一周后,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批级别不高、但情节恶劣的基层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被通报的相关人员有监区指导员、看守所管教民警,有交警大队副中队长、派出所所长,也有镇党委书记、村监委主任等[18],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4.发挥信息公开和群众监督、社会监督作用,并及时将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查办情况传达给社会公众,增强社会公众对遏制基层扶贫领域违法犯罪的信心。
(二)把好两个关口, 严禁扶贫干部带病上岗,压实责任、倒逼基层组织认真履职尽责
1.完善选人机制,把好 “入口关”。严把基层扶贫干部、村(居)干部入口关,严把村(居)“两委”换届人选的政治关、廉洁关、用人关,禁止干部带病上岗,特别是要加强村(居)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大量案例表明,基层扶贫领域的多发的职务违法犯罪,往往与选人用人把关不严,一部分人还是带病上岗有关。
2.加强党性和法纪教育,把好“教育关”。防治基层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应充分运用法纪警示和思想政治引导的有力武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的要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发挥法纪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廉政文化氛围的基础性作用,筑牢法纪防线和思想道德防线。
3.压实责任,把好“责任关”。十九大以来,随着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监察范围涵盖所有村干部(包括农村非党员村干部),应抓紧这一契机,全面从严整治村(居)基层党组织,固本培元,加强对村(居)干部群体的日常监督管理,稳固党的执政根基。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履职尽责不力,甚至纵容“村霸”“街霸”的行为,必须压实责任、坚决惩治,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倒逼村(居)基层组织积极作为、履职尽责。
(三)处理好三个关系,努力实现纪律法律惩治效果与扶贫成效的有机统一
1.处理好打击面上犯罪与遏制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犯罪的关系。要围绕十九大以来中央的决策部署,找准当前基层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易发多发的突出领域和环节,加强预防措施和查办力度。
2.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加强扶贫领域的纪律法律政策研究,严格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要做到把握法律政策、宽严相济。尤其是在处理扶贫领域失职渎职违法犯罪案件时,要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法纪政策,注意听取多方意见,防止把一般违法违纪、工作失误甚至改革创新视同违法犯罪,实现纪律法律惩治效果与扶贫成效的有机统一。
3.处理好治标与固本的关系。如,运用纪检监察建议权、司法检察建议权和行政审判司法建议,促进地方区县、乡镇(街道)、村组(居委会)进一步建章立制;将刑事追诉与检察建议相结合,加大办案力度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延伸办案职能,拓展线索渠道,深入剖析发案原因,寻找制度上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及时提出纪检监察建议书、检察建议书和行政审判司法建议书,协助和推动有关部门及时汲取经验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建立和完善基层扶贫领域惩治预防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
(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一套完善的防控预警机制
为了及时发现和解决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以及诱发违法犯罪的苗头和特点,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完善预警机制。要及时总结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和诱发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展前瞻性专题调研,探索建立预警机制,研究从源头上预防的对策措施[19]。建立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预警机制应抓住几个重点。
1.抓住信息收集、信息研判和预警风险这些主要环节,把握信息收集处理的广泛性、及时性,可充分利用检察机关自身查办职务犯罪的信息库。
2.把扶贫领域职务违法犯罪预警的工作重点方向放在区县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组(社区):一是要充分发挥乡镇纪检监察室和司法检察室的作用,建设信息收集平台,完善乡镇(街道)和村组(社区)的信息收集网络;二是与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组织联动,使检察机关能够快速、全面且准确地掌握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信息动态;三是发挥人民监督员的作用,动员群众参与预警机制的建设[12]。
3.利用预警机制平台,针对特定对象定期开展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警示教育活动,针对扶贫对象定期开展切实维护扶贫对象利益的权利保护教育、做好举报违法犯罪的宣传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