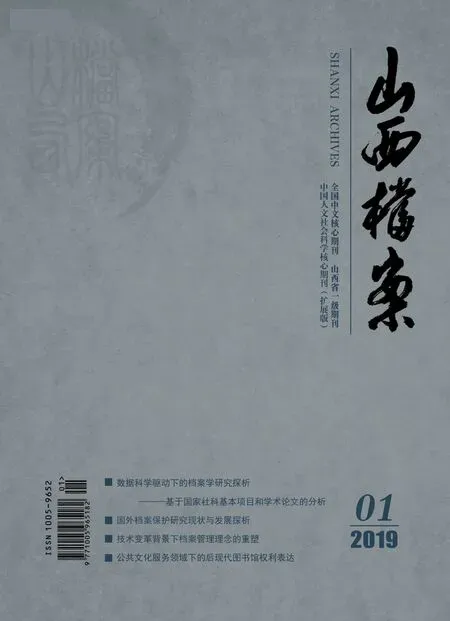文学档案征集之“山药蛋派”作家手稿*
张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 100029)
“作家在创作活动中会形成不少档案材料,档案界称之为‘文学档案’。文学档案,按现在的通常说法,就是作家在创作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作品或作家创作活动的全过程。”[1]更具体来说,文学档案主要包括作家手稿、手札、日记、笔记、作家之间的通信、作家相关照片和音像资料,以及文学会议、评奖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资料等。
文学档案作为档案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跟传统意义上具有“文件”性质的档案相比,二者既有交集,也存在不同。有一部分文学档案,诸如作家之间的通信、作家相关照片和音像资料,文学界的文件和会议资料等等,它们跟普通档案一样,“是具有清晰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2]。但如作家手稿、手札等文学档案却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有些许区别、因为它不是对事物或事件的一种原始记录,而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经过自己思考和再创作的艺术化产物。它所记载的内容本身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档案记录性质,但是它的原始记录性体现在它完整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和思考过程,反映了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思路,而这个过程存在着不可逆和绝对的不可复制性,手稿的独一无二决定了它独特的价值。
文学档案的价值不言而喻。在当今电子写作时代,电脑写作早已取代笔纸手写等传统的书写方式,名家手稿、信札等纸质材料随之成为稀世珍品。“最近一两年,在拍卖市场上,两页鲁迅书写、周作人题跋的《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万元成交,一页鲁迅致陶亢德信札则拍出 655 万元的高价”[3]。这样的“手稿热”现状,一方面要归功于“收藏热”的兴起,收藏市场的火热,使得手稿的经济价值水涨船高;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今处在书写方式急速转变的时代,电子书写的冰冷性,反而让大众对手写时代产生了一种情感的回望和怀念。作为一名基层档案工作者,笔者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就职,从事文学档案的征集工作,其主要工作模式即通过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有影响力的平台,与海内外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建立联系,从他们手中去征集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在丰富本馆的馆藏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学档案的社会价值,为文学研究和文学事业服务。
笔者参与文学档案征集工作的第一个案例,即2013年7月赴山西太原征集在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山药蛋派”作家手稿。“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小说界重要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该流派的小说主要以农村生活为主要题材,代表性作家有赵树理等。对于赵树理先生,大众并不陌生,其耳熟能详的小说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这些作品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学的风格和模式。除此之外,“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西李马胡孙”。我们此次的征集计划以征集马烽先生的手稿为主,同时也与另外几位作家家属建立联系,探查有无开展征集工作的可能性。
与笔者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计蕾主任,我们拟定了具体的征集计划,确定首先拜访的对象为马烽先生家属。马烽先生,1922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市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后因家境贫困,同母亲寄住舅父家。1937年秋,日寇侵入山西,年幼的马烽不忍中华民族陷入沦亡的绝境,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于1938年参加了革命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过程中,马烽也逐渐崭露他的文学才华,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侦察》,由此开始他一生的文学生涯。马烽先生的主要代表作有《我的第一个上级》、《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胡兰传》、《结婚现场会》、《咱们的退伍兵》等。他的作品大都以农村生活为大背景,擅长以刻画农村人物为切入口,通过描述一系列农村事件的发展过程,展现各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面貌。不过遗憾的是,马烽先生早在2004年就已因病去世,所以我们此次拜访的对象是马烽先生的女儿——梦妮女士。
马烽先生家住太原市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很多山西文学界的老同志都栖居于此,例如与马烽先生统称为“山药蛋派”作家的西戎、孙谦、胡正等都在这里安家。作协大院里的房子都是类似于“联排别墅”的二层小楼,每家楼前还有一个小院子,既可以乘凉歇息,也可以种花种菜,颇有情调。虽然小楼年代有点久远,看起来有些旧,但放在上个世纪来说,这样的建筑应该是相当气派的,自然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居住。
因为之前已和梦妮女士沟通好,所以当我们到访后,梦妮女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带领我们参观了马烽先生生前的书房。女儿梦妮说,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和不舍,自父亲去世以后,家里人再也没有动过书房的任何东西,她想让书房一直保持着父亲去世前的样子,就像父亲一直还活着一样。后来,梦妮女士把她保存下来的父亲手稿全部转交给我们,一共二十多件,这其中就有马烽先生非常著名的作品《我的第一个上级》的原稿。捧着那一沓手稿,感觉沉甸甸的,仿佛那不是一叠稿纸,而是一件用心血铸成的雕塑。手稿与书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书本的油印和华丽装帧早已把作家最原始的情感和思路掩盖,而手稿则能让我们最直观、最迅速地了解一部著作从孕育到降生的全过程,甚至是一些修改的细节。
从梦妮女士手中接过手稿,除了感谢,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还应该对家属说些什么,只能在心里默默感念,家属的信任决不能辜负,将这些手稿保存好,并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价值,才是对作家和家属最行之有效的感恩和致敬。因为“山药蛋派”的其他几位作家家属也居住在院子里,由梦妮女士引荐,我们又看望了胡正先生的家属。胡正先生也是为现当代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作家,他的作品同样以农村题材为创作素材,他创作的如《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汾水长流》等一些列优秀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广大读者中产生过极大反响。见到我们的到来,胡正先生的爱人郁波女士,一位非常优雅的上海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我们讲述了老伴生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及去世的前前后后。胡正先生因突发重病,走得突然,对于自己的后事并没有作过多的交待,但好在他之前已经向文学馆捐赠过许多自己的手稿和照片,似乎冥冥中早已为自己的文学遗产选好了归宿地。郁波老师深深理解他的爱人,可能是早已做好了打算,她捧出胡正先生未完成的遗稿《汾水南流》交给我们,这应该是她仅存的唯一一份胡正手稿,她托我们将之好好存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相信这也是胡正先生的遗念。《汾水南流》从题名上来看,应该是《汾水长流》的姊妹篇,但是原稿还未完成,胡正先生便与世长辞,实为遗憾。
至于其他几位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手稿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的工作没能继续开展。“山药蛋派”作家手稿征集计划,作为一次重要的征集工作,我们一共征集到20多件珍贵文学档案,从成果来看,征集工作算是取得圆满成功。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作家家属们的支持和配合,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深明大义,助成了我们的文学档案征集工作和文学事业发展,再次为他们的义举致敬!
每一件手稿都是作家心血和情感的凝结,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无价之宝,于家属和亲人来说,遗稿更是未亡人对故人的一种思念和寄托,不能随意地取舍。其实“档案本身是我们对过往情感的承载。档案的情感属性集中表现为档案既是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又能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唤起人们心中的情感记忆。”[4]这种由档案所衍生出来的情感,从诞生、传承,再到触发档案参观主体的情感共鸣,则是档案的情感价值和属性。档案的情感属性,正如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所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5]很多文学档案就是这种情感的产物,它承载了个人,甚至还有群体和时代的记忆。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它传承的不单是个人的情感和记忆,更大的价值则在于,当后人面对这些文学档案时,能够从深层次唤起他们对某种情感和记忆的怀念、体味和共鸣,让观众从内心获得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和肯定。作为媒介,从专业、从馆藏需要的角度,我们将大量的文学档案征集入藏,一方面是为了保存文学档案,为文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真实的资料;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储备文学档案其独特的情感价值,在适当的时机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情感记忆,发挥其情感价值。
在征集过程中,我们还会面临档案所有者与档案之间情感的割裂、取舍、以及情感的重建,看似简单的档案征集工作,却隐藏着不同主体复杂的情感裂变,所以“在档案收集阶段,制度设计应关注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保存不同群体的情感记忆”[6]。在我们获得档案的同时,帮助作家和家属从情感上对他们档案的捐赠行为做好疏导和转移工作,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在充分保证档案情感价值的同时,让作家、家属和档案之间建立新的情感关系。如果有条件,一定要以最完整的状态收集档案所有者的情感记忆,使之成为“档案之档案”,尽量建构完整的档案记忆和情感体系。
文学档案征集工作,作为文学档案馆、文学博物馆所有业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有着关键的作用和重大意义。同时,文学档案的征集,对于文学和作家的研究,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建构和修正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好文学档案的征集工作,是我们文学档案人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应该更加关注档案本身的情感价值以及在征集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需求,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开展征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