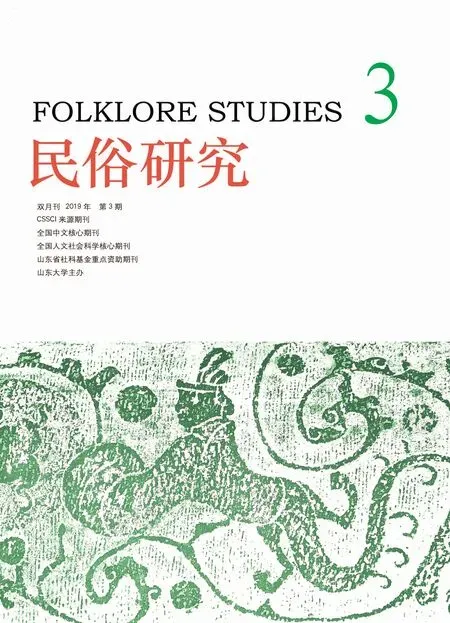近代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的民间审美特质
唐 玮
山东淄博处于鲁中地区,在历史上兼受齐、鲁文化的交相影响,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滥觞于明、兴盛于清末民初的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即是淄博地方文化的重要民俗标志与文化载体之一。
淄博青花鱼纹盘总是将鱼纹样置于盘子中心,可能与当地传统饮食中“食有余”的习俗有关。在山东民间饮宴规矩中,有酒菜不能吃光的习俗,必须要有剩余;宴席结束,如果盘子里剩有鱼头(谐音“余头”),则为生活富裕、年年有余之象征。民间陶瓷匠人发挥聪明才智,遂制作鱼纹盘,使得寻常人家也能天天眼见盘中有“鱼”,也就意味着“食有余”。诚如吴中杰所言,人类由最初无意间触发生产陶瓷的想法,到后来有意识的批量生产,意味着通过意义赋予,使得陶瓷制品寓实用与艺术于一体。[注]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页。淄博民间陶瓷艺人对于青花鱼纹盘的创制,青花鱼纹盘在淄博、山东乃至全国各地的广为流传,乃至最终成为淄博地方文化的重要民俗标志与文化载体,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一现象何以发生呢?
一、淄博青花鱼纹盘:生活与艺术的混融
淄博青花鱼纹盘俗称“大鱼盘”,因盘内彩绘有一条硕大的鲤鱼而得名。淄博青花鱼纹盘,或称“博山大鱼盘”“淄博大鱼盘”,遂成为近代淄博彩绘陶瓷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当地民间艺人的口述中,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的诞生虽可追溯到明代,但真正成熟的时期却在清代晚期。据说,在当时博山窑炉火正旺的时候,制瓷师傅从特色鲁菜“糖醋鲤鱼”中突然得到创作灵感,在对盘胚进行彩釉绘制的时候,运用流畅圆润的笔触与线条,彩绘出一条姿态丰满圆润、首尾相接的鲤鱼形象。盘中彩绘的鱼纹样,形象生动传神,承载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彩绘青花鱼纹盘问世以后,大受欢迎,民间多用此盘盛放水饺、面食等,既方便实用,又看着称心如意。到了清末民初,淄博青花鱼纹盘制作技艺日臻成熟,社会需求量大增,使得淄博各处窑场纷纷效仿制作,名扬一时。目前,能看到的淄博鱼纹盘品种达300多种,可谓异彩纷呈,体现出民众丰富的文化创造性。
淄博鱼纹盘产生初期,以形象写实居多,边饰复杂多样,用笔稍显拘谨。至清末民初,边饰趋简或出现无边饰的鱼纹盘,鱼的形体也愈发变得丰满流畅,充盈了整个盘面,且手法也不再拘泥于写实,而多为大写意手法,追求流畅丰满的意境之美。此后,鱼盘的画法更趋于流畅率性,线条更加简练夸张、洒脱自然,并大致固定为淄博大鱼盘彩绘程式。其主要艺术特色体现在如下层面:首先,体现在线条的均衡性上。分析淄博青花鱼纹盘的300多个品种的装饰纹样,可以大致分为单条鱼纹、双条鱼纹以及金鱼纹三大类。在这些类别中,几乎所有的鱼纹装饰都用网格纹,有的在网格纹上再加点状装饰,鱼鳍部分则运用排列有序的放射状线条。鱼纹盘中造型线条的均衡性特征,不仅可以在制作过程中把鱼造型纹饰的质朴与趣味性表现出来,还与鱼造型本身的弧线形成对比,给人一种流畅洒脱而又具象细致的视觉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装饰与被装饰的关系,增加了鱼纹盘的艺术魅力。其次,鱼造型的线条充分运用回环重叠的技法,以青花单色创造出300多种纹样,曲折流畅,结构紧密,层次感强,整体造型活泼生动、清新秀丽。韵律与节奏是线条表现的重要形式,这在淄博青花鱼纹盘的装饰线条中有着充分表现。例如,淄博青花鱼纹盘中的典型样式“多子多福”,其装饰纹样采用螺旋的发散性线条,再加上一个或多个圆点,形成了既有韵律又有节奏变化的风格,极富美感。再次,淄博彩绘青花鱼盘的色彩,因矿物原料有一定差异,在不同炉温的烧制下变幻奇瑰,并在以后长期的使用中发生色变,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
二、近代淄博青花鱼纹盘中鲤鱼意象的凸显
鱼作为吉祥的象征,自古以来在中国民间就有着崇高的地位,“鱼为吉祥恩主,鱼人间有人伦联系和情感互通的认识,使鱼类又被尊奉为辟邪消灾的护神”[注]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94页。。淄博青花鱼纹盘,正是以鱼作为造型主体,其人伦与情感的社会基础极为深厚。
在我国各地民俗文化中,鱼的形象普遍具有富足、有余、高升、多子、吉庆等象征意义,其优美身形更是民间审美系统中曲线美的典型代表,令人赏心悦目。象征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意义,诚如张道一所言,中国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普遍具有两层含义,除表层的意义外,还借用语言的读音,巧做安排,赋予更为深邃的第二层意义。[注]张道一:《吉祥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这里的第二层意义即象征意义,与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大有关联。淄博青花鱼纹盘对于鱼纹造型的设计运用,正是对于传统吉祥文化的巧妙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由于本身的生理特性,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象征,这为淄博大鱼盘的吉祥象征寓意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在中国传统的民间观念中,人们对于鲤鱼的崇拜尤为突出,“‘鲤鱼跳龙门’这一传统题材的形象也是频繁出现在民间的年画、剪纸以及生活器具中,来表达金榜题名、高升昌盛的象征性寓意”[注]王冬梅:《淄博鱼盘中鱼符号的民俗含义及美学形式》,《装饰》2015年第5期。。淄博青花鱼纹盘所绘的鲤鱼形象,通过夸张的头部与肥硕的形体等造型特征,凸显“出人头地”“年年有余”等人文意象。由于淄博地处鲁中地区,兼受齐、鲁文化的交互影响,并在秦汉以降深受制度化儒学思想的影响[注]王文灏:“自汉已降,儒家文化已经转变成为中国民间的指导性思想,这一思想的精髓也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传统吉祥纹样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王文灏:《吉祥装饰纹样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应用及儒家思想内涵探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并与当地民众生活之间呈现出礼俗互动的复杂关系[注]张士闪认为:“中国很早以来就已形成所谓‘礼俗社会’,呈现出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联合运作的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礼’与国家政治结合成为一种文化制度,是有着一个逐渐联合的过程的,‘俗’则在地方生活的运作中呈现出民间‘微政治’的多种社会样态。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社会悠久历史进程中的‘礼俗互动’,起到了维系‘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作用。”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再看鱼纹盘中的鲤鱼形象,所以在造型上极具夸张,意在凸显鲤鱼跳龙门的灵动之势。“鲤鱼跳龙门”之影响深远,鲤鱼二字中“鲤”与“利”、“鱼”与“余”谐音,鲤鱼历来又有“鳞介之主”“诸鱼之长”之称,使其在民间备受宠爱,称为“红鱼”或“喜鱼”,乃至普遍有“崇鲤”情结,体现出人们求吉纳福、生活富裕的美好心愿。在淄博近代民间彩绘青花鱼纹盘创作中,鲤鱼形象随处可见,成为运用最多的素材,也就绝非偶然。
细看淄博近现代各种各样的青花鱼纹盘,盘中鲤鱼造型是各有讲究的。如硕大的鱼头,再加上鱼身上装饰的网格状鱼鳞与用线条装饰的鱼鳍,多运用点点与网格相结合的形式,既体现出大鱼盘中鱼造型的生动活泼与质朴美,又贴合人们对于庄稼收获与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想象。鱼的繁殖能力很强,而鱼与莲花的图案既体现了男女交媾之意象,也成为家庭幸福美满的象征,因此作为鱼纹盘装饰的莲花纹样在早期的淄博青花鱼盘中多有所见,而在清后期作品的应用虽逐渐简化,却坚韧存留,显示出人们对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追求依然强烈,但对与之有密切关联的男女交媾意象的表达却趋于含蓄。推其因,这与清后期淄博青花鱼盘在当地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使用,不便凸显男女交媾的意象有关,也与传统社会对于“男女之大防”之类封建礼教的日益强化有关。
三、近代淄博青花鱼纹盘的民俗审美特质
淄博青花鱼盘的器型以彩绘见长,运用流畅的曲线笔触,形成自由洒脱的意趣,乃是其审美特质所在。诚然,“以人类生存的必需为目的的民间文化观念以及民间审美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美术的最具审美特征的尺度。人们也是常常把一些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寄托在一种精神的追求与满足上面”[注]刘忠红:《试论民间美术中的审美意蕴》,《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淄博青花鱼纹盘集审美形式与民俗寓意于一身,体现出民间造物鲜明的民俗审美特质。
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的民俗审美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简约的线条、富有韵律的造型以及丰富的意蕴。线条的简约,主要体现在塑造鲤鱼形象时,以轮廓线来勾勒鱼形,强化线条变化的灵动与率性。当地窑工在圆盘的陶胚上,用釉彩随手勾画出一条盛放在粗瓷盘中的鲤鱼形象,线条如行云流水,鱼身则硕大而夸张,完美地将鱼纹与盘融合在一起,又给人一种质朴又不失豪放的韵律。一鱼在盘,三餐常用,容易引发人们美好的想象与聊天话题,如“鲤鱼跃龙门”“富贵有余”“多子多福”“合家团圆”“喜事临门”“和睦美满”等等,这其实又是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丰富意蕴的展现过程。上述三者,在长期的淄博地方社会生活中,共同凝结为当地窑工及民众独特的民俗审美特质。
美来源于现实生活,制作淄博青花鱼纹盘的陶工也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以鱼纹寓意表达审美意趣,这又构成了当地社会生活与民俗观念的一部分。诚如张士闪所言:“民俗的本质是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自无可疑。民俗传统,即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促使某种价值规范发生从世俗到超验的升华过程。”[注]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淄博青花鱼纹盘在民间的最初出现,是作为生活实用器皿而制作和使用的,只是后来不断衍生出审美因素,并在贴近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日渐丰厚,完成了对于简单日用品的超越。同一款造型的鱼盘,因为绘制了不同的纹饰,就有了丰富多元的审美意趣。淄博彩绘青花鱼纹盘制作不乏精品,深受民众欢迎,并通过民众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同解读,逐渐成为淄博地方社会的民俗标志与文化载体。
四、结 语
陶瓷,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器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理解地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依据。吴中杰认为:“陶瓷制作从总体上来说,其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机械复制,就在于它贯穿了独特的创造精神和特有的美学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又很自然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自然契合,其最高境界即为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注]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页。这种“真善美的统一”,其实又是离不开具体的地方社会生活语境的。就淄博青花鱼纹盘而言,无论是其悠久的技艺创造与发展过程,还是独特民俗审美意蕴的形成,都说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它已经主要不再是民众餐桌上的实用器皿,更多的被视为风格独特的民间艺术珍品,似乎脱离了民众生活的具体语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恰好是其生活实用功能的泛化,及其文化意蕴在当代社会中的多元发掘与审美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