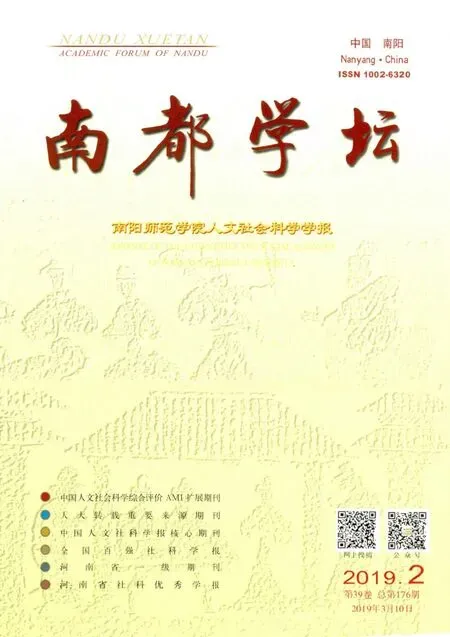儒学与范晔《后汉书》的编纂
张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学术思想多元并存的格局。范晔(398—445)生于儒学世家,“少好学,博涉经史”[1]1819,但他却生逢儒学式微的时代。他有复兴儒学之志,与他的祖辈不同的是,他并不是通过注疏儒家经典来阐发己说,而是采取以史明道的方式表达他对儒学的传承。这表现在,他所著《后汉书》虽以载事为主,却贯穿着以儒学为指导的著述宗旨。以往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大多聚焦于《后汉书》的史料价值、体例创新、史论境界等内容的探讨,而对其以儒学为指导的史学撰述实践关注较少。实质上,对于范晔《后汉书》中蕴涵的儒学思想的揭橥,关乎对范晔学术思想的整体评价,因而有必要对此问题作出探讨。
一、出身儒学世家
梳理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范氏的家族网络,我们会发现范晔的曾祖、祖父、父亲与叔父均以儒学见长,世代传承。尽管范晔一生倾心于文史研究,而很少在经学领域里有所著述,但是他却在《后汉书》中常常称颂先祖学说,颇见家学对其史学撰著的影响。
范晔的曾祖范汪“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2],尤精于礼,所论丧礼之文,多为杜佑的《通典》收录。《晋书》记载他在担任东阳太守期间,“大兴学校,甚有惠政”[3]1983。田余庆评价说:“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4]范晔在《后汉书·黄宪传》中曾称引范汪对黄宪的评价:“余曾祖穆侯以为宪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5]1745范晔引用曾祖范汪之言,一方面是为彰显范汪的学术识见,另一方面则说明了范晔对于范汪观点的认同与推许。
范晔的祖父范宁,更以儒学显名于时。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范宁崇尚儒学、反对玄学,《晋书》本传记载:“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所以范宁著文驳斥玄学的清谈,凸显其“崇儒抑俗”的学术旨趣。范宁在担任东晋豫章太守期间,重视培养儒学人才,“大设庠序……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终其一生,“犹勤经学,终年不辍”。“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为之集解”,所著《春秋谷梁传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3]1984-1989。对于范宁的儒学研究,范晔曾在《后汉书·郑玄传》中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5]1213范晔的言论,道出了范宁儒学研究的渊源,认为范宁的治学与东汉郑玄的儒学研究一脉相承[注]朱维铮认为,范晔在《后汉书》中为郑玄立传,“违反按时代排列或按行事归类的体例,将他提到八十列传的第二十五篇内,放在东汉诸经学大师传记的首位”,这种处理方式暴露了“范晔个人的偏见”,因为论时代,郑玄“居于东汉诸经学大师的最后”;论名望,郑玄“与古文经师马融、今文经师何休等相仿”;论气节,郑玄“依违于东汉末权臣军阀何进、董卓、袁绍之间”。范晔立传之所以将其放在东汉诸经学大师传记的首位,缘于“范宁治经专守郑氏家法”。参见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47页。。
范晔的父亲范泰在东晋时曾为太学博士,入宋后担任“国子祭酒”[1]1616。范晔于《高凤传》说:“先大夫宣侯(范晔父谥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5]2769因而,李慈铭指出,范晔在《后汉书》中称引其先世之说凡三,“皆以见其前人学识品概,非泛泛指称”[6]237。实际上,范晔出生之后,因伯父无子,便过继给了范弘之,而据《晋书》记载:范弘之“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常博士”[3]2362,秉承了儒学家风。范晔生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自然潜移默化地受到儒学的熏染。
综上所论,俱见范晔以儒学彰显的家学渊源。因此,身处儒学式微时代的范晔,却成长于儒学世家。观其著述,并非通过注经来传承家学,而“是借助于史学的方式来完成儒学的传承事业的。所以,儒学的奖崇和弘扬成为范晔创作《后汉书》的主旋律”[7]31。故而,儒学对于范晔《后汉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撰成最早的东汉儒学史
范晔继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儒林列传》和班固在《汉书》中设置《儒林传》后,在《后汉书》中继续设置《儒林列传》,这既是对传统历史编纂体例的继承,也是儒学在东汉时期发展兴盛的真实写照。范晔在《儒林列传》的序中,以精练的笔法对东汉时期儒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总结与概括。他以时间为序,爬梳了东汉各朝当权者对待儒学的态度以及儒学的盛衰,内容涵括光武帝访求儒雅之士,“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修建太学、三雍;明帝恢复儒家传统的三老五更之礼,并以身示范,“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并以天子的身份亲自裁决;和帝曾“数幸东观,览阅书林”;邓太后临朝称制,“学者颇懈”;安帝理政期间,“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时期,“更修黉宇”;梁太后时期,“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灵帝于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儒林列传》的总序,虽内容不长,但基本囊括了影响东汉经学发展的政治因素。正是由于当权者的提倡,所以东汉一朝儒学兴盛,经学名家层出不穷,据范晔所言,“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所以他于《儒林列传》中仅“录其能通经名家者”[5]2545-2548。即便如此,《儒林列传》所载人物也达四十余人。在此之外,范晔还为贾逵、马融、郑玄等儒学名家独立设传,详细书写其人生轨迹,以凸显他们在东汉经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此,则既从面上反映了东汉经学的整体成就,又别具匠心地彰显了影响东汉经学甚巨之儒学大家的学术特色与风范。
从范晔所撰东汉诸儒列传中,可以看出他向后人传递了东汉经学发展的新信息与新特点。
一是东汉诸儒多“兼通数经”。颇具典型者,如任安“兼通数经”;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何休“精研《六经》”;许慎“少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时人谓“《五经》无双许叔重”;蔡玄“学通《五经》”;郑玄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5]1207。相较于西汉时期经学家多专一经、很少兼通的情况,东汉经学可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是东汉诸儒多广收门徒。最为显著者,如张兴的“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曹曾的“门徒三千人”;牟长为“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杨伦的“弟子至千余人”;杜抚的“弟子千余人”;丁恭的“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张玄门下“著录千余人”;谢该的“门徒数百千人”;蔡玄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5]1972。据此反映,儒学之风盛极一时,不仅儒学名家层见叠出,而且一般士子研习经学蔚成风气。
三是东汉诸儒多著述丰厚。尤为突出者,如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程曾“著述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而通儒贾逵、马融、郑玄更是遍注群经,著述丰硕,立言百万。这与“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8]的状况相比,又有所推进。所以范晔在《儒林列传》的论赞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5]2545-2588
三、以儒学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范晔一生推崇儒学,奖掖儒术。王鸣盛曾评价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9]其后,晚清学者李慈铭也特别指出:“《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琬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又说:“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6]235,237这实际上指出了儒学思想对范晔编纂《后汉书》之列传、评价东汉人物的影响。
范晔以儒学为衡量标尺,借此表达了他对东汉史上重要史事与人物的看法,有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譬如,他褒奖正义之士,歌颂他们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精神,塑造了李膺、李固、陈蕃、范滂等历史人物守节不屈的形象。在《党锢列传》中,范晔强调在当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的环境下,李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5]2195。在《李固传》中,他以对比的方式称誉李固持重守义的品格:“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夫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5]2094-2095特别是他对处于宦官外戚专权时代范滂刚介不屈形象的刻画尤为深入,《后汉书》记载说:“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5]2207展现了范滂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为正义事业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同样,对于陈蕃的行为,他也推崇甚高,指出:“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阸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5]2171
从儒学的角度,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的做法提出了反批评。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史论中,从两个方面对班固进行了评价:一是肯定班固有“良史之才”,所以能撰成《汉书》并流传后世;二是对班固历史撰述的儒学倾向提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范晔对班固的评论,总是有意识地将之与司马迁进行比较。从撰史的才能来说,范晔对司马迁与班固二人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不同点在于,范晔不同意班固从儒学角度对司马迁的批评,并从他自己的儒学观出发,对班固历史写作的儒学倾向提出了反批评[5]1386。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又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即在是非观上与孔子和儒家学说有很大的差异[10]2737-2738。范晔不同意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恰恰是《汉书》在历史撰述上背离了儒学思想的指导。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的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汉代初年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至汉武帝时期,儒学经董仲舒的提倡,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但不容否认的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在当时社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在班固生活的东汉时代,儒学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学不仅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学术的指导思想,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他各家学说在儒学面前黯然失色。范晔则生活在南朝刘宋王朝,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从东汉末期不断下降,尤其是受到来自道教与佛教的挑战,这刺激了儒学家对儒学的复兴。其次,由于儒学在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所处时代的地位不同,以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儒学观及他们对于前代史家的评价。司马迁处在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地位不断上升的时代,他对儒学非常推崇,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曾向儒学大师董仲舒问学,并明确指出他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继承孔子修《春秋》的事业;他还打破自己史书的体例,为孔子设立世家,记载了孔子及其众多弟子的生平,同时在《史记》中多处引用孔子的言论作为评价人物与史事的标准。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司马迁是尊崇儒学的。然而班固却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10]2738。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写了道家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但这并不是他记载的重点,他甚至没有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单独设立传记,而是将老子与韩非子两人合在一个传记里,并称老子为“隐君子”[11]2142,而称孔子为“至圣”[11]1947。所以,班固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拿东汉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要求司马迁,未能做到知人论世。班固曾撰写过《典引》[5]1375-1385,他的父亲班彪撰写过《天命论》[10]4208-4212,这两篇文献都是从“天命”的角度论证前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使得他们的儒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班固还在《汉书》中一再称述“汉承尧运”[10]82,意思是说西汉是尧的后代;在对西汉人物的记载上,他多撰写政治人物的历史,而很少记载有德行的小人物的历史。可以说,他的儒学思想主要是服务于当时政权的。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评价说:“和《史记》相比,班固等人的《汉书》是按照更严格的说教的原则写成的,因而一方面对儒家传统较少批评,而在另一方面则对非儒家的言行较少宽容。”[12]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会从儒学的角度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范晔出生在儒学受到佛教和道教相互排挤的时代,致力于恢复儒学的传统。他试图去除儒学发展中的神秘成分,注重倡导儒学的“仁义”观念,这表现在他在《后汉书》中重视叙述具有正义感的东汉人物,表彰社会中下层节操高尚和品行端正的人物,而对于没有多少事迹可以记载的宰相、公卿等社会上层人物,反而不予记载。从这一理念出发,范晔批评班固父子的《汉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5]1386。据此来看,范晔在历史撰写中的儒学倾向,与班固借助儒学为当权者服务、注重记载社会上层人物的实践有所不同,而与司马迁重视记载社会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的撰写理念较为接近。
在儒学思想的指导下,范晔的历史编纂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他为经学大家马融独立设传,表彰其成就,尤其是对于马融上奏讽谏朝廷的《广成颂》予以了全文收录。马融曾因进谏触犯了当朝邓太后,并因此而滞于东观,不得为官升迁。其后,马融又得罪外戚梁冀而遭剃发流放,自杀未遂,得以免罪召回。有鉴于此,马融不仅不敢再触犯朝廷,而且为权贵梁冀起草了陷害李固的奏疏,又作《西第颂》以歌颂梁冀。对于马融的屈节,范晔仅寥寥几笔带过:“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埶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5]1972又在传论中发表感慨道:“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5]1973这一番议论,看似对马融有所批评,实则为马融屈于权贵的做法予以辩护。追根溯源,在于马融被时人称为“通儒”,范晔对其有所推崇,故而评论有所隐晦。正如李慈铭所说:“《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存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未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6]232-233
再者,儒学的指导思想使得范晔无法正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对于推进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正面意义。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互擅权,再加上边疆危机、自然灾害频发,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使得东汉统治大势已去。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揭竿而起,“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5]2299,已经形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支力量,给予腐朽的东汉王朝巨大的打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理应对这次影响甚巨的农民起义予以载录,但范晔囿于其儒学思想的局限,未在《后汉书》中对此列专传加以记载,仅仅浮光掠影地将此事附记在《皇甫嵩列传》中。而对于起义中的人物,范晔均以“贼”称之,这与司马迁为陈胜设立世家、礼赞农民起义的伟大思想相比,则反映了范晔历史思想的局限性。
四、批评佛教、谶纬,旨在推崇儒学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无神论的角度评价范晔对于佛教、谶纬思潮的批判,实质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首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得到当权者的扶持,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教义主张与儒家学说产生了不少矛盾,大有成为学术主流的趋势,这对于有着显赫儒学家世传统的范晔而言,是有所刺激的,故而也成为他批判佛教的主要立足点。其次,谶纬学说在两汉时期与儒学相杂糅,但在范晔看来,“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5]2703,所以谶纬之言绝非儒家学说,应将其从儒学中剥离出去。
南朝是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范晔生逢其时,自然受到时代的感染。他对于佛教的评论,既反映了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时代思潮的一种映射。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范晔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佛教的看法:
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5]2932
范晔认为,由于佛教宣扬“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大多喜爱佛法。范晔所言,“并不是说佛法仍有其优点,而是讽刺当时当权人物崇佛的微词”[13]。在范晔看来,佛教的“好大不经”与“奇谲”要远远超过邹衍谈天的辩论与庄周对蜗牛触角的论述;佛教有关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阐释,看似说得明白透彻,实际却模糊不清,具有一定的蒙蔽性,因而“通人多惑焉”。范晔基于自身对佛教的认识,生前“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临终前“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1]1828-1829对此,范文澜曾独具慧眼地指出范晔反对佛教的言论,体现了他“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14]。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范晔应是从儒学的立场,对佛教展开批评的。
范晔对谶纬学说的批判,在《方术列传》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5]2705从中不难看出,自王莽用符命、刘秀信谶纬之后,一些儒者争谈图谶之风成为一时之尚,其主要目的是迎合人主之意。范晔将司马迁所言“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引为同道,表达了他对阴阳学说与谶纬迷信的基本态度。他指出,这些图谶有时也会与史事相符,但只不过是偶合罢了,“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5]960。而真正的通儒硕生对于图谶是“忿其奸妄不经”的,所以也不愿与之为伍。这些论述,表达了范晔努力将图谶学说与儒学作出区分的意愿,体现了他传承儒学和发展儒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