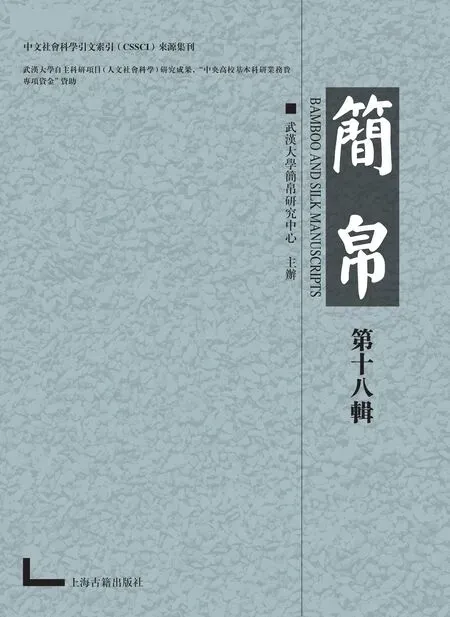肩水金關漢簡濟陰郡及其所屬桂邑考
趙爾陽
關鍵詞: 肩水金關漢簡 濟陰郡 都關 桂邑
《肩水金關漢簡》(以下簡稱“金關簡”)中包含有大量的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初期政區地理信息,這對我們瞭解、復原西漢後期的政區地理有極大的幫助,也進一步印證了《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記載的準確性。其中,濟陰郡所轄的幾個縣邑名和《漢志》記載有出入。究其原因,《漢志》反映的是西漢末年元延、綏和之際的政區建置,(1)馬孟龍: 《西漢侯國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頁。而肩水金關漢簡記載的政區地理信息則囊括了從武帝後期到東漢建武初年,絶大多數簡牘的紀年集中在昭、宣至王莽時期。在這期間,濟陰郡政區變更頻繁,數次在濟陰郡與定陶國之間更替。其中不僅僅是名稱的變更,轄縣和轄域也隨之增減和盈縮。
金關簡公佈後,涉及濟陰郡的簡較多,多數爲戍卒名籍簡,這些簡較完整地記載了戍邊吏卒的籍貫身份等信息。其中有幾支濟陰郡簡反映了濟陰郡所轄縣邑的變遷,其記載的縣邑名稱不在《漢志》所書“濟陰郡”條下,尤其是簡73EJT37∶1320書有“濟陰郡桂邑”更是在《漢志》中找不到蹤迹。我們争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傳世史籍及金關簡文,擬對這幾支簡作一簡單分析,並考證濟陰郡桂邑的地望。不妥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金關漢簡中提到濟陰郡的簡較多,現將金關簡中記載濟陰郡所屬縣邑與《漢志》不同的簡羅列如下:
濟陰郡廩丘左里卜捐
(73EJT24∶328)
從者濟陰都關樂里公乘行博德年卌長七尺三寸黑色 閏月丙辰入 鐱一
(73EJT25∶11)
(削衣,73EJT34∶40)
(73EJT37∶1320)
濟陰郡在西漢時政區變化非常繁雜,不僅名稱經歷了濟陰郡和定陶國的交替,轄縣和郡界也隨每次調整而有所盈縮。馬孟龍先生較詳細地梳理了濟陰郡的建置沿革,基本清晰地勾勒了其發展演變。(2)馬孟龍: 《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我們綜合前人的研究,認爲濟陰郡初爲濟陰國,國除後復爲濟陰郡,至遲在甘露二年(前52)時被設爲定陶國,其後又在定陶國與濟陰郡名稱間往返。王莽時期,濟陰郡又更名爲濟平郡。(3)《漢志》“濟陰郡”下班固自注曰“莽改定陶曰濟平”,《後漢書·耿純傳》載“父艾,爲莽濟平大尹”,可證王莽改郡名。西漢時濟陰郡的變化大致如下: 濟陰國[景帝中六年至後元年(前144—前143)]——濟陰郡[景帝後元年至甘露二年(前143—前52)]——定陶國[甘露二年至黄龍元年(前52—前49)]——濟陰郡[黄龍元年至河平四年(前49—前25)]——定陶國[河平四年至建平二年(前25—前5)]——濟陰郡[建平二年至王莽時期(前5—9年)]——濟平郡[王莽時期(9年以後)]。
《漢志》記載濟陰郡轄九縣,分别是定陶、冤句、吕都、葭密、成陽、鄄城、句陽、秺、乘氏。但肩水金關漢簡記録濟陰郡曾轄有廩丘、都關、成武、桂邑等縣邑,此四縣(邑)在《漢志》中或爲别郡所轄,或《漢志》未載。根據乾嘉學者及今人周振鶴先生、馬孟龍先生的研究,《漢志》的斷限爲西漢末元延、綏和之際。周先生認爲,《漢志》所書的濟陰郡九縣乃元延末定陶國所屬,《漢志》濟陰郡名是據元始二年(2年)户口籍而來。(4)周振鶴: 《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頁。馬孟龍先生進一步指出: 《漢志》的行政區劃斷限爲成帝元延三年(前10)。(5)馬孟龍: 《西漢侯國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頁。如是,則《漢志》記載的濟陰郡轄縣實爲成帝後期定陶國的轄縣。
我們根據金關簡的時間範圍爲武帝後期至王莽時期,絶大多數簡爲昭宣及以後簡,依據西漢後期濟陰郡、定陶國、濟平郡的名稱及轄域變遷,可以推斷出金關簡中涉及濟陰郡簡的時間範圍,分别是甘露二年(前52)之前、黄龍元年至河平四年(前49—前25)、建平二年至王莽時期(前5—9年)。下面分别對金關簡中提到的濟陰郡轄縣廩丘、都關、成武、桂邑進行討論。這幾個縣邑在《漢志》中皆非濟陰郡所轄,“濟陰郡桂邑”不僅《漢志》未載,《史記》《漢書》中更找不到蹤迹,筆者試探究其地望。
濟陰郡廩丘左里卜捐
(73EJT24∶328)
廩丘在《漢志》中屬東郡,《續漢志》中屬濟陰郡。此簡所在探方出土簡牘1006枚,絶大多數簡極爲殘碎,但紀年簡卻有規律可循。此探方有明確紀年的簡有本始(T24∶97、(6)爲行文方便,以下列舉簡編號時都省去探方號T24。244、262、895、945),地節(101、251、252、262、267A、269A、532A、566A、748、809、828、872A),元康(705),五鳳(35A),甘露(92A),初元(44),建始(28),永始(23A、133),建平(217)、元壽(300),元始(9A、31A、32、68、145、315、336、378、426、439、506、574、587、616A、646),居攝(75A、153),始建國(22、36、214、228),從中可窺T24的簡以宣帝時期和平帝王莽時期居多。馬孟龍先生認爲廩丘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由濟陰郡改置定陶國時劃入東郡,之後訖至西漢末廩丘一直是東郡轄縣。(7)馬孟龍: 《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李曉傑先生認爲東漢初年廩丘沿襲西漢末年的行政建置屬東郡,和帝永元二年(90年)漢廷從濟陰郡析置城陽國時將廩丘從東郡劃入,永元六年(94年)城陽國除時廩丘又併入濟陰郡,降至東漢末時廩丘又别屬東郡。(8)李曉傑: 《東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頁。因此,綜合前人的研究及金關簡的時代範圍,此簡的年代當爲宣帝時期且在甘露二年以前。
從者濟陰都關樂里公乘行博德,年卌,長七尺三寸,黑色 閏月丙辰入 鐱一
(73EJT25∶11)
都關在《漢志》中屬山陽郡。關於都關在山陽郡和濟陰郡間的變更往返,《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以下簡稱《秦漢卷》)認爲在宣帝甘露二年置定陶國時,都關别屬山陽郡。元帝竟寧元年(前33)置山陽國時回屬濟陰郡,成帝河平四年復置定陶國時再屬山陽。(9)周振鶴、李曉傑、張莉: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93頁。如是,則都關隸屬於濟陰郡的時期爲景帝後元年至甘露二年(前144—前52)和竟寧元年至河平四年(前33—前25)。馬孟龍先生認爲甘露二年宣帝置定陶國時,都關並未劃入山陽郡,遲到河平四年,成帝徙山陽王劉康爲定陶王,濟陰郡再次設爲定陶國時,都關才於是年改屬山陽郡所轄。哀帝建平二年(前5),定陶國恢復爲濟陰郡時,原濟陰郡别屬山陽郡之縣、侯國(包括都關)悉數回屬。(10)馬孟龍: 《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如是,則都關除河平四年至建平二年(前25—前5)屬山陽郡外,自景帝後元年至西漢末年的其他時期皆屬濟陰郡或定陶國所轄。此簡所在探方T25共出簡248枚,其中有紀年的簡8枚,宣帝時期6枚,元帝初期2枚,紀年分别是本始二年(T25∶80,前72)、本始五年(T25∶32,前69)、地節二年(T25∶7,前68)、元康元年(T25∶15,前65)、甘露三年(T25∶6,前51)、甘露四年(T25∶163,前50)、初元二年(T25∶30,前47)、初元三年(T25∶121,前46)。我們推測此簡的年代也大致在此一時期,黄浩波先生亦根據西漢後期的閏月丙辰日推斷此簡年代爲“本始二年閏五月乙卯朔、元康二年閏七月戊戌朔、神爵三年閏十二月丙申朔、五鳳二年閏八月辛亥朔、甘露元年閏五月乙未朔、初元元年閏十月癸巳朔、初元四年閏六月戊申朔”中之某一年。(11)黄浩波: 《〈肩水金關漢簡(叁)〉所見郡國縣邑鄉里》,簡帛網2014年7月22日,http: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52。
細察此簡圖版,書寫筆迹工整,隸書風格明顯。此簡所在的探方T25共出土了5枚書有濟陰郡的簡,其中簡T25∶83、T25∶137、T25∶162、T25∶164都是濟陰郡定陶籍田卒出入名籍簡,此4枚簡書寫筆迹相似,風格一致,當可編聯。簡T25∶11的筆迹、書風與這4枚簡相似,時代可能接近。據學者研究,肩水都尉轄域内所出的田卒簿籍多屬昭、宣時代,特别是昭帝時代。(12)關於大灣所出田卒簿籍簡和金關所出田卒簡的時代,詳參陳公柔、徐蘋芳: 《大灣出土的西漢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姚磊: 《〈肩水金關漢簡〉所見田卒史料探析》,《中國農史》2016年第4期。我們結合田卒簡的時代特徵、T25所出簡的時間範圍、馬孟龍先生及周振鶴先生對西漢濟陰郡時間的考訂、黄浩波先生對閏月丙辰日年份的推斷和此簡的書寫筆迹與風格等因素綜合判斷,簡T25∶11的時代當在宣帝甘露二年以前,極可能是宣帝早期。
(削衣,73EJT34∶40)
成武《漢志》屬山陽郡,《續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續漢志》)屬濟陰郡。根據馬孟龍先生的研究,武帝元朔年間,漢廷削梁國八縣時,將鄰近濟陰郡的薄、單父、成武三縣劃入濟陰郡。河平四年(前25),漢廷改濟陰郡爲定陶國時,將成武劃入了山陽郡。建平二年(前5),當定陶國恢復爲濟陰郡時,成武當回屬。(13)馬孟龍: 《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此簡缺紀年,與此簡同一探方所出的50枚簡中,紀年簡有六枚,分别是甘露二年(T34∶1A,前52)、五鳳三年(T34∶6A,前55)、初元二年(T34∶9+29,前47)、黄龍元年(T34∶40,前49)、建昭五年(T34∶38,T34∶43,前34)。由此推測,此簡年代應與之大致同一時期,至遲不晚於河平四年。
(73EJT37∶1320)
此簡中的地名“桂邑”,《漢志》未載,《史記》《漢書》《後漢書》中也未見此地名。邑是漢代的一種特殊的縣級政區。《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續漢書·百官志》稱:“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邑。”由於邑的設置隨意性、臨時性較强,且置廢變更無常,當邑主主體的貴婦去世之後,邑或收歸朝廷,或由子承襲轉爲侯國,不再稱邑。(14)鄭威: 《簡牘文獻所見漢代的縣級政區“邑”》,《簡帛》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1頁。因此,班固在《漢志》中并未嚴格區分邑,常與縣合稱,《漢志》載“(西漢)縣邑千三百一十四”,將縣邑合稱,使今人很難瞭解邑在西漢的置廢情況。
“桂邑”地名兩漢正史未載,但王先謙《漢書補注》對“濟陰郡乘氏縣”的注中提到乘氏縣東北有桂城,其注爲:“乘氏,先謙曰故乘丘,戰國趙地,三晉伐楚至此而還,見《周紀》。齊取之,見《魏策》。景帝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見《表》。後漢因……南濟自定陶來,合菏水逕乘氏縣,與北濟濮水合。北濟自定陶來,逕乘氏縣合南濟濮渠,同入鉅野澤,下入東郡壽良。又《瓠子水注》:‘濟濮枝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下入東郡范。’先謙案: 桂城在東北,故桂陵,齊敗魏於此,見趙、魏、齊世家。《一統志》‘故城今鉅野縣界’。”(15)王先謙: 《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77頁。
王氏的補注可謂旁徵博引、盡全史料,但對乘氏縣的補注中存在問題。王氏將乘氏縣與乘丘縣混爲一地,乘丘屬泰山郡,距魯國不遠,漢亦置乘丘縣;而乘氏縣則屬濟陰郡,濟水於乘氏縣西分爲二,乘氏和乘丘相距甚遠,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縣。王先謙誤將兩地合爲一,蓋是受《漢志》應劭錯注的誤導。顔師古在《漢志》濟陰郡“乘氏縣”下引應劭注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其實,乘丘、乘氏兩地分明,後世學者多有辨析,但受應劭錯注的影響,後世還是有不少地理著作將兩地混淆。顔師古雖在“乘氏縣”下誤引了應劭的注,但在泰山郡“乘丘縣”下亦注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也。”注釋前後不一。王先謙亦誤將乘氏、乘丘混同。但王先謙在“乘氏縣”注的最後提到了“桂城”,這對我們認識此簡中的桂邑至關重要。桂城在乘氏縣東北,是戰國時齊魏桂陵之戰的發生地,此城又處於濟陰郡境内,很可能就是簡中提到的桂邑。爲了進一步求證,筆者翻檢了漢唐正史、相關地理志及唐以後的地理總志,發現史籍中都有關於“桂城”“桂陵”的明確而大量的記載,且其地望就在漢濟陰郡境内。我們按史源學方法梳理“桂城”“桂陵”的文獻記載,進一步明確其地望,辨析其和“桂邑”的關係,并考證其今天的具體位置。
通過查找文獻,我們發現王先謙補充的“乘氏縣桂城”史料當來源於《括地志》和《史記正義》。唐皇子李泰所著《括地志》早已佚失。今人賀次君整理的《括地志輯校》在“曹州乘氏縣”下載:“故桂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即桂陵也。”(16)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 《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1980年,第164頁。這條記載是從《史記·趙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中輯出。
《史記·趙世家》“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17)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趙世家》,中華書局2014年,第2170頁。《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二十六年),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正義亦引。(18)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華書局2014年,第2294頁。張守節是唐代人,他在《正義》中引《括地志》明確指出了桂城的地望,即在唐代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唐代乘氏縣地望清楚,位於今山東菏澤市區,(19)關於唐曹州乘氏縣的地望,後世地理志書皆有明確清晰的記載,今人亦對應了現地名,即今天的山東菏澤市。詳參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44—45頁;吴松弟編著: 《兩唐書地理志彙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6頁。桂城在其東北,此地在漢代位於濟陰郡轄域内,但唐乘氏縣非漢乘氏縣,漢乘氏縣位於漢鉅野澤西南,治今山東省巨野縣西南。(20)周振鶴編著: 《漢書地理志彙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3頁。
王先謙提到桂城在乘氏縣東北,當是引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的注文,但王氏錯把唐乘氏縣當作漢乘氏縣,以爲桂城在漢乘氏縣東北,誤。漢乘氏縣位於今巨野縣西南五十余里,自兩漢至晉不改。元魏太和中,乘氏縣治地遷到今荷澤市區,但沿用漢乘氏縣名,至隋唐北宋治地不變,(21)樂史: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十三》“曹州乘氏”條,中華書局2007年,第261、262頁。故張守節引《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不能用於漢乘氏縣注。我們通過其他文獻進一步梳理乘氏縣的變遷及其與桂城的關係、桂城的地望。
《水經注·濟水》記載:“(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有桂城。《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22)陳橋驛: 《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204頁。《水經注》記載濟水一支從乘氏縣東北入鉅野澤,乘氏縣有桂城。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乘氏縣,緊,南至州五十四里。本漢舊縣也,屬濟陰郡。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曹州。大業末年廢,武德四年重置。”(23)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七》“曹州乘氏”條,中華書局1983年,第293頁。《元和郡縣志》記載了唐乘氏縣的地望,即在曹州北五十四里,但未注意到漢至唐乘氏縣的變遷。
《太平寰宇記》對河南道曹州所轄乘氏縣的記載較爲詳細:“乘氏縣,北五十四里,舊八鄉,今六鄉。本漢舊縣也,屬濟陰郡,後漢及晉不改。按: 前乘氏縣,在今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乘氏故城是也,宋廢,後魏太和十二年於縣置乘氏縣,取漢乘氏縣爲名也。隋開皇三年罷濟陰郡,屬曹州,大業末年廢。唐武德四年重置,屬曹州。……故桂城,《史記》齊威王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與魏戰於桂陵,大破魏師。”(24)樂史: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十三》,“曹州乘氏”條,第261、262頁。《太平寰宇記》是樂史在北宋初年撰寫的全國地理總志,他詳細地記述了乘氏縣自漢至宋初的置廢沿革。從中我們瞭解到: 兩漢乘氏縣位於北宋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治今山東巨野縣西南),劉宋時縣廢。北魏時於今縣重置乘氏縣(即今菏澤市區),其後時有置廢,至宋初曹州轄乘氏縣。樂史還記載了乘氏縣下的故“桂城”,指出是齊魏桂陵之戰發生地。
《讀史方輿紀要》:“桂陵城: 在(曹)縣西北五十里。本齊邑,《史記》‘齊威王二十六年,以田忌爲將,大破梁軍於桂陵。’其後秦穰侯葬此,世謂之安平陵,亦曰安陵鎮。明初移曹州治焉,今爲安陵集,有安陵巡司。孔穎達曰‘桂陵在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似誤。”(25)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山東四》,“兖州府曹縣”條,中華書局2005年,第1575頁。顧氏對桂陵城的位置記載和判斷皆有誤,但書中提到了一條重要信息,即唐人孔穎達對桂陵城位置的判斷,顧氏認爲孔穎達判斷錯了。其實,由於曹州治所在金、明反復變遷,致使顧氏錯誤地認爲桂陵城在曹縣西北五十里的安平陵,而懷疑孔穎達説法錯誤。其實,孔穎達的説法更早,和李泰、張守節關於桂陵城地望的判斷一致,當無誤。
《大清一統志》(以下簡稱《一統志》)系統地總結了清中葉以前的地理學著作,是傳統地理學時代内容最豐富、體例最嚴密、考訂最精詳的地理總志。(26)楊光華、馬强編: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導讀》,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4頁。《一統志》對桂陵、乘氏廢縣、乘氏故城都有記載。《一統志》對“桂陵”的記載爲:“桂陵,在菏澤縣東北二十里。《史記》齊田忌大破魏師於桂陵,《寰宇記》乘氏縣有桂陵,即田忌破魏處。”(27)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一一)》卷一八一,“山東統部·曹州府·古迹·桂陵”,四部叢刊續編本。其對桂陵的記載引《太平寰宇記》點出了桂陵與乘氏縣的關係,并確指了桂陵的地望。《一統志》對“乘氏廢縣”的記載爲:“乘氏廢縣,在鉅野縣西南……漢置乘氏縣,屬濟陰郡,景帝封梁孝王少子買爲侯邑,應劭曰: 乘氏故乘邱也,後漢和帝封梁商爲乘氏侯。晉屬濟陽郡。《寰宇記》漢乘氏故城在鉅野縣南五十七里,後魏太和中移治句陽縣界,而故縣遂廢。”(28)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一一)》卷一八一,“山東統部·曹州府·古迹·乘氏廢縣”,四部叢刊續編本。從中我們可知漢乘氏縣在清鉅野縣西南,後魏太和以後縣廢。《一統志》對“乘氏故城”的記載爲:“乘氏故城,今(曹州)府治,後魏縣也。漢乘氏在鉅野縣界,宋廢。後魏太和十二年復置,取漢故乘氏縣爲名。隋屬濟陰郡,唐屬曹州,《元和志》乘(氏)縣南至曹州府五十四里,《金志》大定八年遷曹州治於古乘氏城,《金史·康元弼傳》‘河決曹、濮,遣元弼相視,改築於北原。’明洪武元年省縣入州,又以水患徙安陵集,二年徙盤石鎮,今爲曹州府治。”(29)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一一)》卷一八一,“山東統部·曹州府·古迹·乘氏故城”,四部叢刊續編本。《一統志》辨析了乘氏故城和乘氏廢縣,指出漢乘氏縣在清代山東鉅野縣界,劉宋時縣廢。隋唐乘氏縣北魏時設置,唐北宋因之,金大定年間縣廢,後移曹州治於此,元明因之,清代爲曹州府治,今地在山東菏澤市區。(30)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一一)》卷一八一,“山東統部·曹州府·建置沿革·菏澤縣”載:“(菏澤縣)漢爲句陽、葭密等縣,後魏太和十二年始移置乘氏縣於此,屬濟陰郡,北齊北周及隋因之。唐屬曹州,五代宋不改。金大定六年縣廢,八年改置濟陰縣,爲曹州治,元因之。明洪武初縣省入州,尋州亦廢。正統十一年復置曹州,本朝雍正十三年升州爲府,設菏澤縣爲府治。”從中可窺知隋唐乘氏縣在金以後的變遷。
通過梳理、排比、分析文獻,我們對乘氏縣的置廢變遷和桂城的地望有了較清晰的認識。桂城即戰國桂陵之戰發生地,其地望在唐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西漢乘氏縣劉宋時縣廢,今地在山東鉅野縣西南;唐乘氏縣元魏時設置,隋唐北宋沿襲,金時廢,明清時此地一直爲曹州(府)治所,今地在山東菏澤市區。李泰《括地志》、張守節《史記正義》、唐人孔穎達、樂史《太平寰宇記》都記載了桂陵城的大體方位。《大清一統志》更是梳理和區分了漢乘氏縣和隋唐乘氏故城的沿革置廢,通過桂城與唐乘氏縣的方位關係,我們可以考證出桂城的地望。
桂城(桂陵)是桂陵之戰的發生地,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地名,學術界對其地望有過討論,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形成了兩個觀點,一個認爲桂陵在今天的河南長垣,一個認爲桂陵在今天的山東荷澤東北。(31)關於桂陵地望的討論,較代表性的文章有: 韓達夫、張德書: 《桂陵之戰故址在今山東菏澤東北何樓一帶》,《菏澤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田昌五: 《談桂陵之戰及其相關諸問題》,《文史哲》1991年第3期;仝晰綱: 《桂陵之戰諸問題辨析》,《史學集刊》1999年第3期。經過學界討論和梳理歷史文獻,絶大多數學者認爲菏澤説證據更多,史實更清楚,材料更充分。1988年菏澤地區邀請文史學者專門召開了桂陵之戰地望論證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們對桂陵之戰故址進行了詳細論證,比較一致的認爲古桂陵在今山東省菏澤市東北牡丹鄉何樓一帶。(32)孫世民、張存儉: 《桂陵之戰故址論證會述要》,《東嶽論叢》1988年第5期。經過學術界的討論與争鳴,桂陵的地望已清晰確鑿,此不贅言。我們查閲地圖,古桂陵所在的菏澤市正位於西漢濟陰郡境内,位置恰好居於濟陰郡中間,漢乘氏縣在其東部偏北,隋唐乘氏縣在此處附近。桂陵、桂城皆有“桂”字,此枚簡中的“濟陰郡桂邑”亦當是此處。桂邑的地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菏澤市牡丹鄉何樓村一帶,隨着城市化的發展,今天這裏已被納入了菏澤市區,政區的名稱也調整爲菏澤市牡丹區牡丹街道辦,這裏現建有“桂陵之戰遺址公園”供游客懷古憑吊,西漢桂邑的核心地域當在今菏澤市牡丹區東北牡丹街道辦事處(鄉級)所轄區域一帶,這裏既是桂陵之戰的古戰場,也應是西漢桂邑的邑治中心。
綜上所述,桂陵地處漢濟陰郡境内,至北魏酈道元時桂城仍存,桂城位於唐宋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今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区牡丹街道辦)。兩漢正史及《漢志》《續漢志》雖未記載“桂城”或“桂邑”,但通過魏晉以後的文獻梳理和地望分析,肩水金關漢簡中提到的“濟陰郡桂邑”其地當是戰國時的桂城(桂陵),在西漢後期曾短暫設置爲“桂邑”,估計存在的時間當不長,旋置旋廢,故在《漢志》中未留下記載。
附記: 拙文“桂邑示意圖”(33)此圖據馬孟龍《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文中插圖5改繪。(見插頁圖八)蒙師弟祝昊天博士、廉超博士幫忙繪製,謹表感謝!拙文在編輯、排版過程中,但誠先生惠賜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