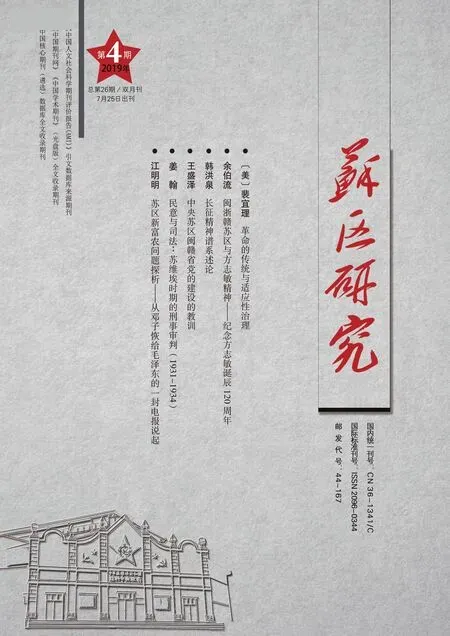苏区新富农问题探析
——从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
提要:1950年邓子恢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提到新富农对1929年苏区的土地分配表示满意,也就是说,在土地革命之前新富农已经存在。而这与新富农是中共土地改革后的产物这一学界共识相矛盾。通过探究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历程,可知邓子恢所言新富农和学界所重视的新富农都在中共认识范围之中,并不矛盾。由此再探究邓子恢所言苏区的新富农问题,则苏区时期在中共的判断中已经出现新富农,并制定了如何对待新富农的政策,这一切都和苏区革命中的“富农路线”问题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并对苏区革命乃至此后的中共革命影响深远。
何谓新富农?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认为新富农分两种:一种是指抗战中为鼓励农业生产而新产生的富农;一种是土改后农村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出现的新富农。[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尽管学者对新富农的研究时段和角度不一,但大都持此种观点,亦即新富农是指中共变革土地制度后产生的富农。[注]代表性研究可参见苏少之:《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新富农政策》,《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杨利文、邹腊敏:《土改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张永泰道路”的宣传——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尤国珍:《嬗变与重塑:中国特色的富农政策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换言之,新富农应该是中共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之后才会产生的。但笔者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却发现1950年邓子恢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到:“我记得一九二九年闽西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后(当时只分土地不分浮财),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民,包括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在内,都很满意。后来经过一九三〇年反富农,社会上便引起纷乱。”[注]邓子恢:《关于对富农出租地的方针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共文件中,“新富农”和“新式富农”通常是一个概念,经常出现混用的情况,如任弼时在致毛泽东的同一封信中就用“新富农”和“新式富农”指同一类人。参见《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47年11月12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邓子恢的这封电报,答复的是毛泽东询问关于新中国建立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应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邓子恢的意见是原则上要中立富农,但可以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而其回忆闽西苏区的土地分配,则是为了以当年在闽西的经验证明中立富农的正确性。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认定,邓子恢这里说的新旧富农表示满意,是指他们对1929年闽西苏区的土地分配中怎样对待富农的政策表示满意。换言之,在邓子恢的回忆中,1929年土地革命之前,新式富农已经存在,所以1929年土地分配中才会涉及他们。[注]在解读史料过程中,同学贺怀锴等人提出是否可能因为苏区的土地改革催生了新富农,所以他们表示满意?笔者认为可以否定此种可能性。因为首先正如正文所言,这封电报整个的中心意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中应怎样对待富农,因此其举例证明也应是苏区土地改革中怎样对待富农;其次,如果新富农因为土地改革催生了自己而满意,那旧富农的满意如何解释?最后,尽管邓子恢的电报中说分配后,新旧富农表示满意。虽然有一“后”字,但下文还有“后来一九三〇年”,则邓子恢这里说的分配后,只是1929年至193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绝难产生新富农。考虑到他们的这种解读具有一定代表性,特此提出进行辩驳,并向各位同学致谢!这就和学界普遍认为的新富农是在中共变革土地制度(包括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才产生的这一观点相矛盾。但邓子恢和毛泽东都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亲历者,并且还提到了当时“只分土地不分浮财”的具体细节,对这一重大事实应不会产生记忆错误。因此真相如何,值得深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理清楚的是,此时(1950年)邓子恢电报中的“新式富农”所指为何?这就要对中共认识新富农的历程进行考察。
一、何为“新富农”?
中共在苏区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土地革命后会产生新富农。例如周恩来当时就认为虽然土地革命后农民的土地都一样多,但富农有较好的基础(如有好的农具、有耕牛、人口多、懂农业知识、会经营),所以富农在土地革命后照样可以“成为新的富农”,中农也是如此。[注]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417页。中共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未曾到来之前,富农会一直存在,今天的贫农中农乃至富农,明天都有可能变成新的富农,“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注]《反富农斗争决议案》(1930年9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而新富农,在此时的中共看来,就是“新的富农”,亦即土地革命后产生的富农,和旧富农除了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同,并无其他区别。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眼中的新富农则特指“吴满有式富农”。吴满有原本是一个逃荒的贫苦农民,由于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并勤劳肯干,最终变成了经济基础良好(经营85垧土地兼喂养四头牛及一马一驴)的富农。《解放日报》由此认为:“当我们把吴满有当做富农看待的时候,是有一种新的含义的。”新在何处呢?新就新在他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成长起来的富农。中共通过土地革命,给吴满有式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帮助其发展,使他在经济上变成富农,因此这种富农是“得到革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可以有两种富农,即革命的富农与普通的富农,而吴满有则是属于前者。”[注]《关于吴满有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第1版。此时的“吴满有式的新式富农”,指的是“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中农上升为富农者”[注]《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47年11月12日),《任弼时选集》,第411页。,且支持革命。在《解放日报》看来,这种新富农与旧富农(即普通富农),有本质区别。而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之一的张闻天,则对新富农存在着自己的看法。张闻天认为,原有的地主经济因为受到战争、中共的革命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等影响,会被削弱,这就会导致一部分地主改变经营方式,向富农经济发展,成为新富农。但张闻天并未明确宣布旧地、富转变而来也应称之为新富农。[注]《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1942年7月9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20页。此时中共的主流认识和《解放日报》的宣传中,都是以“吴满有式富农”作为新富农的典型代表。如新富农问题传达到地方,晋察冀边区就认为:“由于深入的减租减息及合理的负担政策(统累说)贫农中农经济发展了上升为新富农,这种新富农的发展将不再踏旧资本主义的覆辙,他们将要成为一种新型的富农,即吴满有式的富农。”[注]方草:《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的实施(节录)》(1944年12月23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要进行土地改革,中共愈发认识到新富农的复杂性。在1948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在土地改革中划分社会各阶级的草案中,将新富农分成两种:一种是按照革命性质划分的,认为在中共民主政权领导下,一些“贫苦成分的农民”,因为中共采取的各种“扶助农民的政策”而“得到土地及其他正当利益,勤劳致富”,在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已经发家致富,则应当认定为新富农,亦即特指“吴满有式富农”;另一种则是按剥削性质划分的,认为在经济基础上已经达到富农标准(租入或占有较多较好土地,占有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劳动)的农民,如果是“经常依靠以资本主义方法”来进行雇工剥削或者获得“其他资本主义剥削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那就可以认定为新富农(其中也包括佃富农——笔者注)。[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122、123页。由此可知,此时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范围扩大了,新富农不再是其建立的根据地独有的产物。不仅如此,此时对根据地的新富农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吴满有式”在根据地政权的贫苦农民因分得土地并勤劳致富而被认定为新富农外,根据地政权中一些旧地主、旧富农在土地被重新分配后“又勤劳生产上升”的,也被认定为新富农;而在一些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根据地,那些自己改变经营方式,不再进行封建剥削的旧地主、旧富农也被认定为新富农。[注]《习仲勋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48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页。总而言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认定的新富农,既包括:1.根据地内的“吴满有式”由贫、雇、中农上升而成为新富农;2.由旧地主、旧富农在平分土地后再次上升为新富农;3.根据地内未平分土地地区旧地、富改变经营方式成为新富农;4.全国范围内以资本主义方式剥削的新富农(不论其是否在根据地内)。
行文至此,我们再结合邓子恢发电报给毛泽东的时间(1950年)可知,此时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已经完全成熟,以上四种都是他们当时所认识且存在的新富农。并且,邓子恢的这封电报,针对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的富农问题。因此其电报中的新富农应是与中共的根据地以及中共的土地改革无关的新富农,那就只能是第四种“以资本主义方式剥削的新富农”。由此可知,邓子恢这时候是以1950年的概念去说明1929年的现象,即1929年进行土地革命时,一些纯粹以资本主义方式剥削的新富农和那些既有资本主义剥削又有封建剥削的旧富农都对“只分土地不分浮财”的政策表示满意。
这一推断能在1929年前后的史料中得到证实。1930年在毛泽东和邓子恢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共党史中著名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其中对富农的分类给我们判断邓子恢电报中的“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提供了证据。这份决议案中判定:
富农有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第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注]《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98页。
其中的第三种富农在此后中共的认识中多被判定为“富裕中农”,[注]如1931年苏区中央局就批评“初期性富农”的概念,认为它其实是富裕中农,不能作为富农对待。见《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1931年2月8日),本书选编组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与我们要分析的富农无涉,此不赘述。但结合上文解放战争时期对新旧富农的认定:资本主义剥削为新富农,封建剥削为旧富农。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邓子恢电报中所言“新式富农”正是《富农决议案》中的第二种富农,即“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电报中所言“旧式富农”则是《富农决议案》中的第一种富农,即“半地主性的富农”。由此可知,1929年前后以毛泽东、邓子恢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富农存在“半地主性”(即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的区别;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渐渐提出了“旧富农”“新富农”等专有名词对其进行涵括;但在后来的回忆中,则会用后来的专有名词来指代此前的现象。由此我们厘清了邓子恢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的“新式富农”与“旧式富农”所指为何。但本文还想深究两个问题:第一,苏区是否存在新富农?第二,苏区的新富农政策为何?邓子恢电报中所言新旧富农对苏区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否一直表示满意呢?
二、苏区有无新富农?
苏区在土地革命后是否产生了新富农,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苏少之在研究抗战以后的新富农时曾顺带讨论,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来缺乏正确的富农政策,二来根据地战争形势严峻,“至今尚未发现土地改革后由中农和贫雇农上升为新富农的文献”。[注]苏少之:《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0-131页。温锐在研究中央苏区的“限制富农”政策时,认为“中央苏区内被称为‘新富农’者不过是土地革命后(还不到二年时间)刚刚由贫农、中农转化过来的富裕农民”[注]温锐:《试论中央苏区的“限制富农”政策》,《南开史学》1986年第2期,第181-182页。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对这一定义注明出处。笔者近期曾向温锐老师请教,温老师现在认为苏区由于存在时间短,不太可能产生新富农。,但这一定义并未见诸史料记载。王明前曾论及毛泽东注意到了苏区革命后产生的新富农,[注]王明前:《平等与效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查田运动》,《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第73页。不过根据他的注脚追本溯源,毛泽东当时描述的是“分田后的富农情形”,说的是富农在分田后继续剥削,[注]《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而非产生了新的富农。张鸣则判断查田运动中,查的就是新富农,但也未给出判断依据。[注]《红色的个案——苏维埃乡村追求》,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笔者在爬梳苏区相关史料的过程中,虽然找不到确切史料证明苏区有哪些人成为了新富农,他们的财产状况如何,但有一点确能肯定,那就是在当时中共的判断中,苏区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新富农。而中共之所以会有此种判断,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土地革命中的某些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革命理论的推导。
先从苏区革命中的某些现象说起。当时中共认为在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出现了富农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富农分子把持苏维埃政权,操纵土地分配,在土地革命中攫取了贫苦农民的革命果实,因此富农不仅未在土地革命中受到损害,反而保留了资本继续剥削和生长,成为新富农。例如刚开始有的地方政策规定分田的时候,田里种的谷物归原耕种者所有,或者分得田地的人补给原耕种者“相当工资”,就被中共认为是“实际上保护了原有富农,并创造了新富农”[注]《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8日至2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310页;《永定县苏关于土地问题草案》(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为什么呢?因为分田大都是将富农多出来的田分给贫雇农,因此这个政策就相当于让富农多收了一次谷子,“这是好了、便宜了富农”,[注]《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节录)》(1930年10月7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33-334页。为他们在土地分配后继续发展成为新富农提供了条件。
不仅如此,苏区土地分配的标准也有利于富农。土地革命初起时,苏区大部分地方一般都以人口或者劳动力为标准对土地进行平均分配,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较为平均和迅速,以劳动力为标准则有利于发展生产,这是当时的主要考虑。但后来中共则发现,如果单纯以人口为土地分配标准,则富农家庭人口特别多,而贫农、雇农则大多为单身汉,家里人口少,因此还是对富农有利。[注]《中共中央给长江局转中夏同志并湘鄂西特委的信(节录)》(1930年11月21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62页。而如果单纯以劳动力为标准,则富农家庭多是以自家人口为主体进行生产劳动的,不仅家里劳动力比贫农多,而且还拥有更充足的畜力、农具和资本,而这些生产工具贫农极度缺乏甚至没有。并且如果以劳动力为分配标准,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贫农中产生贫富分化。“劳力多的贫农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劳力),因为多得了田,便比较劳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两人有劳力)具备迅速发展为富农的条件。”[注]《富农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273页。不仅如此,个别地方还有以生产工具为标准而分配土地的,就更“完全是富农的利益”[注]具体参见瞿秋白:《关于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节录)》(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1930年10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31、349页。。如此一来,富农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因为有人口和劳动力乃至生产工具的优势,自然较一般贫苦农民分得了更多土地,也就更容易成为新富农。
土地革命以前,富农一般兼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两种剥削,土地革命虽然扫除并禁止了封建剥削,“但资本主义的剥削,确是一般的存在”。富农凭借自身优势,获得更大发展。例如在闽西:
大多数富农取得了政权,一般富农资本不独未受损失,而且少有增加。因此,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更加开展,最厉害的就是雇佣劳动,一般雇农不论长工、短工、散工,工钱很少增加,有些地方反而减少;待遇丝毫没有改良,而工作却异常苛酷;其余就是耕牛对贫农的剥削(暴动后耕牛工钱多数是增加),养牲畜(猪、鸭、羊、猪牳),种山经营小作坊,如做粉干蒸酒等,也同样是剥削雇佣劳动;分田时留肥短报,所以,革命后富农日渐生长。
同年,乾隆帝携倪瓒《狮子林图》游览狮子林。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乾隆帝在长春园东北角仿建狮子林,并仿倪瓒《狮子林图》绘有长卷,藏于园中清閟阁。由于乾隆帝嫌长春园狮子林不能尽同倪瓒《狮子林图》,于乾隆三十九年在避暑山庄再次仿建了一座狮子林,命名为“文园狮子林”,并记其事说:“兹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度地复规仿之,其景一如御园之名,则又同御园之狮子林,而非吴中之狮子林。且塞苑山水天然,因其势以位置,并有非御园所能同者,若一经数典,则仍不外云林数尺卷中。”⑩
不仅富农在革命后变成新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注]以上均出自《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04页。换言之,随着土地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农、中农及贫农都有成为新富农的,并且还有更多农民向往成为新富农。
由上可知,在当时中共看来,苏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很多政策并未削弱原有的富农,反使他们有所获益,并且在土地革命后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不仅使得富农变成新富农,部分中农和贫农也在变成新富农,并且更多人在企图成为新富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此后中共的土地政策逐步升温,苏区革命为何愈发“左”倾了。但必须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只是中共当时出于阶级分析话语而产生的判断,至于真实情况是否真的如其所言是富农路线和机会主义泛滥导致富农夺权并操作土地革命导致富农遍地滋长,则是另一个需要进行专文论述的问题。遗憾的是囿于史料,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中共认识中的这些新富农他们的经济来源和财产状况如何,不能对这一群体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过从上文可以肯定,至少在中共眼中,苏区时期已经有一些人在土地革命后成为新富农,并诱发了其他农民成为新富农的愿望。这就向中共提出了应如何对待新富农的问题,并和中共理论推导中新富农的产生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演变问题紧密相关。
三、中共革命逻辑中的新富农及对其政策
苏区时期,中共并未严格区分富农与新富农(至少并不认为二者有何本质差异)。要探讨苏区时期的新富农政策,则必须追溯此前中共革命理念中由富农到产生新富农的发展逻辑和由此带来的革命政策。
对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而中国作为农业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六大认为,尽管在理论上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有四种可能途径:一是发展富农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富农经济的发展道路;二是大地主改变经营模式走上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道路;三是通过外国资本投资中国农业,组成大型农业公司,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进化之路;四是通过革命的方法(尤其是土地革命)消灭封建余毒,开辟中国农村资本主义自由而又快速的发展道路。中共在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后,认为前三种途径即使可能,也“必然是非常之慢、非常之痛苦”,中国农民还将遭受各种苦难。因此只有第四条革命道路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但在革命成功以后,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又必将遭受帝国主义的阻碍。想要在与帝国主义的剧烈斗争中获胜,就必须提高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而力量和觉悟获得极大提高的工农群众一定会要求“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而如此一来,就不是为原先设想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而是要努力准备社会主义的发展条件。[注]《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417-421页。
既然要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发展条件,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限制,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代表就是富农。但富农不仅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具有“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形式”。富农兼有的封建性导致其不可避免要走入反革命阵营,所以要提前做好“下一阶段的斗争”的准备。因此对待富农,已经暴露反动面目的就与其他反革命势力同等看待,一概斗争;面对军阀、官僚等的压迫而在继续斗争的富农,则尽量在与共同的敌人(军阀、官僚等)的斗争中与其统一战线;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富农,则既不故意加紧对它的斗争以免促其反动,但也不应对其让步以免妨碍贫雇农的力量。[注]《农民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425-426页。因此,此时对待富农的政策,其实是一种限制政策:暗中准备斗争,但表面却既不让步,也不故意抓紧敌对。
正是在这未刻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的阶段,毛泽东和邓子恢于1929年7月在福建上杭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以便更好的指导闽西的土地革命。其中对富农的政策则规定随着革命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土地革命初期集中力量对豪绅进行激烈斗争,对富农一不没收土地,二不派款,三不烧毁地契,四不废除其债务,采取的是安抚政策。而随着革命的逐步发展,则要响应贫苦群众的呼声,一方面要在经济上“进攻”富农,没收富农除自己耕种自食以外的多余田地;但另一方面则规定仍不许过分打击,允许富农放债(但禁止放高利贷),允许富农出售余粮(但不准抬高价格),允许富农雇工(但工资要符合标准)。在政治权利方面,也允许富农中亲自参加劳动者参与政权(但不可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15、716、720-721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03-305页。这显而易见是一种限制政策。由此可见,邓子恢电报中回忆的对富农在闽西土地革命中“只分土地不动浮财”,大体上是准确的,这种做法也确实有利于在革命中稳定和中立富农,从而使他们“表示满意”。不过在当时的这些文件中,并未出现后来邓子恢所说的“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这样的名词,而是不加区分的运用“富农”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等名词。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传来新的指示,中共中央随即转变了富农政策,认为应该“坚决的反对富农”。因为中国的富农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兼有封建剥削,他们在土地革命中是必然会动摇妥协并最终走向反革命营垒,所以中共的革命策略是不应该企图联合他们,而是及早准备对其斗争。而以前的策略之所以错误,则是对富农的认识过于机械,将富农身上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截然分开。虽然富农身上的性质可以兼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但它的行动只有一种,那就是反革命。即使有所谓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它向往的目标依然是成为封建地主,将来也会拥有封建剥削。[注]《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9月1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11、314-315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已经认定了富农反革命的必然性,因此当然要采取反富的政策。更何况在此时的中共中央看来,苏区因为之前对富农的错误策略而导致富农路线盛行,给苏区革命带来极大危险和阻碍,因此“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注]《中共中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报告大纲(节录)》(1929年12月15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159页。。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认定此前对富农的策略是错误的,是富农路线,所以在中共中央看来,由于这些错误的富农路线,导致富农不仅未在土地革命中被消灭,反而产生了大量新富农。因此,“反富农斗争不仅反对革命前遗留下来的继续剥削的富农,而且要注意对于苏维埃政权下所产生的新的富农的斗争,所以这一斗争是很长期的”[注]《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1931年2月8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78页。。
苏维埃政权下新富农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土地革命既使农民分得土地,又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解放,将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新的富农就必然出现。并且这种发展还不能“机械地将其阻止和破坏”,因为如若破坏,则会造成社会经济困难,雇农失业,中农恐慌等情况。[注]《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通知第八十八号(节录)——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议》(1931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477-478页。那是否会就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不会。因为这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无法避免的过程,来帮助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彻底消灭富农,消灭资本主义。由此可知,在中共当时的革命理论中,有一个以新富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要确保其最终转变成社会主义。打个比方,资本主义就像一匹马,既要让他跑,又要控制他跑的方向。[注]把资本主义比作一匹马,这是陈毅曾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说法。参见陈毅:《如何正确执行中央五四指示(节录)》(1946年5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261页。如何控制以确保最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这就要制定政策以限制新富农的自由发展。因为随着新富农的发展就会产生剥削,如果苏维埃不对其各种剥削方式进行限制而任其自由生长,则富农的私人资本必将日积月累逐渐坐大;与此同时,雇农贫农方面的利益则要饱受新富农的剥削而苏维埃则丧失了其保护与帮助贫农雇农之责。由此,不仅将导致农村经济继续分化,无法平衡发展,“而且根本要妨害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注]《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06页。。因此反富农斗争当然要包括新富农,但对待新富农则主要还是以限制为主,通过限制新富农的各种剥削以达到限制私人资本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再三致意:这种限制新富农绝非“打富农”,更非打倒或反对某一个新富农。为何?因为在社会主义未曾实现之前富农不可能被消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新富农,所以富农是“打不了”也不应该打的,只要经济上限制其剥削便可。而在政治上,则要发动雇农贫农群众,将他们团结组织起来,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制止一切富农(包括新富农——笔者注)违反苏维埃法律的种种剥削行为,“顺利实现苏维埃的政纲与法令,而达到限制私人资本的目的”。最后,还要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要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反富农的意义与策略,进一步明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与过程,这样才能根本克服富农路线,根本推翻富农在任何时期的领导权,而把群众领着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注]《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307-308页。总而言之,就是要对土地革命后出现的新富农进行经济、政治、理论上的全面限制,使新富农经济的发展始终不脱离由工农群众掌握的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以便时机成熟后向社会主义转变。
另一方面,对新富农的政策还要考虑到中农的情绪,因为中农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新富农。张闻天就认为在苏维埃农村中不可避免将要产生新的富农,而对待这些新富农则不能同对待以前的富农那样,没收他们的好田并分配以坏田。因为这样会引起中农动摇,从而丧失生产积极性,不利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待这些新富农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一方面通过累进税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组织雇农群众对新富农进行阶级斗争。[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1933年5月26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254页。总体上看,张闻天虽提出对新旧富农要区别对待,但对新富农总体上也是要求“限制利用”,在可控范围内发展一方面稳定中农,一方面促进苏维埃经济发展。[注]关于中共对新富农的“限制与利用”政策,详见江明明:《表现与本质:中共新富农问题研究(1927-1949)》,赣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42页。
对新富农既要限制又要发展,这个度在实际操作中极难把握,要么会因为注重发展而陷入所谓“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对富农妥协让步;要么会限制过头,走向“打富农”“消灭富农”甚至“杀尽一切富农”的“左”倾。[注]《土地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编》(1932年9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606-607、610-611页。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在此时的中共看来,新富农的产生主要还是旧富农窃取革命果实,在革命后继续发展导致的。因此其反富农的重点还是要肃清“富农路线”,于是“左”倾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并在随后不断推广和加码,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并在之后的“查田运动”中达到顶峰,富农几乎与地主同等对待,成为敌对阶级并遭受毁灭性打击。[注]孙启正:《1927-1934年中共富农政策再研究:基于发展生产与争取群众视角》,赣南师范学院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8-52页。富农如此,夹杂其中的新富农命运如何则可想而知。但必须指出的是,查田运动虽然事实上对富农和新富农造成强烈冲击,但在政策文件上,中共依然强调地主和富农有别,“绝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注]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8月29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史料选编(1927-1937)》,第693页。。回到本文开篇的邓子恢电报,则其说新旧富农在土地革命刚开始时都感到满意,而在1930年反富农之后引起纷乱,确是实情,也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子恢等人坚持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难能可贵。
结语
本文从邓子恢发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重点探讨了苏区时期的新富农问题与中共革命逻辑。通过对中共认识新富农历程的追溯,我们可以确定邓子恢1950年电报中所言的“新式富农”指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在中共的认识中,新富农不仅包括学术界所注重的中共土地改革后产生的新富农,也包括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富农。因此,邓子恢所言与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矛盾,也由此提醒我们要加强对新富农,尤其是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富农的研究,要充分认识到新富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通过对苏区时期新富农相关问题的考察也可以发现,苏区时期中共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出发,已经意识到土地革命后不可避免会产生新的富农,并思考应怎样对待新富农以确保中国最终向社会主义转变,最终提出对新富农既限制又发展的政策,为此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正确制定新富农政策提供了经验和启示。但在苏区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随着整体形势的日益严峻和革命路线的日益“左”倾,苏区的新旧富农最终同归于被打击的命运。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对邓子恢电报中新式富农的追寻,我们可以发现,苏区时期是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对新富农认识的萌芽期,已经注意到了富农的“半地主性”和“资本主义性”的区别,为以后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日益成熟和完备奠定了基础。邓子恢的这封电报也提醒我们,历史人物在回忆历史时,会有将后来概念倒用回来指代之前现象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概念的演变发展,也要注意历史的此时此刻;既要注意中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更要注意其实践。只有将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看待,我们才能更好地揭示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复杂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