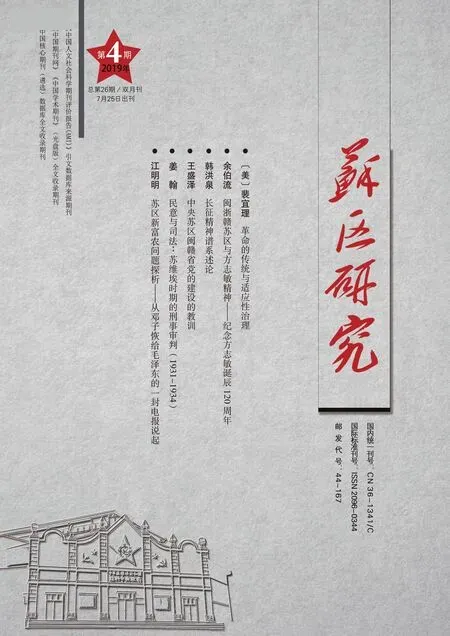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政治与历史的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等校,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Henry Rosovsky Professor of Government)、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社长、浙江大学蒋研中心客座教授。其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等,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1980)、《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1993)、《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管治的政治基础》(2011)、《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2014)、《什么是最好的历史》(2015)、《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2016)等。
一、革命的意义: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苏区研究】欧美学者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曾经极为重视,出现了费正清、史景迁、施拉姆等一批著名学者和一批富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相比之下,您觉得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著作与学者?您认为他们的成果呈现出什么样的研究趋势与特点?
【裴宜理教授】你们在这里提了三位非常著名的老一辈学者——费正清、史景迁、施拉姆。我们认为他们大部分的学术成果不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成果,比较著名的研究是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他在1962年写了一部《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在他看来,抗战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段,因为在那个时间段中共开始崛起。他的重要论点是中共能够快速扩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族主义,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后,中共就动员普通的民众起来反抗日本。
1971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写了一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他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看法不同。他的观点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侵略中国,而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分田以及所实施的各项社会政策。
1974年,日本的一位政治学家片冈铁哉(Tetsuya Kataoka)写了一部《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将以上两种说法进行综合,提出中共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些比较进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后来也有不同的学者写了一些关于某一个根据地的比较细的历史,但主要也是论述抗战时期各根据地的发展历程。
从研究趋势来看,在美国,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并没有像1960-1970年代那么热门。因为1960-197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当时很多年轻的美国学者,也包括我自己,开始对中国革命感兴趣。感兴趣的原因是,越南的革命是模仿中国的革命,在美国与越南作战的时候,我们很好奇,想知道这些东亚革命的过程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做法是什么?
当然,现在没有了这种目标,但是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解放后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开始去研究中国1950-1960年代的历史。他们发现要写那一时段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及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由此他们开始对革命感兴趣。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纯粹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很少,即使有一些,也多是从文化角度来分析中共的革命手段。比如我自己写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这一角度切入的研究,写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运用各式各样不同文化资源来动员老百姓。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写的是戏剧团等文化团体是如何动员的,绝大多数是研究解放后的情况,主要集中在1950-1960年代。
【苏区研究】在中国,近些年来一度冷淡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革命史研究出现总体回升或学术性研究走向深入的趋势。您如何看中国国内革命史研究的现状,您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裴宜理教授】我不十分清楚中国学术界的这种趋势,但现在西方很多年轻学者对革命史不是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还有很多反抗运动,会有民众起来夺取政权,这个到处可以看到,但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是很少的。从伊朗革命以后,几乎没有太多的真正的社会革命。很多年轻学者认为这个题目是老的,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学家来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看那些国家之后的情况,不管是美国、法国、中国、俄罗斯,他们都经过不同的革命,那些不同的革命经历也影响了他们当代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政治情况。所以我自己认为,不管革命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革命的影响在表面上看也许有时候不怎么明显,但却是非常的重要。
在美国也是,我们也在讨论革命传统的意义,这在美国也还没有解决。每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对革命的研究,会有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新的看法。我想,中国也是如此。2011年,我跟一个德国学者、政治学家塞巴斯蒂安·海尔曼(Sebastian Heilmann)合编了一本书,题目是《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管治的政治基础》,其中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对当代政治情况还是有多种不可忽略的影响。我们这本书刚出版时,受到一些批评,认为中国都已经告别革命了,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本书现在在国外政治学界非常热门,大家认识到,中国革命还是有重要性,对了解现在的情况也许有帮助。
【苏区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多个阶段组成的长过程。苏维埃革命是其中为期十年的一个阶段,提出了制度、道路、思想、组织、方式方法等许多新内容。国外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关注度如何?如果从中国革命的长时段来看苏维埃革命,您认为苏维埃革命应该处于一种什么地位?苏维埃革命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与意义,对其后中国的革命与发展影响如何?
【裴宜理教授】苏区时代主要是1927-1937年,说实在的,在美国,可以说是比较忽略这个时代,美国学界主要是注重抗战时期,比较注重1937-1945年。关于苏区,应该说这是一个研究上比较空白的时段。据我所知,虽然有一位韩国政治学家金一平(Ilpyong J.Kim)写了一部《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描写了江西苏维埃的情况,但是除了他的这本书以外,国外关于苏维埃时期比较有名的著作很少。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也编了一本关于江西苏维埃的书,但恐怕影响不是很大。有一些学者研究苏维埃时期以前的阶段,如毛泽东和彭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海陆丰等建立苏维埃之前的情况。
关于苏维埃十年的著作很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苏维埃时期中共只是模仿苏联的一些手段,所以不怎么有意思,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整个中国革命历史都非常感兴趣,也包括苏区时期。
【苏区研究】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再小一点在哈佛大学,您觉得年轻学者、未来一代的学者会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或者是苏区时期的研究有兴趣么?
【裴宜理教授】也许会有,但是现在他们主要对中国1950年代、1960年代的历史更感兴趣。
二、跨学科的视角:政治学研究的功用与必要性
【苏区研究】现在一般的,假如不是做中国史的这些美国年轻学者,也是做历史的,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
【裴宜理教授】西方学者对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是民间文化史特别感兴趣,但是有时候忽视了政治情况。因为我自己是政治学而不是历史学的博士,而且我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教书,所以我当然对政治情况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西方很多年轻的历史学家对政治情况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如果不了解那个整体的政治情况,你就不知道那个社会的反应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美国年轻的学者有时会忽略前一辈学者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学科的原因。以前大部分做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在美国,以前有一个学科的区别,研究中国解放后的历史或者研究中共党史的就属于政治学。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但是大部分只能写中共以外的民国史,也不写1949年以后的历史。但现在不同,年轻的历史学家都愿意写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由于这些学者是学历史学的,他们觉得以前所写的关于中共党史或者革命史的那些作品属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范畴,跟他们的研究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对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现在年轻的学者也经常重复以前学者已经研究过的课题,假若他们先读了那些原有的学术作品的话,他们或许可以比较好地发现新的问题。
大概在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学科体系跟我们不太一样,以前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问题,现在还是如此,所以年轻学者应该不会忽视老一辈的作品。在美国,我认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苏区研究】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有些年轻学者不太关注老一辈的成果。现在主要是比较浮躁,所以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比较强调学术规范,你要研究什么东西,一定要把已有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裴宜理教授】这很重要。做社会史虽然可能提出了一些新的、小的、低层次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它会显得比较碎片化,如果不从政治这个大角度去研究问题,就根本说不清中国历史的内部规律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毕竟社会史是受政治史制约的,上面政治上有什么政策,底下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上面的东西搞不清楚,你就搞不清楚下面东西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结果怎么样。现在学科划分太细致,还是要从整体上、整合起来研究,才可能更有助于认清历史的真面目。所以政治学、政治史仍是离不开的。
【苏区研究】您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也用新的视野对苏维埃革命进行研究,在苏区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经济和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您对此怎么看,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裴宜理教授】“多元视野”并不代表漫无边际、漫无目的,应该在关键问题上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在核心概念上有继续深挖的空间。从“中共苏维埃革命”的逻辑到革命的逻辑,我们要继续推进思考,比较各种革命的异同。我们在讨论“长时段”的同时,也要在连通性上继续努力,要有一个联通的角度。
三、工作队:灵活有效的治理方式
【苏区研究】您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共工作队的研究,涉及中共施政的一个常用的工作方法。这个方法,最初可从苏维埃革命中见到,是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工作方法的一个创造。您为什么如此看重工作队的研究?
【裴宜理教授】我为什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是因为我不但是政治学家,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政治学家,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中国的政治和治理跟其他国家有什么类似的特点,或有什么区别。工作队很有意思,据我了解,工作队原来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后来中国化了,中国化之后,大家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有机的、传统的、适合中国情况的一个工作方法或手段。这个演变是非常有意思的。
工作队虽说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1950年代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就取消了这个方式,认为这种工作方式代价太高、浪费资源。在1950年代,革命性的治理方法被认为是过时的,普遍认为要用比较现代化的官僚制度。1989-1991年苏联和东欧所有的那些共产主义政权都垮台了,但是中国没有,这对我们研究比较政治学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存在,而那些原有的在欧洲的共产主义政权已经消失了?大部分的西方学者、政治学家研究东欧和苏联垮台的原因,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不理想的,那些正式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关是失调的,是很失效的。
问题是,中国的正式政治制度跟原苏联和东欧是几乎相同的,但中国这几十年以来,不但是生存了,而且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经济的快速发展、脱贫的巨大成绩,等等,这些都是之前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做到过的。所以我感觉,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它的正式的政治制度也许没有多大的关系,而应该是与它治理的方式很有关系。
中国和苏联政治治理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工作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虽然中国最初是模仿苏联的模式,但是后来经过中国化,工作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有效的治理方式。
【苏区研究】在您看来,工作队起源于何时?它主要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与苏联时期的工作队相对比,它有何独特性?
【裴宜理教授】工作队最开始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也注意到广州讲习所特派员的情况,但没有强调讲习所和苏联的关系。也许可以说在讲习所有一个比毛泽东、彭湃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鲍罗廷。他和他的一些共产国际同事在讲习所演讲,他们介绍苏联的一些革命方式,包括特派员,就是前苏联的全权代表。这个革命动员方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集体化的时候,斯大林也用了这个方法。很多西方学者写这方面的历史,都认为苏联集体化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故事,因为共产党派出的特派员大部分是从城市来的,他们不懂农村的情况,采用非常暴力性、强制性的手段。
中国也有特派员,但是到了土改时期,农民好像欢迎那些土改工作队到他们那里去。中国工作队与前苏联工作队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的工作队包括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进村之前经过一定的培训,因此他们跟前苏联的特派员、突击队、青年工作队等等不一样,前苏联的工作队很少包括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工厂里面的工人,而且没有受到多大的训练。在前苏联,他们强调农业集体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个跟前苏联不同的是诉苦的方式。我觉得诉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但我们不太明白诉苦的来源。1940年代左右,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开始采用这个方式,后来土改工作队也利用这个方式。中国的土改也不是完全和平的,有些场合也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在里面,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些农民也被发动了。土改不是另外一个政权去占领农村,而是经过当地的农民自己给工作队动员起来了,他们自己成为斗争队的主角。
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土改的工作队,不但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美国的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好像觉得自己在工作队的经验支撑下,自己被改造了。所以工作队对知识分子,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也起了很重要的改造的作用。
【苏区研究】中共早期创立的工作队制度在当代乡村治理和社会转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或者说,发轫于中共早期的工作队制度有何当代性价值?
【裴宜理教授】从乡村治理角度来看,工作队发动群众的特性尤其值得引起注意。我认为跟前苏联比较,这也许是最大的区别。前苏联当时派了一些粮秣工作队、突击队、全权代表等等,他们也是上面派来的,也有一个很明确的任务,但是他们的任务不包括真正地发动群众。中国派工作队的话,它始终是表征着中共要和群众之间要有一个纽带,要发动群众。所以我觉得,工作队通过动员群众完成一个特定任务,体现了中共在农村动员农民的独特方式。
那么,我们可否说上面派工作队,是因为对原有的官僚的正式制度有点怀疑,或者觉得他们不可靠呢?或者他们也许可靠,但是他们能力不够,所以需要支持帮助?但是不能光靠正式的机关、正式的制度。总之是出于对既有制度的一种不信任或者是怀疑,才需要用到工作队这种非常规的治理方式。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把这种革命性的手段给废除掉,但是在中国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和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运用了这个治理方法。所以我觉得,群众卷入的程度是能够表现出中国政治不同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独特性。
我问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的工作队来源在哪里?一般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说这是从苏联进口,而多以为是中国古代“钦差大臣”制度的遗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认为这是自己历史上的出产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比较好接受的一个治理方式。把前苏联的治理方式中国化,虽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于当代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演变。
四、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
【苏区研究】您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影响很大。您如何看待安源与苏维埃两个时期的关联与不同,如何评估安源革命对苏维埃革命的影响?
【裴宜理教授】安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虽然有关安源的研究之前比较忽略,但是中共后来很多的工人运动的方式,都是在安源时期发明的。
我为什么对安源感兴趣,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先生的推荐和邀请,他说你去了就会认识到那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可以研究毛主席去安源的背景。我是政治学家,所以对当代政治情况非常感兴趣,也想要知道当代情况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去了安源才发现,安源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研究安源跟研究苏区时代的一个很大区别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军队,所以完全是靠动员群众搞革命。安源对中共的影响和意义深远,它虽然不是成熟的苏维埃模式,但就像李立三所说,是苏维埃的一个雏形。因为在安源,有中共的中心在那边发生作用,有那么多中共的干部在那边都能领导工人,所以中共当时叫它“小莫斯科”。参加中共的工人也不少,可能也模仿苏联的政权建立各式各样的机关组织,但是因为还没有建立一支军队,所以它面临的问题跟后来的不太一样。中共后来要对军队进行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挑战。
【苏区研究】受民族、教育等方面影响,我们习惯了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看安源,您就能发现更多的新东西。您来研究安源,从您的角度就可以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交流确实重要,角度不同,对问题的理解也不同。
【裴宜理教授】我想大部分的美国政治学家会认为,研究美国政治最成功的一本书,就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勒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虽然这本书出版时间较早,而且是由外国人写的,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关于美国政治学很尖锐的研究著作,因为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外国学者虽然没办法去搜集、掌握比本国学者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等等,但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问题,有时候也许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新的问题。
【苏区研究】非常感谢裴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对本次采访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