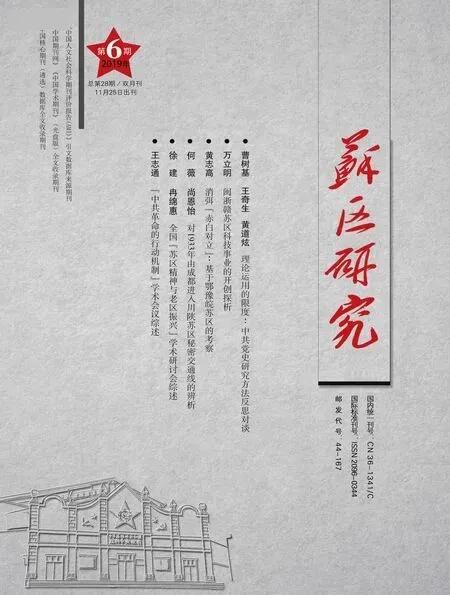军事“误判”遭遇政治“误解”
——“张汉民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研究
提要:杨虎城所辖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部是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陕军主力之一。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名义上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实则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由于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的政治身份颇为怀疑,决定消灭该旅。张汉民却过于自信与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约定”,未能保持必要警惕,并对不断显露的险情疏于防范,最终该部被击溃,张汉民被俘后遭错杀。“张汉民事件”一方面促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产生了负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陕北肃反”;另一方面,该事件破坏了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造成杨虎城及其部属对中共的防范和敌视。
张汉民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重要人物:红二十五军转战陕西后,他名为奉命率领所部(1)该部参加“围剿”初期为陕西省警卫团,1935年2月27日奉命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参见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51页。参与“围剿”、“堵截”和“尾随追击”该部红军,实质上对其起了一定掩护和帮助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他却受到红二十五军领导层的怀疑。由于对张汉民政治面目一直存有“误解”,加之战争环境复杂,为摆脱张汉民部一路“跟踪追击”造成的被动局面,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决定消灭该部追兵。随后,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柞水县九间房设伏,一举击溃警备第三旅两个团,并消灭其一个团又一个营,俘虏旅长张汉民及其以下官兵一千余名。当时,红二十五军及随其转战的鄂豫陕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中共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最终误将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142页。这就是中共西北党史上有名的“张汉民事件”(3)由于红二十五军击溃陕军警三旅张汉民部发生在陕南柞水县九间房地区,因此有些著作也将“张汉民事件”称为“九间房事件”。本文研究的内容是张汉民与红二十五军之间从双方接触到张汉民被错杀过程及该事件的影响,不管是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等都远远超出“九间房事件”,因此笔者认为以事件主要人物来命名该事件更为适宜,故统称“张汉民事件”。。
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后,即对“张汉民事件”作了初步处理。时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回忆:“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4)《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鉴于当时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张汉民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出于统战西北地方实力派杨虎城部考虑,对“张汉民事件”的初步处理十分慎重。一方面,中共党内高层默认张汉民为“烈士”,为受“张汉民事件”牵连入狱的汪锋等人平反,并委以重任。(5)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丹心素裹》,第289页。另一方面,由于这一事件“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6)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丹心素裹》,第297-298页。,中共中央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又长期未曾为“张汉民事件”遇难者公开恢复名誉。不过,中共中央并未忘记张汉民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随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张汉民受到中共中央高规格的公开纪念。中共“七大”期间,中共中央通过正式决议,将张汉民载入“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名单,(7)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3页。并召开追悼大会对其进行了隆重悼念。(8)《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1945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0页。
但是,该事件在当事人和研究者之间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至今仍然存在争议,有必要对该事件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张汉民事件”发生后,深知张汉民在陕西革命经历的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汪锋等,以及原杨虎城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知情人阎揆要等,曾先后多次向中共中央反映张汉民被“误杀”的史实,强调张汉民的革命经历,最终推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期间将张汉民正式列为“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得到纪念。(9)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0-253页。“文革”结束后,汪锋、阎揆要等“张汉民事件”亲历者、知情人在相关回忆文章中仍坚持上述观点。(10)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0-252页。相对而言,原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不论在“张汉民事件”发生后,还是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对该事件的认识大都有别于以上观点。他们虽然也同意张汉民为“误杀”,但是更强调该事件的发生是张汉民“尾随”太紧,威胁太大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是为了摆脱张汉民部一路“跟踪追击”被动局面,才不得已最后决定伏击张汉民所部。(1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41页。此外,有关“张汉民事件”的学术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朱理治传》对“张汉民事件”与“陕北肃反”的因果关系有一定介绍,但是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未作深入探究。(12)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笔者收集到了现在尚未公开的原红二十五军重要领导人程子华、戴季英、郭述申等在中共西北高干会上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发言材料,其中涉及“张汉民事件”部分内容。结合上述回忆材料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汉民事件”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从红二十五军方面而言,既有因信息误导所造成的误判,也有特殊军事环境下反复权衡不得已的军事抉择,还有当时其主要负责人“左”的肃反认识;从张汉民方面而言,则主要是过于自信和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约定”,以及行军过程中疏于必要的军事防范。“张汉民事件”对中共党内团结和党外统战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这一事件促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产生了负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陕北肃反”;另一方面,该事件破坏了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造成杨虎城及其部属对中共的防范和敌视。
一、杨虎城对红二十五军入陕的应对策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反复“围剿”,难以立足,逐渐开始向西部地区运动,谋划创建新根据地。经过多次辗转,红二十五军最终进入陕西南部地区,并决定以陕南地区为中心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对陕西地方实力派陕军杨虎城部构成了威胁。杨虎城立即组织所辖部队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堵截”作战,但遭到红二十五军多次打击,损失惨重。随后,杨虎城对“围剿”红二十五军渐趋保守和消极: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督责和压力,表面上继续组织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围追堵截”和“跟踪追击”;另一方面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积极谋求与中共合作,避免与红二十五军发生直接军事对抗。
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加强是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主要原因。1932年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集重兵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首先将进攻目标确定在战略位置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由于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错误的军事部署和领导,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活动的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从一开始即陷于被动,随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主力部队最终被迫转移到外线作战。10月10日,张国焘在安徽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部分部队坚持在根据地斗争。(1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2-19页。1934年4月16日,这些留下的部队根据鄂豫皖省委4月13日“对红军二十五及二十八两旧部完全编为二十五军”的决定,将当时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合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1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95-96页。虽然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总的形势仍然是严重的,敌人力量强大,而且已经构成了堡垒林立、公路纵横的封锁网,建立了严密的反动统治,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压缩分割,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15)《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12页。。
鉴于当时鄂豫皖根据地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对红二十五军的生存和发展十分关注,多次指示其向外转移创建新根据地。1934年7月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2月12日的指示和中央及军委6月13日《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训令》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但同时也提到‘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的问题。”(16)《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06页。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还指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红二十五军发展的具体指示。程子华回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周副主席讲如何建立新区时指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该有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17)《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实施了外线作战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军事行动。程子华回忆,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同意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向东、南、北都不合适,向西比较容易发展。西面鄂豫陕边是三个省的边缘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里又是山区。会议还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18)《程子华回忆录》,第71页。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部队行进的沿途,经过认真勘察和调查,很快了解了伏牛山区的情况,认为该地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这一带为豫西‘内乡王’别廷芳的势力范围,反动统治严密,盗匪出没无常,凭险据守的地主围寨很多,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都比较困难;加之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相继追来。红军难以在伏牛山区立足发展。因此,省委决定继续西进,准备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19)《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27页。。
红二十五军领导层认识到在伏牛山地区难以创建新根据地后,继续率部向西行军,最后转战抵达陕南地区。在陕南地区,红二十五军和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部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红二十五军入陕也使杨虎城及其部属感受到了压力和冲击,如何处理与红二十五军的关系,成为摆在杨虎城面前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棘手难题。
红二十五军入陕后与杨虎城部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今陕西洛南县铁锁关击败当地民团阻击,进入陕南境内。这时陕军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二五二团已赶至陕西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正面堵截红二十五军入陕。当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陕军二四八团三营凭借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阻击。(20)《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1935年初,杨虎城由城固向东巡视,由张汉民率警卫团护送。“此时,红二十五军由豫入陕,杨即令警卫团堵击。”(21)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0页。随即,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四十四师一三○旅三个团,配合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等部,对红二十五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企图趁红二十五军立足未稳时对该部予以歼灭。陕军积极参与了“围剿”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红二十五军反“围剿”亲历者刘震回忆:“一月下旬,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向我逼近。”“三月八日,我军进到洋县华阳镇。这时,敌警二旅尾追而来。”(22)《刘震回忆录》,第56页。“三月下旬,我军主力东返葛牌镇。陕军警三旅紧追不舍。”(23)《程子华回忆录》,第86页。但是,杨虎城所部陕军在“围剿”过程中也遭受重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击溃陕西洛南县铁锁关守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随后又在该县三要司歼灭陕军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2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275页。1935年2月1日,陕军一二六旅追击红二十五军至蔡玉窑时,突然遭受打击,被歼灭一个多营。5日,红二十五军又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文公岭高地,再歼该旅两个多营。2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消灭了守城的保安队”。3月10日,陕军警二旅遭遇红二十五军伏击,被打垮五个多营,伤亡二百余人,被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名,旅长张飞生被击伤。(25)《刘震回忆录》,第56页。
红二十五军入陕,逐渐打破了杨虎城与中共、蒋介石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杨虎城“与蒋介石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依附蒋介石发展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同情共产党,引用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杨虎城曾对身边亲近的幕僚表达过自己当时矛盾的心情:“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以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26)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为了应对红二十五军入陕造成的政治和军事紧张局面,杨虎城表面继续“围追堵截”和“跟踪追击”红二十五军,私下里积极谋求与该部“接触”,希望与其达成一定程度合作,进而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存陕军实力。
二、“九间房事件”的发生
张汉民是中共陕西地下党员,长期担任杨虎城部中级军官,受命参与“围剿”入陕红二十五军后,名义上执行“尾随追击”红二十五军任务,实质上则对红二十五军暗中进行保护和帮助,并与红二十五军订立了避免军事冲突的“约定”。但是,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部“尾随”红军队伍抱有高度戒备和怀疑,加之“交往”过程中又发生过一些误会,更加深了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的怀疑,最终决定设伏歼灭该部。张汉民则过于自信与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约定”,未能保持必要警惕,对屡次出现的军事险情疏于防范,最终在柞水九间房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而被俘。
张汉民率部“尾随追击”红二十五军过程中,积极谋求与该部取得联系。在陕南商县杨家斜地区,张汉民部与红二十五军开始接触。“红二十五军由豫入陕,杨即令警卫团堵击。张率警卫团到达杨家斜时,红二十五军驻扎在河南,警卫团驻扎在河北,双方隔河对峙,并未交火。张汉民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二人去红二十五军联络,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并规定了联络口号:‘瞄不准不打’。”“红二十五军在杨家斜住了六七天,又速去湖北。警卫团一直‘尾随’到漫川关,相行数日,彼此相隔一日行程,从未交火。”(27)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0-251页。红二十五军离陕后,张汉民部与红二十五军脱离接触,失去联系。红二十五军再次由湖北转战陕南后,又与张汉民部发生接触。1935年2月中旬,“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在进驻商县、山阳的敌四十军一一五旅配合下,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为了掌握主动,又南下郧西地区”(28)《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38页。。随后,张汉民警卫团也撤回,于2月27日抵达镇安休整,并奉命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29)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1页。
张汉民在继续“尾随”红二十五军过程中疏于必要的军事防范。“警三旅正在进行整编时,红二十五军再次入陕,并以神速的行动,在华阳、茅坪地区消灭了警二旅,尔后向东运动。”(30)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1页。此时,西安绥靖公署发出“堵剿”红二十五军的部署命令,并令张汉民旅参加堵击。张汉民接到“堵剿”命令后,即派人给其部下警三旅九团团长阎揆要送信,指示阎把西安绥靖公署发来的“堵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部署电报亲自抄了一份,并说明联络暗号仍然是“瞄不准不打”,然后派人送往红二十五军。张汉民还写信给阎揆要,称派去送信的人“已去红二十五军几次了,比较熟悉”。接着,张汉民即率七、九两个团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张汉民自信与红二十五军之间的“协定”与默契,因此对频频出现的军事险情缺乏必要警惕。4月7日,张汉民率部进抵蔡玉窑时,随行的阎揆要“发现送情报的两个同志没有回来,有些疑心”。就在这一天,阎揆要获悉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汪锋由西安发来的电报,“说他已由上海回到西安,即动身来会我们”。因此,阎揆要为安全考虑,即向张汉民建议等汪锋到后再行动。但张汉民认为:“我们同红二十五军已来往数次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相随也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不会有问题,仍决定按计划继续‘尾随’前进。”8日,部队到了曹家坪。这时,张汉民派往红二十五军送情报的两个人还没有回来。部队继续行军时,阎揆要查看当地地形,发现“两面是森林高山,中间是一条沟”,考虑部队在沟里行军不利,“于是向汉民建议,要继续前进,可以走北山,不要在沟里走”。但是,张汉民“非常相信红军不会违约,同时感到部队有很多牲口,在山上不好走,仍决定在沟里行军”。9日,张汉民部继续向目的地九间房进军。阎揆要团担任前卫。“离九间房还有十几里路时,尖兵连(七连)报告,村里没有人了。”阎揆要“根据红军作战常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法,提请汉民注意,但他仍认为不会发生问题,要求部队继续前进”(31)阎揆要:《九间房事件》,《丹心素裹》,第258-259页。。这样,张汉民及其部属逐渐开进红二十五军已经严阵以待的伏击地九间房。
其实,张汉民近距离“尾随”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引起红二十五军领导层的高度警惕。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本身带有浓厚的肃反意识。在转战中,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在内部不断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掌握肃反大权的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直到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遇害。(32)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1934年,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要加以处理,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才使郭述申免遭杀身之祸。此外,红二十五军“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是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33)徐海东:《生平自述》,第39-40页。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之时,红二十五军虽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但还关押着三百多名跟随部队转战到陕北的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和战士。(34)徐海东:《生平自述》,第47页。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自己的干部战士尚保持如此高的警惕态度,对张汉民部紧跟“尾随”更怀有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决定伏击张汉民所部“尾随”部队。张汉民与红二十五军在接触过程中,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多次产生误会。在商县杨家斜,红二十五军提出要警卫团帮助解决电台、军用地图和医药。张汉民根据红二十五军的要求,曾写信给其所属三营营长阎揆要,指示阎把地图交给张明远等联络人送给红二十五军,并根据红二十五军要求,派王超北去上海、西安购买红二十五军所需的电台和药物。随后,阎揆要曾两次派人给红二十五军送药,均因红二十五军驻地不定,未能送到。(35)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0页。这些被红二十五军领导层视为“违约”的行为,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与其联络的动机更为警惕,对张汉民的政治身份也“更加怀疑”。(36)郑位三:《红二十五军同陕西地下党联系中的两件事》,《丹心素裹》,第267页。而且,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不停“尾随”的目的也产生了戒备。张汉民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络的人员在吴焕先和戴季英的审讯下,招认张汉民曾积极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并因“剿共”有功而由团长晋升为旅长,“从此张汉民退出共产党,加入法西斯蒂”。此次红二十五军入陕,张汉民积极“尾随”,目的为“积极消灭红军,继续报功”。(37)徐文伯:《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6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笔者认为,这份供词极有可能是张汉民所派联络代表受到吴焕先、戴季英刑讯逼供而供出的假供词。但是,这份供词不能不对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在处理张汉民问题上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期间,“张汉民旅追击红二十五军很紧,使部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为了保存革命的动力,使红二十五军不受损失”,红二十五军领导层最后决定“坚决打一仗”,并决定在九间房设伏,消灭张汉民所部追击部队。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当时还留了一个余地,如果张汉民真想消灭我军,继续尾追,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如果不再追来就算了”(38)徐文伯:《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革命史资料》第6册,第250-251页。。但是,张汉民率部“跟踪追击”过程中却没有对频繁出现的险情有所警觉,也没有听从部属阎揆要等的提醒,而继续“尾随”红二十五军至九间房。
最终,张汉民部在九间房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损失惨重。1935年4月9日,“当部队到达九间房正准备宿营时,忽然山上枪声、手榴弹声骤起。张汉民即与阎揆要商定,快向西撤,并令阎揆要率队先撤。由于红二十五军三面包围,警三旅很快被打散,大部分人员被俘,只有少数官兵沿来路撤回。当晚,阎揆要在曹家坪收集七、九团撤回的官兵,10日回到蔡玉窑。”(39)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2页。正在此时,代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恢复与其已经失掉联系的红二十五军关系的中共中央军委特派员汪锋(40)《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突然赶来积极营救张汉民。(41)汪锋:《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丹心素裹》,第263页。汪锋由西安到达蔡玉窑,遇到从九间房幸免被俘撤回来的警三旅军官雷展如。雷告诉汪:前方失败了,张汉民可能被俘了。汪锋立即启程前往九间房寻找红二十五军,营救张汉民和其他被俘人员。但是,当汪锋见到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徐海东、戴季英等,经过一番交流后,并未实现解救张汉民等的目的。随后,“戴季英带4个战士把汪锋绑起来,没收了东西。说汪是反革命。汪在红二十五军管辖下,经过几个月的游击生活,于1935年农历八月十五日(9月12日)进到陕北苏区,接着又第二次进了监狱,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苏区,汪锋才被释放出来”(42)汪锋、阎揆要、雷展如:《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丹心素裹》,第252-253页。。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间房事件”。
“九间房事件”后,在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审讯俘虏的过程中,张汉民“说明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说明了军中一百多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说明了与中央军委、陕西党组织、西安党组织及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的联系。许多共产党员也站出来作证明。但是,令张汉民至死也想不明白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和他的一大批战友被红二十五军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他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二岁”(43)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13页。。虽然张汉民在陕南杨家斜已经被误杀(44)汪锋:《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丹心素裹》,第265页。,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却并未因此而终结,而是在随后发生的“陕北肃反”中又掀波澜。
三、“张汉民事件”的影响
“张汉民事件”对后来中共在西北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该事件造成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产生了负面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陕北肃反”。另一方面,该事件促使杨虎城加强了对红二十五军的“围剿”力度,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关系。
“张汉民事件”成为“陕北肃反”发生的重要诱因。“张汉民事件”造成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中共陕西党组织、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印象和成见。1935年7月17日,时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民国〕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陕西党内、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中都有他的布置)。陕西党的领导机关在此种分子中。”“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斯分子。”报告还强调:“我们不是神经过敏,污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不深入、不刻苦下层劳动群众的工作,尽是上层阶级的活动。”报告还紧迫地提出:“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45)《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21页。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46)郭述申:《陕北“肃反”的一点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第5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西北高干会期间,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致电任弼时及中共中央表示:“二十五军陕南处决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他有不少学生在二十六军,这是我、徐、郭、戴对二十六军内部混入反动动摇分子,已有成见。”(47)《程子华同志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11页。在西北高干会上,原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在会上发言也承认:“二十五军的同志认为张汉民是叛徒右派反革命,认为他说的与西安市委和陕甘党有关系,也就是右派反革命关系。我们就认为‘陕甘有问题’,这样预先成见。”(48)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04页。“张汉民事件”造成红二十五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后积极支持“陕北肃反”。1935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为解决西北根据地存在的所谓“严重问题”,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加强领导、解决问题。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虽然通过各种途径发现了西北根据地所谓的“严重问题”,但是手中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尚不能在西北苏区全面推行肃反。正在此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北,并且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明确告诉朱理治:“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49)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15页。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迅速改变了西北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朱理治、聂洪钧等要开展肃反,不但有了理论支持、政治基础,而且拥有了有力的军事后盾。红二十五军对“陕北肃反”事件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朱理治回忆:“恰在此时,25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即张汉民——引者注)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17路军警卫旅旅长,红25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许多人到26军。因此,又怀疑26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25军过去和陕北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50)《往事回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页。
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肃反的支持态度是“陕北肃反”发动的重要组织基础。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人在“陕北肃反”期间大都担任西北根据地重要领导职务。为了进行肃反,朱理治等从组织上对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调整。原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干部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人都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重要领导职务,成为“陕北肃反”发动的重要依靠力量。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永坪,与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党政军领导人朱理治、刘志丹等胜利会师。永坪会师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51)再次使用该名称,除直接引用外,一律简称“中央代表团”。成立,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中央代表团是中共在西北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干部在永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主要决定有: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兼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通过上述组织调整和人事布局可以看出:西北根据地改组后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务由中央代表团的三人担任,程子华任军团政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朱理治任省委书记”(52)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00-102页。。另一个重要职务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也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担任。这种人事安排,带有对原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明显的政治怀疑和组织排斥意味。正如朱理治后来就“陕北肃反”问题检讨时所讲:“红二十五军来了以后,徐海东做军团长,刘志丹做副军团长,聂洪钧做军委主席,程子华做政治委员,高岗做政治部主任,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53)朱理治:《我到陕北后的错误》,《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第5卷,第270页。朱理治的检讨明确表明,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朱理治等倚重红二十五军力量,将刘志丹、高岗等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排除在新的党政军核心领导圈之外,削弱西北红军在红十五军团和西北根据地的力量和影响。“红二十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它也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指令。他们长征来到陕北,带来了好经验,好作风。同时,也带来了错误处理张汉民的‘左’的材料,带来了对陕西党、西安党和红二十六军的严重的不信任。而这对于已经处于矛盾之中的西北党内关系,起到了进一步催化和恶化的作用。”(54)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11页。
由于受“张汉民事件”影响,红二十五军部分主要负责人不同程度介入了“陕北肃反”事件。曾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的戴季英在“陕北肃反”上责任重大。戴季英在审讯因“陕北肃反”遭到逮捕的所谓嫌疑人过程中经常使用肉刑,“不承认就吊起来打,打昏了用冷水喷醒”,继续拷打,严刑逼供,指名问供。(5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戴季英甚至还亲自动手毒打受审者。(56)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在西北高干会检讨“陕北肃反”问题时,戴季英在会上发言:“鄂豫皖肃反错误与陕北肃反错误实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带来了张国焘路线肃反错误经验,二十五军领导上要负责任,我应负大的责任,我运用了这肃反错误经验如严刑逼供、指名问供等。”(57)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04-405页。程子华受“张汉民事件”影响,对“陕北肃反”也持积极态度。西北高干会期间,程子华致电任弼时及中共中央表示:“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来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直到“中央对陕北之肃反问题决定发布后,我始认为错了”(58)《程子华同志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3页。。程子华对“陕北肃反”持积极态度,从知情人郭洪涛在西北高干会上的发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我到前方后,首先见程子华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高岗、刘志丹最大不过是封建集团,私人结合,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程子华的态度就很坚决,说他们是反革命。”(59)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09页。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作出的处理“陕北肃反”决议《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60)该文件名后来在有些著作和文章中有时也被写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等不同名称,实为同一文件。也指出:“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翰(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61)《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62)《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8页。
“张汉民事件”还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部的联系。“张汉民事件”造成杨虎城对中共政治态度有所疑虑。据杨部军官陈子坚回忆:
孙蔚如部被调到汉中防共后,杨将军为了不和红军打仗,乃密派参谋武志平与红军在川北部队订立互不侵犯协议,并帮红军购买药品和其它物资。以后红军徐海东由河南进入安康地区,蒋介石严令杨将军派兵堵击。杨将军在形式上不能不派兵应付,乃派警一旅唐子封部和警三旅张汉民部进入秦岭。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杨将军面嘱张汉民要尽可能找到红军指挥员,商订互不侵犯协议或打假仗,以达到不与红军作战之目的。但张汉民没找到与红军指挥员的关系,与唐子封一样,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而处死。杨将军对此思想上感到非常苦闷,他是一向拥护三大政策并在他部队使用和信任共产党员的,至此他不知共产党近来是什么政策而困惑不安。(63)陈子坚:《对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回忆》(1985年5月25日),《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65页。
“张汉民事件”强化了杨虎城对红二十五军的“围剿”力度。1935年4月,杨虎城统一指挥所部陕军以及入陕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二十五军发起第二次“围剿”。杨虎城在此次“围剿”过程中动用陕军重兵,先后投入“陕军三十八军四个团、警一旅两个团、警二旅两个团,特一旅两个团”(64)《程子华回忆录》,第87页。。而且,杨虎城部也一改过去避战自保军事政策,积极参与“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给红二十五军的行动造成了一定困难。(65)《程子华回忆录》,第89页。
“张汉民事件”还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后,多次派人员与杨虎城协商建立统战关系,但是“张汉民事件”一直是杨虎城及其部属耿耿于怀的心结。汪锋代表中共中央与杨虎城谈判建立统战关系时,杨虎城即质问:“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66)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丹心素裹》,第296页。据汪锋回忆,杨虎城部领导层如杜斌丞等人也很关心“张汉民事件”:“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67)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丹心素裹》,第300页。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派与杨虎城谈判的特使张文彬,致信毛泽东时也谈及“张汉民事件”:“据杜(杜斌丞——引者注)谈,张汉明(民)原是十七路内认为最左倾的分子,终为红军所杀。又曾一次,渠又派一学生到汉中与张、徐(向前)交涉,亦被杀等事,在十七路中有很不好印象,杨、孙等现在犹恐我方不能遵守信义,深望我方注意。我观察他同我谈的态度均很诚恳。”(68)《张文彬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1936年9月8日),《丹心素裹》,第29-30页。“张汉民事件”使杨虎城长期对中共心存芥蒂:“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69)《杨尚昆回忆录》,第160页。
“张汉民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偶然性。如果张汉民在遇到频繁警情时能慎重处理和提高防备,则不至于多次发生可以规避危局的军事“误判”,或许可以幸免于在九间房地区遭受伏击;如果红二十五军在俘虏张汉民后能详细考察一下张的情况,能接受前来营救张汉民的汪锋的解释和说明,可能误杀张汉民这场历史性误会也可以避免。但是,“张汉民事件”的发生更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当时国共内战方兴未艾之际,尤其是在“围剿”与反“围剿”激战之时,都处在双方阵营交战前列的张汉民部和红二十五军,势必会产生种种“误解”,最终很难避免兵戎相见的结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不能假设的,但是总结历史认识则可以多思考几种可能发生的结局,进而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这样可能会对历史事件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张汉民事件”就是这类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党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