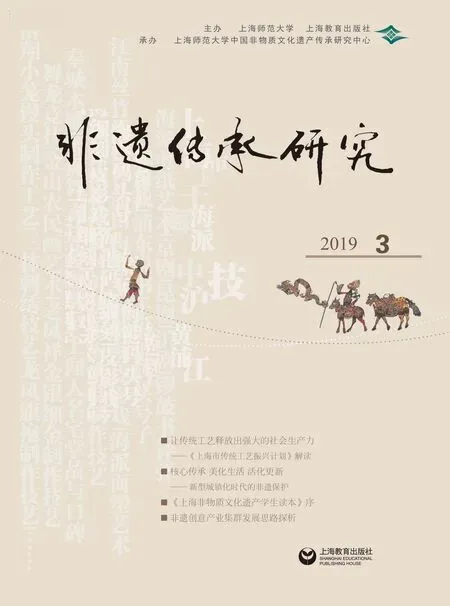非遗保护视野中彝族“梅葛”的活态传承
胡云
一、彝族“梅葛”的文本表述
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文化传统,作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把人类的“口头传统”作为非遗的重要内容和样式进行了表述。史诗“梅葛”作为楚雄彝族最为重要的口头传统,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史诗“梅葛”共5775行,“梅葛”是彝语的音译,意为“口头传唱过去的事情”。整部史诗一共分为四部,其主题分别为创世、造物、婚恋、丧葬。“梅葛”也是一种彝族曲艺曲调的总称,其唱腔颇多,主要有“辅梅葛”“赤梅葛”“娃娃梅葛”“青年梅葛”“老年梅葛”。“辅梅葛”俗称“喜调”,曲调活泼自由,多用于婚嫁和播种丰收等喜庆时节。“赤梅葛”俗称“哀调”,旋律沉郁忧伤,多用于丧葬和祭祀。“娃娃梅葛”的节奏欢快,是大人哄小孩时演唱或是儿童演唱。“青年梅葛”是青年人表达爱情时演唱,曲调欢快流畅。而“老年梅葛”中唱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祖先业绩等方面内容的创世史诗《梅葛》,曲调舒缓,显得庄严肃穆,由毕摩、巫师或老年歌手演唱。
“梅葛”勾画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轮廓,展示了古代彝人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是古代彝族社会的“百科全书”,被在其流传地区的彝人奉为本民族的“根谱”,具有重要的民俗学、文学研究价值。
二、彝族“梅葛”的当下境遇及传承危机
1.民族民俗文化链的断裂与脱节
宗教仪式的消失是史诗“梅葛”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传统的彝族社会普遍信仰原始宗教,毕摩是彝族社会的神职人员,是原始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其灵魂能在天界与人间任意游走,是沟通人与神的桥梁。原始宗教是创世史诗《梅葛》生存的重要土壤,原始宗教仪式如羊神节、祭土主、祭龙、丧葬、婚嫁等仪式场合和与农事密切相关的祭祀仪式,构成了“梅葛”的主要文化传承场。
在过去的马游村,彝人认为葬礼须由毕摩主持仪式,为给亡人指路和安魂,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毕摩去世后,丧葬仪式上吟诵的“赤梅葛”已无人会唱。“梅葛”的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郭有珍,她并不是毕摩,而是一名歌手,并且年事已高。据笔者统计,“梅葛”流传地之一的马游村有各类传承人共58位,这些传承人中年轻人极少,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笔者在彝族地区调查得知,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的神职人员,有些人对此会有敬畏心理不愿学当毕摩。有些人认为“一个家族如果三代人都去做毕摩的话,家里会绝后”,还有些年轻人从小接受学校教育,认为当毕摩、在宗教场合做法事,“都是一些封建迷信活动”,而不愿意当毕摩。现在政府加强宣传和引导,彝族人也意识到这是本民族传统文化,有义务传承下去,村民们也都知晓当传承人享有很高的荣誉。一些彝民,特别是毕摩世家,也会让幼小的孩子学当毕摩,但学毕摩除了要去各种仪式上学做法事外,还要学习难懂的彝文以读懂经籍,领悟其内涵,彝族文化精深繁复,学起来并非易事。而现在的孩子又须到汉族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去学,精力所限,很难学懂、学透,只能是一知半解。
习俗的变化是导致“梅葛”传承危机的又一原因。如在“梅葛”的发源地马游村,当地的彝族在20世纪60年代的婚礼上要演唱“七喷梅葛”和“该磨梅葛”,但这一习俗因婚礼上“退邪神”仪式和“该磨(犁喜田)”仪式的简化而消失了。
近年来,彝族传统民居受到“自建性”破坏,村落中公共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功用。同样在马游村,20世纪80年代前,部分彝族村寨的家庭建有“姑娘房”。“姑娘房”一般是位于正房旁的一间独立小房,少女行过成人礼后会搬到“姑娘房”居住,意味着她可以开始和异性对唱“青年梅葛”,“姑娘房”成为“梅葛”的重要传承场。如今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居多,他们有的从此定居城市,有的攒足了钱回来盖房子,以前具有彝族特色的土基房被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取代。
原始宗教信仰的淡化、习俗的简化和传统民居的损毁,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变化和断裂,是影响“梅葛”传承的重要因素。
2.当前社会生活方式的冲击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昔日闭塞的彝族村寨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彝寨,新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逐渐取代传统观念,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当前社会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得史诗“梅葛”的传承系统遭遇到了危机。
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是导致“梅葛”衰落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马游村逢喜事时,男女老少围坐火塘,边喝酒边唱“梅葛”。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马游村老年人看电视,年轻人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日常闲暇时更多的是发微信,看网络视频。
“梅葛”的演述由神圣性趋向世俗化。过去的人认为“梅葛”具有神性,人们心存敬畏不敢亵渎,关于“梅葛”演唱有很多禁忌。其中的史诗部分,诸如开天辟地、万物起源等内容的传承场域一般是传统节庆和婚丧嫁娶等隆重场合,显得庄严肃穆,由毕摩和老歌手演唱“老年梅葛”。后来的年轻人打破了演唱禁忌,在娱乐场合或火塘边唱述“老年梅葛”,显得较为随意。
当今主流文化与强势文化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正在颠覆彝族传统文化。有些人认为传统代表落后和土气,而城市化的事物才是先进和洋气,很多人的眼光都朝坝区的城里人看齐。服饰民俗方面,年轻人认为传统的彝族服饰穿起来较为繁琐显得土气,只有在重大的节日才会穿上传统的彝族服饰。彝族传统习俗在发生变化,以往约束人们行为的习惯法也逐渐失去了威力。有些家庭认为孩子应抓紧时间做功课,认为唱“梅葛”是贪玩而加以限制。甚至在民族语言上,有些家庭两口子都是彝族,但因受汉族文化影响,担心跟不上学校的教学,孩子一出生就习得汉语而不是本民族的语言,小孩渐渐地不会讲彝话,致使有些彝族村寨的语言有所丧失。2018年8月笔者在云南省罗平县旧屋基彝族乡田野调查时,在对法弯村小学的毛老师访谈时得知,他是现在少有的彝语和汉语都会的老师,即会用彝语和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现在有些村寨,彝语已经失传。但在当年政府举办的火把节晚会上,要求主持人必须用彝话作为晚会的开场,当地彝语失传,只有请毛老师帮忙将汉语翻译成彝语之后,突击练习彝语发音来应付晚会的主持。彝语的失传如今在楚雄并非普遍现象,但周边强势文化的入侵,彝语或多或少处于弱化的状态。而彝族的口头传统必须用彝话讲述、吟诵才会有特色和韵味。一旦语言缺失,“梅葛”将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彝族村寨还面临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笔者2018年8月在云南省罗平县旧屋基彝族乡法弯村田野调查时得知,法弯村小学的学生人数近些年锐减,从200多到现在的40多人,办学规模从以前的幼儿班到六年级缩减到只有幼儿班、一年级、二年级,教师从以前的10人到现在只剩1人。学生人数的锐减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经济发展,有些人读书、打工走出了大山,在城里安家,孩子在城里就读;另一方面是现在村里的单身多,一两百人口的小村寨,单身的有三四十人。据法弯村小学的毛老师介绍,因为彝族交通闭塞,经济条件所限,本村外出打工的姑娘都不愿意再嫁回来。此外,这些单身很多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彝族有些男人性情懒惰,嗜好酗酒,家境甚贫。光棍问题的出现使彝族村寨人口减少,影响了“梅葛”的传承,这其实已成为彝族社会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文化和社会语境下“梅葛”的发展和转机
1.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是“梅葛”传承的内驱力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虽然“梅葛”的唱词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民俗事象也有部分变形或丢失,但作为整个彝族文化生态系统的核心,彝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尚未崩溃。因此,当遭遇主流文化或外来文化强势入侵时,彝人追求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主体地位的信念被激发,探索自发进行本民族文化抢救和保护之路。在“梅葛”流传的群山峻岭间,这里的彝人自称“罗罗颇”“俚颇”。“罗罗”是老虎的意思,“罗罗颇”就是“虎人”。他们自称为“虎”的后代,因为在他们的“梅葛”古歌里,虎是万物的本源,山川河流、树木草地、日月星辰都由虎化生而成。“俚颇”是马缨花的意思。马缨花为彝族人祖之花。彝谚云:“马缨花盛开的地方,有祖灵的护佑。”崇尚万物有灵,这是彝人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生活常态。他们视“虎”或“马缨花”为图腾,并把这些图腾用歌声来传递。所唱之歌,就是被《罗罗颇》和《俚颇》誉为共同“根谱”的“梅葛”。他们说:“罗罗颇会唱梅葛,俚颇会唱梅葛,其他人不会唱,会唱梅葛的才是自己人。”基于此,“梅葛”是表达认同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表述。所以当彝族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冲击、岌岌可危时,会产生彝人身份的失落感,促使彝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走上一条寻找传统文化作为认同表达的文化自觉之路。如1949年后“梅葛”在“破四旧”中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受了冲击和重创,就有人冒着风险偷偷吟唱“梅葛”。比如在“文革”前后十多年间,“梅葛”处于彻底禁唱阶段,民间信仰、祭祀礼仪等被当成封建迷信而被禁止,“罗罗颇”“俚颇”便想方设法让“梅葛”传承,他们以“梅葛”调作为唱腔融入彝族戏剧之中,形成了能登上舞台的彝剧,使它成为彝族群众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享受和政治启蒙。再比如马游村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没有毕摩吟唱“梅葛”,“梅葛”就从神坛逐渐流向民间,被大众偷偷地传唱,在某些祭祀等特定场合,甚至老歌手也可以暂时充当毕摩的角色传承“梅葛”。由此可见,民众的内在需要是“梅葛”在过去和将来重归公共文化体系的根本原因,民众的文化自觉是“梅葛”传承的内驱力。
正因为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在国家将“梅葛”列为非遗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当地的有识之士和彝族的文化精英都曾身体力行地进行传统文化的复兴。如1969年马游村成立了业余“梅葛”文艺表演队。1981年以后大姚昙华和永仁直苴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的插花节和赛装节,在节庆活动中,均保留了原生态“梅葛”演唱内容。1992至1998年间,马游村“梅葛”文化站建立,聘请歌手专门负责“梅葛”传承工作。一批文艺工作者将搜集到的“梅葛”调改编成民族音乐,供马游村的业余文艺队排练。2001年,马游“梅葛”传承基地用房落成,作为“梅葛”文艺队的排练场所。“梅葛”作为彝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集中体现,表征了彝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梅葛”之所以遭遇危机却依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是彝族的民族精神历久不变,彝族的民族凝聚力依然很强大。
2.国家非遗事业的建设发展——“梅葛”作为公共文化的社区保护和传承
在国家非遗事业开展之前,国家文化政策对“梅葛”的保护主要是进行文本的搜集、翻译、整理和加工等工作。随着20世纪50年代采风运动的开展,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搜集民间文学的工作。书面文本《梅葛》就是在这样的采风运动中经加工、整理而出版,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外界所知晓和关注。当时由于理论指导的缺位和时代的局限性,这类书面文本往往因演述语境的失真等情况,存在对口头传统的无意识伤害问题,对“梅葛”保护工作停留在保存层面,属于静态的保护。
随着国家非遗事业的建设发展,各级政府颁布一系列法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公众参与方面,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文化遗产日的项目展示都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梅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迎来了生存和发展的新机遇,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名录。
非遗的保护需落实在特定社区。依照现行体制,县域保护是进行活形态保护、整体保护的较好方式。“梅葛”主要是在永仁县的直苴村、大姚县的昙华村、姚安县的马游村、牟定县的腊湾村流传,这些彝族聚居地形成了自然的文化社区,共同享有口头文化传统,“梅葛”在这些区域内既有彝人的文化自觉的内在需要,同时与政治体制中的区划呈现出一致性,能够进行立法、行政的制度建设,便于调动公共财政来支持公共文化,使口头传统在当今的学校体制和传统的社会生态中都能够有效传承。[1]
各级政府对彝族“梅葛”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极为重视,除了对《梅葛》文本、音频、视频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工作井然有序开展外,还公布命名姚安马游、永仁直苴及大姚昙华等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梅葛”文化纳入了保护区的长远规划;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具体措施着力保护民间“梅葛”老艺人;从挂牌成立“中国彝族梅葛文化传习所”,定期拨款建立“梅葛”文化站,到建立马游“梅葛”传承基地用房,使“梅葛”的传承和表演有了固定场所;利用“梅葛文化节”“葫芦笙文化节”等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对“梅葛”文化进行推介展示;将“梅葛”传承延伸至校园,聘请演唱艺人到校传授“梅葛”调,推广“梅葛”课间操。“梅葛”被列为非遗进行保护之后,对它的保护有了相对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制度支持,便于调动彝族内外各方力量,使其重归公共文化体系之内,属活态、动态的保护。
四、彝族“梅葛”的创新性发展模式建构
1.“梅葛”的创新性发展需遵循的原则
当下我们进行的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离不开理论原则的指导,结合彝族“梅葛”的处境和具体传承情况,其创新性发展需遵循的原则有整体性原则、活态性原则、本真性原则和创新性传承原则。
任何文化传统都处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下,往往其中某一文化要素缺失,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因此在对“梅葛”进行传承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对其生存空间实施全方位保护,包括宗教信仰、节日民俗、建筑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语言民俗等的关注。“我们只有保护好传统,才会为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看到,越是勇于创新的人,就越是重视传统。一部分人专门负责传承传统,坚守传统。一部分人则负责创新”。[2]
活鱼还要活水养。“梅葛”是活形态的口头文学,它总是随着民众生活的变化而变迁,不能把活态“梅葛”当博物馆的展品一样保存。每走过一个时代,“梅葛”的唱词都会填充这个时代新的词汇和思想,打上这个时代新的烙印,年年岁岁,它也随之扩充自己的内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后来成为规模宏大、影响颇广的史诗。对它的保护也不是越原生态越好,“梅葛”源于生活,就应在生活态下进行创新。彝人作为“梅葛”的创造者、传承者、享有者,具备主动地改造文化的能力。民间文学不仅仅是静态的被保护的对象,还可加以发掘和利用。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振兴地方文化和经济的一种人文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梅葛”进行创造性转化,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能使它成为复苏地方文化和带动地方经济的一种资源,为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2.彝族“梅葛”的创新性发展模式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口头传承的彝族民间文学,“它不断地被民族社区、民众或个人创造、延续、再创造”[3]。例如昙华、直苴彝剧的出现就是对“梅葛”创造性转化的成果,昙华、直苴的彝族在“梅葛”被当作封建迷信被严厉禁止的年代,灵活地将“梅葛”曲调融入彝族戏剧之中以适应政治的需要,得以广泛传播并受到彝族群众好评。动态地看,传统的形式一直处于变动和调节之中。民众会根据实际境况不断变换策略,进行适应性转变。反观过去,我们所要强调保护的传统也许在当时所处的时代即是一种“新事项”和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试图融合旧有的习惯而产生出适应社会新变化的一种“传统”。文化传统的根在民间,民俗生活也在民间。传统文化必须融入民间,使其成为一种自在的生活常态,否则就将失去生命力。
民间文学包含内容广泛,有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对民间文学进行探索和开发实践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现阶段,民间文学的开发模式主要呈现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方面。非物质性方面主要是影视剧、曲艺演出的母本应用和民间文学的出版发行;物质性方面主要凸显在民间文学源地的文化产业。[4]
3.以当今科技为动力,健全保护传承数字化体系
彝族“梅葛”应抓住国家重视非遗数字化的时机,运用数字化技术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运用虚拟现实和可视化展示技术创建史诗演述的虚拟民俗场。采用数字动画与数字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将“梅葛”中的创造天地万物、初始的造物和发明、婚事和恋歌等史诗主题融入进去。将彝族先民盖房子、狩猎和畜牧、农事、造工具等场景进行原始画面再现,实现史诗原型的虚拟再现、知识可视化及互动操作,使人们不再通过枯燥的文字和数据,而是置身荒野之中,调动多种感官,亲历彝族的原始舞蹈和歌谣来了解远古神话的独特内涵,感受彝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利用新媒体技术,搭建史诗立体传播平台,利用多样的数字媒介将“梅葛”文化资源从平面传播转化为交互立体传播,深化史诗文化内涵的传播,使人们得以更大范围地学习、研究、传承和开发利用这一全方位呈现的文化遗产。
4.以产业开发为手段,利用“梅葛”德育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
“梅葛”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应顺应楚雄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道路,深挖彝族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加强“梅葛”文化与相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品之间的连接融合更为明显,小说、动漫、影视剧、游戏等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多重产业链发展路径。第一,打造一部《梅葛》动漫影视作品,“梅葛”由丰富的彝族传统文化元素组成,如天神形象、造天地的创举、老虎化生万物、人类的诞生和灭亡,洪水泛滥和兄妹再殖人类、彝族早期人类的各种发明创造等关键文化元素。“梅葛”的德育资源包括: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影视作品通过综合利用“梅葛”德育资源“寓教于乐”,借助“梅葛”的庞大容量,充分融合彝族的其他传统文化元素,如彝族的传统民居建筑、传统生活用具、古时狩猎、撵山,先民们的恋爱和婚姻等文化主题,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和品德。第二,进行“梅葛”文化衍生品的多元化开发,“梅葛”本为彝语吟诵和流传,可将彝语翻译成多种语言以适应产业化需要。以“创意”为核心,打造出“梅葛”文化创意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甚至国际平台上进行营销。
5.以非遗旅游为契机,打造楚雄非遗主题公园
楚雄地处滇中交通要道,旅游资源丰富。吸引游客的除了秀丽的风光、古朴的小镇外,独具地域特色的彝族民俗对游客来说也颇具吸引力。遗产旅游是一种将非遗作为消费品的旅游形式。通过遗产旅游让民间文学得以流通和传播,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人的讲述与游客的聆听中流动。为避免遗产旅游因盲目商业化而沦为毁灭民间文学的杀手,杨利慧抽绎出为保护民间文学类非遗有重要启发的“一二三模式”,以促进遗产旅游与非遗保护二者的良性循环[5]。我们可灵活运用“一二三模式”,根据楚雄非遗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梅葛”的活态传承。
楚雄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众多,民间文学类有《梅葛》和《查姆》,传统戏剧类有姚安花灯、元谋花灯和彝剧,传统音乐有姚安坝子腔和彝族酒歌,传统舞蹈有左脚舞和老虎笙,节日民俗有彝族火把节,服饰民俗类有彝族服饰,传统医药有彝医水膏药疗法和拨云锭制作技艺。可打造楚雄非遗主题公园进行物质性的园区建造来进行旅游产业开发,通过宣传招徕旅客,从中赚取旅游费用作为盈利渠道。楚雄非遗主题公园模式可以将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民间歌舞、传统节日和服饰、医药技艺等众多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合为一体,从而打造具有参与性、观赏性、娱乐性的旅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