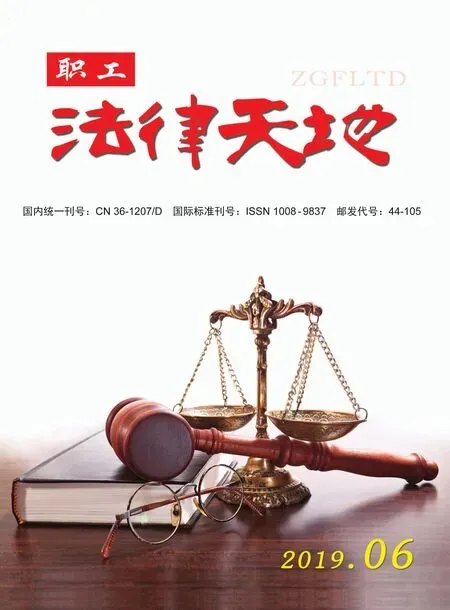漫谈法律经济学研究
陈 丽
(100088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一、在纠纷解决市场上,各种纠纷解决制度均有其存在合理性
了解法律的起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消解、褪去法律和司法机构身上的光环。根据波斯纳的研究,即使是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会有默示的或明示的规范,在一个“还没有出现法律的(prelegal)”简单社会中,如果违反了某个习惯性规范,造成了某人的伤害,这就会激起受害人或其家庭的复仇本能。这种同态复仇模式规范就是最初的法律制度形式。有专门人员来制定和执行规范,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而一旦社会养得起这些人时,也就出现了这种专门人员。波斯纳的这段论述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色彩,其所指的专门人员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构,“社会养得起这些人”的隐含义则是司法机构必然受制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是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限制下回应民众的需求。比如,有限司法资源限定了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制度:两审终审制。如果正义是无价的,那么应该允许无止境地允许当事人上诉。现实的诉讼制度选择显示出司法机构所提供的司法正义是有成本的,一国之审判制度同样遵循经济理性。
波斯纳论述的另一个启示是:从功能上看,无论是由同态复仇制度所支撑的原始习惯性规范,还是现代国家司法机构所使用的正式规范性法律文件,它们最直接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与正义与否无关,而法律和司法机构都只是达成纠纷解决目的的工具。解决纠纷是民众的合理需求,从解决纠纷目标看,司法机构是“纠纷解决市场”的供方和参与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意味着在纠纷解决市场上有多个供方,供方之间应存在有效的充分竞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中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体系;民事诉讼、人民调解和仲裁制度是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三驾主力马车”;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存续资格都取决于其对拟化解纠纷的适应性。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涵盖范围上大于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后者指司法诉讼以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由于司法机关必然是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限制下回应民众的需求,所以司法机关不可能垄断全部的纠纷解决市场,真实情形是各种纠纷解决制度均有其存在合理性。比如一般情况下,调解与诉讼相比对事实真相的查明力度要大打折扣,调解是比诉讼成本更低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向法院诉讼,让法院依据正式规范性法律文件来裁判案件只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调解、仲裁以及其他更广泛意义上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都是纠纷解决市场的供方。民众作为纠纷解决市场的需方,在权衡了各类供方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预算约束之后做出以某种方式解决纠纷的选择。
二、找出真正影响法治效果、法治的成本与收益变化的因素和变量
笔者在前文论证了如欲民众信仰法治,必要法治的收益大于成本方可。这启示我们要找出真正影响法治效果、法治的成本与收益变化的因素和变量,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学等经济学交叉学科大有作为。
比如根据经典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威慑效应取决于预期的惩罚,而预期惩罚等于惩罚的严重性乘以罪犯受到惩罚的概率。由此可知概率是影响法律效果的重要变量。桑本谦教授认为法律制度区分侵权和犯罪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违法行为的破案率远达不到100%,而破案率就是某违法行为受到追究的概率。经济学家艾萨克·埃里奇假定潜在的谋杀者在预期惩罚和预期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谋杀犯罪的预期成本取决于三个变量:犯罪被逮捕的概率(用谋杀犯罪逮捕数除以总立案的谋杀犯罪数衡量)、被证明谋杀犯罪成立的概率(用谋杀犯罪成立数除以谋杀犯罪逮捕数衡量)、以及罪名成立被执行的概率(用总执行数除以总谋杀犯罪成立数衡量)。埃里奇预计以上三个概率与谋杀犯罪之间负相关。类比该研究,一个动态的司法过程,至少包括了对以下几种概率考量:违法行为被起诉到法院的概率、起诉方得到法院支持的概率、违法行为经法院作出生效经判决后得到实际有效执行的概率。困扰司法系统的“执行难”问题的实质即生效判决得到实际有效执行的概率太低。原告空有一纸有效判决,但不能享有实在的利益,长期的低执行概率使得民众对国家成文法律和司法系统的信任消耗殆尽。鉴于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概念遭受了很多批评,经济学界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给予了更多关注。比如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有“心理账户”,人的行为受“锚定效应”、“框架效应”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经历来推断未来的趋势,然而人们对概率判断经常失误,比如低估大概率事件、高估小概率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法律经济学研究使我们逐渐认识到那些真正影响法治效果、法治成本与收益变化的变量,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让我们关注到这些变量在实际上如何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决策过程。与传统法学研究相比,这些经济学研究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法律、法治的认识,也引导我们更有效率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消解了法律和司法机构身上的光环。在经济分析下,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人们某种需求的工具,如同卡多佐所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
——满足与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