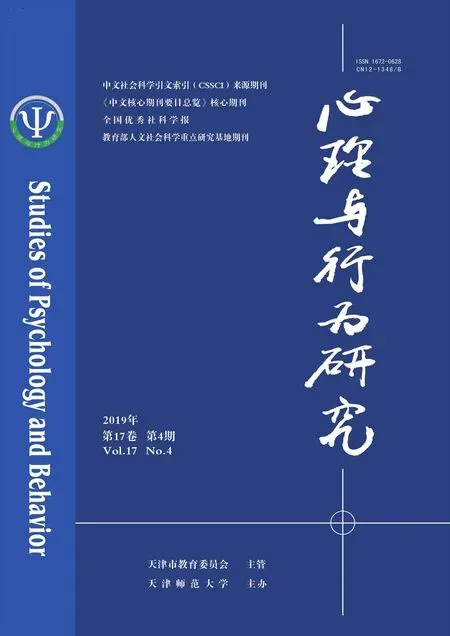双语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
刘 艳 朱 智 马 谐
(1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明 650500) (2 云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500)(3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双语学习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据估计,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会说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语言(Grosjean,2012),在全球化趋势下,双语学习的收益与习得成本越来越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Diamond,2010; Bialystok, 2011)。以往的研究在双语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结果发现双语者在注意控制、抑制控制、认知控制、认知转换和冲突监控上的表现都显著地比单语者要好(Costa, Hernández, & Sebastián-Gallés, 2008;Bialystok & DePape, 2009; Adi-Japha, Berberich-Artzi,& Libnawi, 2010; Prior & MacWhinney, 2010),这些任务都需要执行功能的参与,调控注意资源获取相关信息,并忽略干扰信息(Poulin-Dubois, Blaye,Coutya, & Bialystok, 2011)。双语者长期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需要执行功能选择目标语言并且抑制非激活语言的干扰,由此在执行功能上体现出显著的双语认知优势效应(Bialystok, Craik, & Luk,2012; Costa & Sebastián-Gallés, 2014)。
以往的研究虽然发现了众多双语经验对执行功能起促进作用的证据,但仍有学者认为这种影响具有局限性,对于双语优势效应的存在性目前仍存争议。本文将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综合讨论双语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其次,双语经验影响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虽然前人从多种角度对执行功能中的双语优势效应做出了解释,但现有的理论仍然存在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最后在展望中提倡对双语学习和教育的优化和推广,并更多地考虑其对“热”执行功能的影响;未来还应更多关注双语经验在不同人群中的作用,优化双语教学可以促进更多群体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有利于提升其情绪调节的能力。
2 双语经验与执行功能
2.1 双语者与双语经验
双语者是指掌握两种语言的个体(Nagel,Temnikova, Wylie, & Koksharova, 2015),长久以来,对于如何界定双语者,学界内部一直没有达成普遍共识。有一些定义比较严格,如有学者认为双语者的第二语言应该像母语一样熟练;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双语者只需要能够熟练运用母语,第二语言能够清晰明确的表达交流即可(Hakuta, 1986)。在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分类是根据个体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否达到与个体年龄相当的水平,将双语者划分为平衡双语者和非平衡双语者(龚少英, 方富熹, 陈中永, 2002)。国内外对双语的认知研究很多,证实了双语经验会对个体的脑功能和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对执行功能具有促进作用(Miyake &Friedman, 2012; Kroll & Bialystok, 2013)。
执行功能是以目标导向的行为控制和自我控制中必不可少的认知功能,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和认知发展密切相关(Hughes & Ensor, 2007; Best,Miller, & Jones, 2009)。一般来说,执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认知转换、工作记忆、自我监控和问题解决(Jurado & Rosselli, 2007)。同时,执行功能也可分为“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冷”执行功能是由去情境的、抽象化的刺激材料引起的认知活动;“热”执行功能是由情境性的、情感高度卷入的刺激材料引起的认知过程,在情感决策领域起到重要作用(Zelazo & Müller,2002)。双语经验对“冷”执行功能的影响方面研究众多,主要体现在抑制控制、认知转换和工作记忆三大方面。
2.2 双语经验与抑制控制
最早研究双语经验影响执行功能是从抑制控制开始,抑制控制普遍表现为一种在任务加工过程中,选择和保存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并能无视干扰信息的能力(Botvinick, Braver, Barch, Carter, &Cohen, 2001)。抑制控制通常包括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Robertson, Manly, Andrade, Baddeley, & Yiend,1997)。前者通过注意控制,选择与任务相关的刺激,并忽略干扰刺激来实现冲突解决;后者主要是抑制不符合当前需要的行为反应(Bunge, Dudukovic,Thomason, Vaidya, & Gabrieli, 2002)。干扰抑制的经典范式有Stroop 范式、Flanker 范式和Simon 范式,后期的研究者更多的采用经典范式的变式,如有研究者通过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发现双语者在识别字体颜色方面比单语者更加具有优势(Coderre & van Heuven, 2014)。Bialystok, Craik 和Luk(2008)采用Stroop 范式对青年被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双语者的Stroop 效应更小;青年双语者在Simon 范式中,冲突任务的反应时比单语者要快;中年双语者在Flanker 范式中也表现出了双语优势效应(Emmorey, Luk, Pyers, & Bialystok, 2008)。
除了成年人群体的结果以外,研究者在儿童群体中也发现双语经验会对干扰抑制起促进作用。Bialystok 和Viswanathan(2009)挑选了三组分别生活在加拿大和印度的8 岁单双语儿童,发现双语者具有更高的干扰抑制能力。在幼儿园儿童中,有双语经验的儿童在模糊图像任务上(Ambiguous Figures Task)的得分要比单语儿童要高,重新解释图像需要干扰抑制能力和注意控制能力,这些能力可能在双语儿童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Bialystok, Barac, Blaye 和Poulin-Dubois(2010)利用Stroop 任务对3、4 岁的儿童进行了测验,该任务需要被试抑制非目标刺激,结果双语儿童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控制能力,并且随着语言经验的加深,这种效应更加显著。Poulin-Dubois,Blaye, Coutya 和Bialystok(2011)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让8 个月大的儿童完成图片Stroop 任务,双语儿童的表现显著地比单语者要好。国内学者陶云等人(2015)采用语码切换范式对傣-汉双语小学生在二语切换过程中的干扰抑制能力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双语小学生的干扰抑制能力比单语小学生好。
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者在反应抑制上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双语优势效应,研究反应抑制的经典范式有昼夜Stroop 范式、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和眼跳任务,在反应抑制中,刺激并非如同干扰抑制中一样是互相冲突的,而是需要被试对单个属性做不一致的反应。有研究者发现,在昼夜Stroop 任务中,4~6 岁的单、双语儿童的正确回答次数无显著差异(Martin-Rhee &Bialystok, 2008);另外在停止信号任务和眼跳任务中,无论成年还是儿童被试,其任务结果均未发现双语优势效应(Morales, Gómez-Ariza, & Bajo,2013)。这说明在抑制控制领域,双语经验的促进作用可能只存在于干扰抑制中,这也与双语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两种语言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抑制非目标语言的干扰,而不需要抑制言语表达的行为反应的特性相一致。
2.3 双语经验与认知转换
双语经验还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转换,认知转换是指在不同的任务要求和规则模式中进行转换的能力。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语言切换,可能会需要更高的转换能力。以往对双语者的认知转换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即基于双语的语言转换和基于认知能力的任务转换。由于语言转换的研究主要考察语言转换的流畅性,大部分对认知转换的实验研究都集中于任务转换。在任务转换的研究中,普遍采用转换代价作为衡量个体转换能力的指标。如有研究者发现,低熟练度的二语学习者在简单语言转换任务中的转换代价显著高于复杂语言转换任务(Calabria, Hernández, Branzi, & Costa, 2012)。
虽然有少部分研究者认为双语者的认知转换并没有显著优势(Paap & Greenberg, 2013),但更多的实验结果均倾向于双语者的转换能力优于单语者,如Pior 和MacWhinney(2010)采用线索任务转换范式对大学生被试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双语者在转换能力方面存在优势效应。Hernández,Martin, Barceló和Costa(2013)采用间歇式线索转换任务对西班牙双语大学生和单语大学生的转换能力进行了测验,任务线索分为内隐和外显两种,结果发现在内隐线索的情况下,双语者的重启代价(restart cost)更小。Garbin 等人(2010)利用非言语转换任务对西班牙语单语者和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双语者表现出较低的转换代价。国内的学者利用威斯康辛卡片分类任务(WCST)在汉-英双语者中同样发现了双语者的转换能力存在显著优势(Dong & Xie, 2014)。
双语儿童在认知转换上的表现同样比单语儿童要好,具体表现为双语儿童能够完成维度变换卡片任务(DCCS)的起始年龄更早(Martin-Rhee& Bialystok, 2008),同时在Go/No-Go 任务中,双语儿童不仅得分更高而且速度更快(Engel de Abreu, Cruz-Santos, Tourinho, Martin, & Bialystok,2012)。Kovács 和Mehler(2009)通过有线索提示的转换任务发现,在7 个月大的婴儿中,有双语经验的婴儿可以更快地根据线索调整寻找奖励的方向,这说明即使在婴儿期,双语经验的认知优势效应依然存在。Akhtar 和Menjivar(2012)的研究采用了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imension change card sort task),在该任务中,先前习得的规则会对后续规则转换后的任务造成干扰,使被试变得更加容易犯错误。而双语儿童的错误率显著地低于单语儿童,这说明双语儿童可以更好地将先前的规则转换为新的规则。
2.4 双语经验与工作记忆
双语经验对双语者的工作记忆也有影响,工作记忆是指在任务加工过程中,对信息暂时的保持与操作的系统(Baddeley & Hitch, 1994)。Feng(2009)发现,在数字记忆广度相同的情况下,双语者比单语者的空间位置记忆能力更好,说明双语者能够更好地组织刺激材料以获得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Baker(2013)发现双语经验对工作记忆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其他形式,实验要求被试完成即时回忆测验后5 天进行重测,结果发现5 天后双语者对目标词汇的记忆显著多于单语者,即双语优势体现为减缓遗忘过程。Bialystok,Poarch, Luo 和Craik(2014)对双语者的言语/非言语工作记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双语者仅在非言语任务中有优势,而言语任务的差异并不显著。
在儿童群体方面,有研究选取了3 岁、8 岁和11 岁的儿童完成情节记忆任务(episodic memory tasks),结果发现双语儿童在再认和复述上的表现均比单语儿童要好(Kormi-Nouri, Moniri, & Nilsson,2003)。Morales, Calvo 和Bialystok(2013)利用青蛙矩阵任务(frogs matrix task)发现,5 岁的儿童在工作记忆上依旧存在双语优势效应。Blom,Küntay, Messer, Verhagen 和Leseman(2014)为了分别探测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在视空间记忆和言语记忆方面的差异,采用点矩阵任务(dot matrix)和找不同任务(odd-one-out)对工作记忆的视空间部分进行了探究,并采用正序及倒序数字回忆任务(digit recall/backward digit recall)对工作记忆的言语部分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双语儿童在视空间记忆和言语记忆方面都比单语儿童要好。以往的研究更多是针对学前儿童和中学儿童进行研究,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婴儿期的双语经验和学习,如Brito 和Barr(2014)在18 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现有双语经验的婴儿在模仿行为上要表现的更好。
但是与此同时,双语者在工作记忆上是否存在双语认知优势效应仍存在争议,Namazi 和Thordardottir(2010)选取15 名法语-英语双语者、15 名法语单语者和15 名英语单语者进行了实验,比较他们在言语工作记忆和视觉工作记忆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双语者与单语者的任务得分并无显著差异。与之相类似,Ratiu 和Azuma(2015)在对52 名双语者和53 名单语者的工作记忆容量测验中,依旧没有发现双语认知优势效应。由此我们发现,在对双语经验影响工作记忆的争论当中,现有的研究普遍支持一种观点,即双语经验可能并非直接影响工作记忆的广度和容量,而是在语言切换的过程中,提升了认知操作的能力,从而在更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中体现出双语认知优势。
3 双语经验影响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普遍运用,双语经验影响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正在逐渐明晰,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双语切换和选择的脑区和完成执行功能任务的脑区有所重叠,使得更高强度的双语训练可以增强个体的执行功能(Rodriguez-Fornells, De Diego Balaguer, &Münte, 2006)。如背外侧前额叶是执行功能的核心脑区,个体在完成任务时背外侧前额叶会被激活,同时当双语者对两种语言进行转换和控制时,背外侧前额叶也将被激活(Buchweitz & Prat,2013)。同样在执行功能和双语切换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的脑区还有基底神经节,它在语言加工过程中主要负责控制语言的选择(Ullman, 2001)。执行功能的神经基础即以背外侧前额叶和基底神经节等脑区共同组成的联结网络(Abutalebi & Green,2007),双语者在日常的语言切换过程中,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神经网络得到不断训练,因而使个体的执行功能得到增强。
第二种观点认为,双语经验影响执行功能是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即通过双语训练可以影响个体的神经系统可塑性,从而增强了双语者的认知加工能力。前人的研究确实发现了双语经验对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Mårtensson et al., 2012; Hosoda,Tanaka, Nariai, Honda, & Hanakawa, 2013)。多数研究也发现各种经验,如音乐学习会对相应的神经网络产生显著影响。双语者在日常对话中需要执行功能选择目标语言并且抑制非激活语言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额叶、顶叶尤其是前扣带回皮层(ACC)的激活(Dosenbach et al., 2007)。更多的证据来自于对双语经验可以延缓老年人认知老化的研究,如Luk,Bialystok, Craik 和Grady(2011)利用磁共振技术发现,双语老年人与单语老年人相比,在脑功能尤其是白质组织上存在差异。说明双语者的日常语言转换训练,即高强度的双语经验可以使他们激活更多与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增强个体的神经可塑性,从而在脑功能上增强了个体的执行功能。
第三种观点则更多地着眼于双语者在双语训练的过程中,更高强度的双语经验促进了左右脑的共同激活,从而提高了个体的认知加工能力。如Garbin 等人(2011)发现,在处理非语言的任务转换时,单语者激活的脑区域是右下额叶和前扣带回,而双语者则表现为左下额叶皮层(IFG)的激活增强,该区域也被称为双语神经标签,是重要的语言加工区域之一,它的激活增强说明双语者在处理语言任务时需要更多认知资源,并带来更大的认知负荷(Kovelman, Shalinsky, Berens, &Petitto, 2008)。Hull 和Vaid(2007)发现,不同的熟练度的双语者,其大脑进行语言表征的区域有所不同。先天双语者,即6 岁之前学习第二外语的个体,其语言表征的脑区呈现双半球分布,而后天双语者,即6 岁以后学习第二外语的个体,其语言表征为左半球控制。上述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可以增强个体的左右脑交流,进而促进双语者的执行功能,使双语者在任务加工过程中更有优势。
虽然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持质疑态度,如现有研究仅仅证实双语切换和选择的脑区与执行功能的脑区有所重叠,但并不是完全重合;并且脑区的重叠并不能确切说明存在促进关系,脑区重叠的程度还与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有关(Abutalebi & Green, 2007)。其次,关于双语者脑的左右半球同时激活的解释,可能并非由于双语经验存在促进作用,而是因为儿童期个体的脑可塑性最强,而到了青春期以后,个体的脑可塑性降低,需要其他脑区协同合作,才能完成语言信息的加工。最后,现有研究的证据大多来自于已经具备表达能力的双语者的脑功能变化和行为学结果,对于年龄较小无法表达的婴儿则较难使用脑成像技术加以研究。
4 总结与展望
第一,双语教育和双语经验对于个人信息加工能力的影响是近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前人的研究发现双语经验确实会对执行功能产生影响,但其结果仅限于对“冷”执行功能的探究,如大量来自于抑制控制、认知转换和工作记忆的研究证据。执行功能除了“冷”执行功能外,还包括“热”执行功能。“热”执行功能即由情境性的、高度情感卷入的刺激所诱发的认知过程。“热”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Wagner et al., 2010; Rößner et al., 2017)。情绪调节是一种抑制、加强、维持和调整情绪唤醒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Eisenberg & Spinrad,2004),情绪调节能力对个体的人际交往、社会适应、学业水平和人格发展起到重要作用(Rydell, Berlin, & Bohlin,2003; Denham et al., 2011)。尽管如此,以往研究对“热”执行功能的关注却普遍较少。增强双语教育和教学是否可以有效促进个体的“热”执行功能,并对其未来的情绪调节能力带来有益影响,是我们亟需解答的问题。
第二,进一步探究双语经验对工作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对情绪背景下的工作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既然双语经验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并非由于其直接对记忆的广度和容量进行提升,那么在刷新功能上,双语经验是否会存在优势效应,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刷新功能是工作记忆系统中用于处理信息的核心功能,它是指根据新呈现的信息不断更新工作记忆内容的过程,其主要作用是监控输入的信息,用与当前任务相关较大的新信息来替换与当前任务联系不大的旧信息,以不断对记忆中的内容进行修正(Hamann, 2001)。情绪背景下的工作记忆刷新加工是相对于单一工作记忆刷新加工更为复杂的认知操作,与个体的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关联。已有学者对双语经验影响儿童在情绪背景下的记忆刷新做了探究,但是没有发现显著的结果(Janus & Bialystok, 2018)。可能的原因在于,该研究选取的8 ~ 11 岁被试,对情绪冲突可能更多地采用认知再评价等认知策略来调节,并且双语经验对抑制控制的促进作用在儿童早期最为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神经系统的成熟,促进作用会减弱(Landry, 2011; Bialystok, 2014)。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研究从行为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探索双语经验对情绪背景下的工作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机制。
第三,双语经验作为影响执行功能的重要因素,提倡和优化双语教育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双语经验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受到人群差异的调节,如儿童群体和老年群体。以往的研究对儿童群体的探讨,实验范式集中于延迟满足任务,实验类型更多地采用行为学实验,而较少探究具体的神经机制等问题。儿童群体固然由于其特殊性,数据收集较为困难,但是,双语学习的关键期(5~9 岁)和执行功能的关键期(3~6 岁)都处于儿童早期阶段(Hernandez & Li, 2007; Yeganeh,2013)。早期的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执行功能的发展(Yang, Yang, & Lust, 2011; Calvo &Bialystok, 2014),国际学者在双语经验对儿童脑认知功能的影响,以及如何优化双语教学、培养双语儿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Petitto, 2009;Garcia-Sierra, Ramírez-Esparza, & Kuhl, 2016; Jasińska,Berens, Kovelman, & Petitto, 2017; Arredondo, Hu,Satterfield, & Kovelman, 2017)。反观国内,在儿童的早期双语教学上较少将心智、脑与教育相结合,我国学者陶云、马谐、刘艳和俞先茹(2017)探究了教学模式对傣-汉双语儿童汉语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双语双文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傣族儿童汉语的学习。综上所述,在现有双语教学的基础上,着重关注不同教学模式和双语教学对儿童的学习能力和“热”执行功能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增加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度,进一步深入双语学习对延缓脑老化和促进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加深的情况下,如何延缓老年群体的认知老化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长期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可以提高大脑可塑性,如有学者发现,在知觉转换任务中,老年双语者的表现要比老年单语者要好(Gold,Kim, Johnson, Kryscio, & Smith, 2013)。除此以外,第二语言学习还可以推迟阿尔兹海默症的临床症状(Mortimer, Alladi, Bak, Russ, & Duggirala,2014)。这说明老年群体进行第二语言学习,不仅在促进认知功能、提高执行功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还可以促进脑结构和神经可塑性的发展,对于防患疾病也有重要意义。目前,在“热”执行功能领域,对于老年人情绪调节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未来应着重探究第二语言学习对老年群体“热”执行功能促进作用的研究。
第五,在双语经验促进“热”执行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及双语学习对特殊人群的治疗作用。如前人的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个体在“冷”执行功能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热”执行功能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在情感决策任务和抑制反应任务上的表现较差,这说明有人格障碍的个体可能在认知加工和信息处理上与正常人无异,而在情绪调节和抑制控制上有严重问题(Fitzgerald & Demakis,2007; Swann, Lijffijt, Lane, Steinberg, & Moeller,2009)。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成瘾者(如酒精成瘾、药物成瘾和网络成瘾)在执行功能上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行为的关键,他们普遍在抑制控制上存在问题(Dong, Lu, Zhou, & Zhao, 2010)。双语经验可以使个体的脑区结构发生改变,尤其是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等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脑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系统有效的双语学习和教育帮助有行为抑制障碍的个体,促进成瘾和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