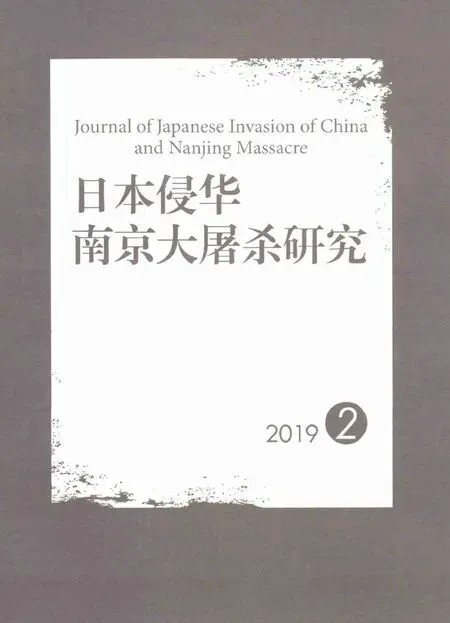附庸帝国:“自闭式”民族主义与“内向型”社会
[美] 酒井直树 王晓阳 译
毫无疑问,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决定日本人民与东亚其他民族交往的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在冷战和“美国治下和平”时期,日本享有所谓“附庸帝国”的地位。得益于此,相较于那些曾遭受日本军事统治或曾屈从其殖民统治的民族,日本民众期望享有某种模棱两可的特权。在“美国治下和平”这一时期,日本现代化是最受日本民众欢迎的话题。毋庸置疑,现代化的沿革对日本国家在想象他们与其他亚洲(以及西方)民族关系方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冷战期间日本的现代化。
一、明治维新150周年
50年前,我在东京读大学时,日本大众媒体热烈庆祝了明治维新100周年。所有的主流报纸都用大量的篇幅刊登历史学家和工业领袖的文章,以及对资深政治家和文化评论家的采访,探讨日本现代化国家100周年纪念的意义。百年庆典被看作是对亚洲最卓越成就的庆祝,当时几乎每个日本成年人都为此感到骄傲。1968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明治维新标志着百年辉煌的开始,这些成就使日本向世界开放,并最终为日本列岛的居民带来了现代文明。此外,它还催生了被美国现代化理论拥护者誉为“日本社会是整个亚洲唯一真正的现代化社会”的理论。
当然,对于这种过分自鸣得意的评论也存在一些争议。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甚至强调,农民必须经历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生活条件,否则,现代化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永远不会在日本发生。而其他相关人士毫不犹豫地提醒日本民众,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农村社区,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持续遭受着环境污染的困扰。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对于明治维新和随后的复兴,日本民众的兴趣骤减,这一点令人震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对日本的现代化不再如此感兴趣了?1968年到2018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治维新经常被描述为日本向现代世界开放的事件。在此之前,从17世纪初开始,幕藩政体(幕府—大名联盟)的外交政策被描绘成“锁国”政策,意为“一个封闭的国家”。直到1868年德川幕府垮台、新的中央集权主权国家成立时,日本才向世界开放。然而,“国家”(“锁国”政策中的“日本”)的含义却远未明确。首先,幕藩政体绝不能与一个民族国家,即现代化国际社会成员的基本概念相提并论。用现代国际政治的术语来说,日本列岛的居民既不是集体地构成一个被主权国家统治征服的统一族群,也不单独接受任何中央当局的管辖。在这方面,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列岛上没有一个国家。严格说来,日本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外封闭;它不是一个有明确领土和标志的族群的政治实体;从地理位置上讲,几乎不可能分辨日本内部在哪里结束,以及外部是从哪里开始的。[注]The absence of clearly bounded territory gave rise to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the subsequent history. For instance,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Hokkaido, except for the southern tip, was not integrated into the Baku-Han System. After 1868, it had to be colonized and its inhabitants brutally subjugated.同样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如何界定一个把自己视为日本人而不是外国人的国民。
1868年,日本政府建立了现代主权体系,宣布自己是唯一的司法权力机构,并由作为整个日本领土的最高统治者明治天皇领导。换句话说,新的日本政府声称,它的领土主权体系可与英国和法国等现代化国家相媲美。当然,被欧洲国家承认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动机,是为了避免日本被其他现代国家殖民。一些日本知识分子非常清楚中国清王朝和西方列强之间发生的冲突。
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整个东亚地区,明治维新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日本首次以一个领土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并宣布其外交政策不是按照“中国中心主义”的附属国协议,而是遵循“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体系——《欧洲公法》。在太平洋西岸,日本可以说是唯一能够理解国际法、理解“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国家间外交政策的政治意义,以及理解国际法基于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国家。而日本的邻国——中国清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却拒绝理解现代国际社会的这些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是东亚少数几个逃脱欧美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至少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如此。
回溯1968年,这一年是明治维新发生100周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随后的现代化进程是积极的,他们为自己这一非凡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对日本过去持肯定态度的(尽管日本实行殖民主义并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背后,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优越感。日本民众相信,在东亚,只有日本成功地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和高效的官僚机构。他们从中吸收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与欧美国家竞争,从建立高标准的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平这一点来看,日本有别于亚洲其他国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仍然是非常贫穷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权,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其仍然可以享有帝国的地位。日本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自鸣得意的优越感最能体现在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坂上之云》[注]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Tokyo: Bungei Shinju, 1999) was serially published in the Sankei Shimbun, a right-wing tabloid from 1968 through 1972.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Clouds Above the Hill by Juliet Winters Carpenter, Andrew Cobbing, and Paul McCart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中。 故事发生在明治时期,主要讲述了在四国松山藩长大的三个男主角的故事。小说体现了日本人对现代化的决心,也彰显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体所进行的努力。这部小说不仅通过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两次胜利,唤起了日本在跻身世界一流强国取得辉煌成功的集体记忆,而且还唤起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亚洲具有现代化象征的民族时所产生的欣喜感。
小说的书名概括了当时日本人对国际社会的积极看法。《坂上之云》勾勒出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民众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当他们挣扎着在陡峭向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时,他们看到了上方模糊而抽象的理想。在山顶上有一些目标,就像遥远的云彩一样,只是以某种抽象和虚幻的形式呈现。这条路是陡峭的,但无论到达山顶有多么困难,一旦旅程开始,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些云不仅在他们的头顶上,而且还在他们的国家之上,它们悬挂在一些被称为“西方”的外国土地上,一个只有外国人居住的遥远地方。想要触及到云彩,他们必须向外看,冒险进入外面的世界。当然,这是现代化最典型的象征之一。
没有比“上升之路(坂)”的更好的比喻了,它示意性地代表一种典型的现代历史感:在山上的云层里,历史被理解为一个连续的线性推进的过程,在其中,每个人都注定要前行。这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中特有的一种历史观点,在这个逻辑中,你要么领先,要么落后于别人,一段历史总是以进化和竞争的形式出现。司马辽太郎不允许历史的时间长河有其他不同形式的呈现,日本读者也不想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想时代的变迁。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非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落后于现代化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按前进或无止境提升的规律组织起来的。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他们完全接受了历史直线发展的规律。因此,现代化进程毫无疑问地被解释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演变过程。
日本民众对这一历史时代的蓝图坚信不疑。由于有此信念,正如司马辽太郎所描绘的那样,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被认为是乐观和外向的,他们不仅对自身未来充满好奇,而且对外国、其他文明和整个世界也充满好奇。从明治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日本的年轻人象征着对外部世界具有强烈求知欲的一个群体,渴望体验异国和未知世界的欲望——这一信念赋予了年轻人某种威望。因此,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是日本年轻人的“神话”形象的表现。1968年,这个“神话”还充满着生命力。
当然,这一模式不能独立于现代国际社会进行讨论,这是一个由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对话构成的世界[注]Stuart Hall,“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Modernity-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London: Blackwell, 1996,pp.184-227.,在这个世界中,西欧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而全球其他地区则被视为欧洲国家殖民征服的成熟“处女地”。在明治时期,日本加入了这个等级有序的世界。《坂上之云》对日本民族来说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他们在没有被欧美国家殖民的情况下成功地加入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获得了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殖民领土,而不是被殖民列强所征服,并加入了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行列。在1968年,这种对日本现代化的描述可以激起日本民众的极大热情。
到20世纪60年代末,绝大多数日本人承认,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积极的,他们为自己这一非凡的成就感到自豪,尽管日本战后的成功只有在“美国治下和平”的情势下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对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它仍然可以享有帝国的地位,成为“附庸帝国”。在生活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方面,日本与其前殖民地之间存在着典型的殖民统治时期的差距。
由于政策的变化,即20世纪40年代末“失去中国”后启动的所谓“回归进程”,美国恢复了日本作为东亚战略中心的地位,并赋予日本一系列帝国或殖民职能,从而促进和维护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建立的跨太平洋共谋,进一步发展成为帝国的分工制度,日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殖民的专长被用来管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可以充当“附庸帝国”的角色。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一历史的转义词(非字面意思),就转义而言,各种各样的过去和未来的集体经历(最重要的是民族经历)被相互展现和叙述,并以某种连贯叙述的方式被接纳。就其所涉及的经历而言,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国家集体的经历,必须放在国际社会的背景下加以叙述。现代化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竞争背景下展开的叙事。因此,在过去的50年中,太平洋西岸的国际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某些变化,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附庸帝国
与明治维新100周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0年后,这种对日本现代化的渐进式叙事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激起人们的热情。如今,在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人们发现相关的宣传相对较少。用从直线上升到山顶的比喻来构想这个国家的历史已经不再流行。现在看来,这种现代化的叙事结构很难描述日本民族的历史进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逐渐瓦解,东亚地区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由于无法摆脱“美国治下和平”的“附庸帝国”的地位,日本民众越来越难以通过现代化理论的这个乐观的棱镜来看待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地位,即“日本社会是整个亚洲唯一真正的现代化社会”。
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1968年之后的20多年里,我第一次不得不批判性地反思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神话”,部分原因是我在那里目睹了一种被称为“自闭式”社会现象的出现。“自闭式”这个术语被一些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健康专家所使用,用来指年轻人(主要是男性,也有一些女性),他们拒绝走出卧室或父母家,从而与社会生活疏离。除此之外,日语的“hikikomori”(蛰居族)一词也揭示了这种极端的社会异化现象。
尽管有点犹豫不决,但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开始使用“自闭式民族主义”这个术语,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大致归为这一类,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出现的反动、歧视和排他性的政治趋势有关。在通常被称为“失去的两个10年”(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期间,可以观察到日本的这一趋势。我认为,在术语“自闭式民族主义”中对“自闭式”的用法:它不是指“自闭式”的人,而是指在许多后工业社会中看到的一种类似的社会政治倾向,有时被称为“冷漠社会”。因此,通过使用这一术语,我将基于对一个国家构想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定义为一个安全的封闭空间,几乎相当于“自闭式”的人的卧室那样的封闭空间。这些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担心他们的国家空间容易受到外国人的入侵,因此他们主张建造一道隐蔽的或有形的墙,以阻止他们的进入。事实上,“自闭式”民众的政治取向与行为,与那些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大肆宣扬“自闭式民族主义”,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民族主义的启发。
当审视太平洋西岸的社会所经历的剧变时,我无法回避日本成功现代化的“神话”这一问题,而这个“神话”曾给日本民众一种殖民者自尊感。但是,同样重要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代化的蓝图是一种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暂时性的投入方式,也是对当前焦虑的一种转移。这是一种将目前的不确定因素转化为对未来有持续决心的机制。换言之,这是一种抵御当前焦虑的防御机制,用未来的保证取代了当前的风险。当然,这种保证从来没有得到担保,但现代化的机制产生了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一种不必要的保证一再得到确认和履行。不言而喻,《坂上之云》是典型的现代化叙事。
在许多方面,在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跨太平洋联盟,意味着对太平洋西岸新的殖民统治。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美国治下和平”逐步得到巩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及其保守势力从中获益良多。正如我在《跨太平洋想象:反思边界、文化和社会》[注]The Trans-Pacific Imagination : Rethinking Boundary, Culture and Society, Naoki Sakai and Hyon Joo Yoo ed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2, pp.279-315.一书中的一个章节“跨太平洋研究与美日共谋”所讨论的那样,美国决定赦免裕仁天皇犯下的战争罪行,将他作为盟军占领日本的美国傀儡,这一决定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使日本民族主义成为美国控制日本国内政治的工具。可以说,美国仿效日本军队在“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的战略,即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君主制,但表面看起来却是“独立的”。无论日本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在伪满洲国所追求的政治意义,最重要的核心都是试图重新定义主权。他们正在创建一种新的主权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同时是“独立的”和被殖民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二战后扶植的国家可以被称为“美国的满洲国”。从裕仁天皇开始,日本政治家哪怕受到胁迫,也愿意接受美国政府的支持。1952年日本“独立”后,在同盟国占领下,美国最高指挥官及中央情报局(CIA)与日本战犯嫌疑人如岸信介和正力松太郎等人结成了联盟,并以美国“封锁政策”的名义,在东亚开展了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日本的国家政治自1955年以来主要由自民党主导,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保守派的半殖民地政权。[注]Abe Shinz was born into a family of politicians.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was Kishi Nobusuke. His father is Abe Shintar?, who served a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s well as a number of ministerial positions. Before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for the first time, Abe Shinz? had accomplished little in politics except for his family ties with a number of prominent politicians such as Sat? Eisaku (his grandfather’s brother and prime minister 1964-1972). For his legitimacy, Abe still appeals to his grandfather’s postwar legacies.正如在《跨太平洋研究和美日共谋》[注]The Trans-Pacific Imagination: Rethinking Boundary, Culture and Society, op cit.以及《“美国治下和平”的终结与“自闭式”民族主义》[注]In『ひきこもりの国民主義』(Nationalism of hikikomori)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7, pp.177-254; also the Chapter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and the Nationalism of hikikomori” in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forthcom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所述,美国从日本帝国手中继承了“大东亚共荣圈”。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战略是假定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中心将设在中国。中国将成为战后经济重建的中心,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设施,成为美国远东军事或者殖民体系的中心。由于将在中国建设军工设施,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战后为日本配备军工生产设施。日本所谓的“和平宪法”就是在这一战略假设下设计和实施的。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国民政府随后在1948年和1949年败退到中国台湾,迫使美国决策者放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帝国设计。这也暴露了美国缺乏足够的专长来殖民远东社会。
因此,虽然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美国也无法避免依赖日本在殖民统治方面的专长。通过从日本继承“大东亚共荣圈”的遗产,美国迫切需要这些东亚地区的殖民专长,这些经验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日本官僚和殖民官员所获得。美国决策者有意将“附庸帝国”的角色分配给战后的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主要由前战犯、反共理论家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参与决策和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或官僚把持。因此,随着大量资本投入日本工业,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反弹,并在此后的30多年内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由于美国继承了“大共荣圈”(当然,中国大陆和朝鲜除外),日本民众可以在“附庸帝国”的庇护下,恢复对亚洲邻国的殖民者地位。
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比岸信介更能代表这种太平洋上的共谋。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东条英机内阁中,他为伪满洲国设计了经济框架,并担任大东亚地区的军需大臣。他负责日军占领区的军需政策,当时被称为“大东亚地区”。日本战败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盟军最高指挥官逮捕,并在巢鸭监狱被关押了3年,但是,随着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改变,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机构释放了他,并使他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因为他在东亚各地有着广泛的殖民经验和关系,在“美国治下和平”下,他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后来他成为首相(1957—1960年)。岸信介是殖民统治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附庸帝国”的化身。1955年,他为自由民主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在过去60年里,日本主要由自民党主导,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注]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Kishi Nobusuke and Sato Eisaku brothers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as disclosed in a multi-page article by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1994.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Kishi and Sato begged for money from the CIA. Also see: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the History of CIA,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7,1964年至1972年成为日本首相,并得到了曾任自由民主党党务秘书、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的支持。
三、帝国的丧失
果然不出所料,尽管日本民众在与美国的关系中经历了向同盟国投降,以及帝国及其殖民地的丧失,但他们从未遭受过亚洲人民所期望的那种耻辱。同时日本民众未曾意识到,他们也被那些他们曾经视之为殖民地“仆人”打败了。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把自己暴露在亚洲人民的注视之下,也没有经历他们自愿非殖民化所必需的耻辱。失去对旧殖民地的主权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必须以自我塑造的方式进行彻底的转变,以使自己非殖民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族通过“帝国的丧失”这一重要过程,错过了非殖民化的机会。
当然,我使用的术语是“帝国的丧失”,这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是殖民者改造自己和使自己非殖民化的一种“平权”行动。在许多情况下,包括美国目前反移民种族主义猖獗的政治气候,以及英国全民公投确认英国脱欧的自我毁灭议程,“帝国的丧失”可能会引起民众的破坏性反应,他们无法应对殖民宗主国自尊心所遭受的沉重打击。然而,为了摆脱殖民遗留的夸张债务,前殖民帝国的国家依然认为自己比其殖民地的人民更优越和享有特权,前殖民者必须为了达到非殖民化的目的,以肯定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面对“帝国的丧失”。事实上,我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们研究了英国的“帝国的丧失”这一问题。
20世纪80年代,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 )等学者以“帝国的丧失”[注]One of the best studies where the theme of the British loss of empire was pursued is in: Paul Gilroy, There Ain’t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这一表述为参照,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大英帝国失去了许多殖民地,英国民众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谓的殖民地的“威望”和对前殖民地居民的“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们被剥夺了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但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大英帝国崩溃后与非殖民化有关的幻灭和焦虑。由于种种原因,幻想破灭的时刻被推迟了,大约30年后才出现: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附属国,英国继续在国际政治中获得特殊地位,作为同盟国的核心国家,英国人被允许在“美国治下和平”下作为胜利者行事,尽管与他们以前的殖民地附属国相比,他们显然是失败者。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即使是普通的英国人也无法再回避英国不再是一个帝国的事实,因此,一些人开始诉诸于美好的旧英格兰的怀旧形象。这种后帝国时代的焦虑一直存在。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他们生来就是为了统治世界的思想,即使在当今,一些英国民众仍然不能接受英国权力的削弱。对他们来说,欧洲窃取了他们国家的主权,他们渴望与美国结盟,夺回其与生俱来的权力,并利用英国的金融实力再次主宰世界。
一些英国人对“帝国的丧失”这一事实怀有强烈的愤恨情绪,是不足为奇的。第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普遍存在的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像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这样的反动政治人物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自那时以来,英国从未摆脱过持续不断的实质性的反移民种族主义。在英国,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很容易受到种族主义仇恨的影响,当具备某些社会政治和情感条件时,这种仇恨很容易就会被触发。如果不提及英国帝国的丧失,以及对大众媒体的蓄意操纵,就无法理解2016年的英国脱欧。因此,在《“美国治下和平”的终结与“自闭式”民族主义》一章中,我引用了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1989),这部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这种“帝国的丧失”所引发的焦虑和怨恨。[注]Kazuo Ishiguro, The Remains of the Da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9.
在我理解“美国治下和平”的终结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英国帝国丧失的例子显得尤为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我发现了日本的“自闭式”的社会现象。据我了解,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已经退出了社会,而且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一种内向的态度。大众媒体对“自闭式”的报道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反动政治运动的出现相吻合,这个社团成功地煽动了大量日本民众,并试图从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日本及其军队在殖民和战时所犯下的暴行的描述。他们不想讨论有关日本殖民主义和战争罪行的历史事实,而是否认和拒绝日本士兵和民众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所做的事情,包括臭名昭著的战时性奴隶,通常被称为“慰安妇问题”。他们只是拒绝与非日本人进行对话,也拒绝与那些关心日本殖民和战时活动的责任与问责的日本人进行对话,他们回避可能被迫对问责指控负责或作出回应的场合。他们否认的重要事实是,他们试图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逃避与可能追究他们责任的非日本人或日本批评者相遇,他们逃避殖民或战时责任的行为,但这只能在幻想中才能实现。
他们行动的根本前提是将自己封闭起来,以避免与外国人或“自虐性”(自我批判的)日本人发生冲突。10年后,即2006年,在这些反动运动之后,谴责给予朝鲜裔和中国裔居民“特权”的公民协会组织了街头示威(通常缩写为Zaitoku-kai)。这些示威活动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虽然现代日本发生了无数起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开鼓吹歧视某些族裔或种族群体的街头示威活动已不多见。也许,谴责给予朝鲜裔和中国裔居民“特权”的公民协会是第一个发起这样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的朝鲜裔和中国裔居民,实际上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却被指控享有并非是过分的“特权”,而仅仅只是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他们所谓的“特权”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即所有日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反对的是一个普通的事实,即朝鲜人和中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就像普通日本人一样。此外,最明显的是,该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完全不了解他们选择攻击的族裔群体是谁、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状况。很明显,即使他们痛恨朝鲜人和中国人,这种仇恨并非源自与他们的任何实际接触。他们痛恨本地移民,完全是基于他们幻想中的预判。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提出的关键问题是,“自闭式”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妄想逃避集体耻辱的后果之一,换言之,他们拒绝承认“帝国的丧失”。
“自闭式”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不能脱离战后日本的历史来分析,即迅速发展的媒体革命——通讯技术的数字化、社交媒体的发展、邻里社区关系的崩溃,以及原子化社会[注]原子化社会指的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这些发生在亚洲的后殖民地时期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然而,正如从后工业化的国家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也确实具有“内向型社会”的许多特征。如上所述,我试图把“自闭式”民族主义定位在二战后“美国治下和平”下的东亚历史中。但是,我也试图从现代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者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的历史分析视角出发,并放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予以分析。
四、“自闭式”民族主义
审视太平洋西岸社会所经历的剧变时,就无法回避日本成功现代化的“神话”这一问题,这个“神话”曾给日本人民一种殖民宗主国的自尊感。也许我们应该在日本现代化前景过于乐观的背景下,理解“帝国的丧失”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到20世纪60年代末,绝大多数日本人承认,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积极的,他们为自己这一非凡的成就感到自豪,尽管日本战后的成功只有在“美国治下和平”的情势下才有可能实现。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这种对日本的过去持肯定态度的背后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优越感。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由于这些改革,议会民主似乎已在这些日本殖民地扎根。此外,这些政治变革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完成的。下列统计数字充分显示了5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趋势:过去40年中,包括美国、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注]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value 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nverted to international dollars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rates and divided by total population.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约为日本的45%和30%,10年后分别是56%和44%。到21世纪初,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1%和71%。在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0年后从3%增长到5%,到2002年增长到11%,到2012年增长到25%,而日本与美国几乎保持不变。[注]74% in 1982, 83% in 1992, 70% in 2002, and 69% in 2012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的GDP超过了日本(107%),[注]1982: USA $14,410; China $327; Japan $10,615; South Korea $3,040; Taiwan $4,466.1992: USA $25,467; China $1,028; Japan $21,057; South Korea $9,443; Taiwan $11,901.2002: USA $38,123; China $2,884; Japan $26,749; South Korea $18,878; Taiwan $21,613.2012: USA $51,704; China $9,055; Japan $35,856; South Korea $31,950; Taiwan $38,357.In current US Dollars, IMF estimates.2017年,GDP(ppp值)超过英国和法国。
当然,这是许多指标之一,不能孤立地从统计数字中得出任何结论。然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在过去40年中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化有多剧烈。这也意味着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日本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地位已被重新定义。作为一个“附庸帝国”,[注]For ‘an empire under subcontract,’ please refer to my recent publication The Nationalism of Hikikomori (『ひきこもりの国民主義』,Tokyo: Iwanami Shoten, 2017) (an English version forthcoming from Duke University Press.)日本过去在美国的“封锁政策”下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从美国的特殊待遇中获益良多。与此同时,美国的专家们认为日本是现代化的“典范”,其他所有“不发达”的社会都应该效仿日本。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理论的追随者过去常常把日本称为“整个亚洲唯一真正的现代化社会”,其隐含的假设是,现代化是一种适用于西方社会荣誉的象征。在冷战的政治气氛中,在“美国治下和平”的全球背景之下,日本人民表现出好像他们仍然是殖民宗主国的一部分,即使日本已经失去了其海外殖民地。换言之,多亏了“美国治下和平”,它才能更多扮演“附庸帝国”的角色。因此,许多日本人未能摆脱瞧不起亚洲邻国的旧习,这往往是前殖民者对来自前殖民地的人民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的习惯。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逐渐瓦解,东亚地区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间政治格局。由于无法摆脱“美国治下和平”下的“附庸帝国”的地位,日本民众越来越难以通过小说《坂上之云》来看待日本与其亚洲邻国的地位。最后,日本民众不得不面对英国文化研究中所说的“帝国的丧失”。作为日本对外部世界态度的一个明证,我需要提及这方面的其他迹象。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学生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都显得引人注目。他们的出现被理解为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就像紧凑型日本汽车开始主宰美国市场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生的数量超过了韩国学生。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容置疑,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从印度和中国来到美国的大学。即使在我任教了30年的康奈尔大学,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生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6年,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总数超过100万人,其中32万人来自中国,17万人来自印度,8万人来自韩国。[注]Time, November 14, 2016.然而,尽管来自亚洲的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但在过去30年中,在美国的日本学生人数却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虽然中国台湾的人口还不足日本的五分之一,但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台湾地区学生总数却高于日本学生总数。不仅仅是美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人数减少了,日本国内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也急剧下降。最近,我在日本从事政治学工作的朋友葛西·弘隆(Kasai·Hirotaka)给了我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在20多岁的日本年轻人中,只有5%曾经申请过护照。在过去5年中,这一比例在5%至6%之间波动。15年前,这一数字约为9%,因此,对出国感兴趣的年轻人显然减少了。由于日本总人口中约有24%持有护照,这一数字低得惊人。[注]This figure may also appear low, but it was 8-9% in the 1990s. http://www.mlit.go.jp/common/001083168pdf,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Tourism Strategy Division, Japan Tourism Agency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尽管人们不能忽视在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经历了经济困境,但统计数据进一步描述了这一态势的变化。
根据2015年对日本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对于“你愿意去国外工作吗?”这一问题,63.7%的新员工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仅有36.3%的新员工的回答是肯定(9.1%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在任何国家工作;27.2%的人愿意在国外工作,但有些国家他们不愿意去)。2001年,只有29.2%的人对同一问题表示否定,而70.7%的人表示肯定(17.3%的人愿意在任何国家工作;53.1%的人愿意在国外工作,但有些国家他们不愿意去)[注]These data are based on an article referr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Sanno University (産業能率大学) in Nikkan Kogyo Shimbun (日刊工業新聞) September 17, 2015.。显然,在对待海外工作的态度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明显,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不想离开日本而到国外去工作。这些发现似乎证实了我在过去30年中观察到的有关日本社会的趋势。我现在确信,把今天的日本描绘成一个“内向型社会”是正确的。
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Winichakul )对当今泰国国家形成的丰富研究中,提出了“国家地缘机体”这一概念,并探讨了现代测绘学是如何从暹罗王国转变为现代泰国国家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以及现代测绘技术如何产生了一种集体想象,使人们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称之为“民族”[注]T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的新集体成员。民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构想的体制与地理边界密切相关,它体现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一个受国家边界所限制的地理空间。因此,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其成员通过血缘关系或氏族归属与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的集体。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其成员通过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称之为的“认同感”而相互彼此相连。[注]John Stuart Mill defined the nation as “the society of sympathy.” See: “Consideration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John Stuart Mill, H.B. Acton ed.,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72, pp.187-428 (first published 1861).从这方面看来,一个民族不仅是一个构想出来的“社区”,而且是一个被奇妙的纽带——“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社区。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认同感是由一个“地缘机体”的形象所产生的,它也意味着,由于居住在一个固定的领土上,人们在地理上受到限制,因此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在这一社区中的成员身份是以国家边界为标志的,而确定其为成员的资格则被称为“国籍”,所有居住在这一边界之外的人都必须被视为被排除在国籍和共鸣之外的外国人。换言之,一个民族的存在,至关重要的是永远不能与外国人分享同胞情谊,因为这是一种民族情谊的纽带,民族性的美学要求你必须对你的同胞存有同情之心,同时也要对外国人存有厌恶之心。因此,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必须由这种模糊的共鸣与厌恶的美学所支撑。
从这种民族共同体的奇妙逻辑中,不难想象出一种典型的法西斯反移民种族主义言论,20世纪30年代的反犹太主义也包括其中[注]Let us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category of immigrants is very unstable. The best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itizens against the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sident Aliens (在日特権を許さない市民の会). Their use of the category “resident aliens”(在日) includes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s of immigrants from Korea and Taiwan.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many Jews who became the targets of racist execution had been residents in Germany for many decades, but that they were singled out as immigrants in the populist motto of “Europe for the Europeans”.。民族主义者很可能会争辩称,除非外国人受到歧视并被排除在国家领土之外,否则,基于地缘机体形象的民族同感就会被玷污和侵蚀,民族认同感必须得到国家边界的保护,防止入侵者从国外进入国家领土。的确,这是一个愚蠢的论点,但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荒谬的言论可以吸引大量迫切需要民族认同感的人。
现在可以知晓,我之所以用“自闭式”这个词来描述近几十年来日本社会所特有的某种民族主义,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我相信美国现在也受到了“内向型”社会的社会弊病的困扰。
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是一回事,对一个国家地缘机体的隐喻性限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方面,“自闭式”的人们害怕他们自己家以外的社交空间,但不一定害怕来自除其自身国家以外的世界入侵。而另一方面,“自闭式”民族主义有一种幻想性的恐惧,害怕来自国家领土以外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自闭式”民族主义坚持建造一堵“墙”,无论是幻想的还是现实的,以防止外来入侵者进入国家内部。因此,必须指出的是,“自闭式”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并非日本所独有,但至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可能在日本最为普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这种基于国家地缘机体的排斥机制,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一个被称为民族的现代化社会的形成,都包含着潜在的“自闭式”现象。
“自闭式”民族主义具有“内向型”社会的许多特征,包括反移民种族主义,就像在许多后工业化国家中观察到的那样。而在日本,“内向型”社会似乎表现为在民众对明治维新态度的转变上,它不再被描述为象征着年轻人开放态度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再对外部世界的外国人感到好奇,而是害怕与他们接触,并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和隔离。是什么历史条件迫使后工业化社会中的这么多人退隐到国家的这种封闭又奇特的空间里呢?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一定在思考其后工业化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意把日本人的“自闭式”民族主义置于内向型社会的背景下。使一个“内向型”社会的问题难以驾驭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国家地缘机体的集体幻想。这使得右翼狂热分子能够利用那些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强烈不满,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各部门和地区,而这些部门和地区由于几十年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被边缘化和掏空。
“自闭式”民族主义的这一方面,不仅仅是日本特有的问题。当沮丧和怨恨没有出路、没有明显的补救办法时,人们求助于民族国家地缘机体,即现代民族共同体赖以建立的最初的集体幻想。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如唐纳德·特朗普就认为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奇妙的补救办法。
因此,问题也随之出现:“自闭式”民族主义会不会诱导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的重演,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