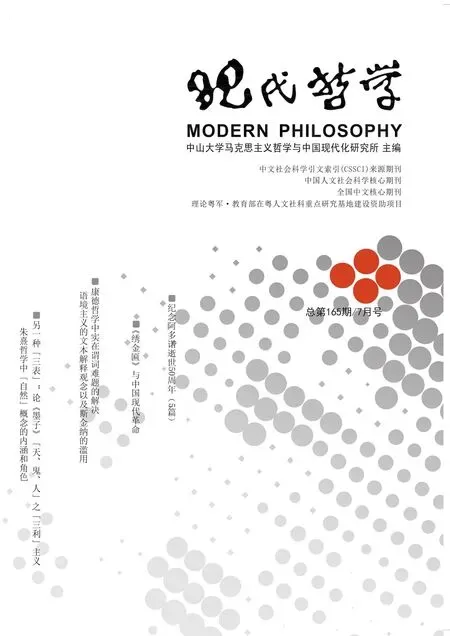清初尊朱黜王思潮中的《孟子》诠释
——以李二曲《孟子反身录》为中心
李敬峰
晚明时期,王学末流弊端丛生,或走向空谈,或流入玄虚,甚至被视为亡国之学,因此在清初形成一股尊朱黜王的学术思潮,正是作为学者回应时代问题和建构学术体系的“他者”而存在。在此宏观学术背景下,与阳明心学联系最为紧密的经典《孟子》无疑成为学者表达其学术思想和立场的重要经典媒介[注]牟宗三明确指出“王学是孟子学”。(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本文以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孟子反身录》为切入点,将其置于清初尊朱黜王的学术思潮中进行观照和考察,通过分析《孟子反身录》的核心特质,以期有史有论地揭示其如何在清初崇朱黜王的思潮中开辟出修正、完善、提振阳明心学的新路径,从而透视阳明心学在清初的演进以及经典诠释与时代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提揭和阐发“心”
“心”论虽不为阳明心学所专属,但它无疑是阳明心学的立论根基和理论内核,故李二曲在诠释《孟子》时不惜笔墨,尤重对“心”的提揭。就《孟子》全书来讲,他认为“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5页。,也就是说,《孟子》全书的核心要旨在于令人“求心”,这是“千古学问断案,千古学问指南也”[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1页。。李二曲对《孟子》要旨的这种定位显然有别于以往学者[注]例如,程颐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杨时认为“七篇之书俱在,始终考之,不过道性善而已”;施德操认为“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王霸而尊三王,四也”;朱子说“孟子之言性善……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宋]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页;[宋]杨时:《答胡康侯》,《龟山集》第20卷,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99页;[清]永瑢、纪昀主编:《孟子发题》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4页;[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2页。),他着意将“求心”从数万言的《孟子》中提揭出来,有着强烈的时代指向,意在心学遭黜之际,重新高标心学的标志性范畴,力图彰显心学宗旨。而就《孟子》的具体内容来说,他更是反复指出:
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5页。
若外心而言学,不是世俗口耳章句博名谋利之学,便是迂儒狥末本支离皮毛之学,斯二者均无当于为人之实,非孔孟之所谓学也。[注]同上,第136页。
在李二曲看来,“心”(道德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根本所在,若离此而言学,不是章句谋利之学,便是腐儒支离之学,必须在“心”上用功才是为学正道。此论可谓抓住儒学的核心,不仅因为“心才是道德实践的用力之地和根本出发点,因而对于人的精神发展来说必须强调‘心’”[注]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更缘于特定的理论诉求。李二曲说:
今之学者茫不知心为何物……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忽虚寂杂于禅。[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13页。
他认为孟子之后,象山、阳明皆知学之要在于求心,工夫“简易直截”,指明机要,使学者有所持循,而后学末流背离先贤指诀,脱略工夫,直求本体,导致空疏或杂禅之病。这是对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由于对“心”“良知”等认识的偏差所造成的“虚玄而荡,情识而肆”之流弊的生动描述。可见,他把曲解、遮蔽“心”看作学术流弊丛生的根源。他进一步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注]同上,第108页。。人心乃天下之大根本处,而提醒、振奋天下之人心则是平治天下的关键、要害之处。在此,他将“心”的重要性由关乎人心、学术扩展至整个天下,凸显“心”在个人修养、社会风气和天下治理上的关键地位。此举既是传统儒学道德至上的体现,更是标举心学的展示。当然,若止于此则不能显其特色。李二曲更深入一层,对“心”的内涵在阳明的基础上进行抉发。他首先以“太虚”来规定“心”:
心不累事,恒若太虚,毫无沾滞。[注]同上,第497页。
心如太虚,乃未发之中,本性真体不落,思想不堕方所,无声无臭,浑然太极,大德之所以敦化也。[注]同上,第145页。
用“太虚”来规定“心”,从学缘的角度看,或直承关学宗师张载,或秉承阳明[注]参见林乐昌:《论李二曲对宋明理学的总结》,《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已不可考其源。无论如何,这一方面将“心”提升到至高无上之境,另一方面表明“心”作为工夫的入手处,必须保证其在源头处没有沾滞,如此发用流行才能纯任天理。他解释到:
心体本虚,物物而不物于物,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如是则虽酬酢万变,而此中寂然莹然,未尝与之俱驰。[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395页。
因为心体本虚,明莹无滞,不着一物,故在与物相交时,能够以大公无私之姿而保持心体的清澈莹然,不滞一物,从而实现发而中节之和。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心”的虚是儒家一直以来的主张,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心”的洁净空阔,不染杂欲,如此才能不偏不倚地具众理而应万事。但“虚”并不是“无”,而是在“这个‘无’中,包含着一切的‘有’,蕴涵着一切‘有’的可能性”[注]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其次,李二曲提出“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我者,此心是也”[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31页。,将“心”(道德)的来源归之于“天”,认为这不仅是上天赋予我的,且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这实际上是将“心”“性”等同为一。李二曲亦曾说:“天之所以与我,而我得之以为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注]同上,第407页。以及“‘道心’即善性也,但异其名称耳。”[注]同上,第210页。这不仅将其心学性质展露无遗,也将“心”的位置凸显、拔高。与阳明不同的是,阳明将心、性关系更明确地表述为“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注][明]王阳明:《传习录》,《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页。,而李二曲在较为模糊或者更为简易的表述中,强化其对“心”的认识和定位。从整个宋明理学史看,李二曲借诠释《孟子》,紧扣“心”这个范畴,从“心”的内涵、地位以及价值来祛除遮蔽在“心”上的种种不实之论。在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弊端丛生、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批判王学的思潮下,这种对“心”的重新发明和提揭显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意义已经超出其内容本身。
二、推阐和扩充“良知”
“良知”说在孟子那本是人心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后经王阳明提揭阐发,上升至最高本体,并成为中晚明以后学界的公共学术话语。李二曲对“良知”高度赞扬: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为之点破……若以良知为偏,为非,是以孟子为偏为非,自己性灵为偏为非矣。自己不认自己惑也,甚矣。[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4页。
孟子论学,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为单传直指,作圣真脉。[注]同上,第503页。
在此,他高度评价孟子将人所固有的“良知”提揭出来,认为其乃单传真脉,圣学宗旨,并将其作为不容置疑的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而对于王阳明融合《大学》的“致知”提出“致良知”之说,他说:
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注]同上,第59页。
他认为,阳明针对陆九渊在本体上的缺陷和不足,提出融本体与工夫的“致良知”以矫其说,从而一言洞彻本体,道破千年不传之秘,为凡夫俗子指明入圣之道,可谓功在万世。由此可见他对阳明“致良知”说的服膺和推崇。在回答学者对此的质疑时,他进一步回护道:
问:“‘致良知’三字,泄千载不传之秘,然终不免诸儒纷纷之议,何也?”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则文字知见,义袭于外,原不曾鞭辟著里,真参实悟;一则自逞意见,立异好高,标榜门户,求伸已说。二者之谬,其蔽则均。若真正实做工夫的人,则不如是。”[注]同上,第41页。
李二曲认为诸儒之所以对“致良知”争议不断,一是只从知识性的角度而非体悟性的角度理解;二是标新立异,阐发己说。此论可谓确然[注]阳明后学对“良知”的理解出现分化,王龙溪概括为八:有谓良知落空,必须闻见以助发之;有谓良知不学而知,不须更用致知;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有谓良知主于明觉,而以虚寂为沉空;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参见彭国翔:《良知异见:中晚明阳明学良知观的分化与演变》,《哲学门》2001年第2期。)。他也并非单纯地羽翼阳明之说,而是有所推阐和超越,着重突出“良知”的以下义涵:
(一)“良知”即良心
“良知”在孟子那是指先验的道德意识,阳明将其丰富和发展,主要有四种内涵:天理之昭明灵觉;是非之心;思是良知的发用;造化的精灵[注]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111页。。李二曲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
问:“良知之说何如?”先生曰:“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130页。
在此,他将“良知”与“良心”直接等同,而“良心”则是“性”,三者具有同一性,只不过是异名同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述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良心”:
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良心发现处,良心即善也。非由学而然,非拟议而然,非性善而何?[注]同上,第190页。
他认为“恻隐之心”是“良心”的显用,而此“良心”是先天具有的,是纯善无恶的,由此,三者具有相同属性。阳明将“是非之心”等同于良知,更加强调“良知”的决断能力;而李二曲将良心、性与良知等同,旨在凸显“良知”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纯善无恶性。
(二)“良知”之知为真知
良知之“知”究竟是何意谓,学者纷争不断,难有共识。对此,李二曲解释到:
问:“良知之‘知’与知识之‘知’如何分别?”先生曰:“良知之‘知’与知识之‘知’分别逈然。所谓良知之‘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念头起处烱烱不昧者是也。知识之‘知’有四:或从意见生岀,或靠才识得来,或以客气用事,或因尘情染著。四者皆非本来所固有,皆足以为虗明之障。从古英雄豪杰,多坐此四者之误……学者必先克去知识之‘知’,使本地虚明,常为主宰,此即“致良知”的诀也。[注]同上,第102页。
对“知”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张载,他将“知”区分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提出“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有隔绝“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嫌。而阳明推阐和修正张载之说,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注][明]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阳明强调良知之“知”虽然不由见闻而来,但不能离开见闻之知。李二曲进一步融合张载和阳明之论,认为良知之“知”与知识之“知”是有差异的,良知之“知”主要是一种决断是非、明辨善恶的能力,而知识之“知”主要是指意见、杂识、尘情等后天知识;学者必须克除这些后天知识,使良知之“知”显发出来,此就是“致良知”的要诀。可见,李二曲对类似于闻见之知的否定与排斥,比张载、阳明更加极端。他认为唯有良知之“知”才是真正的知,且此类“知”具有无可比拟的功能和优势:
此“知”既明,则知其所知,固是此“知”; 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盖资于闻见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则无不知,乃吾人一生梦觉关也。[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420页。
李二曲认为只要此良知之“知”显明出来,则能无所不知。它比“见闻之知”更为广大、灵明,学者若能觉此,即是闯过人生一大关。
(三)“良知为学问头脑”
王阳明以“良知”统领一切,指出“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注][明]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第144页。。对阳明此义,李二曲明确揭示说:
学问贵知头脑,自身要识主人。诚知头脑,则其余皆所统驭; 识主人,则仆隶供其役使。今既悟良知为学问头脑,自身主人,则学问思辨,多闻多见,莫非良知之用。[注]同上,第136页。
他认为为学要抓住根本,如此方能统率一切;这根本、主人就是“良知”,识得“良知”为学问总头脑,则其它一切无非“良知”之发用。此论正是对阳明思想的发明,直接提出“良知为学问头脑”,只要抓住“良知”,便一切皆明。他借答学生之疑重申此意:
问:“学须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中正无弊,单‘致良知’恐有渗漏?”曰:“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注]同上,第504页。
当学者质疑单提“致良知”有遗漏之嫌时,李二曲在此重申“良知”至高无上的统摄作用,认为只要通晓“良知”,朱子所讲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能有落脚和下手处,此乃治本之法。由此可见,他将“良知”作为统摄一切的最高本体,其观点具有宗本阳明、兼摄程朱的理论特质。
三、本体先于工夫
清初,虽然阳明心学因被视为明亡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清算和批判,但在学术舞台上仍与程朱理学相峙而存、互较上下,使原本相对沉寂的“朱陆之辩”再次成为学者绕不开的时代问题。对此,李二曲自然不能置身于外,他说:
辨朱辨陆,论同论异,皆是替古人担忧。今且不必论异同于朱陆,须先论异同于自己,试反己自勘,平日起心动念,及所言所行与所读书中之言同耶,异耶?同则便是学问路上人,尊朱抑陆亦可,取陆舍朱亦可;异则尊朱抑陆亦不是,取陆舍朱亦不是。只管自己,莫管别人。[注]同上,第48页。
李二曲认为辨析朱陆异同,皆是为古人争长短、辨是非,不如反观体察,先从自身上辨异同,看自身与圣贤之言是否有差异。如果相同,无论尊朱贬陆还是相反,皆无不可;若相异,则持何种立场皆是错。可见,他主张搁置争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进一步阐述到:
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惚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谈工夫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子为宗,以孟氏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注]同上,第505—506页。
在此,李二曲详辨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他认为从源头看,阳明与朱子皆无弊,而是坏在后学身上。具体来说,阳明心学直指人心,简易直接,当下洞彻本性,不可谓不快,但后学往往脱略工夫,直探本体,终究失之空虚;朱子则知行并进,博约精当,但后学或陷于工夫而昧本体,或滞于词章,专攻门户之辩。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呢?李二曲认为应当舍去门户之争,各取所长,以陆王之学明本体,以程朱之学为工夫,如此则内外兼备,自然贯通。此分析可谓精准。因此,李二曲反复说到:
学术之有程朱有陆王,犹车之有左轮有右轮,缺一不可,尊一辟一皆偏也。[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6页。
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注]同上,第130页。
在李二曲看来,程朱、陆王之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若能相资为用则相互助益,反之则两败俱伤。在当时,朱子学与阳明学势同水火,如何抉择已成为学者不可回避的学术话题,二曲虽以兼取之姿予以回应,但落实到具体的心性工夫时,他偏好陆王心学的思想旨趣便展露无遗。如说:
工夫不离本体,识得本体,然后可言工夫。今人不识本体,开后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为药,宜其服药而病转增也。[注]同上,第513页。
李二曲认为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但必须先明确本体为何物,然后可言工夫,而今人不识本体,直言工夫,难免以病为药。可见,他仍然主张明本体先于做工夫。基于此,他批评告子道:“告子有志心学,只为不达心体,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注]同上,第513页。告子之失在于不明心体,故工夫走向偏颇。从他对孟子的“能先立乎其大”诠释也可以得到印证。
能先立乎其大,学问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若舍本趋末,靠耳目外索,支离藤,惟训诂是躭,学无所本,便是无本领。[注]同上,第501页。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此孟子契为人示以敦大原、立大本处,象山先生生平自励,励人得力全在于此,此学问真血脉也。[注]同上,第501页。
李二曲认为,若能先立根本即心体,学问方有脉络和本领;反之,根本不立,溺于章句训诂,学问便无统领。他尤其赞赏陆九渊对“先立乎其大”的推阐,认为此乃学问的大本之处。在回答学生之问时,进一步阐述其主张:
问:“学问之要全在涵养省察当何如?”曰:“也须先识头脑。否则,‘涵养’是涵养个甚么?‘省察’是省察个甚么?若识头脑,‘涵养’,涵养乎此也;‘省察’,省察乎此也。时时操存,时时提撕,忙时自不至于逐物,闲时自不至于着空。”[注]同上,第38页。
他认为学问之要仍然是先识本体,只有本体确立,涵养省察才有明确的目标,然后时时操存,无论何时皆不会“着空”。可见,李二曲虽然表面上一再调和程朱、陆王,但实质上难掩对阳明心学的偏好,折射出其宗本阳明、兼摄程朱的学术旨趣。
四、一以反身实践为事
李二曲忧心当时学者“忘身以言书也”[注]同上,第504页。,因此在诠释《孟子》时着意阐发和引申孟子的“反身”思想:
“反身而诚”,则行著习察矣。[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21页。
诚身之乐,孔孟而后,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纷纷之说,总如射覆。[注]同上,第521页。
“反身而诚”主张人的意识向内收缩和用功,使人的意识达到诚实无妄的状态。一方面,李二曲赞同“反身而诚”,认为若此则可以达至明其行为之所以然的境界。实际上,这是对阳明的“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注][明]王阳明撰、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66页。的沿袭,是对在身心上做工夫的推崇。另一方面,他叹学风不古,多数人只是议论纷纷,追逐于外,少有反身体验,达至于诚后的精神愉悦。李二曲并不像朱子那样强调“反身而诚,孟子之意主于‘诚’字”[注][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35页。,而是基于“学问二字人多误认,往往以闻见记诵为学问,故有闻见甚博,记诵甚广,而仁义弗由,德业未成者求诸耳目,而不求诸心故也”[注][清]李颙撰、张波编校:《李颙集》,第500页。的现状,也就是说学者多向外求而不能反身体认,致使学问与个体生命涵养发生断裂,单纯地成为知识性的东西,故择取“反身”之意,以纠时弊。李二曲在诠释《孟子》时反复言到:
为学而矜才能,较胜负,计效验,论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贼之类,吾辈须切己自反。[注]同上,第520页。
他认为为学若只是逞才能、较胜负、论多寡,在今虽被称为良臣,在古则实为民贼,可见古今差异,故他提醒学者要反身体验,以求实有诸己。他进一步说:“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诸已,德业何患不进,人品何患不及古人。”[注]同上,第494页。只要能“反”,能向自身用工,则德业与人品皆能有所提升。同时,李二曲将能否“反”作为判断人有无涵养的关键。
人有涵养没涵养,居恒无所见,唯意外遭逢横逆之来,果能动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与校,方算有涵养。[注]同上,第497页。
他认为判断人是否有涵养,在日常行为中是无法见到的,唯有在遭逢意外的紧要时刻,若能竦动其心,坚忍其性,反身内求,坦荡而不计较,如此则是有涵养。那什么是“反”呢?又该如何做呢?李二曲说:
反之一念之隐,自识性灵,自见本面,日用之间,烱然涣然,无不快然,自以为得向也,求之千万里之隔,至是反诸已而裕如矣。[注]同上,第503页。
在李二曲看来,“反”之工夫即是从意念、意识隐微之处入手,通过克除邪念,复归虚明洁净,然后自能体识性灵,自能体见本来面目,如此日用之间,自然灵明。他进一步说:
先反之一念之隐,以澄其源,次反之四端,以浚其流,视听言动务反而复礼,纲常伦理务反而尽道,出处进退务反而当可,辞受取予务反而合宜,使万古不易之常经不亏,则大经立矣。[注]同上,第505页。
李二曲直接指出“反”之功夫首先是要清理源头,以保证根本无误,再从萌芽之四端入手,以疏导源流,如此视听言动能合于礼,纲常伦理能合于道。可见,李二曲对“反”之工夫层次和次序的界定,条贯秩然,阶梯清晰。同时,他对“反身”之功寄予厚望。
一人肯反身实践,则人欲化为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实践,则人人皆为君子,世可唐虞,此致治之本也。[注]同上,第386页。
李二曲将“反身”作为修身与治世的起点,认为人若能“反身实践”,则可化尽人欲,纯乎天理,若人人皆从事于此,则人人皆可实现君子人格,最终达至尧舜之圣世,这才是治世之根本。必须注意的是,李二曲对孟子“反身”之意的提揭,是针对当时学界弊端而发的。这不仅是其诠释特色之所在,也从根本上与阳明心学理论旨趣保持一致,欲以扭转浮夸不实的社会风气。
从整个学术史来看,经典诠释往往是儒者表达自身对圣贤学问的理解、建构自身哲学体系以及回应时代问题的重要凭借。但这种诠释不是盲目和随意的,而是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的,不可避免地印上浓厚的时代色彩。通过分析清初大儒李二曲的孟子学可以看出,在清初崇朱黜王的学术思潮中,他不避风险,不媚势力,依然立足阳明心学,通过重新诠释《孟子》的“心”“良知”来为阳明心学辩护,又吸收程朱理学所注重的实践工夫来修正阳明心学,开创出以阳明心学为体、为上达之学,以程朱之学为末、为下学之学,且以程朱理学补阳明心学之缺的修正模式。在当时,这因李二曲显赫的学术地位而起到卓绝的示范意义,推动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提振,也为肇始于南宋的朱陆(王)之辨指明新的方向和路径。总之,李二曲的《孟子反身录》有助于我们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初修正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和线索,它不仅是探究阳明心学在清初演进的具体典范,亦是我们龟鉴清初学术面貌的重要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