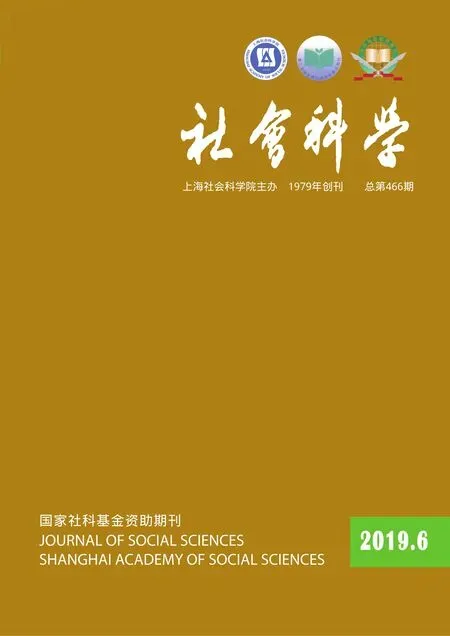论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趣味的认识*
王木青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的分歧不仅是艺术理想与表现方法的差异,更是作家对文学是否应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同理解与评判。“五四”以后,出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为人生、为阶级、为政治)需求,《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对疏离政治的鸳鸯蝴蝶派消遣、趣味文学予以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其影响波及到整个现代文坛,几乎所有著名作家都表明自己的态度,朱自清也不例外。但与主流激进的一边倒式的否定不同,他的评价是平和、适中的。
关于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的认识,范伯群先生曾引用《论严肃》中“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一语说明他对该派文学观是肯定的,但并未进一步展开。本文将朱氏观点置于文坛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的大背景下审视,从而凸显朱自清高屋建瓴,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发展走向的宏观视野。
一、趣味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关系
朱自清(1898-1948)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该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它直接继承了《新青年》同人“文学为人生”的思想理路。周作人在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指出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沈雁冰亦积极支持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其《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思想上剖析了鸳鸯蝴蝶派旧式章回小说最大的错误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周作人斥之为恶趣味[注]子严(周作人):《恶趣味的毒害》,《晨报副刊》1922年10月2日。。郑振铎等人也在《文学旬刊》上连篇累牍地攻击它为玩世享乐的趣味,并且由文品进而质疑作者的人品:他们对于社会上的事情都出之以冷酷的旁观,他们的“良心,死了吧!死了吧!”。[注]西谛(郑振铎):《新旧文学果可以调和么?》,《文学旬刊》1921年第6号。与沈雁冰等人的全盘否定不同,朱自清是非常注意分寸的。
在1922年1月《文学旬刊》第26期、第27期上,西谛(郑振铎)编了一组题为“民众文学的讨论”的文章,其中就有朱自清的一篇。他把鸳鸯蝴蝶派小说看做民众文学的一部分,认为它有粗疏、肤浅、散乱的缺点,需要加以改造。同时,他也肯定了民众文学的第一要件在使民众感受趣味,只是要去除“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之。[注]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文学旬刊》1922年第27期。注:在该文中,作者把“鸳鸯蝴蝶派”表述为“礼拜六派”,在他看来,二者是一回事,都是指以趣味为主的消遣、娱乐文学。为了概念的统一,这里用“鸳鸯蝴蝶派”一词代替“礼拜六派”。这与郑振铎等人发表在《文学旬刊》上一系列声色俱厉的文章相比,可谓心平气和、点到即止。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朱自清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史研究上来,在对史的追溯中,他的目光重新聚焦于对鸳鸯蝴蝶派批评最多的消遣、雅俗、趣味等文坛持续关注的问题。
朱自清认为,五四时期与新文学创作“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它们“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注]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生活文摘》1947年第1卷第4/5期。二者对立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文学的意念”[注]朱自清:《诗言志辨自序》,《国文月刊》1945年第36期。,即:“文学有着重大的使命和意义”,“有其独立的地位”,鸳鸯蝴蝶派重视“奇”,而在新文学看来,“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的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注]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生活文摘》1947年第1卷第4/5期。
在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看来,消遣文学观是旧文学观,应该抛弃。对此,朱自清是持审慎态度的。因为他发现,重“奇”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民间基础。在《论严肃》中,他对古代小说做了一番细致的梳理,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的。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是不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三言二拍”中“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注]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1947年创刊号。
奇与趣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就是指记述杂事的有趣味的作品。关于趣味,在《论雅俗共赏》中,朱自清特别提到唐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送给大人先生看,用来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按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是小说。宋朝笔记也记述有趣味的杂事,作者的议论和批评往往也很有趣。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以后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而目录家是把宋朝笔记归在小说之中的。[注]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出自全集的引文,出版社、出版日期相同,不再标注),第221页。
朱自清不吝其笔,是为了说明小说历来就是不严肃、不正经、有趣的。鸳鸯蝴蝶派继承了传统小说功能,“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注]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1947年创刊号。。言下之意,五四新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赋予文学以严肃的使命固然意义重大,但也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无论怎样变,小说本身的特性还是不能忽视的。
从中国现代文坛的实际情况看,严肃居于主要地位,因为文学总是配合着时代政治浪潮。五四运动以后,又有五卅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时代太紧张了,不允许人们那么悠闲”,于是“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压下了快感”。[注]朱自清:《论百读不厌》,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31页。战争缩短了严肃的尺度,也提高了严肃小说的地位。这自然是符合人情物理的。
问题是,并不能因此一味抹杀消遣、趣味的作用。其实,追逐消遣、趣味对小说创作起着促进作用。朱自清敏锐地发现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小说的读者大大增加了,其中“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趣味和快感,扩大了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自然丰富了。这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注]朱自清:《论百读不厌》,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32页。。对于趣味,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的批评是一贯的。在四十年代中期,茅盾仍然批评低级趣味的东西挤走了正当读物,严肃的读物销量不广,这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是作家的投机和书商的生意眼。[注]茅盾:《如何击退颓风?》,《文萃》1945年第1卷第2期。他看到的是趣味争夺文学市场且不能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消极面,而朱自清则着眼于其对文学本体价值提升的积极意义,确实难得。
有人担心增加趣味性,减少严肃性或降低文学的标准会阻碍文学的发展。而在朱自清看来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在《短长书》中,他谈及学生、公务人员和商人增加带来小说流行的现象时说:读者爱看故事,因为故事“悲欢离合,层折错综”,“容易引起浓厚的趣味。这种对趣味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消遣心理”。又说:
长篇小说的流行,却让一般读者只去欣赏故事和情节,忽略意义和技巧,而得到娱乐;娱乐就是消遣作用,但这不足忧,普及与提高本相因依。普及之后尽可渐渐提高,趣味跟知识都是可以进步的。况且现在中国文学原只占据了偏小的一角,普及起来才能与公众生活密切联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注]朱自清:《短长书》,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50-51页。
而且,小说的这种倾向是必然的,也是健康的。
既然消遣、趣味有存在的价值,那么五四时期批评它是否正确?朱自清态度也很明确:“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候,强调严肃性,指斥消遣态度,这是对的”,好处在于促使读者“吟味严肃的意义,欣赏小说的技巧”,这是文学的基本条件。[注]朱自清:《短长书》,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50-51页。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将严肃和消遣分作不相理会的两端,读者老是正襟危坐,也是一件苦差事。
正确的方法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论严肃》中,朱自清不惮其繁地对“五四”以后三十年间严肃与消遣进退起落的状况做了全面梳理,意在说明:事物向极端发展时都会适得其反。如果一味迎合社会心理,消遣跨过严肃的边界,放纵到色情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这是低级趣味,应当坚决摒弃;另一方面,“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叫人亲近不得”,反而易使人追逐那些色情、油滑的作品,“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注]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1947年创刊号。这里提到的艺术性,自然是不会拒绝趣味的。
总之,严肃提供了文学的主要价值,而消遣利于读者的接受和文学的普及。朱自清的《论严肃》《文学的严肃性》《论百读不厌》《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论雅俗共赏》《低级趣味》《短长书》等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是对严肃、消遣问题思考的展开,可以相互参照来读。他从文学史的走向观察到,严肃与消遣的起伏消长、吸收转化与互渗共融是文学发展的常态,它们各有价值,应兼顾、平衡不同价值而非贬低任何一端,这一结论对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恰切的导向作用。
二、趣味高低、雅俗标准的相对性
朱自清多次论及鸳鸯蝴蝶派的趣味问题,这是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去研究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的民众趣味(民众指农民和都市市民,鸳鸯蝴蝶派读者主要是都市市民),以适时引导他们。
在知识分子趣味与民众趣味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朱自清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二十年代初,他更为重视精英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俞平伯说他“以为文学底鹄的,以享受趣味,是以美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大有对于贵族底衰颓,有感慨不能自已的样子”[注]俞平伯:《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文学旬刊》1921年第19期。。这的确是知音之言。
朱自清醉心于美的艺术带来的乐趣,认为文学的发展主要依靠少数文学天才的引领:“文学一面为人生,一面也有自己的价值,他总得求进步”[注]朱自清:《民众文学谈》,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6页。,“先驱者永不会与民众调和,始终得去领着”。在《民众文学谈》中,他“极力抗议托尔斯泰一派遏抑少数底鉴赏力底主张,而以为遏抑少数底鉴赏力(如对于宏深的,幽渺的风格的欣赏)和摒斥多数底鉴赏权一样是偏废”。[注]俞平伯:《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文学旬刊》1921年第19期。这说明朱自清更加认同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深层次追求。
但很快,他就表示:就阅读权利来说,“多数底文学与少数底文学应该有同等的重要,应该相提并论”[注]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文学旬刊》1922年第26期。。并且现有民众文学发展状况滞后,建设为民众的文学是当务之急。其目的是促使民众的觉醒,提高民众的鉴赏力。
从欣赏习惯看,知识分子与民众有很大不同。前者要求突出文学的个性品质,个性表现得愈鲜明、浓烈,作品便愈能感动人,但它却很难引起普遍的趣味。民众文学多表现一类人的性格,而一类人的性格大都坦率的地方多,所以用不着含蓄之笔。
从阅读趣味看,民众文学“情节得简单,得有头有尾。描写不要精细曲折,可是得详尽,得全貌。……至于整个故事组织不匀称,他们倒不在乎的”。像白话书报,“明白详尽,老老实实,直来直去”,很适合民众的水平,而知识分子读起来却没什么味儿。[注]朱自清:《论通俗化》,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44,142页。
虽然从艺术性来说,知识分子文学更适合朱自清的口味,但可贵的是他并不鄙视普通读者的爱好。民众有自己对作品的期待、理解与鉴赏权,不能拿知识精英的文学标准来贬低他们。
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称鸳鸯蝴蝶派尚“奇”的趣味为低级趣味,如1930年代加入“左联”的茅盾斥责鸳鸯蝴蝶派是“低级趣味的‘封建文学’”[注]丙申(沈雁冰):《今日的学校》,《文学》1934年第3卷第6号。,以其未起到社会批判的作用,钱杏邨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趣味高低取决于其社会价值的大小。而形成于1930年代的京派学院式批评认为,对“奇”趣的追逐是没有登上艺术殿堂的大众趣味,如朱光潜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中把言情、侦探、黑幕等小说均视为低级趣味,[注]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3卷第5期。以其注重感性的满足而缺乏理性的提升与美感的创造。当然,他也批评左翼作家摇旗呐喊,要求文学创作的统一是态度上的低级趣味,会形成一种创作的风气。朱自清并未把“奇”看成低级趣味。他曾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成员,1920年代中后期,与朱光潜等学者交往甚密,在文学观念上亦有类似之处,也因此被视为京派作家群落中的一员。但与这两派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表示喜爱“奇”是传统阅读心理的延续,也是合理的,它与读者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大团圆结局就是一种对“奇”的爱好。自古至今,民众都乐于接受它。照朱自清的说法,小说本来起于民间,起于农民和小市民之间。在封建社会,农民和小市民受着重重压迫,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却有做白日梦的自由。他们寄希望于超现实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侠,以及望之若神仙的上层社会的才子佳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不能实现的奇迹,可是能够给他们安慰、趣味和快感。他们要大团圆,正因为他们一辈子是难得大团圆的。他们同情故事中的人物,“设身处地”地“替古人担忧”,这也因为事奇人奇的缘故。所以,“奇情也正是常情啊”。[注]朱自清:《论百读不厌》,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29页。朱自清从心理学解读民众的阅读习惯,说明他们喜爱大团圆是因为它能给人以情感的慰藉,是一种正常的心理。
大团圆结局被鲁迅称为“瞒与骗”[注]鲁迅:《论睁了眼看》,《语丝》1925年8月3日,第38期。,是文学对现实的遮蔽。沈雁冰称鸳鸯蝴蝶派“大关节尚不脱离合悲欢终至于大团圆的旧格式”[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是对传统的因袭。朱光潜认为它以“道德的同情”代替“美感的同情”,[注]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3卷第5期。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要大团圆,是把艺术硬拉到实用的世界里去。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区别的。
朱自清却没有批评该类小说粉饰太平或者读者品位低,而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趣味的等级或者说雅趣与俗趣上下高低的形成,不仅是文学中的审美问题,还很大程度是由阶级、阶层差异造成的社会问题。
他在为学生讲课时曾论及高雅与低俗的关系,指出雅与俗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文。雅人就是士大夫,俗人就是小市民和农家子弟。“雅是属于高高在上者的,俗则是在下者的。因为以前人民处于为统治者所轻蔑的低级地位,故‘俗’字就有‘浅俗’、‘凡俗’、‘轻俗’、‘卑俗’……不好的描写,以与‘深雅’、‘雅致’、‘典雅’、‘高雅’……相对。不太重功利,不斤斤计较厉害,亦所谓‘雅’;反之则为‘俗’。其实这亦与社会地位有关。能够不斤斤计较,不太重实际功利的,总是较高级的人;而一般最下层的人,是恐怕只能‘俗’的。”[注]吾言:《忆朱自清师》,载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143页。
雅人与俗人所欣赏的作品分别对应着诗文与小说,诗文为雅,小说为俗,但是随着雅人俗人身份的降落或上升,社会生活的变化,都可能带来雅俗标准与尺度的调整。[注]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34-135页。小说本来是“小道”,“五四”以后,它也有了雅俗、高低之分。可见,无论古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雅俗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变化中,对它们的理解也因人、因时空而异。从历代文学的发展看,知识阶级渐渐走近民众,而民众对文学的影响也在渐渐扩大,雅俗界限在缩小,因此无须歧视民众的趣味。
三、宽容的文学理念
朱自清对文学批评取中和态度,在他的老友看来是性格使然。比如:李广田赞扬他批评人生的文字“无处不放射智慧的光芒,心平气和,平正通达,是严肃的,然而并不冷峻,是温和的,但也绝不柔弱。朱先生终其一生,对人处己,观物论事,一直保持了或发扬了这种生活态度,也就创造了并确立了这样的文学风格。”[注]李广田:《朱自清先生的道路》,载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还应该从他的文学观上找原因。
朱自清不以追求趣味性而否定鸳鸯蝴蝶派源于他对文学社会作用的看法是宽泛的。在二十年代初,他就认为文学的感化力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他解释道:有人说,文学能够教导人,鼓舞人,甚至激动人的感情,引起人的行动。比如,革命的呼声可以唤起睡梦中的人,使他们努力前驱,或者靡靡之音使人儿女情长,风云气少,这都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文学的直接的、即时的效用,而是间接的力量。文学的直接效用是片刻间的解放自我 ,是忙碌与平凡的生活之后短暂的舒散,它给人带来中和与平静的情绪,使人得到滋养。而实现自我(以文学来影响人)是通过解放自我而达到的,这样,文学的力量不是极大无限的。他同意周作人的观点,即:承认文学有影响行为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有限度的。而且,实现自我本非文学的专责,只是余力而已。文学的效果也因读者受教育的程度、接触文学的多少而异,无法强求一律。而文学的享受也只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或取或舍,由人自便,绝不可勉强人去亲近它[注]朱自清:《文艺之力》,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注:该文说的是“文艺之力”,但实际上这里的 “文艺”指的就是“文学”。。可见,在朱自清眼里,文学的精神是自由的,文学的作用也是多重的,它有功利效用,但不是唯一,文学的创作与欣赏也是自由的,无需强求一律。这样,具备消遣作用的文学就获得生存的理由。
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茅盾、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作家要求文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工作、宣传工作。倾向于表现被压迫劳苦大众的血与泪,目的是指导人生、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朱自清一方面反对“冷眼看人生”[注]朱自清:《语文影及其他》,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34页。,一方面表示 “血与泪底文学”虽然是“先务之急”,但却非“只此一家”,[注]朱自清:《〈蕙的风〉序》,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53页。所以其他文学也有人生的价值。
朱自清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宽泛的。他曾在为朱光潜《谈美》写序时称许孟实先生“分人生为广狭两义: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距离,与‘整个人生’却并无隔阂”。[注]朱自清:《〈谈美〉序》,载《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65-266页。他赞同朱光潜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即文学所表现的无论与人生远还是近,都脱离不了整个人生,它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与朱光潜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表现的世界是多彩的,因为人生是变化多样的,而表现人生的深浅或方法也没有限定,“无论是记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注]朱自清:《文学的一个界说》,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169页。。因此,朱自清并不像朱光潜那样认为表现人生浅就是低级趣味。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不同的主义、潮流均取宽容态度,而没有正统非正统的框框。以谈诗为例,有些人不承认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是诗,“以为必得表现微妙的情境的才是的。另一些人却以为象征诗派的诗只是玩意儿,于人生毫无益处。这种争论原是多少年解不开的旧连环。就事实上看,表现劳苦生活的诗与非表现劳苦生活的诗历来就并存着,将来也不见得会让一类诗独霸。那么,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者兼容并包,放弃了正统意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注]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载《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20-321页。这种态度移来评价严肃文学与消遣文学似乎也无不可。
对处于不同阵营小说家风格各异的作品,他都能不带偏见地指出其优劣之处。他高度评价茅盾那些描写都市、农村的严密分析社会问题的小说,认为近几年的长篇小说“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现代小说的取材正应该像《子夜》《林家铺子》《春蚕》之类的“才有出路”。[注]朱自清:《子夜》,载《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73、278页。
但他并不因此贬低其他作家的创作,对施蛰存的《石秀》之类“不以故事为主而专门描写心理”[注]朱自清:《读〈心病〉》,载《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78页。的小说也予充分肯定,对穆时英的《南北极》,则称赞其“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注]朱自清:《论白话-读〈南北极〉和〈小彼得〉的感想》,载《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71页。。对于那些与表现现实有一定距离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均能给予正确评价。
结 语
曹聚仁钦佩朱自清是个“最恰当的而又最公正的文艺批评家”[注]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04页。。的确如此,朱自清对现代文学现象的批评都以史的考察为参照,王瑶评价他“因了多年研究古代历史的关系,他分析现实问题也常常从历史的发展来说明,……使人知道今后的发展也是‘其来有自’和‘势所必至’的”[注]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载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这是非常中肯的。由此得出的对鸳鸯蝴蝶派存在合理性的评价亦完全正确,且为文学史实际所证明。
从鸳鸯蝴蝶派的认识史来看,“五四”以后,对鸳鸯蝴蝶派趣味长期规模化的批评导致该派文人在文学界成了一个“卑污”[注]叶圣陶:《过去随谈》,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注:该文写于1930年代初。的名称,从而背负了大半个世纪的精神包袱,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对其评价才逐渐走向历史的真实。可见批评的绝对化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也显示出朱自清宽容文学观的重要性,它并非折中主义或者缺乏对复杂现象的辨识能力,恰恰相反,它对严肃与消遣、趣味高低、雅俗标准相对性的把握,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化解了唯一标准易走极端的风险,体现了辩证思维的力量。对我们正确评价研究对象,树立科学、公正的批评观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