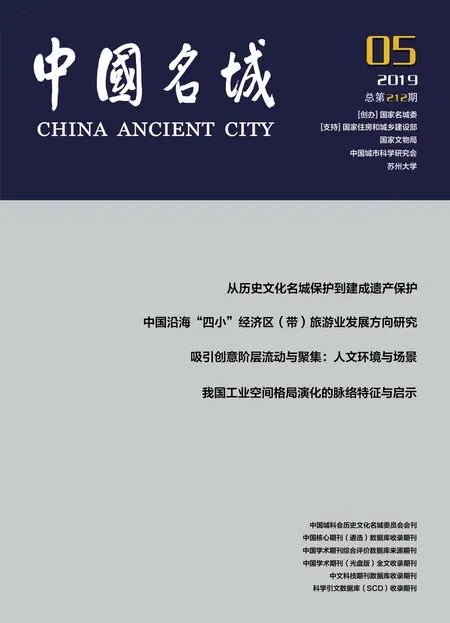吸引创意阶层流动与聚集:人文环境与场景*
——西方创意阶层理论综述
吴 军
1 什么是创意阶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概念,著名社会思想家和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阐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爱华德·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诠释了“消费城市”的理论,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教授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提出的“新政治文化”的理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宣称“后物欲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对“后现代”之类的提法更为熟悉,正如这些学者一样,很多人都强烈感受到现今世界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可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化,他们还尚未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伦多大学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明确提出“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理论,并对这个未定的共识进行旗帜鲜明的回应。该理论强调,工业社会正转入一种创新型的增长模式——创意成为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意不仅改变着生活,还改变着城市形态和社会结构,而创意人才不仅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也是大城市之间竞争的热门争夺对象或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创意产业每天为世界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以高于传统产业24倍的速度增长,美国GDP的7%、英国GDP的8%(伦敦)都来自创意产业(The Creative Industry)。创意产业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大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早在2000年,佛罗里达就敏锐地捕捉到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特征:以企业为中心的“组织化”制度式微,而以文化创意和消费娱乐的经济时代来临。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一书中,他不仅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推动者(创意阶层)命名,而且掷地有声地宣告创意阶层的兴起、特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向城市领导者和企业家们展示了这样的理论:创意人才的聚集自然带来技术、投资和就业等经济增长因素,所以,想办法吸引创意阶层成为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成败的关键。这与爱华德·格莱泽和特里·克拉克的观点一致,即未来大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在——城市作为一个场域或场景在吸引高素质人群方面的能力。研究证明,创意阶层更喜欢选择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城市社区,吸引创意阶层就必须塑造“城市场景”(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综合,基础设施与社区共同体的混合)。
根据佛罗里达教授的中国留学生田方萌介绍,佛氏提出“创意阶层”,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次偶然的会面。1998年,他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正在研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该校的博士生加里·盖茨(Gary Gates)为了撰写论文,用新方法统计了美国的同性恋人口。一天,经系主任介绍,两人坐到一起聊天,佛罗里达拿出一份按高科技产业排名的地区榜单,盖茨则拿出了一份按同性恋人口密度排名的城市榜单。他们惊奇的发现,两份榜单的序列高度重合。换句话说,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同性恋人口相对也比较多。
为何高科技城市偏爱同性恋呢?也许我们会猜想,因为同性恋的智商高人一等,容易在科技产业中胜出。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在同性恋密度最高的旧金山,该群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也不到一成,远不能构成硅谷创意人才的主力,于是,佛罗里达推断,高科技与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出于某一共同因素。他强调,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两者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城市的宽容环境(城市场景)。
城市和人一样,各具性格禀赋。有些城市偏爱自由,有些城市倾向保守。一个同性恋在保守的城市里找不到伴侣,或者找到了也担惊受怕,他自然会搬到更能接受自己性取向的城市。那么,科技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大凡奇才,总有些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那帮科技企业家为“Nerd”,意指不喜欢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书呆子。这种人或许极富创意,却不是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接纳。这种城市场景是他们进行创作的资源,是他们汲取养分的沃土。
克拉克教授用一个例子证明了这一论点。[1]以两个电脑游戏设计公司为例,即技术公司A和技术公司B。公司A位于一个街区场景,该场景孕育着鼓励个人自我表达的价值,公司B所处的场景则相反;公司A位于“艺术之州”,周围被创新的氛围环绕。公司B位于“守旧之州”,周围被传统气氛包围。好的“土壤”能够为公司提供各种资源,比如智力资源(人力)和社会资本。在一个彰显个性、鼓励创新和生机勃勃的场景中,公司A要比公司B的业绩表现更为“抢眼”。
2 创意阶层的类型
创意经济的兴起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学者对工业时期中新兴阶层的兴起,进行着不断探讨。20世纪60年代,皮特·德鲁克对新兴工人阶层的地位与重要性研究后,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2]。70年代,丹尼尔·贝尔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兴的、更为精英化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是生产型的工业时代向消费型的后工业时代转变中造就的,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和教育者等[3]。90年代,在以上基础上,罗伯特·莱特(Robert Reich)又提出了“符号学家”这一称谓,专指那些操作概念和符号的工作人员[4]。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对新兴社会准则和价值体系进行研究后,提出了“X阶层”理论。他在著作《格调:美国阶层体系指南》(Class: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中,把“X阶层”指代“高级穷人”发展起来的上层中产阶级,一支崛起的“X阶层”的存在将会挑战目前的阶层划分[5]。特里·克拉克提出了“新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分析后工业城市革新与财政紧缩的新兴力量[6]。
这些学者和佛罗里达一样,都涉及新兴阶层的范畴,不同的是,佛罗里达把这部分群体称为“创意阶层”,并形成了创意资本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创意阶层出现的根源在于经济性,该阶层的经济职能决定并且表明了其对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创意阶层依靠创意来创造价值。因此,该阶层包含了一大批知识工作者,如科学家、工程师、文化创意工作者、高薪科技人才、金融服务人才、娱乐休闲专业人才等。
在定义该阶层时,佛氏并非通过财产、资本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来探讨阶层,而在于“个体如何在各自的经济职能这一基石上构建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他们的社会背景、文化程度、消费能力、喜好志趣以及身份的建构都来源于此。对于后工业社会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解释力显得不足。佛氏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的划分,基础为“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及其雇佣的工人”这一基本框架。大部分创意阶层在物质层面上既不占有,也不控制巨额财产。他们的财产来自于无形资产——创意。
尽管创意阶层成员尚未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但是,事实上,他们拥有非常相近的品位、旨趣、愿望、偏好和习惯等。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创意阶层并不像工业化时期的工人阶层在全盛时期时表现得那么明晰,但是,其阶层的共同性已经逐步显现并得到加强。
创意阶层由两种类型的成员组成:超级创意核心人群和专业创意人群。前者包括计算机与数学类职业、建筑与工程类职业、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职业,教育、培训和图书类职业,艺术、设计、娱乐、休闲、体育和媒体类职业。后者是指管理类职业、商业与财务运营类职业、法律类职业、医疗与技术类职业、高端销售与销售管理类职业等。佛氏把最具创意的工作定义为创造易于传播并可广泛使用的新形势。例如,设计一种可以广泛制造、销售与使用的产品,或者是提出一种可以在众多领域中应用的理论,抑或是创造出经久不衰的音乐等。这些是核心创意人群的常规工作,并且从中获得报酬。除了解决问题,他们还有责任去发现问题。
与超级核心创意人群相比,佛氏认为,专业创意人群集中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类、卫生保健和工商管理领域。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还利用广博的知识体系来处理具体的问题。胜任该类工作,通常需要接受较高程度的正规教育,因此,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尽管他们会不时创造出用途广泛的方法和产品,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基本工作。他们需要不断做的事情是独立思考。他们用新颖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比如,医生、律师和经理等,他们会采用这种工作方式去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参与测试并改进新技术、新方案和管理方法,甚至尝试独立研发。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研究工作时,只要经历一次跳槽或升迁,就可能会跻身于“超级创意核心”群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易于传播并可广泛使用的新模型。
佛罗里达领衔的研究团队以美国统计局标准职业分类为基础,把参与劳动生产的成年人分为四类:农业阶层、服务阶层、劳动阶层以及创意阶层(超级创意核心人群和专业创意人群)。以此为基础,考查美国近百年来的各阶层变化。他们发现:美国的创意阶层大约包括3830万名人员,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0%。创意阶层的核心是“超级创意核心”,是指那些直接从事创意活动的工作者们。其人数为1500万,占总就业人数的12%。“超级创意核心”阶层包括科学与工程、计算机与数学、教育、艺术、设计与娱乐等从业者。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传统劳工阶层共有3300万成员,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该成员包括生产运营、物资运输、修理、维护与建筑等从业者。服务阶层人数为5520万,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3%。该阶层由低技术、低收入、低自由度、低教育程度的从业者组成,如卫生保健员、餐饮服务员、私人护理、低端办公室工作人员等。
3 创意阶层的价值观特征与流动
人们在价值观、行为准则与习惯方面都发生了重大且深刻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反映出创意阶层的崛起。佛罗里达从三个维度对创意阶层的价值观与行为特征进行了概括。
其一是个性化。创意阶层成员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与自我表达的倾向。他们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指挥,抵制传统的集体性规范。越来越多的个体不服从组织化准则。创意阶层试图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他们创意精神的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动准则。
其二是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重视精英任务所具备的实力,这是怀特所提出的“组织人”阶层具有的一种品质。创意阶层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他们不再以挣钱的多少或经济等级高低作为衡量自我的标准。金钱可以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但是,金钱不能代表全部。
其三是多样性。多样性是该群体的价值观的基本标志,他们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党派、性取向、外貌等来划分等级。
前卫学者们的想法总是异曲同工。克拉克对后工业城市研究后发现了相似的新兴群体,他用“新政治文化”(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的理论阐述了该群体的价值观与行为特征。他认为,随着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 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时代,大批具有更高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在研究和管理领域内就职的人们正成为社会中坚。他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坚”,在价值观上表现出一种“新政治文化”。这种新政治文化有以下一些特点[7]:
(1)传统的左翼-右翼、自由派-保守派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具有新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在社会问题上往往更多表现出自由派或左翼的倾向,比如,关心弱势群体,支持女权运动,对同性恋者认可,主张宽容的基本人生态度。但在经济上他们则往往倾向保守,比如,主张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法则引导经济增长等。因此,在价值观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即价值观本身可以是多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2)具有新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人们,以及代表他们的政府,对具体的城市问题的关心超越了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关心。而在众多的城市问题中,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又超越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
(3)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分化多基于社会政治的群体因素,如阶级、种族和党派等。而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社会分化(Cleavages)则更多基于非政治的个体因素——教育程度和性别的差异所引起的分化。由于注重个人的差异,社会个人主义,随同市场个人主义一起,有膨胀的趋势。
(4)与这种独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传统的等级式的政治组织(如政党)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而掌握了更多知识的居民作为个体在参与决策的愿望在上升。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高学历、高收入的中青年群体中。
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佛罗里达曾经开展一项“城市舒适物(Amenity)设施与创意人才居住选择”的研究。当时,匹兹堡的创意人才外流引发了有关当局的重视,并委托他进行研究。他们大胆推测:是否可以通过投资艺术、文化和土地保护等措施,来帮助扭转人才外流的趋势。
结果发现,体现特定生活方式的舒适物设施对需要高技能创意人才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原因在于:高技能创意人才的收入较高,有能力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位经济学家多拉·科斯塔(Dora Costa)和马修·凯恩(Matthew Kahn)的研究表明,高收入的“创意型夫妇”在居住地选择上,更青睐拥有高水平生活设施的地方[8]。佛罗里达的研究也清楚的表明,许多城市长期以来将城市舒适物(Amenities)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工具。城市当局和领导者动辄就会支付数十亿美元用来兴建体育场馆、购物中心、文化中心、娱乐休闲设施来提升自己的形象。这说明,后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在选择居住地方时,相当看重生活需要或生活品质。
佛罗里达同时指出,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舒适物设施,创意阶层更易被那些活泼随意和分布于街边的设施吸引。克拉克对芝加哥的研究揭示了舒适物设施的“新功能”,他们将城市看作是“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 Machines)[9]。格莱泽完成的一项更为细致的研究,为克拉克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们将城市的这种变化称为“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转变”。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城市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城市在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能力上来[10]。随着高素质人群的不断壮大和日趋富裕,企业和家庭等组织的流动性不断加强,城市构建对个体和组织的吸引力的设施重建与塑造变得尤为重要。
无独有偶。佛氏发现了发表在《经济学人》上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酷”的地理分布(The Geography of Cool)①,从纽约到柏林全世界所有扮演“文化和时尚中心”角色的城市,成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催生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领先区域。为了检验这个观点,佛罗里达和他的研究生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从审视城市气候、专业运动、娱乐活动开始,特别区分了规模较小的街区舒适物设施(便利店、社区服务中心、市民组织等)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博物馆、歌剧院、运动队、交响乐团、芭蕾舞团等)。
结果发现,这些城市舒适物设施、活动与人群等组合场景特征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非常大,在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注意的是,在吸引创意人才和构建高科技产业方面,小规模舒适物设施表现出独特的优势[11]。比如,生气勃勃的街区生活,随时可用的户外娱乐设施和休闲文化中心。佛罗里达以奥斯丁市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该市当局正在有意识地构建一座足以吸引创意人才和高科技企业的城市,尽管该市没有全美主要的体育赛事和专为传统“高品位人士”娱乐的世界级文化机构,但是,他们拥有非常完善的户外娱乐休闲设施、生机勃勃的社区文化中心和各种市民组织与活动等。
4 吸引创意人才的政策转变: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
中国城市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市化率从1978年为17.9%增长到2017年约为58.5%;城区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增加到2017年的80多个。世界城市、国际性城市和区域城市群等构成了中国目前城市发展的框架和目标。然而,当讨论现有的“中国模式”时,我们始终绕不开世界工厂、人口红利、出口加工等称谓。
中国制造业长期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主要处于全球工业链附加值部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著名的国际品牌。中国本土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再加上,传统产业对能源要求高,对环境破坏力强,这种经济结构绝对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过去几十年,低廉且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是,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劳动力过剩时代已经开始转变,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按照佛罗里达的理论来看,中国要想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打造创新型城市,以便在未来的全球竞争获得优势,就必须培养和吸引创意阶层。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意人才红利”,从“招商引资”转到“招才引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将是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2]。
佛罗里达还指出,美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四个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与服务业阶层二者共同构成了第三产业人口。纽约、伦敦、洛杉矶、芝加哥、东京等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80%以上。而北京的这一比例为70%,上海这一数字不到60%。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很多人都意识到中国缺少第三产业。事实上,这个差距主要源于缺少创意阶层。同时,创意阶层的崛起是基于高品质工作、生活的要求,服务业会连带发展。这就要求城市领导者们对城市场景的塑造和更新,因为它对生活品质和城市品质的提升至关重要,也是吸引创意人才的重要因素。
创意时代人口构成模式和社会格局的改变,人口流动性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创意。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是工商业聚集吸引人群,创意时代是创意智慧向创意人才喜欢的地方聚集,人力资本集群远比公司集群更重要。无论对中国国家总体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应该注意到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性空前加强,创意人才将跨越国境和地域,聚集到适宜其发展的地方,并为之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提升。这提醒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创意人才的全国化、全球化、跨区域流动不可阻挡,需要对内开放人口流动体系,对外促进全球创意人才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如佛罗里达所强调的那样,吸引创意人才的关键在建设满足该群体偏好的环境,尤其指出的是,人文环境比商业环境更为重要。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针对创意阶层撰文指出, 对于中国大城市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来说,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来塑造城市场景,提升地方品质,吸引创意人才,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
首先,流动性加速了创意的产生。创意阶层拥有波西米亚人崇尚自由的天性,他们喜欢体验丰富的迁移,寻求“准匿名生活方式”,并在流动中启迪创新。因此,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重庆、杭州、南京等这些大城市,需要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以世界眼光来吸引、争夺全球的创意人才。对外,要面向国际,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和外国友人;对内,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和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吸引和创意人才聚集。
其次,塑造和更新有利于推动创新的城市场景,包括社会文化和地域环境。在美国,创意人才超越了种族、国别、性取向,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旧金山SOMA、西雅图先锋广场、纽约SOHO等区域。这些地方的共同之处在于:提供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比如,便利商店、公园和公共交通,真实参与感的剧场、音乐艺术、咖啡店等。因此,吸引创意人才的社区绝不是那些还在投入大量社会资本建立的大剧院、大型购物中心、体育场地和机场等。这一点十分值得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部分城市领导者,去思考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家园。因为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些城市重复建设着各种大型场馆,也一直认为良好的基建能带来投资与经济增长,但是,却疏忽了吸引创意人才的社区环境。因此,塑造多样、开放、宽容的城市场景,是吸引全球创意人才的必要条件。
最后,佛罗里达定义的创意阶层向往的环境与所谓的“美国梦”非常相似,但是,从城市文化与美学的角度相比,其中确实有不利于创意发展的部分,比如,相对因循守旧、缺少开放心态、人际关系复杂等。不过,崛起的中国,有佛罗里达所没有提及的吸引创意人才的优势。既然创意人才有强烈的实现自我愿望、丰富的体验,而中国恰是充满无限机遇和创造新事物的地方。尤其注意的是,吸引外来创意人才,要留住他们来真正提升创意产业,最终还要依赖城市的人文环境。总之,借助城市场景规划与建设,提升地方质量,吸引创意阶层,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是一项新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该文章刊登在2000年4月的”The Economist”期刊上,网址:http://www.economist.com/node/30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