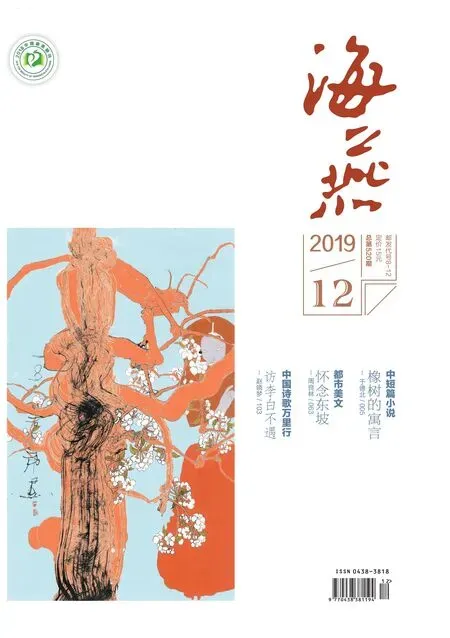我叫胡凯
我叫胡凯,春城日报社专门写时政新闻大稿子的副总编辑,我能和市领导说得上话,也能和著名企业家拉上关系。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每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口若悬河地分析时政总能博得一众人等的追捧和夸赞。我喜欢女人,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源于男人对女人生生不息的热爱,我有万花丛中过半点不沾衣的能力,各种类型的女人都能和我保持着长久而美好的交往,追逐女人对我来说就像拿笔写字一样轻松随意。
当然,我也有失手的时候。在一次社区调研中,我结识了社区妇女主任戴平—— 一个四十一岁的未婚老姑娘。我当着她的面口若悬河,唾液乱飞地卖弄着时政和文学,她躲在眼镜片后的一双“纪检委眼睛”流露出的全是轻蔑和不屑。正当我质疑自己对老姑娘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吸引力时,她偷偷塞给我一张写着她电话号码的纸条。然后我们就一夜情了。从那一天起,我心满意足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我四十岁了,至今未婚,也没有固定的性伙伴,我喜欢女人却不喜欢被女人羁绊。一脸正派的戴平让我对自己的将来担忧起来。
在报社走廊里,我遇到了报社一把手程磊。在热情仰望程总的双眼时,我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会笑了。
我努力牵动嘴角,试图在脸上摆满热情,可是不行,面部僵硬的肌肉在用力牵拉下呈现出了怪异和尴尬。这些年,我最出色的能力就是善于察言观色,精通左右逢源。今天,面对程总,该有的热忱和取悦统统使不上了,程总神情严肃地上下打量着我,不友善的眼神让我瞬间意识到:问题相当严重!
拎着黑色公文包的刘大力踩着上班时间走进办公室。他看上去心情不错,打着口哨,悠闲地整理桌面,不时撩起眼皮看向我这边。“胡编,有啥心事啊?整得这么严肃。”刘大力讨好地冲我挤出笑容。
“这个是给您的……”背对着办公室房门,刘大力神神秘秘地在我半开的抽屉里塞进了一个红包,故作神秘地说,“大江湖的生态农业这几年效益挺好,企业方面希望多多宣传。”我一改往日收到红包时的喜悦,一脸严肃地盯着眼前的刘大力,冷脸思忖的神色让他感到了紧张和不安,他快速退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嘟囔着,“大江湖的生态农业搞得不错,还不错……”
我虎着脸从刘大力身边走过,一脸的严肃劲儿让刘大力心虚得直冒汗,实际上,我比他还心虚,因为我不会笑了。
我随后开车去了趟医院,医生诊断我是因为晚上贪凉,一直开空调睡觉,导致了面瘫。
回到报社地下停车场时已是中午,将车停稳熄火后,我没有马上下车,独自在车里神伤起来。我一脸僵硬、神情绝望地盯着汽车前风挡玻璃,在我的车前停着一辆路虎车,是春城日报社的一枝花李季一的车。过了一会儿,正当我准备下车时,程磊和李季一鬼鬼祟祟地突然出现在视线里,我下意识地低下身子。过了片刻,我悄悄抬头朝路虎车望去,看到路虎在有节奏地晃动着……
李季一人长得美,习惯画着一对高高挑起的细眉,眼角吊着春风,派头十足,爱慕她的达官老总排到了春城五环之外。李季一这种女人和靠爬格子起家的我天生格格不入,我的才华在她看来全是酸腐,而我对她浅薄的文字能力和来路不明的财富从来也是嗤之以鼻。
我躲在车里不敢露头,眼前不断浮现出李季一的路虎车不停晃动的画面,我不禁担忧起来。李季一惦记我副总编的位置不是一天两天了,就目前她和程总的关系,用“危机四伏”四个字形容我的处境并不为过。
李季一和程磊“办完事”后就走了,我总算可以在车里舒展开身子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又是戴平。屏幕上跳动的电话号码像一串串符咒令我心烦,我愤愤地关掉手机。此刻,我一心想回到彭城老家,去找马婆婆快点治好我的面瘫。
我是地地道道农村出来的孩子,这些年我过得一点不轻松,自卑心像野狗一样如影随形地跟随我了很多年。大学期间,为了不让同学们瞧不起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土包子,我边打工边学习。大二下学期,我同时接下了四份家教,除了在学校上课、睡觉外,我一天到晚穿梭于辅导学生当中,用辛苦换来的补课费一点点缩短着我和城里同学的差距。那几年,兜比脸干净的我一天天敏感得要死,心里仿佛总是揣着个兔子,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张惶得不知所措。
开车回老家彭城的路上,这些年走过的辛酸和不易一件件跳进我的脑海,汽车行驶在高速路上,成排的树木向后方倒去。
憨头憨脑的韦二宝是我的家教学生,他爸爸是个大老板,至于到底有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家住着四层独栋别墅,楼下车库有直达楼上的电梯。我在农村的家还赶不上韦二宝家的一个卫生间大。初次走进他家,我惊得后背嗖嗖直冒冷风,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最富有的家庭不过是多养几头猪罢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阔绰的家庭,我大开眼界。很快,我学会了左右逢源,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当然,这里不排除我中文系高材生的天资聪颖,更多的是我高人一等的情商。大学毕业前夕的关键时刻,我用打工赚的钱疏通了系领导,在系领导的大力推荐下,我成功留在了春城日报社。虽然我还是很穷,但能拥有报社这份工作对于我这个土得掉渣的农村学生来说,已经实属不易了。
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我的改变是彻底的。我学会了穿西装,学会了抽雪茄,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吹牛逼。城里人除了命好,比脑子,我一点不差。贤人每日三省,我当日省三千,靠着这份执着和信念,我的工作和生活一天天改善了。
我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上大学期间,我爱上了师姐方子。方子是个上海姑娘,吴侬软语让我十分着迷,那段青葱岁月里,我收获了方子的爱情,每次和方子约会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方子先我一年毕业,临毕业时,她和我信誓旦旦地约定,等我毕业后就去上海和她会合,我们一起写作,一起生活。虽然我没钱,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痴迷。大学期间,我的作品就屡屡见诸知名杂志。方子说她爱慕我的才华,可是,没等到我毕业,方子就和一位部长的儿子结婚了,才华和爱情在权势、金钱面前一文不值。
回彭城的路上一直阴云密布,总有要下雨的感觉,我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些年,我拼命工作,一直想混出点样子给方子看,方子可能并不在意这些了,我的婚事却拖了下来。我不缺女人,方子带给我对女人的认知总是让我对女人愈近愈远。对于这个强行扎进我生活的老姑娘戴平,我真是又气又恨,自己的好运气极有可能是在和她的一夜情中灰飞烟灭的。想到这里,我不禁心生懊恼,汽车快速驶出高速匝口。
戴平和我一样也错过了结婚的最佳时期。按理说,她和我应该有着同病相怜的感觉。在城里,没结婚的大龄男青年被冠以“钻石王老五”的称谓,没结婚的大龄女青年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们总是拿着道德标尺丈量别人,那些貌似坚强实则虚弱的大龄女青年都有着美人迟暮的焦躁和穷途末路的绝望。戴平一定是觉得好不容易钓到了我这个“钻石王老五”,轻易不能撒手。想到这里,我心里堵得满满的。不只是担心被她死缠烂打,更重要的是和她一夜缠绵之后,我就厄运连连,眼下的面瘫就让自己修练多年的八面玲珑武功尽废。
三天前,戴平带着个大行李箱一脸严肃地出现在我家门口,完全一副女主人的派头,她坐在沙发里,上上下下打量着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邋邋遢遢的我。
“你家多少平米啊?不是租的房子吧?”
“结婚前得好好装修一下吧,这也太旧了。”
戴平丝毫不顾忌我的态度,自言自语地从这屋走到那屋。我哭笑不得、懊恼万分地窝在沙发里,戴平翻飞、快乐、急于攻城略地的身影搞得我昏头胀脑。
汽车趁着夜色一路驶去,彭城就在眼前。
彭城胡家村两山夹一河,青壮劳力这几年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留下来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胡家村建村以来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全村上下对返乡回来的我都十分热情,乡亲们不约而同地认定我在城里做了大官儿,纷纷盛情邀请我到家里做客。见到了绷着脸不会笑的我,乡亲们心里也犯嘀咕,“这小子架子端得还挺大。”乡亲们的心思,我一目了然,想到这些年我带着面具混迹春城新闻界,靠着吹牛逼、拍马屁混下的资本眼瞅着就要断送了,我的紧迫感陡然生出。
“老凯在家吗?”孙婶是村子里的活络人,前几年她托我把她儿子送进报社食堂打工。儿子在城里站住脚给孙婶长了不少面子,她对我一直心存感激。孙婶踩着细碎的步子走进屋,“老凯,婶儿刚包的饺子给你端来一碗,趁热吃。”孙婶亲热地拍打着我的肩膀,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努力调整神色,逃避着孙婶的眼睛。“咱村出了你这么个文化人。多给咱村人长脸啊,你看看周围四村,哪个有啊!”孙婶并不在意我的面无表情,自顾自地笑着。她的这番话对我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我用一张冷脸看着眼前的饺子一口也吃不下。
“屋子长时间不住人了,得经常开窗通通风。”孙婶说着,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隔壁院子里一个看起来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正蹲在地上玩。看到小女孩,孙婶边支窗户边自言自语,“丫头一天天大了,守着个老光棍像什么话啊!作孽啊!”
隔着一趟低矮树杈搭起帐子的隔壁住着村子里的老光棍胡六叔。今年六十多岁的胡六叔年轻时家里穷,一直没说上媳妇,听说前些年胡六叔捡垃圾时捡到了一个襁褓中的小女婴,估计蹲在地上玩的小女孩应该就是他捡来的那个小女婴长大了。我暗自思忖着孙婶话里的意思。不知不觉中天黑了。
城市里住惯了,会想到乡村过过散淡的日子;乡村住得久了,又会生出无聊和寂寞。这里没有人计较我的面无表情,我也无需在什么人面前端出虚情假意,整个人很轻松,但我还是会时时想起春城。我知道,自己终究要回到那里。
马婆婆是胡家村的老人了。打我记事起,马婆婆就一直给村里人看病,谁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谁身子不熨帖,谁家产妇需要接生,都会找到马婆婆帮忙。没人知道马婆婆从哪儿学的医术,也没人质疑过马婆婆的医术。这些年,马婆婆担负着这个偏远山村“赤脚医生”的重任。说来也怪,很多医院没治好的毛病,用上马婆婆的土办法却能痊愈。小时候,我生了一场伤寒病,连续高烧了好几天,看过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不中用了。我爹不死心,背着我找到马婆婆,在马婆婆的炕上,我昏睡了三天三夜,在那三天三夜里,我仿佛腾云驾雾一般,身边各种颜色的羽毛,各种颜色的云朵。一会儿在大火中炙烤,一会儿沉入冰冷的水底。昏迷中,我依稀记得,马婆婆一双粗砺的大手反复摩挲着我的后背,一股暖流在我的身体里流窜。苏醒后,我的手被马婆婆紧紧攥在手心里。
小时候,我常常跑到马婆婆家里玩,吃着马婆婆炸的炉果,在她的手背上捏“城墙”,马婆婆手背上松弛的皮肤被我捏起来像座站立的“城墙”,“婆婆的手背有城墙!”马婆婆摩挲着我的脸蛋儿,慈爱地说,“婆婆的手心儿有凯仔啊!”
看到面部僵硬不会笑的我时,马婆婆先是一愣,“凯仔,你这是怎么了?”马婆婆关切地问,我无比沮丧地向马婆婆道明原因。听我说完,马婆婆捏着我的手给我搭了一会儿脉,“婆婆给你几服药,你按时吃。”马婆婆从柜子里拿出了药递到我手上,又轻声说,“无端不必寻累啊!”
我错愕地看着马婆婆,被点了死穴一般。
从马婆婆家回来的路上,我的电话铃声响了!一直沉浸在马婆婆话里的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电话铃响了好多声,我才意识到接电话。电话那头李季一急促的声音传来,“胡编,您跑到哪儿去了?有个女的来报社来找您了,”不用说,一定是戴平,她找我找到单位去了。“那个女的说你骗了她的感情,现在又一走了之……”此刻,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电话那头李季一幸灾乐祸的神情和嘴脸,这家伙一定以为我这个绊脚石可算是栽了,她的机会来了。
接完李季一的电话,我忧心忡忡地往家走。一进院子,看到了蹲在地上玩的小姑娘,我好奇地走了过去。小女孩正在用树枝拼凑跷跷板,我捡起一枚小石子放到女孩拼凑好的跷跷板上,“坐过跷跷板吗?”我看着小女孩问。“没有。”小女孩拿开了我放在上面的小石子。“城里的学校都有跷跷板,很好玩的!”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小女孩一声不吱,默默地摆弄着手里的树枝,突然,她放下手中的东西,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问,“叔叔,人可不可以不长大,就一直这么小?”“那怎么行呢!孩子都是要长大的。”我说。“可我不想长大,爷爷说大女孩了,放在家里就有人说闲话了。”
这两天,胡六叔突然决定要把小女孩送到城里的福利院,事情闹到了大队部,成功盖过了我返乡的影响力!
胡六叔的趴趴房被妞妞收拾得很干净。炕梢顶头的地方,胡六叔给妞妞搭了个小铺,白天折叠起来,晚间放平,妞妞睡在上面。妞妞背对着胡六叔洗头发,一动一动的肩膀下耸起了小小的乳房,妞妞有大姑娘的样子了。胡六叔“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烟丝里裹上了一丝女人的甜腻。
这几年,村子里胡六叔和小女孩的闲话多了起来。村子里男女老少晚饭后喜欢聚到村头大槐树下纳凉聊天。这里也是村子里大事小情的广播站,村子里哪怕谁家死了一只鸡也会在这里发酵传播,孙婶当仁不让地成了这个民间广播站的“站长”。和村民们叽叽喳喳说笑的孙婶一抬眼,看见了领着小女孩朝这边走来的胡六叔,孙婶眨巴着眼睛示意大家不要说话,大家面面相觑掩饰着心底的好奇。胡六叔一定是感觉到了人们眼神中的恶意,皱起眉头,带着小女孩走开了。
“老牛吃嫩草啊!”孙婶捏着嗓子冲着胡六叔的背影怼上了一句。人们哄笑起来,胡六叔的背影顿了一下。
夜幕降临,胡六叔家的窗口透着暖意。小女孩夹着菜送到胡六叔嘴里,胡六叔疼爱地抚着小女孩的面颊。看着这对互相关爱的爷孙俩,我想起了我的家教学生韦二宝。富二代韦二宝的起点是妞妞努力一生也未必能够到达的终点,他们之间长长的差距,我无能为力,胡六叔更无能为力。想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
胡六叔已经很老了,被汗水打湿的白头发耷拉在前额。小女孩的到来给孤身一人的胡六叔带来了生活乐趣。这些年,胡六叔费尽心思地让妞妞吃好穿好,妞妞喜欢裙子,胡六叔就到村子里挑鸡粪卖,攒下钱给妞妞买裙子。挑鸡粪是个力气活,六十多岁的人了,牵着个小女孩沿村卖鸡粪,遇到认识胡六叔的老伙计,都会多给六叔算点钱,知道一个孤寡老人养活个小女孩有多不容易。
今年天旱,孙婶别住了浇地的水流,水顺势都流进了孙婶家的地里,地势较低的胡六叔家的地干得裂了缝,胡六叔拿锹挑开了水流,孙婶就骂到了家门口。
“你一个老光棍,带着个小姑娘,哎呦喂!真是好说不好听啊!”孙婶掐着腰大骂,“凭什么还有脸说我占了公用水源!水流拐弯怨我啊!”
六叔气得浑身发抖,眉毛胡子几乎要抖到一起。孙婶骂声不断,而且越来越秽不入耳,小女孩吓得躲在胡六叔身后,一个劲儿地哭。
“闭嘴!”胡六叔气得抡起铁锹打孙婶,邻居们纷纷过来拉架,这才拉开了情绪激动的两个人。
胡六叔坐在大队部的椅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孙婶这么一闹更坚定了胡六叔送走妞妞的想法。
“六叔,送走妞妞,您老可就一个人了,太孤单了。要不村里出一部分钱资助妞妞上学,孩子还是留在您身边吧。”村书记劝着六叔。
胡六叔掐烟袋的手指一直在抖,几次点烟都没点着火。我拿出火机靠近六叔的烟袋,看见了六叔眼角噙着泪水,担心我察觉,老人边揉眼睛边说,“送走吧!送走吧!姑娘家大了,不留了。”一颗浑浊的泪珠掉在胡六叔的手背上,打个旋,砸在地上。
胡六叔这几天见到我时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老凯,过来坐坐。”
“噢。”我应声走进胡六叔的屋子。
胡六叔迟疑一下,问,“听说城里有专门收养孤儿的福利院?”
“有。”我用余光扫了一眼小女孩,小女孩噘着嘴躲在一边。
“哦,那里能让孩子上学吗?头疼脑热的有人管吗?”胡六叔急切地望着我。
“能啊,六叔。”
“那就好!那就好啊!”胡六叔一连应声道,“你在城里见识多,帮妮子找个信得过的福利院,送走吧。”颤抖的声音出卖了胡六叔,我试图说服他,他扭过头,不再说话了。
胡六叔执意要送走妞妞,谁劝也不行。
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又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最知道钱的重要性。春城日报社一个信息平台建设投入了几百万,没换来预期效果,然后无人打理,就那么一放,浪费得理直气壮。当胡六叔在我面前掏出两万三千六百元钱的时候,我感动地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老凯,这些年我攒了这些钱,都给妞妞带上。到城里万一有个什么需要,用得上。”
“六叔……”
回到胡家村已经有些时日了,胡六叔和妞妞的事情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精力。六叔家暖黄的灯光闪烁在山村的夜色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凡之美。山村的夜色像黏稠的汁液一样四下流淌,裹在夜色里,我睡下了。 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
“老凯,老凯,快开门。”胡六叔大喊着我的名字,“快开门啊!老凯。”我光着脚跑到门口,看到了满头大汗,神色慌张的胡六叔。“六叔,怎么了?”“妞妞高烧晕过去了,快去救她!快去啊!”我快速穿上衣服,跑到六叔家,看到了床上发烧抽搐的妞妞。我二话没说,背起妞妞就往马婆婆家跑。
马婆婆又是按摩又是喂药,忙了一大通,妞妞始终双眼紧闭,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赶紧送孩子去医院,长时间昏迷,脑子就完了。”满脸大汗的马婆婆焦急地对我说,“快开车把孩子送到镇里的医院。”马婆婆从来遇事不惊,见她这样着急,我知道妞妞的状况很危险。背起妞妞,我朝着车停的地方跑去,马婆婆和胡六叔两个老人蹒跚地跟在我身后。
一路上,马婆婆怀里抱着妞妞,怕妞妞神志不清咬到舌头,马婆婆撩起衣襟让妞妞咬在嘴里。夜色里,我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和一个正在发着高烧的孩子向镇里医院高速驶去。
经过医院大夫及时抢救,凌晨三点多钟,妞妞脱离了危险。医院走廊长椅上坐着丢盔卸甲、精疲力竭的三个人。这时,我才注意到马婆婆衣襟前被一大片血迹浸透了,“婆婆,你的手怎么了?”来时怕妞妞咬到舌头,马婆婆来不及在妞妞嘴里塞衣物,情急之下,把手背伸到了妞妞的嘴里,看到马婆婆血肉模糊的手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带妞妞去城里吧。”一脸疲惫的马婆婆望着病床上沉睡的妞妞对我说道。
马婆婆和胡六叔围在病床旁照顾妞妞,妞妞大睁着眼睛看着他俩笑。站在一旁的我看着胡六叔和马婆婆脸上温暖的笑容,这笑容竟十分打动我。此刻,我对自己十几年来的曲意逢迎着实厌恶透了。我期待着他们三人脸上展露的笑容,这笑容让我通体温暖,六脉顺畅。我模仿着胡六叔和马婆婆,牵动嘴角,终于笑了出来。
这几天,我心情大好,面容也和颜悦色起来。山村的田埂坑洼不平,田埂里的小草伸出手,轻抚我的脚背,我张开双臂,大口呼吸着山村里清新的空气。混迹春城新闻界十几年,热闹起来不觉得怎样,在老家静了几天,突然感到很疲惫。毕业时的豪情万丈淹没在虚情假意、曲意逢迎的日常当中,互相吹捧说假话成了我的生活标签。胡六叔对妞妞的爱,马婆婆“无端寻累”的箴言,让我在这个偏远山村里,发现了爱和关怀。
我的电话铃声又响了,是戴平打来的。戴平说了很多话,我一句也没记住,我只记得我要带着妞妞回城了,要帮她找个合适的福利院,供她读书。我也要结婚,我可能会相信戴平吧,相信别人也是给自己机会。我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还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名利场,也许,我会因此失去很多,不过没有关系,马婆婆和胡六叔在我心底装下的对这个世界的善意会一直陪我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