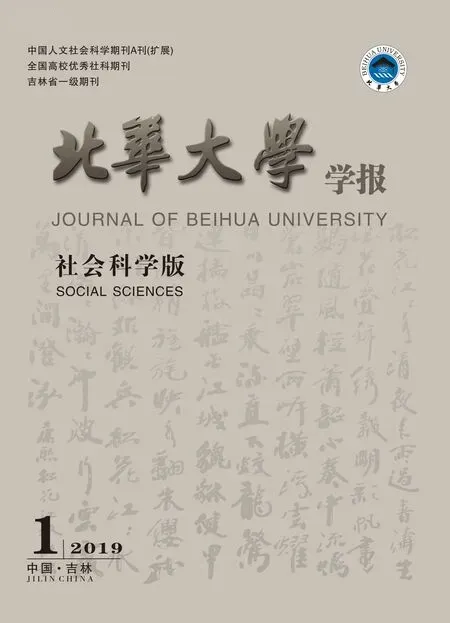《紫钗记》的送别空间书写与情感抒发
刘梅兰
一、引言
“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1]随着嘉靖、万历年间陆王心学的日益兴盛,程朱理学主导地位受到强大冲击,社会掀起了思想变革的风潮。在“主情”文艺思潮席卷中晚明文坛的社会语境下,戏曲作品以真情抒发为美,主张“言情”“写情”。才子佳人剧风靡一时,所谓“传奇十部九相思”[2]也就不足为奇了。洪升认为传奇作品欲胜出,非“言情”不可,即传奇戏曲语意指涉情,内容表达情,叙事结构创设适合抒发情,以顺乎人情,“独抒性灵”[3],强调传奇叙写男女真情的文学功能。
古典戏曲中经典离别场面的呈现,常常与具体空间相结合,通过比兴移情于景,刻画角色对空间景致的感受,来表现角色在特定时空下的心绪情态与内在心理世界。著名的如《西厢记·长亭送别》《汉宫秋·灞桥饯别》《梧桐雨·秋雨梧桐》《长生殿·埋玉》等,都是通过对季节特征明显景物的描绘,寓情于景,将主观情感与客观之景融为一体,形成情感内蕴丰富的情境空间,来呈现剧中角色伤情别离的悲苦凄伤之情及其对真情的追求。
《紫钗记》中也不乏离别之情的书写。剧中男女主人公离别有两次,一是李益赴洛阳参加春试,二是李益参军远赴玉门关外。这两次别离,都给霍小玉带来了无限悲情愁绪。尤其是李益远赴玉门关,前途难料,归期不定,更让霍小玉如历生离死别,伤情难抑。曲家缘情布景,使物我情融,在花院、家门、灞桥等具体空间中,书写别离之人,特别是女主角霍小玉哀怨、悲戚、伤情、不安、期盼等诸种情感与心绪,形塑了霍小玉痴而不舍的钟情形象,构建了足以创造审美意境的送别情境空间。
存在于相同空间的主体,性别不同情感体验亦不同。无论是短暂的赴试别离,还是从军塞外的长久离别,男女主角的情感体验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紫钗记》送别空间建构与性别的强化、区分和塑造具有重要的联系,送别空间的面貌、特征等也因此而呈现出性别化的特征。
《紫钗记》送别空间场景构建,不仅尽情书写了剧中人物的离别心绪情态,形塑了鲜明生动、立体传神的人物形象,还唤起了受众广阔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空间联想,使他们在情感升华中对剧作至情理想产生更深入的体悟与思考。《折柳阳关》送别场景和情境空间书写,也藉以折子戏的形式久演不衰,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二、花院空间:春闱送别惹情愁,花院盟誓言至情
以空间区隔为特征的传统性别文化,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内存的意识形态,也是再传统不过的意识。中国古代社会强调风俗教化之本,“男女大防”的性别空间区隔是政治管理和风俗治理的核心所在,女性的活动空间基本被限制在闺房、花园等家园之内。女性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无论惜春、悲秋,还是念情、思远,基本停留在深闺之内、梳妆台前、亭台楼阁。社会上的大多数空间是排除女性的,大家闺秀更不宜抛头露面,即使对普通底层女性而言,社会空间限制也是非常之多。这种性别空间区隔,虽然事实上并非绝对如此,却是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成了才子佳人爱情故事叙事的前提和基础。
“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性别化格局,使男性可以在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女性只能待在家庭私性空间中。唐代,后花园成为家园的一部分,也因此成了性别空间的模糊地带。作为私人宅邸,后花园成为女性亲近大自然,抒发情感的所在。另外,后花园也是男主人陶冶性情的场所。这又为古典爱情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形塑了哀怨、感伤的女性审美形象。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4]才子佳人婚后恩爱幸福,正当夫妻二人沉浸幸福欢愉之际,书童秋鸿传来了天子留幸东都洛阳,开科取士,京兆府起送的消息。李益吩咐秋鸿“快安排行李,渭河登舟也”,言语间尽显热衷功名的迫切之情,并没有表现出对妻子的留恋不舍,但霍小玉却不无担忧惆怅:
〔旦〕新婚未几,明日分离,如何是好?李郞,你看我为甚宫样衣裳浅画眉?只为晓莺啼断绿杨枝。春闺多少关心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妾本轻微,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生。(第十六出《花院盟香》)[5]67
艺术的魅力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入探索和真实描摹。霍李二人花院游赏,满心愉悦,但恰在这特定时空交叉点上,却面临别离,霍小玉情难自已,她心灵深处交织的依恋、伤情、痛苦、忧虑等内在心理和情感,马上多层次多色彩地展示出来。从着装画眉尽现春愁到和盘托出夫婿未必了解的自己内心的隐忧,再到运用典故加以强化,直接展示她欢爱之际愁从中来的痛苦矛盾心态。
李益一心想跳龙门、登金榜,对前途抱有无限憧憬,并信心满满,霍小玉则怕夫君登第后章台问柳,画眉别描。霍小玉的深情依恋和依依不舍,与李益对新婚生活的满足和考取功名的急切,形成了鲜明对比。春闱赴试具体语境下的送别情境空间书写,男女主公心情何以迥然不同?
其实,霍小玉自婚后,内心隐忧就一直存在。这与当时代女性所处的空间隔离状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是男女性别文化差异致使男女主角面对同一事件,情感体验明显不同的一种体现。庭院深深寂寞锁清秋,离别带来的痛苦愁闷,女性的感受才更强烈,甚至女子的感伤悲戚与男儿的踌躇满志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上不乏赴试高中才子移情别恋,被达官贵人招赘为婿,甚至被皇家召为驸马的事例,这是每一个送夫赶考的女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是她们不无担心的内在顾虑。丈夫考取功名,夫贵妻荣,随之而来的荣华富贵令人艳羡,但由此可能导致的高风险和代价又是她们无力承受的。
古代社会性别空间区隔,使女性活动空间相对封闭和狭窄,也使她们的情感更趋细腻,对春花秋月等外界感受更加敏感和深刻。婚前“由得自家心性”,天真烂漫的少女霍小玉,婚后尽管夫妻恩爱,但对这种幸福的长久未来总是心怀忐忑,不免“镇日纱窗里眉尖半簇”。性别空间区隔因而影响着才子佳人的情爱抒发,推动故事演绎发展,突出了女主角的心绪情感,形成了美满姻缘下感伤的女性审美关照。这又与心情欢快的李益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霍二人,才子配佳人,门户相当,李益春风得意,言语间时时流露出来。此处,剧作中李益唱两句,霍小玉才对一句,且透露出“闲”与“闭深闺”的生活情状,隐含深深闺阁,空间狭窄,故生闲闷情愁。性别空间规划、区隔常使女性感到憋闷,李益提议春游半日,虽然没有突破家园空间,但空间毕竟有了一定转移。景随人移,“夫婿前行少妇随”,霍小玉的伤感才略有消解。花间觅道,空间转换,她的言语也多了起来,此时,李益唱两句,她对两句。到了花院,李益提议两人绕花行走一趟,霍小玉的心情随之明快,唱白明显多于李益:
【黄莺儿】〔旦拈花介〕一枝低压宜春院,芳心半点,红妆几瓣,和莺吹折流霞茜。糁香肩,春纤袖口,拈插鬓云边。(第十六出《花院盟香》)[5]66
春天的花院百花竞放,柳莺啼鸣,使霍小玉的身心得到充分舒展,毕现新婚少妇的娇憨情态:
【啄木儿】〔旦〕狂耍婿游戏仙,豆蔻图中春数点。闲心性皱花呵展,绣工夫葡萄几线,却怎的半踏长裙香径远?和你向银塘照影分娇面,怕溜闪了钗头鬓影偏。(第十六出《花院盟香》)[5]66
情景交融,景情相生。春色几许,完全为人物心情所左右。银塘双双照影,尽享二人世界,温文持重的大家闺秀,在花院春色中展现的憨态可掬形象,充分表现了女主角内心的欢愉。
曲家遵循理想主义的情感逻辑原则抒写角色情感,在花院游赏特定情境空间里,霍小玉的所见所闻所感和言语行动,都与霍小玉情真的渴求息息相关,其目的均是为了凸显剧作的“至情”主旨。上述两支曲子对真情淋漓尽致的展现,体现了曲家汤显祖形塑女主角的“知己”情结。霍小玉出身王府,貌美才高,只有像李益这样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风流才俊才能得到她的青睐,才值得她为情付出一切。
当然,从花院游赏对霍小玉情感细微变化的细腻抒写,我们也可以看出性别空间区隔对人性正常需求的压抑。正是性别空间区隔抑制了女性青春活力的焕发,使霍小玉对李益赴洛阳考试产生种种隐忧。毕竟性别空间阻隔,使她婚前对李益的了解只限于门第和才华,新婚不久的她并不能很快就掌握李益的心性、为人等性格特征,以及他对自己情爱的深度。因此,她对二人今后婚姻生活缺少把握,再加上空间区隔所形成的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体验和感受,以及她把爱情婚姻看得高于一切的“至情”理想,才让她内心非常不安。这正是李益觉决定第二天赴试洛阳,小玉倾诉忧愁担心,二人“生死无悔”“指诚日月”花院盟香情境发生的具体语境。
剧中角色进入新的情境空间,又有新的行动。霍小玉恐怕色衰情移,担心“女萝无托”,在浓情蜜意的“极欢之际”,“不觉悲生”,李益“泣叹”而言。从李益的回应情态,可见他内心对小玉的挚爱,不管后来世事、心态怎样变化,都不能否认此境此刻爱情的真挚。而后强调能与小玉缔结姻缘,乃其“平生志愿”,即使粉身碎骨,也不相舍弃,并在素缣之上著以盟约:“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悔。引喻山河,指诚日月。生则同衾,死则共穴。”[5]67
婚姻关系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丈夫的身份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并不会也没有把婚姻爱情看作唯一的寄托。春闱赴试的短暂离别,李益表现得很淡然。他写下誓言,仅仅由于妻子的不舍和担忧触动了他。当然,李益的誓言句句恳切,闻之动人,虽然带着文人特有的含蓄和矜持,却也可与汉乐府民歌《上邪》的誓词相提并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6]这首被誉为“短章中神品”的自誓之词,感情奔放热烈,气势豪迈,感人肺腑,连用五件大自然中不可能发生之事,来表达至死不渝的爱情和忠贞坚定的信念。
李益表明死生与共的心迹,霍小玉珍藏盟誓,以“永证后期”。李益看重霍小玉的才貌,甚至更重美貌青春,而霍小玉热烈追寻的是真情、深情、至情,追求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生死相依。在花院送别情境空间中,她反复斟酌的是对方的心,不断找寻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寻觅情感世界里的知音。因此,李益的表白和盟誓,让小玉心中甚为宽慰,却不能完全消解担忧:
【川拨棹】……怕只怕笺煤字殷,怕只怕笺煤字殷,道得个海枯石烂。嘱付你轻休赸,好花枝留倚阑。(第十六出《花院盟香》)[5]68
山盟虽在,怕经不起时间的消磨,担心他留恋花丛,免不了再叮嘱夫婿几句。这也体现出性别空间的阻隔作用:男女社会地位悬殊,男子有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三妻四妾,甚至拈花惹草,有无限的可能,女子只能闭守深闺,从一而终。确实,如果不是黄衫豪客的介入和侠义相助,《花院盟香》之誓言,恐怕真会如霍小玉所担心的那样,时间长了字迹模糊,变成一纸空文。曲家通过春愁、春游、盟誓等不断转换、前后衔接的情境空间书写,将把情看得高于一切的女主角内心世界活脱脱展现在受众面前。
花院是有情的自然世界,也是情有所归的空间世界,青春女子可以在这里自由放飞自我,展露内心情感。曲家寓情于景,赋予花院春色春景以强烈的主观色彩,然后通过霍小玉细腻委婉的唱词,把送夫君赶考之际内心的牵挂、不舍、惆怅、哀婉、期盼等复杂心绪,以及心字香前的酬愿,收乌丝阑誓言的欢愉心情和巧笑无眠的情态展露无遗。虽则还有些许隐隐不安,但李益书写的山盟海誓,总归让离情困扰的小玉内心渐趋安宁平和。
春闱赴试晨起送别空间书写,同样融入了性别空间区隔书写,面对半月之期的短暂别离,霍李二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心态与情感。李益自恃才子年少,渴望平步青云,一心想跃龙门,标金榜,一展平生抱负。不曾想昨日才山盟海誓慰贤妻,今晨小玉又被愁云笼罩。面对泪眼婆娑的妻子,李益再次宽慰她莫要伤情,等自己夺得锦袍,还她夫人县君封号,夫贵妻荣共携手。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霍小玉的担忧,临行殷殷叮嘱李郎学张敞,画眉只向妻子描,断不可移情别恋。
春闱赴试送别空间中李益期盼登科所表现的自负,是封建时代士子们的普遍心态,本无可厚非。何况面对妻子的担忧,他也以许夫人县君封号相宽慰,生怕小玉因愁渐消瘦。但曲家还是向观众传达了霍小玉对爱情的执着远胜李益的信息,她要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心心相印的真情和相爱相守。李益此时正处在顺境中,还没有展现出一个人在面临抉择时才能显现的个性特征,受众还不能确定李益对爱情坚守的态度。由此,剧情推进由两条线索展开,受众也得以沿着霍小玉和李益对真情的追寻之路,进一步把握霍李“至情”理想的同与不同。
另外,京兆府尹专门设宴,起送李益赴洛阳参加春试送别情境空间书写,也颇值得一提。府尹席间所唱之词充满了勉励和期待:
【长拍】……李秀才,你此去呵,龙蛇砚影,笔生花绕殿晴熏。今日呵,吉日良辰,醉你个状元红浪桃生晕。只望你乌帽宫花斜插鬓,软带垂袍挂绿云。临上马御酒三杯尽,喧满六街尘。香风细妒杀游人。(第十八出《春黄堂言饯》)[5]73
从中可以窥见唐代社会对人才的重视,也暗寓李益的才华和对此次应试的信心。秀才一旦考中状元,身份马上为之一变,乌帽宫花,软带垂袍,荣耀权势随之而来。引人注目,妒杀游人,霍小玉怎能不担心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性别空间区隔下,女子送丈夫赶考的矛盾心态。果然,后来李益杏苑题名,着锦袍赴宫宴,曲江池边醉,协理朝纲、权势擎天的卢太尉即刻想招罗门下,进而招赘为婿。霍小玉的隐忧不无道理。
春闱赴试送别空间书写论述,本应以临行别离为重点,我们却以曲家在此前安排的花院游赏和盟香情境空间书写为焦点和重点来阐释,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但仔细考究我们发现,在性别空间区隔下,霍小玉内心细腻敏锐情感世界的展现才是曲家书写的重点,也是春闱送别空间书写所着力展现的。正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所谓:“夫曲者,谓其曲尽人情也。”[7]
这正是曲家汤显祖着力凸显剧作至情主旨的重要方式,即以描摹情作为剧作抒情特质展现的基础和审美目的,自觉追求曲家自身情志与审美对象间的精神,或与生命境界合一的艺术境界。霍小玉送李益赴试洛阳,放在花院空间书写,旨在使女主角情有所归,所谓“霍小玉能作有情痴”(《紫钗记·题辞》),凸显剧作的至情主题。
三、家园空间:孤鸾娇啼暗幽咽,门楣絮别显情真
李益赴试走后,霍小玉独守幽闺,思夫婿,懒梳妆。一会设想李郎登第荣归,一会忧心他中举后丝鞭别受,做了他人夫婿,或留恋青楼妓院,醉眠平康里,买笑寻欢而忘了花院盟誓。第二十出《春愁望捷》惟妙惟肖刻画了初经离别少妇的心绪情态,可见功名害了多少佳偶,促发了多少人间悲剧。
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捧得很高的南戏《琵琶记》,讲述男主角蔡伯喈为了功名,抛别年迈的双亲和新婚妻子,带着老父亲的殷切期望上京赶考,有幸高中状元,却被牛丞相招赘入府,辜负了灾荒之年历经艰辛磨难侍养公婆的结发妻子赵五娘。好在牛小姐深明大义,蔡伯喈与赵五娘得以团聚,但终不免二女一夫的结局。再如,唐传奇《莺莺传》中的张生,进京考中状元后便抛弃了莺莺。更有甚者,贫寒士子考中状元,为攀附权贵,不但不认发妻孩子,还杀人灭口。如民间广为流传,被改编为京剧、评剧、晋剧、河北梆子、豫剧和越剧等多个版本的秦腔《秦香莲》。虽然秦香莲的故事发生在清代,经学者研究考证,历史上的陈世美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并无杀妻灭子之事,但从此事例却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士子取得功名后,为了荣华富贵,停妻再娶之事屡见不鲜,给结发妻子带来了深切痛苦。
性别空间区隔,还使留守的妻子担忧丈夫赴京后留恋青楼或勾栏瓦肆。中国古代很多戏曲小说都有上京士子在路途或京城奇遇各种女子,短暂停留或长久居留,甚至与之山盟海誓不回还的描写。而且,士子进京参加科举,到妓院召妓是才子风流身份的一种象征。如《紫钗记》改编之原本,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考中进士,“侯试于天官”,就开始“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8]。这说明霍小玉忧心是正常的,好在身边有一个善解人意的丫头浣纱时常安慰小姐:等李益衣锦荣归,戴花冠,坐香车,同荣耀,共享卿卿我我时光,有何困扰情愁。
果然,李益考中状元,荣耀归家,小玉母亲郑六娘喜不迭地安排萧堂画鼓欢庆。“郎君福,夫人命”,夫贵妻荣真相称。霍小玉也欢喜非常,赞夫君英雄,再以司马相如典故强化,李益高中,终将实现理想抱负。趁李郎年少,自己亲把县君领,再用京兆张敞为妻画眉典实,突出表现她更看重夫妻相守的合和美满,而非外在的光环荣耀。当看到门外使官时,霍小玉本能“惊问”,第一反应是状元去哪里,反映了小玉对外界变化的敏锐感受力,事关夫君去处,纤毫不能逃过她的眼睛。表明在欢庆氛围中小玉内心的隐忧并没有完全消除,稍许动静便会在她心中拂起阵阵涟漪,反映的还是她对两相厮守、心心相许至情的一贯追寻。
第二十三出《荣归燕喜》表现霍小玉追求顺乎人性之真情,曲家对“情”和个体意趣神色的细腻描写,又与第十七出《春闱赴洛》送别空间女主角的内在情感书写遥相呼应。昭示着曲家汤显祖回应时代主流情感思潮,戏曲创作自觉以情为出发点与内动力,突出表现真心、真情、真精神和个性心灵特点。霍小玉对真我至情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性别空间区隔,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自我觉醒意识。这与汤显祖剧作对内在精神美的崇尚,对至情的赞扬,对人的正常愿望、诉求的高度肯定一脉相承,亦即曲家所谓“霍小玉能作有情痴”(《紫钗记·题辞》),“我辈钟情似此”(《第一出《本传开宗》)。但是,“言情”过甚,难免流于情欲。汤显祖剧作对“情”的正确拿捏,使其才子佳人剧超越了当时传奇言情之作书写风流情欲的庸俗浅薄和浮滥景况。
面对妻子“报状元那里去?”(第二十三出《荣归燕喜》)的发问,李益回应朝廷命他参佐玉门关,不久便回。这与第二十二出《权嗔计贬》所述卢太尉原意并不相符。李益唯恐小玉担忧伤情,故才如此回答。另外,春风得意欣欣然接受家人祝贺的李益,应该全然不知卢太尉阴谋设计的内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当下的处境。喜欢聚、共庆贺情境空间氛围下,霍小玉继续沉浸在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歌咏欢饮情境中:
【鲍老催】〔旦扶游介〕从天喜幸,绿衣郞近得红妆敬,与郞醉扶起玉山凭。休酩酊,宜豪兴,当歌咏。守得你探花人到留春剩,你向天街上游衍把香风趁,合欢树今端正。(第二十三出《荣归燕喜》)[5]89
霍李二人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即将面临的长久分离,霍小玉还设想着香风合欢,从此后两人相伴相守不分离。他们哪曾想到“客路朝朝换”,“参佐玉门关”本是卢太尉所设之局,目的是要李益永不还朝。《荣归燕喜》的欢乐场景中,已悄然埋下了《门楣絮别》场面的伏笔,门楣送别又为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光》女主角送别夫君从军远征,销魂断肠情境空间特写作了铺垫。
早年经历情感磨折的霍母,先他人敏锐感受到了转眼在即的离别,从母亲的视角慨叹韶华佳境不并,门阑喜气与乘龙回鸾不共存。“门楣不久去关西”,“流泪眼随流泪水”。《门楣絮别》主要呈现小玉及其母郑六娘、丫鬟浣纱、女伴鲍四娘与李益话别情境空间,她们流露的真情至性,反映了她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门楣絮别》开场先呈现霍母的离情别绪,她感慨好景不常在,女儿小玉又要暗自伤悲幽咽啼哭了。正欣喜招了个名魁春榜的女婿,与女儿琴瑟和谐,指望此后门户有人支撑,不料宴会才罢,李益就要与小玉分别。怕的是女儿窗前泪满红袖,无奈留人不得。刚刚团圆,为什么又要抛下小玉孤鸾一只,怎忍心再看鸳鸯对对成双,真是愁思百转,满腹心事谁与共!
关西吐蕃军情紧急,李益被催促即刻起身,郑六娘心心念念女儿的幸福:
〔悲介〕我的女儿也!
【醉扶归】合欢衾覆着才停帖,连心枕结得好周遮。踹双丝半步不离些,乱花风摆亚金泥蝶。郞马儿站不了七香车,关山点破香闺月。(第二十四出《门楣絮别》)[5]91
郑六娘的唱词念白,由感慨转为悲叹,处处显现对女儿今后生活的牵心和担忧。李益和小玉的婚姻生活才妥帖周全,小玉刚盼来分别半月的丈夫,夫妻才得欢聚,心情正舒畅,夫妻转瞬就要远离,郑氏六娘的心情怎能平静,又怎不痛惜女儿此时此刻的凄苦心情?
封建时代,男子可以参加科举,外出交游、做官,女子只能独守闺门,婚姻便是她们的全部。况霍小玉在新婚不久,尚无子嗣可以寄托依靠的情况下,不能与夫君共享安逸家庭生活的她该多么孤苦愁怨。但是,当李益叮嘱郑六娘“好生护着家门”,表现出对霍小玉哪怕一丁点的不信任时,郑六娘马上驳斥:
【古女冠子】〔老〕深闺淑女,何须疑虑?便待你侯封绝塞奇男子,咱身是当门女丈夫。(第二十四出《门楣絮别》)[5]93
郑六娘的唱词,首先显示了她作为母亲深深怜惜爱女的一种本能反映;其次,体现了唐代女性当门立户的自信心,以及要求获得男性尊重的强烈自我意识。这同时也隐约体现了晚明社会挣脱理学束缚,社会改革思潮在戏曲作品中的反映。
明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思潮,东林学派开其端的实学思潮,泰州学派肯定人欲,提倡自然的离经叛道思想,李贽超越统治思想藩篱的“异端”叛逆思想,狂飙突起的思想解放文化思潮等,无一不对文人士大夫的内心及其创作产生巨大影响。晚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普遍追求金钱,富人纵情声色,士民追求享受等,都有力冲击着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时代对作家的影响无所不在。率性所为,追求个性自由,主张文学艺术“本乎情”,自由表达真情实感和主观心灵世界,成了中晚明文人作品的一种自觉追求和价值观。戏曲作品本来就是人心的产物,“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9],加上戏曲曲辞既高雅又通俗的特点,使其比传统诗词歌赋更利于表现人的主观性情。因此,在文坛主情风潮影响下,晚明曲坛传奇创作勃兴,文人传奇作品繁盛一时。传奇已然成为文人士大夫表现主体精神、生命意识、抒发个人情感的一种艺术表现形态。
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汤显祖,不能不受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的影响。李益叮咛护着门户,可以看作曲家对逐利追欢时代风气的一种不自觉流露。郑六娘的回答,既是女性自尊自信意识的体现,更是女性追求个性解放朦胧意识的反映。
优秀曲家塑造的人物形象绝不单一,即使主角之外的其他角色,也绝不作简单化处理,使其偏离符合生活的逻辑和艺术创作的规律。“别离几许,省可也薄情分付。”[5]93李益抛下小玉去边关,也算是薄情了,就免却吩咐了吧,霍母话语中所含的谴责,表达的是一种自尊情绪。李益牵挂放心不下小玉,拜别岳母郑六娘时,托付她好生照看。郑六娘反而叮嘱女婿,边关军营生活征战苦,一介书生身体单薄娇嫩,要好好将息保重。刻画出一个慈爱的老夫人形象,而“女娘们苦也”,又表现出一个女婿杏苑题名中状元,全家正欢聚相庆,却又惊闻他欲从军远征而愁苦遗憾的老人家形象。
浣纱既是小玉丫鬟,也是小玉知己。她活泼聪明,对小姐的心事把握透彻,也很会说话。生旦离别,她更关心小姐的情绪,劝解的话儿更贴心。藉由浣纱的唱词,受众得以知晓:昨夜灯下,小玉整理夫婿行囊泪千行,备受离情磨折。浣纱宽慰小姐,趁此时赶紧话别,不知再次相聚会是什么时候,从今后探听等待李郎消息,时时咨询杜鹃鸟儿,让小姐心中希望永存。
鲍四娘曾经是“折券从良”的歌妓,也是霍家的常客,小玉的女伴。听到李益金榜题名归来,又要从军远去,特来相看相送。她的出现恰到好处,既让郑六娘的愁苦情状得以鲜活展现,还使郑六娘、李益、小玉的离情别绪得到适时尽情抒发。
鲍四娘“巧于言语”,她对离别双方的劝慰之语恰如其分,充分显示出她聪明睿智的一面。她以堂前燕子比喻,表现出她对霍小玉倾诉的画堂花无主的理解。劝小玉无论怎样难舍难分,也不能为了长相厮守不顾丈夫的鹏程路,让读书人不得志。让他走了又何如?留下以后怎么面对诸多问题?读书人不比闺中女子,小小功名也要拼命追求。当李益拜托她照看霍家母女时,立刻爽快答应,殷切希望他早日归家,反映了“雌豪”鲍四娘乐于助人的义气豪迈。
李益上场唱离情,以雌雄剑寓夫妻不忍分离,“魂移带眼”,担心妻子因离愁而消瘦。“悲莫悲兮生别离。”[10]霍小玉内心最为悲苦,离恨最是难平,出场即“镜台泪雨送夫君”。李益惭愧自己不能常住家里,冷落了用情极深的妻子。霍小玉唱词句句饱含离别情愁,夫妻不能长相厮守,相对无语,唯有泪千行。李益从军前途未卜,母女俩只能对着月中桂树,徒然啼哭。而郑氏的悲哭和闷倒,以及“咱娘儿命薄”的感叹,更生动烘托了小玉内心强烈的悲痛之情,只能嘱咐李郎早晚把音信递传。然而,玉门关遥远偏僻,音讯难通,三年中霍小玉只收到一份家书。李益自认此去多则一年,三年了却还不能回还家门。自此,剧作由前几出霍李缔结婚姻等相关欢愉场景抒写,转入感伤情绪的抒发。生旦爱情悲剧,霍小玉悲苦情愁抒写正式拉开帷幕。
“儒生边关征战苦,出门何意向边州。”不管怎样,门楣絮别重点抒写李益与霍母、鲍四娘和浣纱话别,因此,李益与霍母、鲍四娘的对唱、对白居多,霍小玉的唱白较少。李益从军玉门关,辞别众人,只是霍小玉断肠为君愁,折柳寄情愁送别的前奏和引子。生旦话别才是此剧送别的重头戏,曲家将之放在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以灞桥为宦旅中介空间和抒情中介,集中加以抒发和呈现。
四、中介空间:灞桥断肠泣夫君,阳关折柳销魂情
霍小玉绣征衫,要亲付与征人,乘香车到灞桥送别。停驻灞河桥外,看紫骝马开道,听仪仗队演奏雄壮威武的军乐《芳树》,心中悲怨,不堪西望:
〔旦〕浣纱,这灞桥是销魂桥也!(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5]95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11]霍小玉刚到灞桥便感伤销魂离别,而灞桥作为销魂桥的文化意涵由来已久。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销魂桥》条曰:“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12]灞桥送别空间书写,藉此成为主人公抒发离恨情愁的抒情中介,以及生旦离别话别情的中介空间。
灞桥,长安东郊灞河之桥,原名霸桥,历史久远。灞桥修建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据现存史料推测,秦代霸水之上应该有桥。西汉灞桥是联结东西交通的主要桥梁,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在汉灞桥南边新建了一座石质灞桥,称南桥,汉灞桥称北桥。唐代对隋灞桥作了大规模整修,再涂以红色颜料,宏伟壮丽,气势非凡。唐代,灞桥(南桥)因近汉文帝霸陵,又被称为“灞陵桥”。
据1994年发现的隋唐灞桥遗址推算,隋唐灞桥72孔,长约400余米,宽约7米,两旁设石栏,桥柱约408个,是我国现知跨度最长、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石桥。
长安灞桥地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独特。方回《续古今考》卷五曰:“盖汉唐自长安东出,或之函谷关或之武关必于霸桥分别,唐有南北霸桥,北桥东趋则函谷路,南桥而东南趋则蓝田武关路。”[注]见方回《续古今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行旅过灞桥,意味着出长安,自此踏上往向东、东南、东北三条道路,开始新的宦历征程。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在灞桥东设滋水驿,又称灞桥驿,供过往行人歇息,一直沿用至唐代。灞桥遂成为出入长安迎来送往的首选之地,特别因其作为送别场所而被深深烙上了行旅、留守之人惆怅、奔波和离情别绪的印记,上演了无数感伤、悲壮、牵挂、期盼的黯然销魂故事。
柳树是灞桥标志性景观。每到春天,灞桥两岸柳枝新发,春风拂柳,构成一道美丽浪漫的独特风景线。但离人到此,哪有心情欣赏美景,心中所系只有“柳”“留”,折柳留别而已。灞桥折柳赠别古已有之,《三辅黄图校注》卷六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13]
就文学地理学角度而言,戏剧作品中某时某地的空间或场景书写,更重要的是如何被书写或再现。就空间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它与现实空间并非完全一致,更多情况下这些空间或地景只是寄寓或抒发角色自身情感的心灵图景。如此,灞桥对宦游之人而言,是旅途中介空间,是他们离别家乡亲人,离开京城后艰辛漂泊之旅的浓缩与隐喻。它与灞桥折柳送别一起,构成了灞桥专属地景,表现出与科学、量化、图表地理学全然不同的空间意义,呈现出与文人心灵结合的特性,而被赋予了深层的文化意涵。
始建于汉代,孤耸在茫茫戈壁的阳关,是汉王朝通往西域的关塞、门户。南北朝诗人庾信的《燕歌行》最早将“阳关”入诗,抒发故国乡关之思:“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14]这里的“属国”“阳关”并非实指。“阳关”已由汉代的西北关塞,演化为文学作品中发古幽情的凭借对象,泛指普遍意义上的边塞。此后文学作品中的阳关,往往不再具有写实性特征,逐步演化成了抽象的诗歌意象,泛指通往遥远边塞的漫漫征途和绝域边塞。
“阳关万里道。”(庚信《重别周尚书二首》其一)远在西北万里之遥的阳关,迂远难通,将征人与家人南北阻隔,而被赋予寂寥苍凉之感。所谓“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湜《折杨柳》。汉代内地与西域分野的阳关,又成了两种文化的分野,甚至对征戍赴边之人而言,似乎又是生与死的分野,因而赋予阳关更加厚重的内涵。唐代诗人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别中蕴含的留恋、关怀深情,饱含的平和刚毅诀别之气,诚挚深沉的情谊,写出了普天下离人的共同感受,千百年来深深打动了万万千千离人的心弦情怀,而成为入乐后最流行的送别曲,称《渭城曲》,或名《阳关曲》。后世文学作品常常以《渭城》或《阳关》曲,渲染离别氛围,抒发情怀。
灞桥一曲阳关曲,在霍小玉听来就是子规啼血,声声凄咽。李益跨过灞陵桥,意味着他从此踏上遥远从军路,开始了新征程,明朝相忆笛中折柳,只剩相思悠悠。灞桥话别情境空间里,生旦的别恨情愁,尤其霍小玉的离别痛楚,因受灞桥中介空间的召唤而被进一步强化。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开场小玉携浣纱上场,唱萧史弄玉夫妇共同飞升登仙的典故,委婉感叹夫妻不能同行止,抒发无可奈何人离去的悲情。接着小玉浣纱对白,道出断魂啼血的离别幽怨情:
【好事近】〔旦〕腕枕怯征魂,断雨停云时节。〔浣〕忍听御沟残漏,迸一声凄咽。〔旦〕不堪西望卓香车,相看去难说。〔合〕何日子规花下,觑旧痕啼血。〔旦〕浣纱,这灞桥是销魂桥也!(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5]95
见证了一次次启程与惜别的灞桥,在霍小玉眼中是充满伤感的介质。在霍小玉抒发离情别绪、凄苦悲伤之时,李益旌旗雕鞍,被众人前呼后拥上,出场一句“逞军容出塞荣华”,好不威风,暗含对出塞建功,荣华指日可待的期盼。“喝不倒的灞陵桥”,表明多少年来灞桥岿然屹立,人们的离情别恨之痛也千古不变。于李益而言,灞陵桥,离别地,确实令人无奈伤感,但因它“接着阳关路”,另一头还系着功名事业,因而他的离别之苦远比不上霍小玉来得强烈深刻。生旦两人话别前,灞陵桥上的送别情境空间氛围,因主体感受和视角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意味,或多或少含有了对比的义涵。
在日暖春寒散的灞桥外,李益喝令左右、仪仗队暂时停驻,自己与夫人话别。李益虽不忍与小玉分别,“酒湿胡沙泪不干”,“花里端详人一刻”,但更关注去边州建功立业。霍小玉悲怨不已,“断肠丝竹为君愁”,折柳也留不住离人,害怕听到离别《阳关曲》,设想今后独自留守帝都,渭水都要生寒,自己的心又该有多寒。王献之在桃叶渡迎接爱妾桃叶之事油然浮上心头,眼前汀洲草碧,河桥柳色新,柳絮迎风飘扬,人与景,景与人,相融相谐。霍小玉似弱柳扶风,语调哀婉低回,诉不尽悲怨情愁。李益想昨夜欢娱,叹今朝夫妻劳燕分飞,曾经的美好都成了记忆。霍小玉泪珠千点,打湿了夫君衣袖,脸颊梨花带雨,溅湿珠盘,怎么都收不住。“层波溜折海云枯,潇湘染就斑文箸”,悲苦忧伤难收煞。眼见妻子悲啼不止,眉蹙不展,明眸频频回顾,李益宽言劝解亦自慰,“便千金一刻待何如?想今宵相思有梦欢难做。”伤感中透着无奈。
“夫,玉关向那头去?”霍小玉的明知故问中包含着对未来命运的深深担忧。丈夫远赴关塞后,芙蓉帐寒,烛影孤单,闺房冷清寂寞。关山路远,夫君归途难料,怕只怕他再结新欢,抛弃旧爱。问李郎有何吩咐中隐含幽幽心事,李益也感叹妻子今后孤苦伶仃,叮嘱她闭门闲居时照顾好自己。小玉内心波澜起伏,听这话想他断不是轻薄浪子,应不会轻易辜负自己。可眼下鸳鸯两地分离,孤鸾影单,纵使满庭花雨烟水,侧敲紫钗唤鹦哥,看素女图,离恨别愁总难消解。霍小玉不禁悲叹:“你去,教人怎生消遣?”问对方,也是自问。别离后再无心情听娇莺歌唱,赏春花美景。自己就像无主之花孤苦伶仃。霍小玉诉不尽的相思离别情,着实令李益感叹唏嘘,从塞上风沙使人过早衰老,归后妻子能否认出自己的角度来劝慰小玉放心。他把自己比作常年从军出征在外的王粲,小玉好似初嫁东吴的小乔,感慨“正才子佳人无限趣”,却不得不抛下新婚妻子远赴边关。这里,灞桥作为从军宦旅征程的中介空间被强化,浓缩与隐喻了李益跨过灞桥后,将面临沿途的荒漠戈壁,以及塞外的苦寒艰辛。
灞桥作为抒情中介空间,还体现在霍小玉的离情悲愁与苦恨,也因灞桥宦旅中介空间被进一步强化。李益此去茫茫不知经年,归期未卜,玉门关山遥遥,时空阻隔很难相见。霍小玉忧患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更感伤地理空间阻隔带给两人身心的距离感及其可能带来的情感变化。她担忧有人仰慕李郎的才貌名声,忧心他“丝鞭陌上多奇女”“红粉楼中一念奴”,忧虑他宦途结佳姻,往昔盟誓成虚幻。李益也被妻子的深情感染,回想与小玉结为夫妻,情正浓时便遭离别,不禁“乡泪回穿九曲珠”。
在受历时典故、共时空间和别离氛围等因素影响而深深担忧的心态下,霍小玉再邀盟约,提出相守相伴的“八年之约”:
〔旦〕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5]98
霍小玉只愿一生欢爱集于八年。她的痴情、不舍、感伤、忧患、无奈、挣扎等情愫,都因灞桥历来建构的送别空间和气氛召唤而被强化。她内心的忧愁,也一步步显露出来,并被慢慢强化:
【前腔】是水沉香烧得前生断续,灯花喜知他后夜有无?记一对儿守教三十许,盟和誓看成虚。李郞,他丝鞭陌上多奇女,你红粉楼中一念奴。关心事,省可的翠绡封泪,锦字挑思。(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5]98
霍小玉运用多个典故寄寓自身景况,字字真情。多重空间叠合呈现,透露出她不无矛盾的心态:愿痴情厮守终生,却因分离在即而不敢奢望;愿盟誓常在,却又怕时空变迁,致使心愿成虚幻,充满了不得不然(八年之约)的无奈和与决绝。灞桥空间成了见证她这种情绪与矛盾的介质。
李益闻此言,马上泣涕明志,重提昔日花院死生与共的偕老誓言。他请妻子不要怀疑忧心,只管端居家中等待。李益运用多个典故,夸赞小玉才貌俱佳,抒发对妻子的浓情蜜意。即使空间阻隔,千里之遥,也忘不了窗前抱憾伤心的小玉。灞陵桥头,长杨、绿柳、画桥、树荫,物物含情,处处染愁思,情景交融,角色情感抒发与景物描绘浑然一体,给受众以强烈的美感享受。
花院盟誓因李益赴洛参加科举引发霍小玉的离恨情愁而起。花院盟誓言至情的情境空间书写,又是霍小玉送夫赶考,展露其内心最大隐忧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是曲家充分把握人物心理基础上创设的别开生面送别书写。因此完全可以将其视作送别空间空间书写,二者之间实际上已经融为一体,不可截然分割。花院盟誓在灞桥送别中几次被提及,既充分抒发了霍小玉内心的焦虑,突出她对真情的追求,显现剧作的至情主旨,同时还为霍李爱情婚姻走向埋下伏笔。也就是说,性别空间区隔下的花院盟誓书写,其实质就是送别空间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性别空间阻隔和送别空间书写水乳交融,也使霍李情感发展描绘呈现一波三折之态势,避免平铺直叙,使剧作得以藉此尽情抒发霍小玉内心细腻的情感体验,表现她对外界事物及其变化的敏锐感受力。而霍小玉对夫妇间真情、至情的追求,还包含有自我觉醒的意义,寄托了曲家肯定爱情与青春的情怀。
霍小玉灞陵桥头送别李益,两人难舍难分。李益早晨启程,日午还在红亭,军中箫鼓催行色,崔韦两书生相继上场催促李益早行。李益一句“小玉姐话长,使人难别”,道出了妻子心中多少留恋不舍情。崔允明提醒,箫鼓喧天,良辰吉日应早启程;韦夏卿言,男儿耻露离别颜,不该留恋如此,当对酒壮行色,仗剑隔离情,并劝霍小玉军行有程,不要耽搁李益起行。李益也只得拜别,回送妻子上车转回家。
参军李益启程赴任,踏停灞陵桥外时“后拥前呼”,且有“封侯昼锦”之望。此去玉关三千里,霍小玉内心十分害怕誓言成空。李益起行踏上灞陵桥,“千骑拥,万人扶”,致使小玉恍有“人如隔彩云”之感。这里,灞陵、灞桥、折柳、柳色等空间和意象形成的特定情境,渲染了别情离愁的氛围,处处彰显了李益对妻子的留恋不舍和牵挂。
灞桥杨柳,销魂伤情!这里长安和塞外空间书写,将整体性大空间描述和小空间叙述相结合,通过空间意象书写集中呈现出来。上了灞桥,意味着离开京都长安,踏上茫茫关山路,开始塞外军旅新征程。灞桥作为中介空间,一边是京都长安,家人居住地,妻子在这里日日相思盼夫归;一边连着边塞路,是苦寒艰辛、遥远孤寂的离人戍守征战地。因而灞陵高处,帝都春色依旧,只是离别惹春愁,灞桥杨柳更教人怅惘相思。
曲家运用系列边塞意象表现离愁别情,为李益从军关西营造氛围。如霍李灞桥分离别,众人所唱:
【金钱花】〔众上〕渭城今雨清尘,清尘。轮台古月黄云,黄云。(第二十六出《陇上题诗》)[5]100
“渭城”“轮台”对举。渭城,本是王维诗歌中的送别地名。轮台,军事重镇,曾经的汉代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渭城、轮台都非实指,《渭城曲》代表离别,轮台泛指西北遥远的边关。“今雨”“清尘”与“古月”“黄云”相对,以两组高度浓缩的对比意象,将眼下离别空间场景与即将赴任地的空间景致和人物心理有机融合,意与境浑,隐喻建功立业与家人别离的深刻内在矛盾。
门楣絮别、灞桥折柳、《阳关》留别,剧中角色性別不同、感情境遇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心理体验感受不同。对霍小玉而言,灞桥是与丈夫离别,前途未卜的中介空间;对李益而言,灞桥又是宦旅征途的中介空间。身临这样的中介空间,感受到的不再是春寒散日暖花开,柳色如烟,柳絮漫天的静好欢愉,而是留恋、不舍、感伤、无奈与悲怨。崔韦两书生,作为李益的表兄弟和朋友,表现自然与霍小玉不同。他们一边催促李益早行,一边劝霍小玉军行有期,适时割舍离情。灞桥对他们而言,是送别亲友的空间,也是男儿意气慷慨从军征途的开端,不该留恋如此。透过对角色特定情怀与意愿的抒发,塑造了霍小玉、李益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舞台艺术形象,使剧作更近人情,从而有效呈现至情主旨。
五、结语
优秀的古典戏曲作品,往往能够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诗意化曲文,细腻地抒发角色的内在情感。《紫钗记》门楣絮别、折柳阳关、灞陵送别等曲文,密切配合剧情,取象写景,因事造形,随物赋象,将人物情感与物象空间交融契合。或寓情于景,或咏物抒怀,或借人表意,或直接披露自己的矛盾意绪心态,突出抒发霍小玉绵绵不尽的离别情。这也是曲家汤显祖凸显剧作至情主旨的重要方式,确如李贽《读若吾母寄书》所云:“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15]
戏剧艺术表达的情感要出于自然,出自至情者才能真切,才能感物而遇,得乎自然之理。汤显祖有意借助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的异质同构状态,以深刻的心灵解悟,以灞桥等为中介空间,融通了角色主体世界与客体空间的界隔,使《紫钗记》及其送别空间书写,超越了平庸肤浅的才子佳人式剧作的普遍模式。灞桥中介等空间书写也使人物情感表达更为强烈、深刻而细腻,由此点染的李益、霍小玉等人物性格,超越了个体经验局限,形象传达了人世间共有的至情,创造了品味不尽、余音回荡的艺术境界。
主体存在于空间之中,空间是舞台及其丰富戏曲内涵展现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中国古典戏曲的舞台空间,往往借助想象的力量,通过演员的唱白、程式化的表演等方式,来呈现各种必要空间,藉此支撑剧情发展。这也使观众暂时忘却自身所处的真实空间,引领他们进入舞台空间,瞩目舞台营造的虚构空间。《紫钗记》送别情境空间,作为包含人、物、时、空且不断运动的有机整体,把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婚姻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心情感世界,直观形象地展示给观众,使他们对男女主人公整体形象的把握渐趋明晰。观众通过对此艺术境界的鉴赏,很容易体会到抒情主体的精神世界,并与之发生共鸣,自然而然产生心灵震动和情感激荡的审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