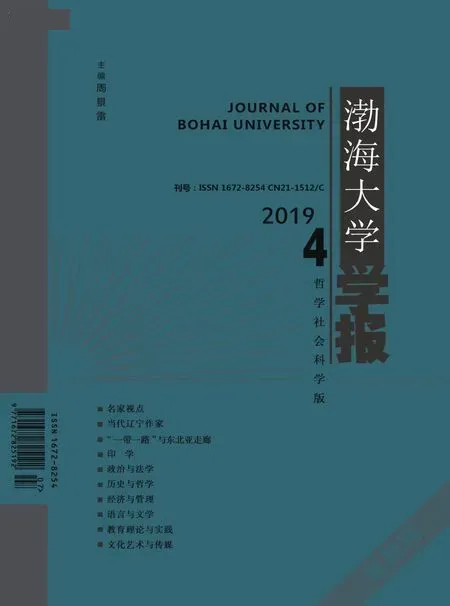辽朝皇帝对“谏言”的心态与应对
张国庆(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中国古代官员向皇帝进谏,是约束皇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契丹辽朝亦不例外。有辽一代,关于“谏言”问题,皇帝和官员的交流是双向的,既有官员的积极进谏,也有皇帝的虚心纳谏或粗暴拒谏。若单就“皇帝”一方而言,他们对臣下谏言的心态和应对,大致表现为“求谏”或“禁谏”,“纳谏”或“拒谏”,以及与之相应的褒奖或惩处措施等。当下,辽史学界尚未见有关辽朝皇帝对谏言的心态与应对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一问题略作论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求谏:欲达“兼听则明”而广开言路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有几位皇帝在执政期间,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布过诏令,要求臣下广开言路,直言进谏。譬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乘唐末五代之初中原大地藩镇割据、战乱不已之机,统率契丹铁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最终建立起强大的契丹王朝政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比较重视臣下的谏言,能够虚心纳谏,知错就改。如太祖六年(912),契丹军队进攻据守幽州的燕王刘守光,耶律阿保机即接受了皇后述律平的谏言,没再坚持用“猛火油”攻打幽州城,避免了一场因战事而伤及无辜百姓的惨剧发生。《辽史·后妃传》即载:“吴主李昇献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述律)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呼?'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1]辽太祖重视臣下谏言,还表现在他对前朝敢谏直臣的尊崇。比如,他曾于神册六年(921)五月“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2]等等。
辽圣宗耶律隆绪刚刚即位,便与他的母亲、摄政的承天太后一起,诏令朝野中下层官员要敢于直言,遇上级官僚“非理征求”时不得曲从阿顺。《辽史·圣宗纪》即云:统和元年(983)十一月“庚辰,上与皇太后祭乾陵,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3]圣宗皇帝是辽朝的中兴之主,在位时间近半个世纪,他在母亲承天太后的帮助下,致契丹辽朝的社会发展达到了鼎盛,这与母子二人虚心纳谏、乐于听取臣民直言不无关系。比如,北院宣徽使耶律阿没里曾就律条“兄弟连坐”的不合理性向圣宗皇帝和承天太后进谏,请求修改。圣宗皇帝和承天太后接受了耶律阿没里的谏言,并最终修改了这条法规,以免再有无辜者遭受“连坐”之刑罚。《辽史·耶律阿没里传》即载:“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连坐。阿没里谏曰:‘夫兄弟虽曰同胞,赋性各异,一行逆谋,虽不与知,辄坐以法,是刑及无罪也。自今,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太后嘉纳,著为令”[4]。
辽道宗耶律弘基即位,亦曾诏令朝廷百官直言进谏。《辽史·道宗纪》载: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兴宗崩,(耶律弘基)即皇位于柩前,哀恸不听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请,许之。诏曰:‘朕以菲德,讬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其体朕意。'”清宁元年(1055)“十二月丙戌,(道宗皇帝又)诏左右夷离毕曰:‘朕以眇冲,获嗣大位,夙夜忧惧,恐弗克任。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数月,未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传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5]道宗皇帝在位期间,有时对臣下的谏言是能够接受的。如马群太保萧陶隗曾就辽朝后期国有“群牧”制度出现的种种弊端,向耶律弘基上书言谏,提出“群制度牧”改革方案,即被其所接纳。《辽史·萧陶隗传》载:“咸雍初,(陶隗)任马群太保。素知群牧名存实亡,悉阅旧籍,除其羸病,录其实数,牧人畏服。陶隗上书曰:‘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不若括见真数,著为定籍,公私两济。'从之。畜产岁以蕃息。”[6]当然,道宗皇帝拒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反映了他对待“谏言”的矛盾心态。譬如,他对都林牙耶律庶箴所上关于增广契丹人姓氏的谏言就没有采纳。《辽史·耶律庶箴传》云:“(庶箴)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厘,不听”[7]。
唐太宗朝铮臣魏征曾就帝王广开言路、兼听臣下谏言的重要性对李世民说:“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8]。的确,对皇帝而言,诏令臣下进谏,虚心听取谏言,是延展视听、了解下情、清明朝政的重要手段;而对于那些要答谢皇恩、报效朝廷、施展才华的官员来说,闻诏进谏、遇事直言也是其实现个人理想的主要途径。辽朝的一些皇帝和官员亦不例外。元朝史官在撰《辽史》评论景宗朝政及圣宗用人时曾云:“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盖承穆宗醟虐之余,为善易见;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室昉进《无逸》之篇,郭袭陈谏猎之疏,阿没里请免同气之坐,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9]“张俭名符帝梦,遂结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两朝,世称贤相,非过也。邢抱朴甄别守令,大惬人望。两决滞狱,民无冤滥。马德臣引盛唐之治以谏其君。萧朴痛皇后之诬,至于呕血。四人者,皆以明经致位,忠尽若此,宜矣。圣宗得人,于斯为盛。”[10]此言不虚也。
二、禁谏:唯恐“鼓惑眩众”而壅蔽视听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譬如性情人格、道德修养、执政理念、文化素质以及心态情绪、场合环境等等,辽朝皇帝对待“谏言”的心态并非一成不变,时而求谏,时而又禁谏的情形为其常态。他们求谏,是为广开言路,以达兼听则明,减少执政失误;他们禁谏,是害怕直言会鼓惑眩众,扰乱视听,危及到皇权专制。所以,有辽一代,有些皇帝为禁臣下直言而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先以辽兴宗耶律宗真为例。兴宗皇帝执政期间即曾多次颁布诏令,禁止臣下谏言。譬如,有官员遇前朝所定法禁有乖、当下刑罚不当时,即对皇帝进言劝改,为此,辽兴宗便于重熙十年(1041)七月下诏,“诸敢以先朝已断事相告言者,罪之。”[11]辽朝官员(包括伶官在内),有时在君臣宴乐的特殊场合,曾就皇帝的一些不当言行进行过“讽谏”,对此,辽兴宗于重熙十六年(1047)二月颁诏,“禁群臣遇宴乐奏请私事。”[12]很显然,耶律宗真就是想用禁止官员于宴乐场合奏“私事”为由,避免“言谏”行为借机出现。类似的借禁止官员奏事“言私”而限制言论的诏令还见于重熙十七年(1048)二月,“诏士庶言国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见,许白其主,不得自陈”[12](238)等等。
前已述及,道宗皇帝耶律弘基一方面下诏求直言,同时也找各种理由钳制舆论,禁止臣下谏言。这种前后相互矛盾心态的出现,应与道宗皇帝敏感多疑的性格有一定关系。他既想听到谏语规劝,又怕直言伤己;批评稍稍过度,便认为是臣下鼓惑眩众,即刻堵塞进言通道。我们再联系此前道宗皇帝曾经发布的一道诏令,就不难理解他对善进谏、好直言官员的防范心理了。清宁二年(1056)六月“辛未,(诏)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5](254)因为“朝议”时难免君臣意见相左,同时,“朝议”地点也是官员“言谏”最多的场合之一,所以,辽道宗取消史官“预闻朝议”,即可减少“谏言”入史的机会,有利于皇权专制。其实,道宗皇帝早在即位之初,在他诏告天下求直言的同时,即曾诏令相关机构,严禁臣下奏书中含诽谤之语,否则,进言者将受到刑罚之惩处。《辽史·道宗纪》载:清宁元年(1055)十二月“辛卯,诏部署院,事有机密即奏,其投谤讪书,辄受及读者并弃市”[5](253)。
辽朝某些皇帝害怕直言、限制言谏、惩处进谏官员的直接后果,就是朝堂之上百官噤若寒蝉,朝议时万马齐喑;臣下进言奏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譬如穆宗朝,《辽史·耶律贤适传》即云:穆宗“应历中,朝臣多以言获谴,贤适乐于静退,游猎自娱,与亲朋言不及时事”[13]。又如道宗朝,《辽史·道宗纪》即载:咸雍八年(1072)“二月丙辰,北、南枢密院言无事可陈”[14]。
三、纳谏与拒谏:褒奖进言者或惩处逆鳞人
辽朝皇帝若对臣下的谏言接受并采纳,说明此谏言迎合了皇帝的心意,与皇帝的志向不谋而合,或是臣下的谏言比较委婉,皇帝能够接受。因而,每至于此,进言者大都能得到皇帝的褒奖,或是口头嘉赞,或是加官进爵。反之,如果皇帝感到官员的谏语言辞犀利,不合朕意,或臣下进言时恰逢皇帝心情不佳,“玉色怫然”,进谏的官员有可能轻者被叱责,重则遭惩处。
先说“纳谏”并褒奖进言者。如太宗朝的北院大王耶律图鲁窘曾劝谏太宗皇帝在征伐后晋遇阻时不要轻言撤军,耶律德光欣然接受谏言并褒扬了图鲁窘。《辽史·耶律图鲁窘传》即载:“(耶律图鲁窘)从(辽太宗)讨石重贵,杜重威拥十万余众拒滹沱桥,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后图,帝然之。图鲁窘厉声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域,出师远攻,讵能无厪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征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帝喜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于是塞其饷道,数出师以牵挠其势,重威果降如言。(图鲁窘)以功获赐甚厚。”[15]景宗朝南院枢密使郭袭曾劝谏景宗皇帝不要过度游猎,耶律贤接受了郭袭谏言,并予以嘉赞。《辽史·郭袭传》即云:“以帝(辽景宗)数游猎,(郭)袭上书谏曰:‘昔唐高祖好猎,苏世长言不满十旬未足为乐,高祖即日罢,史称其美。伏念圣祖创业艰难,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无厌之欲,不恤国事,天下愁怨。陛下继统,海内翕然望中兴之治。十余年间,征伐未已,而寇贼未弭;年谷虽登,而疮痍未复。正宜戒惧修省,以怀永图。侧闻恣意游猎,甚于往日。万一有衔橜之变,搏噬之虞,悔将何及?况南有强敌伺隙而动,闻之得无生心乎?伏望陛下节从禽酣饮之乐,为生灵社稷计,则有无疆之休。'上览而称善”[16]。
圣宗朝谏议大夫马德臣曾劝谏圣宗皇帝不要过度迷恋马球运动,耶律隆绪接受谏言并大大表扬了马德臣一番。《辽史·圣宗纪》即云:统和七年(989)四月“甲子,谏议大夫马德臣以上(辽圣宗)好击球,上疏切谏:‘臣伏见陛下听朝之暇,以击球为乐。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争胜,君得臣夺,君输臣喜,一不宜也;往来交错,前后遮约,争心竞起,礼容全费,若贪月杖,误拂天衣,臣既失仪,君又难责,二不宜也;轻万乘之贵,逐广场之娱,地虽平,至为坚确,马虽良,亦有惊蹶,或因奔击,失其控御,圣体宁无亏损?太后岂不惊惧?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继承之重,止危险之戏。'疏奏,大嘉纳之。”[17]耶律隆运,原名韩德让,圣宗朝重臣。统和十二年(994)六月,身为北府宰相、领枢密使的耶律隆运曾就地方京道法官受贿渎职及朝廷应重用贤良等问题书奏进谏,得到了圣宗皇帝和承天太后的嘉赞与褒奖。《辽史·耶律隆运传》载:隆运“奏三京诸鞠狱官吏,多因请讬,曲加宽贷,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请任贤去邪,太后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优加赐赉”[18]。
辽圣宗耶律隆绪不愧为辽朝中兴之明主。有时,他对臣下之谏言会因某种缘故未予采纳。但过了一段时间,经过验证,他认为臣下谏言是对的,于是,便采取补救措施,褒奖言谏者。比如他对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即是如此。圣宗皇帝欲任用一名高官,王继忠进谏,认为此人不能胜任,圣宗没有采纳。事后,实践证明王继忠所言不错,圣宗皇帝便用加官进爵作为对王继忠的褒奖。《辽史·王继忠传》即载:“上(辽圣宗)尝燕饮,议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继忠曰:‘合卓虽有刀笔才,暗于大体。萧敌烈才行兼备,可任。'上不纳,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丽,继忠为行军副部署,攻兴化镇,月余不下。师还,上谓(继忠)明于知人,拜枢密使。”[19]圣宗皇帝一开始没有采纳王继忠的谏言,原因是他怀疑王继忠与萧敌烈有同党之私。《辽史·萧敌烈传》即云:“(萧)敌烈为人宽厚,达政体,廷臣皆谓有王佐才。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其材(才)可为枢密使,帝(辽圣宗)疑其党而止。”[20]看来圣宗皇帝是错怪王继忠了。
再说“拒谏”与惩处逆鳞人。封建帝王君临天下,即便是皇权专制,也需要百官扶持,辽朝亦然。故而,在某种场合下,皇帝既要“言路”通己,亦需臣下进言。然而,一旦有官员直言过度,或言事忤旨,便会遭到当事皇帝的谴谪贬斥。辽朝皇帝拒谏并惩处进言者的案例亦不少见。譬如,兴宗皇帝即曾用诏令的形式禁谏,并找各种理由或借口惩罚那些直言进谏者。如重熙十六年(1047)十二月“庚申,南府宰相杜防、韩绍荣奏事有误,各以大杖决之。出防为武定军节度使。”[21]杜、韩缘何奏事有误,奏何事有误,史籍均未载,但不排除二人“奏事”中夹杂了兴宗皇帝不爱听的谏语。
道宗皇帝亦曾对一些所谓“奏事有误”的官员予以惩处。如《辽史·耶律俨传》即载:俨“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宁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误奏事,出为榆州刺史。”[22]耶律俨本姓李,后被赐姓“耶律”。耶律俨的父亲、北院宣徽使李仲禧因何“坐误奏事”,史书亦未说明,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有要事必奏却因故而耽误;二是奏事中言语有“误”,亦不排除含有道宗皇帝觉得逆耳的直言,因而,李仲禧才遭降职左迁之处罚。辽道宗不仅惩处过直言进谏者,对直笔书史的史官也不曾放过。中国古代皇帝身边有修《起居注》的史官,专门记录皇帝日常言行举止,“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契丹辽朝亦不例外。按规定,《起居注》记录的皇帝之言行,当事者是不允许查看的。但道宗皇帝担心史官直笔所记自己言行中可能有贬损帝王形象的内容,因而,他强烈要求查看《起居注》,以利删削。耶律弘基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史官拒绝,于是,他便立即惩处了当事史官。《辽史·道宗纪》即载:大康二年(1076)“十一月甲戌,上(辽道宗)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部”[14](278)。
无论是太宗、景宗,还是圣宗、太后,他们之所以在纳谏的同时,还要褒奖进言者,原因就是“言谏”的最大作用即在于事发苗头之际,能及时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将皇帝的失误尽力扼杀在萌芽中。元朝史官在评论穆宗朝“言谏”状况时曾说:“虽然,善谏者不谏于已然。盖必先得于心术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则易为功。穆宗沈湎失德,盖其资富强之势以自肆久矣。使群臣于造次动作之际,此谏彼诤,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则以讵至是哉。”[23]这就是说,太宗、景宗和圣宗等多数时候都能虚心纳谏,做到了防患于未然,没有因为政令失误而造成损失,故而,他们一定要赞扬或褒奖进言的官员。而穆宗则不然,穆宗皇帝耶律璟与上述诸帝有所不同,一生错误多多,又不大肯接受臣下劝谏,然尽管如此,一些胆大而正直的官员,为了辽朝江山社稷,依然会冒险进谏。
结 语
传世文献史料和出土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着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有辽一代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
辽朝官员的“言谏”行为是否能对约束皇权、清明朝政起到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官员是否善谏(责任感)和敢谏(胆量),二是皇帝对臣下的谏言是求、纳(广开言路),还是禁、拒(壅蔽视听)。当然,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后者的决定性因素更重些。宋代著名史家司马光曾以隋唐之际名臣裴矩为例,比较了隋末和唐初不同政治环境对言谏者的影响:“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24]司马光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而言之,辽朝官员向皇帝的进谏应该是被“纳”多于遭“拒”,因而,可以说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