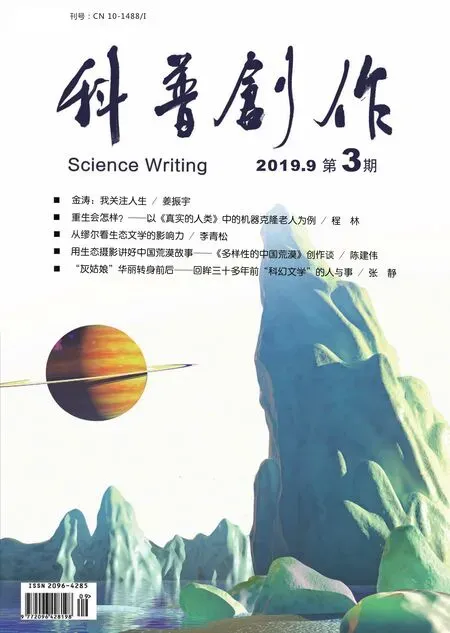讲故事的人
刘赫铮
普利普利大叔已经一百六十五岁了。即使在红星人当中,也算是长寿的。过去五十年间,他一直留在我的小酒馆里,客人正多的时候,就用他那浑厚的、富有磁性的嗓音,给客人们讲几个故事。每当此时,我也会和来来往往远离故乡的地球人、红星人,还有各种偏远星球的外星客人一样,静静地听。我的酒馆开在客运空间站里,从来不缺乏客人。最可贵的是,这里绝对没有那些红星游击队员们制造的“恐怖袭击”,想要离开红星的旅客们在这里可以完全放松他们的神经。
普大叔一般会讲一讲他年轻时的逸事,对那时红星的乡土人情颇有怀念之情。作为地球人,我难以分辨真假,却每每和从地球来的客人一样听得入迷。地球旅客在空间站等船的时候,往往要来我的酒馆点一杯红星传统软饮料。这杯饮料加上普大叔的故事,会成为他们回地球后最好的谈资。
可惜总有红星人跳出来打断。他们喜欢喝从地球运来的廉价啤酒或红酒,以示他们对地球文化的好感。我当然毫不介意赚他们一百倍的差价。每当普大叔讲起百年前的红星旧事,他们就会说:“净瞎编!这些糟粕,能不能别拿出来丢人?真是我们红星人的耻辱!”每当这时,普大叔就会微微摇头,轻轻颤动他圆圆的小耳朵。我知道这是他伤心的表示。接着,他就会弯起他厚实的脊背,缩起来不再说话了。不过,约莫十分钟(当然是按地球的方式计时)之后,假如有个客人(往往是地球人)要求他再讲一个,他还是会满足客人的愿望。那些红星年轻人,自然不会不识趣地一再搅乱地球客人的兴致。
比如此时,不管红星人喜不喜欢,地球的客人们不管不顾地叫道:“再讲一个吧大叔!就一个!”于是普利普利大叔就缓慢地打开了话匣子。
“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大降临’的故事吧。”
大降临,这是红星人对地球人第一次来到红星的描述。当时到红星的都是和平居民,不像后来,成批的军人(包括我,我当时是个军医)来到红星。能听到红星人视角的故事,也是挺好的体验。
“那时候,我也就二十啷当岁吧。那天晚上,长明星还是在头顶上,把整个天空都照成蓝紫色,除了它,就看不见别的星星了……”
“长明星就是地球人说的老人星,天上第二亮的星星,只比天狼星差一点点,可惜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见。”一个地球女客人对她的朋友说,“红星离老人星特近,白天晚上都能见到。”
“我正想睡呢,忽然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我走出门去,看见野外的灌木全都不停地哆嗦着,动物们要么疯了似的挖洞,要么互相撕咬起来,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不光是我,别人也都出来了,看来他们也都有一样的感觉。我估计全世界的人,能出门都已经出门了,就像每次光环节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出门来,看着太阳变成一个光环。光环节,现在也没人过了。”
“好神奇,怎么做到的?”地球女客人被勾起了好奇心,不过她很快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夫人,只不过是日环食而已。你们地球人来之前,我们都还以为那是什么神仙显灵呢,真是可笑。”这个说话的红星年轻人我见过几次,好像是被推优到地球去上了几年大学,给自己起了个地球名字叫“大卫”。
“我问的是你们为什么能同一时间感应到。”
大卫答不出了。
我刚到红星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困惑,这些红星人好像会心灵感应似的,能够突然间集体行动,好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是一种神奇的微生物给了红星人这种能力,但是后来这种微生物灭绝了,对此我应该负一小部分责任。但是此时在我的酒馆里,普大叔好像没听见地球女士的问题,接着讲他的故事。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那儿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几分钟之后,所有人好像听到命令似的,一起抬头向天空望去。我们从没见过那么多的星星,而且越来越亮,变得全都比长明星还亮。
“慢慢地,那些星星都显出形状来,有的是一个球,有的是一个环,有的是方方正正的,大得像座山一样,就在我们头顶上狂风大作。它们逐渐落到空地上,把地上的灌木烧得一干二净。我们也吓得全躲回房子里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再走出去看的时候,风早就停了,太阳升了起来,那些山一样的巨物外面,多了好多更加奇怪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之间,我就看到了你们地球人。”
这个故事普大叔以前讲过十多次,不过我确信现在这批客人都没听过。刚才那位提问的地球女士显然对红星的一切都感兴趣,她说:“我也想看看只有一颗星星的夜空。”
“即使在白天,有时候也能看到的,”刚才和她搭话的大卫说,“要不怎么叫长明星呢?”他的地球语言说得挺好,他接着说道:“不过这只是故事而已,地球人来到红星,是先派了联络员,然后才开始移民,不是不打招呼就来的,当时红星还很野蛮,你们带来了……”
“再讲一个吧!”有人喊道。
“对,这个太短了!讲个长一点的!”有人附和。
普利普利大叔喝了口水,说道:“那好吧,我就讲个红星人集体犯罪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他很少讲,尤其是酒馆刚开张的那几年,他从来不讲。不过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不新鲜,就是因为这次集体犯罪,我才跟随地球军队来到了红星。说起来,这次事件真是给了地球人绝好的借口。
“那是大降临后三十年了。红星上的地球人越来越多,几乎比红星人还要多。我开始觉得每天都不太舒服,脑子里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似的,总想发火。世界也不太对劲,那些草啊树啊什么的,枯黄的时候多,返绿的时候少。
“在一个没有长明星的晚上,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接着我就知道,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我拿起火枪,装好火药,走出了家门。
“大部分地球人都已经睡熟了。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批新人到来,我们知道,下一批新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赶到保留地当中,永远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大家都已经知道,地球人就是这么决定的。
“其实我和他们相处得还不错,他们有很多奇妙的玩意儿,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从某一个时刻开始,我已经开始厌恶他们了。我知道大家也都这么想。”
“毫无逻辑,简直是个跳大神的。”大卫打断了普大叔,可是大卫的新朋友,那位地球女士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好像有点不耐烦,所以他立刻闭上了嘴。
“在这个没有长明星的夜晚——几十年才能遇到一次的黑夜——我们红星人,进行了一次集体犯罪。我们杀地球人,杀了很多,我们还烧毁了他们几艘大飞船。三十年前的那些奇怪的物体,我们后来知道它们叫作飞船。我们所有人同时动手,杀掉他们的人,烧掉他们的房子和飞船。他们事先毫不知情。
“我们冲进他们的房屋和帐篷,把他们杀死在床上。有的房子很坚固,我们就在房子周围堆满稻草、浇上油,把他们烧死在里面。他们对我们毫无防备,因为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和他们和睦相处,和他们一起庆祝光环节,给他们喝我们最好的酒,学他们的语言,还帮助他们盖房子。但是现在,我们全都一心想杀死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强占我们的家园。我们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却这样对我们,这是背叛。我们要保卫家园。我们想把他们全杀了。
“但是我们低估了他们,仍然有一部分地球人活了下来。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最致命的是,他们的飞船重新飞了起来,瞬间就把我们的家园夷为平地。只用了一个晚上,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游击队员。我捡起地球人的武器,藏到森林里、山洞里,伺机杀死那些地球人。可惜他们的人太多了,不知从哪儿来的飞船把他们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地球在哪儿,可是我至今也没去过。”
“简直野蛮!”大卫又憋不住了。在这个地球客人很多的酒馆里听到这样的故事,对他来说确实很难堪。“就是因为你们的野蛮行径,才导致我们进了保留地!直到十年前我们才有了合法身份!如果不是你们这些游击队员,我们……”他已经气愤得说不出话了。然而普利普利大叔并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半闭着眼睛,喝水。
地球客人们倒是没那么激动。他们应该都听说过这次事件,也许版本不同,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胜利者,他们早就满不在乎了。
“如果真是我们先要把你们全关起来,那么你们反抗倒也正常。”地球女士说。她的表情十分严肃,活像一个法官。
有人问道:“当时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咱们可从来没想过跟他们商量!”有人回答,接着有好几个人笑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做到同步行动的?”地球女士问。普大叔没有回答,他在休息。于是女士问我:“老板,你一定知道吧?”我觉得应该把舞台让给普利普利大叔,于是摇摇头撒了个小谎:“普利普利老朋友的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大叔,讲讲你的恋爱故事吧!”有个地球人叫道。他是今天店里为数不多的熟脸,一直很爱听异域爱情故事。听说他在红星有好几个本土相好的。
普大叔此时已经歇够了,他脸上好像露出了笑容。
“我在五十岁时和我的伴侣认识了,并且很快有了女儿。”
“我都已经知道啦!讲讲别的,我没听过的!”熟客说道。
“好吧,”普大叔好像犹豫了一会儿,“我就讲讲我失去她们的事吧。”
“自从成为游击队员,我和我的家人就聚少离多,常常东躲西藏,很少见面。我们总能从地球人的扫荡当中逃脱,虽然有损失,可是他们也消灭不了我们。但是几年之后,地球人的行动好像能够瞒过我们了,我们的损失明显增加。从那以后,我更是很难和我的伴侣和女儿见面了。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仿佛我的伴侣和女儿正在遭受折磨。我以前虽然也常常想念她们,可是从没有这样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灵魂出窍一样。我完全能感受到她们的恐惧和痛苦,我仿佛得到了指引,要我去寻找她们。”
“又来了,满口胡说。什么心灵感应!当时红星人根本没有那种科技水平,即使是现在的地球也基本上做不到,这老头!”又是那个三番五次打断普利普利的红星年轻人大卫。说实话,这样的客人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不过普利普利大叔从来不会反驳他们。
“如果你不爱听的话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地球女士决定不再容忍这个讨厌的大卫,“其他红星人都挺老实的,只有你素质这么低。”大卫的脸色很不好看,仿佛是在主子面前丢人的仆人一样惶恐。我猜他可能真的不会再插嘴了。
“我就沿着我脑海中的道路离开了藏身的山洞,先是从崎岖的山路小径走过,然后渡过一条不宽的河流。河流另一侧是一片森林。于是我走进这片森林,用了足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到森林另一侧,我发现了一栋房子,依着山势修建,好像有一半在山体之中。
“这时候我的感觉更加强烈了,我觉得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妻女。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进房子里。奇怪的是,门没有锁,途中也没有地球人阻拦。假如有人阻拦的话,我想我大概会跪下来请求他们放我进去。
“于是我走过了一条又长又曲折的走廊,走廊两侧有很多房间。我走到其中一个房间门口,我知道我的妻女就在里面。我走进这个房间,看见她们躺在白色的大床上,身上连接着很多奇怪的东西。我猜这是地球人的仪器。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那就是你向日本人供认的时候,已经想好要牺牲这些女人了。”激动的法比发音含糊但语速飞快。他看老神甫吃力地在理解他,便又重复一遍刚才的指控。他从来没像此划这样,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那么排外甚至有些封建,企图阻止任何外国男人欺负自己种族的女人。
“我走过去看我的妻子,她非常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笑。但是很快她就哭了起来,她说:‘你不该来,我已经尽力了,我尽力不让你发觉,但是他们想出了办法。’我擦掉了她的眼泪,并且最后一次亲吻了她。然后我到另一张床上去看我的女儿,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好像想要叫爸爸,可是发不出声音,我感觉到她的生命正在逝去,她还没有成年,身体不如她的妈妈健壮。我就这样目送着我的女儿去了天国。”
地球女士的眼泪流了下来,问:“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
“然后有几个地球人走了进来,把我围在中间。他们穿着纯白色的衣服,我之前曾经见过,这是地球人的医生穿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又有点像军服。有一个人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总算能够彻底掌控这种小东西了。真是神奇!你看,只凭着磁感菌的同步效应,就能进行近百公里的远距离通信,要是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充当中继站,通信距离会更远,也许能做到全球同步通信。’其他的地球人在附和他,还祝贺他的研究成功。接着他又说:‘我总算能升上去了。’我不知道‘升上去’指的是什么,只感觉他说话的语气非常愉快。
“于是他们就把我也关了起来,和我的妻子关在一起。他们好像觉得我们没有用处了。可是我的妻子没撑多久,也去了天国。我孤身一人,不知过了多久,才被放出来。”
“我不明白,”地球女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明显是军方用他们做实验了。你没听说过磁感菌吗?那是和红星绝大部分生物共生的一种类似细菌的东西。他们之间好像能通过红星的磁场产生联系。”有人解释道。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有个红星人说,“至少现在红星上没有。”
地球女士的心情好像一直没有平复,她泪眼婆娑地说:“在地球上,有人说地球人又开始搞殖民主义了,我一开始还不信。地球人可真残忍。”
“没准是假的呢?”有人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帮他们进入了太空时代,没有我们他们还不如地球中世纪先进呢!你说是不是,小伙子?”被问的是刚才被女士呵斥的那个大卫。他好像被赦免了似的,说:“反正我个人很感谢地球人的到来。”
“地球人来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这么说对得起你的祖先吗?”地球女士说。
“我的祖先不希望我永远做个野蛮人。”大卫仿佛鼓起了莫大的勇气,反驳了女士的诘问。接着他自己反而不知所措起来,干脆转身离开了酒馆。
“真是的,弄得这么严肃,下次别再讲这些啦!”有客人喊道,然后将手里的饮料一饮而尽,带着自己的红星人随从离开了。这是个刚来红星不久的纨绔子弟,将来会继承他老爹在红星的不动产。接着更多的客人离开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留下来,也许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刚刚听到的故事。
这下,我的酒馆迎来了难得的片刻宁静。普利普利大叔上次讲这个生离死别的故事是多久之前的事呢?当时的情形还都历历在目。那时候,大规模战争早已经结束,游击队却一直活跃着,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我的科研主管指望着磁感菌的研究能够让他一步登天。他幻想着用磁感菌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步兵通信网络,既便宜又耐用,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游击队的骚扰。这种细菌当时遍布红星,与红星所有生物都能产生生物电网络。虽说对地球人没有直接效果,但是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可惜他失败了,军方并不想用这个红星独有的微生物来代替已经服役多年的制式通信设备,因为这样做的预算实在太高,而且会得罪军火商。军方用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直接消灭磁感菌。没有它们,红星人的游击队失去了组织,大部分分崩离析了,只剩下一些坚定的抵抗分子,各自为战。虽说最后效果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但是局势基本上稳定了,所以除了少部分特种部队留下来清剿剩余的游击队,大部分军人都复员了。
我的主管对此失望至极。他的研究贡献并不小,也得到了回报,但是和他想要的相比,差得实在太多。所以他回了地球,之后就和我断了联系。
我选择留在这里,通过军队中的关系,在红星的客运空间站开了一家酒馆,接待来来往往的星际旅行者们。当然,离开科研基地之前,我没有忘记带上普利普利大叔。不知道是磁感菌灭绝让他感到精神上的隔绝,还是目睹妻女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总之他一直非常迟钝。我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也许是我内心有愧想要偿还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算稍微恢复了一些,就成为专门给客人讲故事的人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又像往常一样,蜷缩在自己宽大的单人沙发当中,圆圆的耳朵偶尔颤一颤,逐渐进入梦乡。在我们的脚下,透过玻璃地板,我看见红星大陆逐渐陷入阴影当中,不知那些残留的游击队员们正藏在哪里,也许他们之中还有普利普利大叔的朋友吧。夜晚降临,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来,新的一批客人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