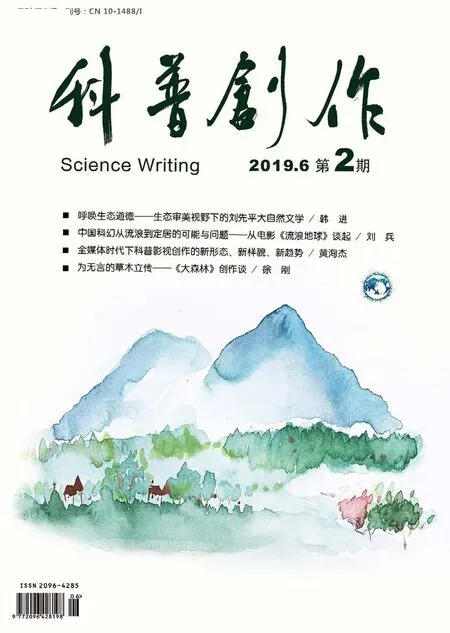《流浪地球》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之思
宝 树
2019年春节我们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刘慈欣原著和监制、郭帆执导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四十多亿的票房横扫春节档,代表了中国科幻大片的强势崛起。2019年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一说法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
当然,几十年前,中国也曾有过几部科幻电影佳作,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等,但这一脉络后继乏力,沉寂已久。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科幻大片横扫全球的时代,所谓中国科幻影视中还充斥着圆圆的飞碟、山寨浮夸的机甲或戴着头套的喜感外星人……并非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没有看过《星际穿越》或《阿凡达》,不知道一流的科幻片是什么样子,而是潜移默化觉得中国人现阶段只能也只配拍出这样的科幻电影,甚至更软——披个科幻的噱头用五毛特效讲个尴尬的爱情喜剧。
在这种比较下,《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气象一新。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原著,采用了其基本设定和框架:太阳灾变,人类设法移动地球,让它“流浪”到另一个星系求生。但电影主体情节是重新打造的,讲述了地球在逃逸过程中险些坠入木星,临时拼凑的救援组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让地球继续流浪之旅的故事。不过,电影并没有像某些影视改编那样随意安插一些和原著毫无关系的情节,故事主线中的要素,像地下城的生活、掠过木星的轨迹、行星发动机的作用等,都是取自原著,与原著的设定紧密结合,也保留了原著小说中气势宏大、想象瑰丽的风格。
事实上,《流浪地球》改编自一部中国科幻小说这一事实本身,就将其与《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几乎所有的国产科幻片区别开来。从方兴未艾的中国科幻文学中引来的满满元气,成为科幻影视开辟元年的一大助力。
但当我们说到“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时候,仅仅是说中国也能产生出和好莱坞类似的科幻大片吗?不止于此。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大年初一观看这部影片时,电影中某句台词提到过嘉兴这座小城,此时整个放映厅内响起一阵惊喜的笑声——因为我观影的影院就位于嘉兴地区。来看电影的本地人大概从没想过,自己生活的地域居然会出现在一部似乎远离现实的科幻片里。这种喜悦感单纯而亲切,并不是出于某种“爱国主义”的自豪思想,而是来自日常生活本身。
当然远不只是嘉兴,《流浪地球》的故事发生在地球上,发生在中国——虽然早已面目全非。故事中有北京、上海的高层建筑,出现过的济宁、杭州的局部城区,以及提到的其他许多地方。还包括中国式的校服、广播、流行歌曲、顺口溜,还有电影内外交相辉映的春节,南腔北调的中国各地方言……看到这些,中国观众都会会心一笑,这种观影的愉悦是欧美大片很难给我们的。
当然,这种中国性并非毫无节制地充斥银幕,而是融入更具国际视野的框架里。故事中出现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人物、对话和文化元素,虽然一般只是作为背景,但是在故事逻辑中却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主角战队并非个体英雄式地包打天下,只是世界各国“饱和式救援”中的普通一支,而主角看似奇妙的救援方案,也早有外国科学家想到过……正是依靠人类整体的精诚合作,铸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让地球转危为安。
有一些影评认为,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本身就是中国科幻电影不同于西方科幻电影的特色。又有人认为,西方人喜欢塑造超级英雄而中国喜欢平民英雄,甚至将其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精神联系起来……这些看法可以深入探讨,在此难以详论。但是我以为,其实没有必要急于确立中国科幻电影的某种独特内涵。西方科幻电影,哪怕仅仅是好莱坞的影片,已经是涵盖极广的光谱,其中自然有超级英雄,也不乏平民的好汉,《独立日》《天地大冲撞》《火星救援》等科幻名片中,显然也有人类集体的协作与牺牲……《流浪地球》本身也明显受到好莱坞电影结构的重大影响。甚至其中对于家的眷恋,也很难说一定是中国而非西方的——在好莱坞影片中,家庭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差别,但迄今为止,中国只有这一部拿得出手的科幻大片,缺乏系统对比的基础条件。
说到这里似乎是有一些自相矛盾,那么《流浪地球》到底有多“中国”呢?撇开某种精神内核,单说地名、春节、方言等文化元素是不是太肤浅了呢?别的外国电影里也可以,而且的确经常加一些中国元素。但关键在于,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一部分,作为主角生长和行动的土壤,这些并不是点缀猎奇的元素,而是想象中未来生活的有机组成。通过电影所构造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纵情想象人类与中国的未来。在我们的想象中,中国人自己成了主体而不是旁观者或配角。这让我们体验到了自身的无限可能。
电影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我们大概永远用不着建造巨大的行星发动机,但可能建造同样震撼的核聚变发电站或太空站;也许我们将来不会在地下城庆祝春节,但大可以在海底或外星新城舞狮舞龙;也许地球永远不会飞向黑暗深空,但我们的航天员和飞船一定会……未来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未来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
因此这里借用一个哲学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中国人作为自我表达的主体在科幻电影中的确立,可能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最重要的贡献。在此没有必要进一步定义“中国”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自己,由我们自己创造。以前我们谈到中国科幻时,经常担心的一些问题,如“中国人拯救世界是不是很假”“为什么未来社会都是西方式的”,通过电影本身的感染力,原则上这些都不再是问题。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年轻人或许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
另外,在征服亿万观众的同时,影片也受到了许多批评。比较值得认真看待的是,许多人指出设定和情节上有若干严重的错误或硬伤(或者叫bug),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其为“不及格”。要探讨“科幻电影元年”是否成立,对这个方面显然也不能够回避。这不光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也涉及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路径。
首先,需要将“疑问”和“bug”区别开来,这恰是许多评论经常混为一谈的。某个设定或情节令部分观众产生疑问,并不等于其有错误。比如质问“地下城如何能养活35 亿人”或相反“既然能养活35 亿人为什么不养活70 亿人”“为什么科技那么先进了还没有自动驾驶”“为什么卡车能那么快开到苏拉威西”……事实上,其中不少只需要加一些简单的补充就能解释,即便有不易解释处,也不能贸然认定为硬伤。
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部虚构电影,并且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交代清楚历史的方方面面。很可能也会有观众质疑“为什么日本明明比美国差那么多还敢去偷袭珍珠港?太不合理了!”或者“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那么悲惨也能反败为胜?完全违背战争的基本原理!”如果给出进一步解释,又会被挑出若干新的问题。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事件,连历史学家都难以解释,但这些是无疑的历史事实。对于电影所展现的世界观,也应该这么看待:这个世界有无穷丰富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不应该妄下结论。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提出疑问,如果不抱挑刺的心态,这完全可以成为创作者与观众之间互动和激发想象的契机。
不过,影片的确也有若干非常明显、无可讳言的硬伤,有些对情节还十分重要。如木星引力激增,将地球拽向木星,造成了故事的主要危机。事实上按照牛顿力学,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引力是不会改变的。即便如一些人所辩解的,由于木星大气运动造成其重心有细微变化,对于大天体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否则木星的几大卫星早就坠入星体或者四处飞散了。
在影片的结尾,通过混合地球与木星大气层并引爆的方法来把地球反推出去,似乎是十分令人震撼的办法。但事实上,大气层总质量约为5.15×1018千克,地球质量约为5.965×1024千克,大气层的质量小于地球的0.0001%,其中一小部分气体燃烧所产生的冲击波,又只有小部分能传到地球上,对于地球的推动力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硬伤是改编产生的。原著比较严谨,特别提到人类工程师精心设计的路线和利用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加速的问题,说明作者完全明白引力法则的精确,不会出现引力忽增忽减的问题。但基础设定上也不是全无可议。比如故事的前提——太阳短期内发生氦闪或膨胀——按照公认的恒星核聚变物理模型来说是不可能的。又如以巨大推力从一边推动地球,其压力必然会导致地壳的支离破碎,熔岩布满全球,地下城不要说深度5 千米,就是50 千米也难逃毁灭。这些硬伤就很难通过加补丁的方式去辩护。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硬伤与科幻小说或影视一直如影随形。譬如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以炮弹将人打上太空,但瞬间的巨大加速度足以把人变成肉饼;威尔斯的《隐形人》设定能让人体变得和空气一样不可见,但这样就会丧失吸收光线才能产生的视觉;《后天》中将几百年才能形成的温度变化集中在几小时内发生,让温度一夜之间下降数十度;《2012》中让太阳中微子加热地核,让地球产生灾变;在号称非常科学的《星际穿越》中,主角进入黑洞,结果发现是神秘的高维空间,甚至让他穿越时空回到数十年前自己家里……都和已知的物理学理论严重不符。
在这里列举其他科幻作品的诸多硬伤并非为《流浪地球》辩护,而是要意识到硬伤本身的某种本体论意义。刘慈欣本人曾对硬伤问题进行过专题探讨,在此很值得我们引述。在评论《无奈与美丽的错误》中,他将硬伤分为四种,前两种是疏忽和知识不足的硬伤——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的,对读者来说没有太大区别;第三种是背景硬伤,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约定”“为了给那些真正的科幻的东西搭一个舞台”,也就是说,相比于故事所要呈现出来的精彩之处,不得不牺牲一些科学和逻辑的严谨;第四种是灵魂硬伤,指幻想出一种新的宇宙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世界。
前两种硬伤没有太多好说的,属于基本可以避免的瑕疵,第四种根本上不能算是硬伤,也暂且勿论。较有探讨价值的是第三种硬伤,它既是无可推诿的错误,又是作品成立所必需的基础。《流浪地球》原著及电影中的一些关键“硬伤”,可以划归到这一范畴,事实上是为了展现思想意境而不得不承担的“原罪”(当然也有不少是可以避免的)。相对于小说而言,电影的局限更加明显。电影既需要在两小时内交代完整个故事,又需要震撼的场面和强烈的戏剧效果,因此不得不更多向硬伤妥协,带“伤”上阵。
应该认识到,科幻的两个基本方面——科学与幻想,在本源上就是相爱相杀的矛盾,科幻本身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细则可能束缚想象力,而想象过甚又可能超出科学,套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完全没有任何瑕疵而又精彩纷呈的科幻,但那是神的艺术,人类只能尝试通过带着硬伤的具体作品去接近。可想而知,未来的科幻电影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方面的问题。对此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一棒打死,而需要有理论上的进一步认识。
《流浪地球》当然有不少缺憾,绝非完满。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个期许所预示的,它并非圆满的终结,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属于中国科幻自己的开始。从这个角度讲,其成就和缺陷都是元年之为元年的一部分,也是未来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元年”这个提法本身意味着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意味着一个持之以恒、光辉灿烂的传统。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元年”又是未完成和悬而未定的,需要今后数年中更多和更好的作品,才可能令真正的历史意义完成和凸显。因此我们仍要怀着期许,也怀着忐忑,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