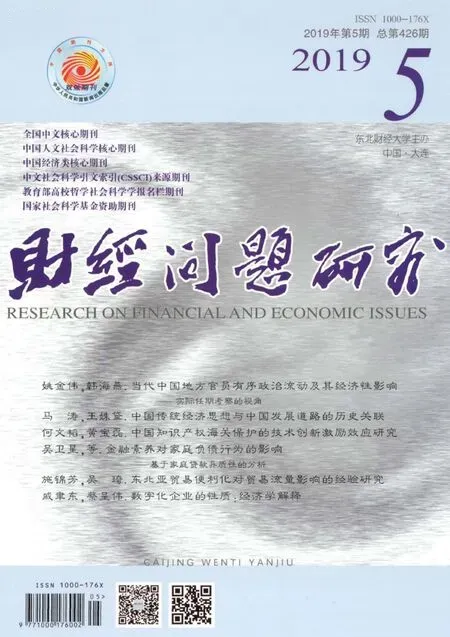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关联
马 涛,王姝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当下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与历史转换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1]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并特别引述了一句中国经典名句“与古为新”。在文明起源的早期,由于面临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形态不同,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也就具有了诸多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强调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经济思想,然而“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2]。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对这一论题研究的论著不多。其中,巫宝三[3]提出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在于:两方都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都早已产生;政权都归于土地贵族;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都创造了有各自特点的灿烂文化。不同点为:土地关系上,古希腊罗马是土地私有,直接生产者是奴隶;古代中国的直接生产者既要在公田上无偿劳动,又要在授予的份地上劳动,公田产品归公候,份地产品归劳动者。后经过“初税亩”等一系列改革,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封建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剥削关系从劳务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古希腊罗马的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较中国古代更为发达。古希腊通过梭伦改革,在政权构成上,所有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力;古罗马通过改革,传统的血缘关系被财产关系所取代,随着新兴骑士阶层的兴起,富有的工商阶层得以参政。古代中国则是宗法制与土地私有制相结合,形成了政治上的绝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经济上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和官营工商业。鉴于目前这一论题研究的论著不多,希望本文的思考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影响
对一个民族而言,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流变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发生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文明创造的自然基础。不同的地理环境使生活于该环境中的人类必须选择相应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制约或影响着他们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华夏文明诞生的这块土地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是处于一种自然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
在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里,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封闭性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文明在早期呈现出一种“黄土文明”的特征,与古希腊罗马形成的海洋文明明显不同,造就了先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和文明。这一生活方式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文化的同化和融合,而与海洋文明重视商业贸易、不断追求强烈的向外扩张和文化间的冲突与武力征服有所不同。古希腊罗马的海洋城邦结构对其经济发展路径有重要影响。对于古希腊文明的成就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总结认为,公元前6世纪时古希腊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阶层团结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古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使古希腊社会在其形成时期内大为变样,并为古典时代扫清了道路。古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古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的是中东、印度和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供养是建立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今天的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因而古希腊人没有可以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相反,在外来者入侵之后,他们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以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形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则称为卫城或高城。出于策略安排,城邦常常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从而吸引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4]。
中华文明起源虽呈多源特点,但重要地区是黄河流域。中华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面临黄河泛滥的危险。也正是在治理黄河的基础上,中华文明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形态——夏王朝。夏商周三代,延续的都是一个有利于治水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动荡,秦始皇统一中国,改西周分封制为郡县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血缘关系。大一统帝国的体制既有利于黄河水利工程的实施,也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把财富集中起来,从而创造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以造就都市经济的繁荣。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
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系统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概括言之,这些特点在研究本位、重点、主导和文化思维上都与西方不同。
“本位”指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国家本位特点。所谓“国家本位”,是指分析经济问题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关注国家的利益。如古代中国所谓的“经济”含义就是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讨论的多是治理大一统国家必须解决的诸多经济政策问题,诸如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土地及财税,这就与西方早期经济思想讨论的多是诸如个人家庭(庄园)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微观问题明显不同。纵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历代思想家们集中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土地、赋税和货币,这三大问题的讨论都是从国家本位的立场出发。土地问题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讨论最多的,因为土地兼并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形成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所以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如何抑制土地兼并展开的。赋税收入是国家机构的经济基础,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解决好财政问题对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就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讨论的重点。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对于如何实施专卖、赋税征收等财政问题的讨论十分丰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围绕财政经济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诸如西汉的盐铁会议、唐代的两税法改革以及宋元明清的关于货币问题的朝野争论。历代王朝关于货币发行权、货币价值的高低乃至货币形式等种种问题的讨论也几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论述经济问题时而不论述租赋问题”[3]。以至有学者认为,“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决不能采用‘商品—资本’的模式,而只能采用‘地产—地租、赋役’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真正中心,才能找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条件和规律”[5]。
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重农抑商”观念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对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维护。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农业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又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农业基础薄弱,社会将面临不稳定的威胁,国家政权就难以稳固。因此,“重农”自然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不论先秦还是秦汉以后,不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其他学派的学者,都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从战国中期开始,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出现了“抑商”的观念。他们认为,私人工商业的收入较高,如果不加以抑制,弃农经商的人就会增多,必然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会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危及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秦汉之后,“重农抑商”(抑私商)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主流。直至宋代,随着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学派为改变商人社会政治地位而发出呼声。明中期以后的思想家延续了浙东功利学派的这一观念,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了“工商为本”的口号,反映出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相对于古希腊罗马的重农思想主要关注农业经营与管理而言,先秦重农思想的主旨是在于说明农业对于国家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和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关注家庭农庄的经营与管理效益。国家本位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考虑的是宏观问题。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延续长达两三千年之久,历史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抑制土地的兼并问题。在古代中国,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由于地主阶级地产占有欲的无限性与自耕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古代中国一方面出现了“人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的现象,经常呈现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6],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古代中国周期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土地产权的频繁变动导致社会经济的经常性破坏和政治间歇式动荡,构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宋人董煟[7]在论及土地兼并给社会带来的动荡时说:“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赈贷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狈无策,只有流离饿莩耳”。因此,土地制度自然也成了历代思想家关注的重点。
与欧洲关注庄园的分工与效益不同,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的思考、学说异常丰富,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为解决因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思想家先后提出了很多方案。汉儒董仲舒是第一个对因土地自由买卖而导致兼并进行深入论述的思想家,他认为土地兼并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提出了限田论主张。董仲舒之后,西汉末王莽进行的王田制改革在经济史上颇有影响。王田制的核心是对土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由国家授田给无田地的农户,禁止私人进行买卖。西晋占田制是王莽之后封建地主政权和思想家们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北朝时期的李安世是均田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均田制的特点表现在:将土地分配与封建租税结合起来,确定了土地的使用者与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不仅解决了土地的兼并问题,还解决了封建国家的财政赋税问题。从宋代开始,由于宋初推行“不抑兼并”政策,宋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现象又开始泛滥,土地兼并问题再次引发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抑制土地兼并一直占据土地政策的支配地位。
与国家本位相对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以管仲为代表的轻重论占据着主导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形成了轻重论和放任论两大思想体系,西汉后进一步发展成型,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始终。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轻重论的国家干预主义一直居于经济政策上的主导地位。轻重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干预的方法不外乎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或政策来调控经济,或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实行专卖和禁榷。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办法包括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垄断市场,左右物价;国家对重要自然资源如矿山进行垄断,实行“官山海”(即国家垄断)和部分专营制度,调控物品的轻重,增加国家收入;国家采取行政手段和立法等手段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即所谓“官国轨”。这里的“国轨”是指国家通过调研而形成的干预计划,将国家的经济管理纳入有序的轨道。通过这些“轻重之术”就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实现控制经济的目标。汉代桑弘羊是运用轻重论调控经济的典范[8]。轻重论在古代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轻重论的理论和政策,轻重论也成为历代理财家所利用的理论武器。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与当代复杂科学的综合思维不谋而合。按照这一理论思维,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与万物彼此相连,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一切学问的最高意境就在于“究天人之际”,追求中庸思想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道”[9]。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表现出强调综合统一的辩证思维特点,如本末论、源流论、轻重论、奢俭论等,其表述方式都是在阴阳、对冲、反向运动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中的对称和对立中来形成其经济思想的观点。这一辩证思维的优点体现在用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与西方分析性的、强调理性分析的形式逻辑思维不同。这一综合辩证思维的特点在经济思想上就表现在先秦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和先秦法家的《管子》等经济思想极为丰富的论著中。从经济思想的内容来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论述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常常不仅着眼于经济规律的探讨,还往往注意与此相关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如其“重农”思想,不仅要求农民努力增加生产,更看重的是由此可以富国强兵,稳定国家政权。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抑末”思想,不仅因为奢侈品生产消耗了社会紧缺的资源,费时费工,更在于能杜绝人们因抵抗不了诱惑而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轻重论不仅突出了对经济的调控,更看中的是对君权维护的政治考量。
儒家的“义利观”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文化思维的特点。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被历代政府推崇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强调把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之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价值取向不是指向人的欲望、需要,而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秩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一项经济政策和经济观念的评价,往往不是从其可行性的技术分析出发,而是强调要从“道义”为先的道德价值评价出发去研究经济问题。儒家认为“义”与“利”相较而言是义重于利,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和孟子都提出人的行为必须以道义为准则,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是“以义统利、见利思义”[10]。汉以后的儒家学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些义利观念,如董仲舒明确提出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要求把物质利益的追求置于道德约束的范围之内。唐代陆贽以本末的关系来比喻道德秩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维护好社会的道德秩序,经济才会繁荣。“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而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11]。有人把这一学说概括为“贵义贱利”,并称之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另两个是“重本抑末”和“黜奢尚朴”),但“贵义贱利”不是不要利,而是强调要用义来统利,把人们对私利的追求规范在合乎政治道德的范围之内。从先秦的孔孟、汉儒一直到宋明理学乃至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等,提倡的都是这一观念。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等,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实施仁者爱人之政;主张抑末、困辱私商、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等,是出于担心破坏纯朴、敦厚道德风气的考虑;财富分配观上提倡均平、抑兼并等,是因担心财富收入差距过大,人心失衡,会破坏社会的政治道德秩序。从西周的井田制到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主张先要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就要施之于“谨痒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2],而“不违农时”“薄赋敛”“抑兼并”和“募民屯耕”等经济政策也都是为了体现“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所谓“重本抑末”“黜奢尚朴”,也都有维持社会风气纯朴这一道德规范要求的考虑。
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关联
比较中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发现,中央集权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儒家伦理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关联。
中国发展道路强调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权威,中国发展道路的治理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从国家的治理而言,中国的政治是中心式的,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天然的封闭居住地域和商品经济的落后是中国形成集权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之路,对于古代中国国家体制的发展影响极为深刻。在漫长的中国国家发展之路上,宗法血缘关系显示着中国国家发展的特点。在东方式的中国政治专制体制中,宗法制度支撑着这一集权体制的存在。宗法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相依赖,互相支持,形成了古代中国如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形态”的集权体制。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研究发现,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既不能归属于原始的部落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开始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说明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东西方社会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13]。顾准比较分析了东西方地理环境对古希腊议会民主与古代中国集权制度的影响。顾准[14]提出,东方诸国(包括中国、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等)属于大陆文明,从历史的发展看无一例外地走向集权,而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西方诸国,属于海上文明,则走向了议会体制。人类发展的两条道路从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文明起源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社会保持了希腊文明的传统,中国则保持了东方集权的传统。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官员代理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鲜明特征。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代政府始终围绕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继承和创新。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从经济发展政策上看,有助于推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规划协作,具有一定的优势。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不存在“无为而治”的政府。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依靠国家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15]。
中国发展道路在经济所有制结构上呈现出多种所有制的特征。在古代中国,土地制度分为土地国有、地主土地所有和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基本形式。在工商业经济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多种所有制特点。在整个封建社会,官营工商业都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因而受到格外的重视。官营工商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官营工商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工商食官”制度则继续存在,主要手工业由官府垄断。“工商食官”制度作为官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但也仅仅是对官营工商业的补充,“工商食官”制度仍占据主导地位。从秦汉开始,国家建立起了完整的官营手工业管理体系。官营手工业在历代都受到政府的重视,从先秦直至明清,官营手工业始终存在。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很广,大体说来,城市和宫室等土木建筑、矿冶、铸钱、兵器制造以及皇室所需要的丝织品、金银器皿和各种御用器物的制造,通常都由官营生产部门负责。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官营手工业在整个手工业生产领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技术和产品质量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也都具有示范导向作用。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带动了民间手工业的技术进步,也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技术水平。
官营商业与官营手工业一样,除盈利目的外,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自身消费的需要。官营商业表现为多种经营管理方式,如禁榷、均输平准等。所谓禁榷是指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垄断某种商品的产和销,禁止民间私人经营。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的“管山海”的政策,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是古代中国实行禁榷制度的开端。比较完备的禁榷制度是西汉武帝时建立的。西汉以后,禁榷制度作为一项传统的经济政策,为历代政府所沿袭,禁榷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唐代开始榷茶,宋代将茶、盐、酒、醋、香料、矾、药材等也都列为禁榷对象。元代国家经营的物品则包括了茶、盐、酒、醋、金银、珠玉、水银、朱砂、碧甸子、铁、铅、锡、矾、硝、碱、竹、木等。专卖制度为解决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元代为例,天历年间仅盐课收入即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占政府钱钞收入的一半以上[16]。均输平准是国家运用行政力量调剂运输、平衡物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中央物资供应的政策手段,其实行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王莽新朝时期,进一步推行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就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立五均官,“掌均平物价,以利四民”。将政府对盐、铁、酒的专卖,以及铸钱、山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称为六筦。五均六筦实际上是汉代禁榷制度和均输平准政策的继续。北宋王安石变法,把均输法和市易法也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平准,到王莽新朝的五均六筦,再到王安石推行均输法和市易法,其政策和内容虽不尽相同,但本质上都是运用中央集权的行政力量干预或调控商品流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儒家伦理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基本内涵。商业伦理是任何商业组织在从事盈利活动时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包括价值观和从事商业活动时的行为方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伦理必然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影响,也表现在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影响上。儒家伦理可简括为“以人为本”的仁爱观、“以德为先”的义利观和“以和为贵”的和合观,这使得中国传统商人在伦理上表现为推崇以义制利的信义观、勤奋敬业的职业观及修身正己、同舟共济的和谐观,并以儒家的伦理价值观作为经商的指导理念。儒家伦理在中国工商人士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成为他们工作经商的精神动力。战国初年的大商人白圭的经商之道是“(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17]。白圭在这番话中,举出了“仁、智、勇、强”四个德目。而其“薄饮食”的行为,又可以归纳为“勤俭”二字。这五个德目都是儒家提倡的伦理精神。儒家伦理对古代商人工作伦理的影响,还包括有“忠信”和“敬”等内容,“忠”即“诚”,故“忠信”即“诚信”,是儒家所强调的最基础的道德人格。古代中国商人就是以“诚信”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取胜之道,“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由此形成了诚信的商业伦理传统。“敬”的职业意识也是儒家所一直倡导的商业伦理之一,周初统治者训诫人们“不可不敬德”[18]。孔子强调“居敬而行简”“言忠信,行笃敬”[10]。宋明理学家也崇尚“人生在勤”的敬业态度,“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19]。这一“敬业”精神,对古代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伦理思想在战国以后的社会发展中进一步融于工商人士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如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对于信义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有过精辟透彻的议论。他认为,商业利益的大小取决于顾客的数量,顾客人数越多,商人获利也就越多,所谓“利之出于群”;讲究商业道德,就能招引更多的顾客,因而商德乃“万利之本”[20];经商者应守信重义,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不能光顾眼前的利润,所谓“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唐人陆贽在肯定商人追求物质财富、物质利润的同时,也强调商人必须遵循儒家“以义为本”的思想,显示了唐代商人义利结合的思想观念。“诚信”的道德观念在宋代商人伦理中更占有中心地位,如宋儒范仲淹就认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21]。司马光更强调“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而致“诚”之道又在于“不妄语人”,即“不欺”。“诚”和“不欺”上通“天之道”[21],这便为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依据。诚信的观念经过新儒家的提倡,也已深深地印刻在明清商人的心中,表现在商业运作上则是讲究货真价实,礼义经营。只有以诚待人,才能建立稳固的商业合作关系。天道不欺的观念对明清商人的影响非常深刻。
韦伯认为,清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根据韦伯的解释,西方资本家全心全意经营赚钱的宗教动机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是为了要用经营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在尽“天职”方面已才德兼备。在古代中国,儒家伦理则发挥了类似新教伦理的作用。儒家的“成德”观念在明清商人中发挥着与新教“天职”观念相似的作用。“成德”是儒家伦理的“要义”,“成德”的具体内容是成圣成贤,儒者不但要修身见于世,更要泽加于民,“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22]。商人经商的成功也是他们“成德”“不朽”的一个方面。明清商人认为,他们的商业生涯也具有一种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如十五世纪山西商人席铭曾有“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的豪言壮语。他们认为,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与士人治国济世的事业对国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也足以传之久远。明晚期婺源商人李大祈说,“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23]。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经商,与士人的“成圣成贤”具有相同的价值,并无逊色可言。这说明儒家“成德”的观点也已成为明清商人经济活动的一种精神趋力。
中国发展道路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关联,它必然具有可持续性,自然也会影响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